导演普次和编剧尼顿的“跨界”人生
2022-08-04孙芮茸翻拍孙芮茸
◎文/孙芮茸 图、翻拍/孙芮茸

1970年话剧《沙家浜》
A “演员”当“导演”
退休老导演普布次仁将近77 岁,低调的穿着打扮让人很难猜出这是一位依次毕业于上戏和中戏的知名演员兼导演。唯有谈话间隙,他瘦削修长的手指夹着“软中”,凝神思索,然后缓慢吐出馥郁流畅的烟圈。你会知道,这位老人故事一定不少。
普布次仁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小时候他的家就在现在鲁固一带,八廓街的老院子、大昭寺的讲经场都是他童年的游乐场。除了这些玩的地方,普布次仁记忆特别深刻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印度人开的电影院,鲁固往东一点。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萨的第一个电影院。说起来那个电影院有意思得很,影片放到一半有个休息时间,可能是给观众上厕所的,我们一群小孩守在门口,等到有的人不想看了把票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去看电影了。”戏剧的种子,不知不觉地种在了小普布次仁的心田。
初中,我们就读于拉萨中学。因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跳舞,普布次仁成为拉中宣传队的成员:“我当时跳得还不错,‘文革’的时候歌舞团的人不够,我还被当时歌舞团的团长罗布老师叫过去跳过舞呢。”
西藏话剧团刚成立第二年,为了充实团里的人才队伍,话剧团到拉萨中学来招生。“当时拉中规模很小,只有初中3 个班,高中3 个班,总共6 个班。在这6 个班中挑选出了5 个小孩,当时被选中的有我、丹增卓嘎、央金卓嘎、马昌林和索朗次仁。”普布次仁回忆道。参加完考核之后,录取的几个孩子被直接送到上海戏剧学院上表演课,学习了三年,他们后来都成为了西藏响当当的老戏骨。
1966年,适逢他们毕业,本来准备排一出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话剧,还专门深入生活到井冈山待了好几个月,准备投入排练的时候。学院来电报说要进行“文化大革命”,通知他们赶紧回校,最终没能排成毕业剧。匆忙赶回学校,毕业后返程回西藏。那段特殊的日子,学成归来的孩子们排不了什么戏,整天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批斗,对他们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谈起当时贫乏的文化生活,普布次仁还是觉得很可惜:“没有电影,其他种类的戏剧更是没有。除了样板戏没有其他的选择,让藏剧团学《红灯记》,让话剧团演《沙家浜》,歌舞团演《白毛女》。”演出的票并不售卖,而是送给各大单位,由单位组织观看,一切按部就班。演员没有太多可发挥的余地,观众也就随便看看。

自治区成立20 周年 班禅大师在拉萨饭店总统府接待《意翁玛》剧组人员(右一为普布次仁)

普布次仁导演在给演员说戏

普布次仁获第五届中华文华奖导演单项奖留影
据说,当时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团差一点就合并了。“有这回事,后来没形成。那时候是文化局准备弄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然后合并起来。有用的留下了,没用的就调走。当时听说我也是计划要被调走的人之一,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没什么事情,天天到拉萨河去游泳,晒得黑黑的。”好在那时候的拉萨河边到处都是树,就是个“林卡”,风景很好。普布次仁将自己的苦闷排解到拉萨河中,随波逐流。
十年结束,文化生活逐步恢复。当时话剧团只有三个科班出身的导演,而且全是汉族: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盛励;四川人艺的演员卢进之,后来当了导演;还有向东。这样的情况下,话剧团需要培养一个藏族导演,领导决议让普布次仁去学导演。“那时候我思想很乱,学导演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我已经从上戏学出来这么多年。而且我觉得做艺术工作应该有点天赋,如果完全没有天赋,那可能不行。我反思了一下自己身上是否有这种学导演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一是导演学不成,二是表演的功夫万一也丢了。”继续做轻车熟路的“演员”,还是去当充满未知的“导演”,普布次仁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思来想去,他也意识到这是领导对他有心培养,机会很难得,也许是件好事。他决定试一下,但保险起见,普布次仁主动请求让他参加一次考试,看是否合适当导演,领导欣然应允,并开始张罗起来。“当时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西南组在成都设了一个考点。团里的人先跟他们联系,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藏族学员,想去参加考试,那边也同意了。”普布次仁动身前往贡嘎机场,准备飞到成都考试。

1964年 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一年后在上海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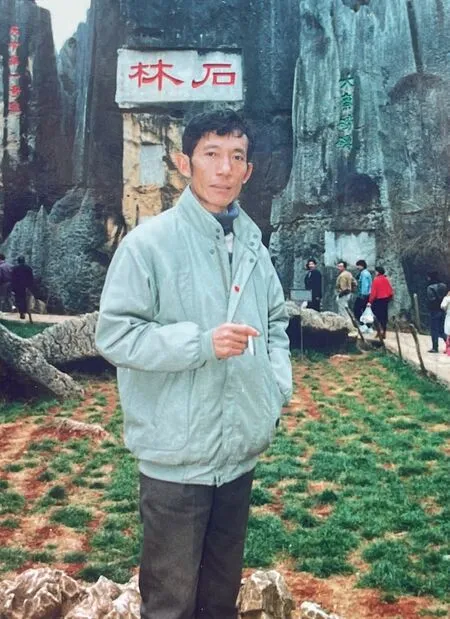
普布次仁赴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云南石林前留影
说起这段坎坷的赴考经历,普布次仁哭笑不得:“那时候的机场很不正常,等了七天还没飞。老飞不走,哎呀,那时候又是个夏天,住的地方臭虫又多。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差不多过了十多天,终于飞了。然后一到成都,我就马上去找考试点,结果已经考完试了,主考老师都已经走了,时间过了。”后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那段时间话剧团刚好在成都拍一部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冰山雪莲》,同事们都在成都,普布次仁也暂时没回拉萨。
没想到这阴差阳错的滞留,反而成就了另一场“因缘”。从东北过来的一个剧组那时候也在成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恰巧要拍一个西藏题材的电影,导演孙羽在食堂碰到过几次普布次仁,几番观察之后,这个藏族小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问我是不是话剧团的,我说是,然后把我的个人情况大概给他讲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里有个角色特别适合你来演,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好啊,我就是演员啊。”就这样,普布次仁跟着剧组回藏拍电影,这部后来名震一时的电影就是《丫丫》,普布次仁在里面演根宝。
结束西藏的拍摄,普布次仁又跟随剧组到长春去拍内景。戏份杀青之后,普布次仁得知团里两位领导都在上海,他又专程从长春跑到上海去打听学导演的事情。“领导回复说,会再帮忙去给中央戏剧学院联系。那时候是打电报给学院问这个事情,后来学院说,既然我们考试结束了,但是他(普布次仁)上过上海戏剧学院表演课,有良好的表演基础,可以来学习。就这样,我又从上海去北京了。绕了一圈。”兜兜转转,绕了大半个中国,已经32 岁的普布次仁终于踏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进修班大门。

80年代普布次仁在布达拉宫广场前《拉萨大剧院》旧址前独照

普布次仁拍摄《宗山魂》期间在江孜白居寺留影
在导演进修班学习两年多时间里,远在家乡拉萨的老母亲一直牵挂着普布次仁,毕竟这是五个孩子里,她最疼爱的小儿子:“我也想母亲,但那时候私人没有电话,单位里才有电话,打电话是很贵的。所以只能捎个信、打个电报。”思念家乡亲人之余,普布次仁十分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那段师从中国戏剧学界的泰斗徐晓钟老师的经历在现在看来,他仍然觉得闪闪发光。
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因为是定向培养所以同学都是藏族,但是到北京的时候,班里只有普布次仁一个藏族,所以也得到了很多特别的优待。“当时班里的人特别关照我,喜欢我。因为我上过上戏的表演课,所以每次他们导演小品作业,包括画面小品、背景小品、音响小品等,大家都喜欢拉我去演。有时候我一场要演三四个角色。但是每次有个什么观摩的机会,还有一些难得一看的剧目,票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大家都说让普布去。有一次英国皇家剧院来演莎士比亚的一个剧《哈姆雷特》,当时票特别紧张,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去看,他们不争,他们说让少数民族去吧,让普布去。”普布次仁那届78 班的同学们还建了一个班级群,现在为止,大家偶尔还联系。“我们班里出名的人特别多,演曹操的鲍国安是我的同学,李保田也是我的同学,他演了不少电视电影。在班里的时候,他的表演特别出众,那时候搞小品作业,他也经常被拉来表演。”提到自己的同学,普布次仁眼里充满了光。
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学得特别扎实。而且导演课兼修导演和表演,可谓是一举两得,普布次仁因此对表演的理解更上升了一个层次。“演员上导演班,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表演,是另一种提升。”
B “场记”当“编剧”
十几年后,中央民族大学藏语系毕业的尼玛顿珠。正好赶上西藏话剧团在全国各地物色编剧人选,当时的领导顿珠多杰在北京遇到了尼玛顿珠,问他有没有意愿到话剧团工作。尼玛顿珠有三个选择,一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留校任教,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要人,三是话剧团。“我选择了话剧团,因为前两个都是在北京,只有最后一个是回西藏。我们在外求学的藏族孩子都担心留北京远离家乡父母,所以大多选择回西藏工作。而回西藏里面最好的就是去拉萨,比这更好的没有了。”于是尼玛顿珠爽快地答应了,尽管前两个跟他所学的专业比较贴近,但为了回拉萨,他需要转型写剧本了。
1993年7月尼玛顿珠毕业回藏,9月就正式被分配到话剧团。刚到团里报道的同时,他也接到安排好他到上海戏剧学院去学习的通知。没几天,他又离开西藏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完成一年的进修回藏,尼玛顿珠直接被安排下乡了。“现在叫驻村,以前有个名词是社会主义教育,我被派到山南琼结县去了。”
1995年,尼玛顿珠回到团里,赶上普布次仁导演排《雅砻之恋》,他被安排当场记,一开始他也纳闷,让他来是当编剧,怎么又干起了场记呢?很久以后,他才明白这个安排的意义所在。“那个时候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还经常说,不要小看场记,尽管有时候节目单已经很厚了,场记排到最后。但是场记能学到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跟着导演排戏、去跟舞美部分沟通,太锻炼人了。”场记的经历使尼玛顿珠对话剧的整个流程更加具象化,也为他后来的剧本创作打下基础。“像我们作家大部分时候自信心是不够的。除非你非常地有把握,才能说出这个我行。不然的话只能说我试一试看行不行。如果不了解舞台细节,写的时候会很不好把握。”

尼玛顿珠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期间

工作后尼玛顿珠重返中央民族大学

尼玛顿珠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期间

工作后,尼玛顿珠重返上海戏剧学院

尼玛顿珠早年在那曲体验生活

年轻时候的尼玛顿珠
时隔多年,回忆起这次非正式“合作”,普布次仁只记得尼玛顿珠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小伙子,话不多。但在尼玛顿珠心里,一直把老导演普布次仁当作他的伯乐。

话剧《情满草原》
排完《雅砻之恋》之后,尼玛顿珠并没有马上入行干起编剧。因为团里管得比较松,他大部分时候都在和西藏大学的老师一起泡在茶馆里。“因为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是学文学的,大家比较聊得来。他们建议我调到西藏大学工作,还有一个很熟的藏大老师说他要招研究生,让我去考,但是最后没考成,现在说起来有点惭愧。不是怕考不上,而是担心交不起学费。”三年的学费是两万多,当时尼玛顿珠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三百多。
没有什么任务,也没有人管,尼玛顿珠担心自己这样无所事事下去地待在团里可能会荒废了。于是主动请缨,给团里写了一个报告,申请到那曲采风,而且不要一分钱,团里很爽快地批准了。“我就去那曲待了一个月,有的地方徒步,有些地方坐车。”回到群众中间,写他们的故事。
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里,尼玛顿珠最喜欢、模仿最多的是作家老舍。“因为老舍先生本身也是北京本地的一个很底层的劳动人民。他说过一句话,‘我就熟悉这些人,所以我就写这些人。’所以他可以写得很生动,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从劳动人民中出来的,所以更高层次的人我也接触不到,也不熟悉,所以我写我最熟悉的人。包括我的小说也一样,都写的底层劳动人民,都是一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从那曲回到拉萨没多久,尼玛顿珠完成了《情满草原》的初稿。因为比较年轻,而且刚毕业没多久,很多人都不太信任尼玛顿珠,于是剧本被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了,被改得面目全非。“普次老师特别鼓励我,他说这个题材特别好,要坚持你自己的观点。”这句话成为了尼玛顿珠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我在团里的成长跟普次老师是分不开的,他是我的伯乐。比如每次排一个小品,老师拿到我的本子,他非常清楚戏核在哪里,也清楚哪些地方有价值。而不是听一遍就马上发表意见,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作为导演,普布次仁有一个整体观,即使尼玛顿珠有些台词看起来比较啰唆,但他能很快把握住重心,理解到台词背后的一些东西。
“如果一个编剧不遇到一个好的导演的话,那就非常可惜了。”回忆起两人过往的合作尼玛顿珠感慨到,“我提供一些原材料,导演相当于高级厨师。如果搭档的导演不行,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呈现你的作品。”

荣获中国话剧金狮奖(右二为尼玛顿珠)
C 话剧团“最佳拍档”
“我记得1996年西藏电视台的藏晚停了,只有拉萨电视台的藏晚,我写了一个小品剧本《花伞下》,那个小品是普布次仁老师排的,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合作。虽然是我的第一个搬上舞台的作品,但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当时节目中的一些台词。”从那以后,尼玛顿珠和普布次仁相继合作了多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藏晚小品,联手打造出了观众最喜欢的“铁三角”组合。
尽管“铁三角”的小品在群众中呼声极高,但在普布次仁看来,他们两人合作最成功的作品是在江孜百年抗英斗争纪念活动期间排的大型话剧《宗山魂》。那是他导演生涯中排过的最大场面的戏,调度起来很困难,角色非常多,以至于团里的炊事员,司机都轮番上阵,身为编剧的尼玛顿珠更是在剧中一人分饰了好几个角色。“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有些地方我运用电影的手法,为了在舞台上达到逼真的效果,我还邀请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爆破;从视听方面考量,我专程去四川请了罗念一老师为这部戏作曲。”在舞台上直接爆破,又要保证防火,又要达到真实的效果,在现在不能有一丁点儿火星的舞台上不可能再见到。
而创作《宗山魂》本身对出生于江孜的尼玛顿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我自己从小有写这个题材的愿望,领导又给了这样一个安排,就刚好凑到一起。”其实话剧团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这部话剧的构思,首稿由中央戏曲学院导演系主任裴福林写成,中间改了五六次,但看起来不像发生在西藏的故事。于是剧本又交由尼玛顿珠负责修改:“当时我们团里的几个老同志一起住在赛康酒店里面,白天聊,晚上我再写。”虽然是几个人集思广益,但也符合尼玛顿珠的创作思路。很多时候大家都想到一处去了,这样集中的集体创作特别有成效,而且特别顺利。“这是全团人一起完成的,意义比较重大。”


话剧《宗山魂》
2004年,这部戏拍完在拉萨连演15 场,反响强烈。“刚开始的时候送票,越往后越一票难求。那是我导的最大气最满意的一台戏。”普布次仁回忆当时的盛况仍然激动不已。
无论是历史题材的大戏,还是轻松的小品,在多次磨合后,他俩又展开了新的尝试。2007年8月12日,西藏第一部藏语情景喜剧《快乐生活》在拉萨正式发行。同一天,为期一周的 2007年中国拉萨雪顿节也拉开了帷幕。那段时间刚好也是收青稞的季节,但是再忙,大家也会把手头的农活放下,赶回家里看西藏电视台播放的《快乐生活》。
这部片子是由西藏电视台里的三个年轻人卖车、贷款筹集80 万拍完的。谁也没想到这部小成本、小制作的电视剧会引起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一举夺得西藏电视台最高收视率。直到现在,这部电视剧里的片断常常被剪辑出来投放到短视频中,还能获得很高的点击量。很多剧中的台词仍然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着。

西藏第一部情景喜剧《快乐生活》

西藏第一部情景喜剧《快乐生活》
为了节约费用,剧组租了日喀则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剧组人员从拉萨到日喀则,多住一天酒店就多产生一些费用,所以拍摄时间很紧:全片20 集,一天拍一集,一共拍了20 天。导演和编剧分别是普布次仁和尼玛顿珠,当时给的薪酬不高,他们主要是想做这件事——拍一部西藏没有拍过的情景喜剧。“我们就简单地想通过故事本身、还有演员的表演来吸引人,而不是那种大制作、豪华的。”编剧尼玛顿珠其实对这次拍摄寄予了其他一些想法。在普布次仁看来,那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剧本用时两个多月完成了,但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电视开拍了还在改剧本:白天剧组人员拍戏,尼玛顿珠晚上在宾馆里加班加点地写。
《快乐生活》是普布次仁退休前和尼玛顿珠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尽管退休了,普布次仁的艺术工作并没停下。年近古稀,普布次仁身体健康,精神状态也很棒,几乎每年和尼玛顿珠合作,为藏晚创作明星“铁三角”的小品。舞台上,他俩是演艺事业中的好拍档。舞台之外,两人是兴趣相投,归隐自己小院的好朋友。
D 小隐于院,别样的浪漫

普布次仁家的房子,院子里没有封阳光房,就是自然的样子

普布次仁在打理家里的花
回到家中小院,两个话剧团的主创“大咖”只是最普通不过的养花人。
西郊话剧团的大院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院子,但是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院子装修成了阳光房,尼玛顿珠和普布次仁家的院子始终保持露天状态。
“很多人喜欢把院子包起来,做成阳光房什么的,我根本就不动,然后在院子里种很多的树,养很多的花。我只种一些好养的花,名贵的花我不养。”无论别家如何,普布次仁坚决不动自家院子,让花儿自然地接受风霜雨雪的洗礼,这一点和尼玛顿珠的想法不谋而合。“现在很多人都包起来了,弄得干干净净的,很高级的样子。有时候下雨看起来可能脏一些,因为灰比较多,我们的院子就是很自然的。”
交流养花心得,分享其他种类的花种子成了现在二人日常联系紧密的主要因素。“我家院子里现在有一盆洋菊,七八月之后进入秋天,花开得特别大,花瓣很大,花很饱满特别好看。这是老师给我的种子。”尼玛顿珠说道。退休后的普布次仁变身种子猎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四处寻找收集其他颜色的花种子:“今年花的颜色就多了,之前只有一种颜色,我到处去找别的,后来终于在甘丹寺转的时候,偶然在一个僧人的院子里发现了我没有的红色。我特意等到今年快出苗的时候,再坐车过去,问那个僧人能不能给我一粒种子,他说可以,于是我现在为止有了三种颜色。”直接去花市买回来种容易又便捷,但等待、跋涉和分享的过程不失为一种别样的浪漫。
另一边,尼玛顿珠也做了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情。他家后来盖了厨房的地方,以前是块空地,他在那里种过青稞:“为什么种青稞的?这是有讲究的,我会提前问好老家的人们哪一天开始种青稞,他们种的那一天,我在拉萨也同样种下。这个事情有点浪漫,就是我院子里的青稞长到什么程度,我就联想到家乡的青稞长到什么程度。我这边青稞成熟了,那边的也好像成熟了。当然后来发现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毕竟院子里的条件和农田还是不一样。”尼玛顿珠笑言。
尼玛顿珠特别喜欢老舍的散文《养花》。“他谈到花是怎么种的,而且他的很多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比如说,‘北京的天气不好,所以名贵的花种不了。所以我就种一些比较好养的花。可是有的时候天气不好,风吹雨打,有些花就被冰雹打死了。’他就会伤心好几天。实际上是在影射当时北京大的社会环境,花其实是指他的那些学生。意思就是我可能养不了那些能成为总统的人才,但是我能养一些老百姓的孩子。”在字里行间尼玛顿珠寻找到老舍先生的很多生活小情趣和自己不谋而合,更添惺惺相惜之感。
藏族有一句老话:搞音乐的人,会听懂鸟的语言,能听懂水的声音。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也是一样,尼玛顿珠这样认为:“我们艺术创作者和普通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更有文化什么的,而是对生活的细节的关注。我们会从某些普通人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东西看出一些可爱来。比如小狗小猫,有的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啊,多脏呀,不要去弄那个。但是我们觉得看着它们的眼神,能发现很多可爱的东西。”
因为空间有限,尼玛顿珠说家里的院子不能种很大的果树。不是为了果实,而是享受繁花满园的美丽:“比如去年我老婆就在家里种了一棵桃树,不是为了吃桃子,就是为了春天的时候赏桃花。”尼玛顿珠和妻子之前一起合作完成了《哈姆雷特》的藏译版,将来他们准备继续合作,朝儿童文学发展。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以及生活在其中的虫子、蚂蚁、蝴蝶等,将来也许都会成为他们儿童文学作品里面的主角。不得不说,院子与人的这份互相成就,也十分浪漫。

工作中的尼玛顿珠

这棵洋菊花的种子是普布次仁送给尼玛顿珠的,以后会开粉色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