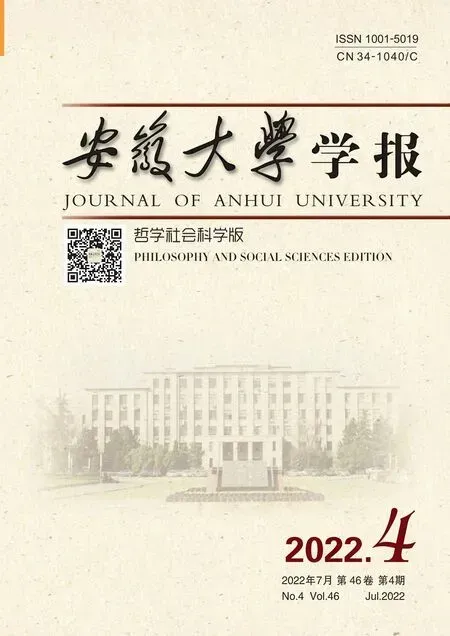图绘仙山:峨眉道教形象的塑造与表述
2022-07-25王浩
王 浩
中国自古便有以图像绘制山岳的传统,“流观山海图”是了解地理、想象宇宙的一种方式,山岳图的绘制过程中就已蕴含了时代的观念与想象。峨眉现在以佛教四大名山为人所熟知,其作为道教“第七洞天”的历史却往往被淡忘和忽视;峨眉是道教名山之一,早在汉晋以前当地就有较多神仙修道的传说。当前学界对峨眉山道教的研究多集中在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峨眉佛道关系(1)骆坤琪:《峨眉山佛、道关系试探》,《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韩坤:《峨眉山作为道教名山的早期历史刍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 张妙:《唐宋峨眉山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韩坤:《峨眉山及普贤道场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道教传说景观(2)骆坤琪:《峨眉山仅存的两通道教碑》,《四川文物》1988年第2期;余红艳:《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以“白蛇传”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肖遥:《峨眉山风景名胜区寺庵理法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考察较多,在研究视野上忽视了一类围绕峨眉山的道教图像材料;另一方面,道教图像的专项研究(3)许宜兰在《道经图像研究》中专辟一章对洞天福地图像进行研究,参见《道经图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61~313页。中也缺乏对洞天福地图像个案的深入分析。本文将从图像研究的视野对峨眉的道教图绘作人类学的“浓描”(4)蔡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和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的对话》,《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和阐释,旨在回答峨眉山道教图像系统是如何动态生成的?峨眉道教图绘蕴含和呈现着怎样的道教想象模式及宇宙意识?峨眉道教图绘如何植根于地方社会历史并隐喻这一过程?
图像人类学的方法是近年来图像研究领域在符号学、现象学取向后开辟的新路径(5)邹建林:《影子与踪迹:汉斯·贝尔廷图像理论中的指涉问题》,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50~61页。,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主张用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透视图像(6)Hans Belting,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Body, tr. by Thomas Dunlap,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1.,关注人的身体和想象在图像生成、感知中的作用,从而弥补图像的符号学研究取向的限度(7)刘晋晋:《图像与符号: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中的符号学与反符号学》,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4年。——对人的感知和想象力的忽视;对图像主体性的关注将其从艺术的禁锢之中、文字的附庸位置释放出来,获得了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图像—媒介—身体”(8)Hans Belting,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Body, pp. 19-36.的三元结构是人类学方法对图像的考察进路,图像与媒介需要区分,前者是观念性的、心灵性的文化存在,后者则是物理性的存在;图像往往是跨媒介存在的,人的想象可以将图像从媒介中激活。从“心灵图像”的角度考察图像,其本质就是观念中的“形象”(9)邹建林:《关于“心灵图像”——从人类学角度看图像的性质》,《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因此峨眉图像系统的深描需要以历史流变为经、以媒介转换为纬,进而阐释这一图像意义之网和图像背后的地方想象。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文化之网上的动物(10)[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峨眉图像系统的意义在人的地方实践过程中得以实现,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
一、心图·景图·绘图:跨媒介的峨眉道教图像系统
峨眉在不同的媒介中被呈现和表述,作为“道家仙山”与“道教名山”的峨眉形象的流变过程并非线性的演进和转换,而是历史的“层累”与交叠,这其中每一种图像媒介——口传心像、景观物像、文本绘像(11)李菲:《心像·物像·绘像:阿尼格冬与藏边社会地方历史的图像隐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2期。——有各自侧重的表述功能:从分散式的景点到集群式的景观,从弥散式的口头传统到系统性的图画绘像,这是一个“叙仙山之景”与“绘真山之形”共存的生成过程;峨眉山被道教图绘为一个物产丰富的人间仙境。
(一)叙仙山之景:心图、景图与峨眉符号化
峨眉的口头传说、故事书写与景观叙事相互生成,传说故事依附于景观并构成景观图像叙事的一部分,地理空间的命名、地域传说的生产是人经验地方的过程与结果;峨眉山独特的地文环境为民间传说提供了重要的叙事动力和言说空间,口传心像与景观物像彼此依存,地理现实与文学虚构错杂交融。“写仙山之景”是峨眉道教图绘一以贯之的主题,从汉代葛由入山成仙传说到宋代大量道教景观命名,在历时的维度中, “仙山”图绘从峨眉道教兴起、兴盛到与佛教争辩、融合的过程中一直存续;从共时的维度看,在弥散性的口头传统和景观叙事中,峨眉山被意象化和符号化为道家仙人的修炼之“洞”、授道之“台”、 祭祀之“观”;峨眉山成为一种“道家仙山”的存在。
被认为成书于西汉的《列仙传》作为第一部系统叙述神仙事迹的传记作品,较早记载了作为道家修仙之山的峨眉,绘制了早期仙人入山、结庐的图景。周成王(西周)时期的羌人葛由乘木羊入峨眉绥山修道的传说(12)(汉)刘向,邱鹤亭注译:《列仙传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开启了峨眉仙山的图绘,这一图绘中可以看到从各个层次对峨眉山的印象勾勒。峨眉被定位在“西蜀”,这是对峨眉山文化地理的定位,葛由的羌人身份展现出峨眉位于汉羌文化交融地带;峨眉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被呈现,体现出一种纵深感觉,这种勾勒与中国古代山水画法“深远”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纵深、重叠之处完成了峨眉文化区域的定位。葛由上的是位于“峨嵋山西南”的“绥山”,此处的“绥山”即是二峨山,是峨眉山脉的一部分,“高无极”是从山下仰望山巅的视角描绘,此时描绘峨眉的视角和构图方法从“深远”转换为了“高远”;接下来又从由近及远的“平远”视角描绘了山下的数十处道祠,绥山上可助得道的仙桃。最后,在三个层次的描绘完毕之时,用八句诗进行了画面的综合和主题的升华(13)原文可见《列仙传注译》第33页:“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爰涉崇绥,舒翼扬声。知术者仙,得桃者荣。”,诗句总结出这幅图的核心主题乃是——“灵”,这一入峨眉山图展现了三重灵验叙事,骑手雕“木羊”是第一重灵验叙事,葛由“舒翼”“成仙”是第二重灵验叙事,得“桃”知术是第三重灵验叙事;峨眉因而在此三重叙事中被想象和绘制成了位于西蜀之地汉羌之间的、人人向往登之、可以摘桃修炼得道的“仙山”。
最初的道教口传心像展现了峨眉山作为养生、隐居、成仙的去处,道家的理念、想象与山脉形成关联。这一时期和类型的图绘还只是对峨眉仙山的一种印象式勾勒。景观的命名是口头传统对仙山之景的叙说,道家神仙传说通过命名与物质景观结合,峨眉道教景观的命名以三字偏正结构为主,一般以道教神仙(如“九老”“药王”“仙皇”“八仙”等)或道教活动(如“炼丹”“授道”)为前缀,以地景特征(“洞”“台”“坪”“观”)为后缀,地文与人文相互结合。同时,不同的地景特征则对应着相对稳定的故事主题,洞窟(14)峨眉山上被道教命名的洞窟有白龙洞、药王洞(又名炼丹洞)、九老洞、十字洞、仙人洞、三仙洞、桂花洞、左慈洞、伏羲洞、女娲洞、鬼谷洞、三霄洞、丹砂洞、祖师洞、龙门洞、猪肝洞、烂柯洞、乾洞、飞手洞、刘海洞、迎仙洞、玉簪洞、鸡公洞、八仙洞。一般被想象为修炼、成仙的地方,授道、斗法的活动在台坪(15)峨眉山上被道教命名的山坪有宋皇坪、授道台、仙皇台、歌凤台、三望坡、升仙台、斗龙坝、华严坪、雷洞坪等。上进行;宫观(16)峨眉山上最早的道观是乾明观,另有纯阳殿(吕仙祠)、牛心寺、遇仙寺等。是民间祭祀道教神仙的地方,作为道教景观中人工构建的部分,宫观与洞窟、台坪共同构成了峨眉道教景观叙事体系。峨眉山道教景观的命名逻辑以道教神仙在峨眉山上的各处停留与活动轨迹为核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传说圈”(17)[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9页。的集群效应,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葛由成仙”传说景观群、“轩辕问道天真皇人”传说景观群、“九老仙人”传说景观群、“白蛇”传说景观群等。
口传心像与景观图像完成了峨眉的祛魅化、神格化和符号化过程,峨眉山被塑造为一个可以抵达的“人间仙境”(earthly paradise)(18)黄士珊:《写真山之形:从“山水图”、“山水画”谈道教山水观之视觉形塑》,《故宫学术季刊》2014年第4期。,为道教的“入山”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黄士珊指出,相对于佛教遥远难抵的天边净土,这一理念是中国宗教宇宙观的一个独特贡献;这种人间仙境的图绘植根于道教形成初期所宣扬的“乐生”的思想主旨,主张延长生命、追求长生的“乐生”思想与佛教死后涅槃、来世轮回的观念有着根本差别,这也是道教图绘峨眉山的思想根基。
(二)绘真山之形:图画、造像形塑峨眉洞天
视觉性的景观图像经由身体感知投射在物质媒介上成为图画与造像,这个过程是视觉图像到观念图像再到视觉图像的转换。人可以从各种媒介中激活和抽象出关于峨眉的道教图像。
峨眉山的道教图绘种类多元。第一类是功能性的图,以《二十四治图》、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为代表的道教洞天图、山岳真形图,以谭钟岳《峨山图志》为代表的峨眉山道观和景观地图;第二类是艺术性的画,有叙事性的民间故事画,也有观赏性的山水画;第三类是道教碑刻、造像,如纯阳殿碑刻、白娘子的造像、赵公明的造像等,这类物像也参与了道教图绘系统对峨眉的形塑之中。民间故事画与景观地图对峨眉山的绘制还属于对“仙山”之景印象式勾勒的范畴,而系统性较强的真形图、宗教性绘制动机的造像则是对峨眉作为道教“真山”之形的绘制与形塑。
东汉,张道陵在蜀地鹤鸣山创建五斗米教,构造了作为教区的“二十四治”(19)王纯五:《天师道二十四治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20页。,这二十四治大部分在巴蜀境内,鹤鸣山与峨眉山距离很近,饶宗颐在《张道陵著述考》中列张道陵著有《峨眉山神异记》三卷和《二十四治图》,但认为《峨眉山神异记》疑为伪托。而后张陵之子创立八品游治,意为流动的、具有巡视功能的教区(20)王纯五:《天师道二十四治考》,第73页。,其中峨眉山为游冶第一。现存道书中流传下来的“二十四治”图见表1。

表1 道书中的“二十四治”图
以上所录《二十四治图》所构建的道教治所体系可以总结为表2:

表2 “二十四治”结构表
据王纯五考证,当时与峨眉同属犍为郡范围的有中品八治中的第四治稠稉治、第五治北平治、第八治平盖治,下品八治中的第五治平冈治。另外本竹治、主薄山治也普遍被认为与峨眉山相隔甚近,当时已经有观念认为本竹治有龙穴地道与峨眉山相通(21)卿希泰:《关于峨眉山佛道兴衰的历史演变刍议》,载永寿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五斗米教当时在峨眉山及其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因而被纳入教区之内,构建了巴蜀天师王国的教区图。
道教的“福地”观念比“洞天”观念形成早(22)[日]三浦国雄:《论洞天福地》,载《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2~359页。,峨眉在东晋就已被视为“炼丹福地”。葛洪在《抱朴子》中借《仙经》叙述峨眉作为“可以精思合作仙药”的山脉(23)(晋)葛洪:《抱朴子》,卷四《金丹》,载《道藏要籍选刊》(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同时叙述了其他二十七座山,这些山中有“正神”,有神仙助力可以生成“福药”。作为炼丹药的山脉,峨眉与其他山上“上皆生芝草”,灵芝、草药等植物资源充沛,“可以避大兵大难”,环境安稳祥和,这是对福地自然与社会状况的描绘,因而在山中也有“地仙之人”修炼和居住。陶弘景在《真诰》中用“兵病不往”(24)(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一《稽神枢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1页。确立了“福地”的概念和核心特征,在这二十四座山中福地的系统中,峨眉与青城是最西边的位置;与天师道二十四治相比,此时的福地之山分布范围更广,峨眉从一个蜀地天师道较为中心的治所变成了最西边的福地。
陶弘景在《真诰》中将峨眉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一,其从洞天排序、所在山脉、洞体大小、洞天命名几个角度对洞天进行描绘,成为后来描绘道教洞天的基本程式:
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坛华阳洞天……句曲洞天,东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罗浮,皆大道也。(25)(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一《稽神枢第一》,第195~196页。
陶弘景指出洞天之间是相互连通的,地处西边的峨眉与包括金陵句曲洞天的其他山洞之间有大道相连。陶弘景描绘的福地系统范围东至会稽天台山、括苍山,西至青城山、峨眉山,北至嵩山、少室山,南至罗浮山。这一广阔的福地图像经过唐、宋道士的绘制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和系统化。峨眉洞天图绘存在三种知识性文书中,分别是唐代司马承祯《天宫地府图》(26)(宋)张君房《云笈七笺》,卷二十七《洞天福地》,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08页。、唐末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27)(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藏·洞玄部·记传类》第1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5页。和北宋李思聪《洞渊集》(28)(宋)李思聪:《洞渊集》卷1~6,见《道藏·太玄部》第2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5~841页。。
这三者对峨眉的图绘在洞天大小、位置、命名上基本相同,峨眉位列三十六小洞天中第七位置,洞的范围空间也都被描绘为周回三百里。但其中对治居峨眉的神仙描述有些微不同,司马承祯《天宫地府图》中峨眉为真人唐览的治处,而到了北宋李思聪《洞渊集》中变成了天真皇人的治所,并且描绘了一幅皇帝问道峨眉天真皇人的画面。唐览在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中绘制在“第六右位地仙散位”(29)(梁)陶弘景,王家葵校理:《真灵位业图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1~272页。,注曰“华山”,在《真诰》卷十又详细描绘了唐览居林虑山时遭受鬼击被道士救活,现在居住在华山,“合服得不死”(30)(梁)陶弘景:《真诰》卷十《协昌期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8页。。杜光庭将峨眉作为华山之佐理,应该也与唐览有关,两山本同处于西边,这也许是蜀地五斗米道北上之后传播所致。李思聪的峨眉洞天图绘叙述了道教一个经典的传说图景:天真皇人授道黄帝于峨眉,这一传说最早从魏晋开始建构,作为一个跨派系的较有影响力的神话形象(31)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03页。,天真皇人更加巩固了峨眉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形象。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峨眉山的图绘形象从巴蜀天师王国的一所“游治”变为道教的“第七洞天”,而这一图绘形象转换的关键就是峨眉山天真皇人传说的建构。下文将以此出发,探讨峨眉山图绘形象与图绘方式的转变。
二、仙山·名山·真山:峨眉形象转换与图绘的非具象化
与弥散式的景观叙事、口头传统相比,峨眉山道教绘像完成了形象转换、系统整合和非具象化的过程。
峨眉形象从“道家仙山”转换为“道教名山”,图像的绘制植根于宗教历史的发展之中。六朝时期各种宗教都在进行权威的建构,其中经典建构是最重要的环节,而此时峨眉山就被道教想象、形塑成藏有天书之地,道教中翻译和传播经典的天真皇人在此时也被建构出来,峨眉山是其居所,这一“皇人之山”形象的图绘完成了峨眉作为道教名山建构的关键环节。从天师道二十四治图绘开始,峨眉山被纳入一个更大的体系之中,这一范围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开始蜀地天师王国的“八品游治”之一到《天宫地府图》三十六洞天之一,峨眉山的道教图绘是融汇于洞天福地系统的建构过程之中的,这与峨眉成为道教名山的过程是一致的。
经过名山形象转化和洞天福地系统整合,峨眉的山脉形象呈现出“非具象化”的转向;司马祯所作《天宫地府图》的插图业已散佚,配文是一种印象化的书写,三浦国雄认为原图应该与《道藏》所收的《五岳古本真形图》是相像的(32)[日]三浦国雄:《论洞天福地》,载《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0页。,峨眉在杜光庭的描绘中出现于“中国五岳”中的西岳范围,从道教图像的绘制传统来看,三浦国雄的判断应当是准确的,道教常常提到“真形”的概念,黄士珊经考察指出“真形”亦即“无形”(33)黄士珊:《写真山之形:从“山水图”、“山水画”谈道教山水观之视觉形塑》,《故宫学术季刊》2014年第4期。,峨眉道教图绘经历了山脉形象和视觉语言的双重“非具象化”过程。
(一)“皇人之山”的建构:名山形象转换的关键关节
李思聪《洞渊集》中峨眉变成了天真皇人的治所,关于峨眉山天真皇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魏晋《抱朴子·地真篇》与《太上灵宝五符序》所引的《太上太一真一之经》中。《抱朴子》中黄帝来峨眉山向天真皇人求真一之道(3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3~324页。,而《太上太一之经》则叙述天真皇人为皇帝解读《天皇真一之经》的故事(35)《道藏》(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16~333页。,这个典故一直流传到唐宋,天真皇人传授神话成为道教一大跨派系的神圣传统。宋代神仙传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详细记载了这位仙人:
天真皇人,不治其得道之始,然是前劫修真极道之人也。身长九尺,玄毛被体,皆长尺余。黄帝时在峨眉绝阴之下,苍玉为屋,黄金为座,张华罗幡,然百和香。侍者仙童玉女,座宾三人,皆称泰清仙王。黄帝再拜问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又在峨眉山以太上灵宝度人经授黄帝,又授帝喾于牧德之台。一云蜀岷山江北有慈母山,天真皇人修炼之所。(36)(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正统道藏》,卷四,第1页。
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中可以得知天真皇人主要的职能是传授经书于黄帝,峨眉山是藏有道教天书的宝地,也是皇人修炼、黄帝问道之场所。峨眉山与道教的经典及神仙联系起来。而《抱朴子》和《太上太一之经》所记载的是传授“真一之经”,此处却变为了灵宝经,这说明故事流变中部分经典被替换,但是峨眉授道的主题被保留下来,天真皇人也一直作为道教经文的记录和传播神存在。据上描述天真皇人有记录、翻译、传播的神力,作为黄帝时期的“前劫修真极道之人”,被定位为峨眉山的治理者,这位神仙是道教天书的翻译者,从魏晋到唐宋的材料可以看到峨眉山与这位对道教经书权威建构十分重要的神灵联系起来,到了宋代,天真皇人在峨眉山授黄帝《灵宝经》,此经在当时道教内部十分重要,这一叙事范围的不断扩大将天真皇人塑造成了整个传世道书的源头(37)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42页。,峨眉山也就成了天书产生的神圣之地,北宋李思聪在《洞渊集》中绘制的峨眉第七洞天的掌管者从唐览变为天真皇人便可以理解,其绘制的信息来源是这则天真皇人的神话。进一步可以追问,天真皇人的神话渊源何处?
骆坤琪在《峨眉山宗教历史初探》(38)骆坤琪:《峨眉山宗教历史初探》,《宗教学研究》1984年第1期。中提出《三皇经》中对峨眉山的叙述,《三皇经》乃晋代经书,已经失佚,《三皇经》将峨眉比附为《山海经·西山经》中的“皇人之山”,大概是因为位置相似的缘故。《太平御览》中确实引述了《三皇经》中“天真皇人”的传说,《云笈七笺》卷六记录了峨眉山藏有《三皇经》的线索(39)(宋)张君房:《云笈七笺》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6页。,峨眉山又恰是天真皇人所居之地,因此可以判断天真皇人确实与《三皇经》有关;由此推测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仙被魏晋六朝的道书汲取了古典中的传说,将其塑造成了天书的翻译者,从魏晋到唐宋,从授真一之法到授灵宝经,这一天真皇人授道黄帝的主题已经被广泛记载于道书之中;天真皇人的权威性通过辅佐听命于元始天尊,授道于黄帝、帝喾的情节被树立起来,而峨眉山作为皇人之山,藏经授道之地的形象也被固定在了跨派系的各种道教经典之中。
除了道教经典文书中的建构,民间也一直参与到“皇人之山”的建构中。天真皇人授道的传说在峨眉山的景观空间中被附会定位,授道台、仙皇台等景观被命名和叙说,《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还记录了峨眉山中建造了天真皇人的祭祀宫观。正是文书与传说的交互绘制,使得峨眉山“皇人之山”的形象得以明确并广为传播;《魏书·释老志》记录“道家之源,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40)(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8页。,这是正史第一次对宗教的书写,就已经有在峨眉授道的情节了,此处老子是作为皇人的化身而存在,从这一正史记录中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宗教经典、民间传说还是官方正史,都已经将峨眉视为重要的道教名山了,其神圣性就是建构在“藏经之山”“授道之山”的形象上。
“天真皇人”作为道教特有但并非主要的神灵,其最初的形象十分模糊,王承文在研究古灵宝经时曾提及天真皇人可能作为古代南方传说中的一位仙真(41)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91~739页。,这一传说在蜀地流传多时,甚至已经形成了祭祀传统。目前对道教经书中天真皇人形象建构与流变研究最系统的是学者谢世维(42)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39~166页。,他追溯了天真皇人最早的传统应是三皇文和三一修行传统。结合几类文本追溯可以发现,民间黄帝问道皇人神话的流传与道教三皇文、三一修行传统是这一形象母题最初的源头,魏晋道家又将其改造为天书的翻译、解读者,这种天人之间的中介身份直接建构了其神圣性存在,这种神圣叙述的框架被不断充实进新的道书经典,巩固和传播了天真皇人的形象,峨眉作为“皇人之山”的形象就这样在多元并行的笔墨中被绘制、勾勒,得以清晰和传播。《山海经》中对皇人之山的论述也被纳入峨眉这一形象的建构中,“西山”这一位置被作为建构的对象,应该说这是道教传播到更宽广的区域后,峨眉属于“西山”的地理境况被认知和比附,在陶弘景绘制的洞天图中就将峨眉作为最西边的代表,而后在五岳文化兴起后又被建构为西岳的范围,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峨眉超出了二十四治的蜀地范围被建构成了全国性的“道教名山”和“第七洞天”,天真皇人传说被经典化和正史化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二)真山之形与宇宙秩序的对应
山岳洞天图绘在道教中被称为“真形图”, “真形”的命名和概念通过观察真形图像的特征得以理解。真形图以方形构图为基础,外部是黑色方框,内有曲折蜿蜒的黑色条状图像(图1、2),中有文字填充或说明,规则的方框和不规则的抽象图案形成一种对比;文字的加入既可能与中国传统“诗书画”一体的图文观念有关,又是道教认为“文字乃山岳妙气一部分”的“天书观”的体现(43)谢世维:《圣典与传译:六朝道教经典中的翻译》,《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7年第31期。。 而单色木刻的图像工艺所形成的白底黑图则蕴含了“阴阳有致”的观念。结合“山岳”的主题与背景,扭动的黑色抽象符号所指或为仙山所凝聚之“气”的观念,此乃山岳之“真形”——流动变化之“妙气”,在此,山岳的“真形”所具备的短暂、流动的特点引入了一个“无形”的境界,而这也导致了真形图视觉语言的“非具象”(non-representational)(44)黄士珊:《写真山之形:从“山水图”、“山水画”谈道教山水观之视觉形塑》,《故宫学术季刊》2014年第4期。特征。道教视觉呈现的特征应放在宗教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解。

图1 《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西岳华山)(45) 取自《道藏》第6册,第737~743页。道教洞天系统发展中曾认为峨眉为华山佐理。 图2 《青城山真形图》(46) 取自《道藏》第6册,第739页。距离峨眉较近的青城山真形图。
葛由入山图将“桃”作为仙山的象征,洞台、芝草、仙人塑像也相继成为仙山形象图绘中的符号化意象,但是道教教义、教区完善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峨眉山道教图绘中越来越呈现的非具象化的一面。这种非具象化一方面体现在不断地把峨眉在二十四治、三十六洞天中与其他山脉联系起来,这种变化使得峨眉的道教图绘获得更大范围的方位确认。另一方面体现在视觉语言的神秘性特征,在图绘中就是“山岳真形图”的绘制。《天宫地府图》中的图绘被认为与《五岳真形图》(图1)相似,杜光庭又在论述西岳华山时提及峨眉,这种图绘是一种“神秘性图像语言”(47)黄士珊:《写真山之形:从“山水图”、“山水画”谈道教山水观之视觉形塑》,《故宫学术季刊》2014年第4期。,图像中黑色的条状图形在白色方框中有流动之势,这应该与道教“气”的观念有关,山形如“气”一样流动变化,“真形”正是这种变化之中得以体现;事实上这种山之真形变化与神仙真人变化是相通的,二者的本源应都是“道”的无穷变化观念。道教的山脉图绘希望用这种变化着的“真形”去接近山的真实本质,在图像的视觉语言选择上就呈现出一种“无形”,这是对现象、表相的一种剥脱和超越。在追溯了这种视觉语言的宗教哲学源头后,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与绘制者对山脉的切实认知相关的,有学者提出了真形图的“地图学”特征,这类山岳真形图也确实为道士入山提供着实践性的功能,从这一视觉认知出发,“真形”图绘的视觉语言应该与云气环绕的山脉印象有关。总之,对山脉的“气”的想象和模糊的认知,与“道”的哲学思维结合,形塑了这一非具象化的视觉表达。
所谓“真山之形”,指向的是峨眉道教图像中呈现出的宇宙秩序和想象模式,山脉形象和视觉语言的“非具象化”的过程意味着道教宇宙想象的成熟化。系统化的《二十四治图》到《天地宫符图》中呈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想象。《正一炁治品》首先叙述了二十四治的来源是太上在汉安二年“下付”给张道陵天师的(48)(北周)宇文邕:《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正一炁治品》,《道教典籍选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93页。,这一“天降”旨意从发生学的角度将二十四治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上品、中品、下品各八治是“应天二十四炁,合二十八宿”。“炁”与“气”相通,指代一种神秘的能量,是道家哲学的一种观念;“气”存在于人身体内,也存在于宇宙起源之中。“宇宙”是一个中国本土传统观念,“四方上下”乃是“宇”,用“房屋”比喻天地空间概念,“古往今来”则曰“宙”,代表的是古今时间的概念。《二十四治图》绘制的治所大多靠近成都平原周围的山川地区,山脉体系的绘制对应了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星宿。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总结了二十四治与节气、星宿、干支、五行的对应表(49)[法]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师道的空间与科仪结构》,《法国汉学》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2~253页。,这种绘制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分野观”的体现;将天上星宿与地上空间一一对应,因此这种体系化、非具象化的图绘所植根和呈现的就是本土道教观念中的宇宙秩序。
二十四治与节气、星宿、历法的对应,同时峨眉山在洞天福地系统中处于三十六洞天的“第七洞天”,这一数字也有着天地之间的对应。三浦国雄指出这是道教融合了佛教三界二十八天和道教八天的成果(50)[日]三浦国雄:《论洞天福地》,载《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0页。,进而将天上与地面对应,从二十四、二十八到十、三十六、七十二,这些神圣数字都是宇宙观念的象征,将其运用到图绘中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的投射。
综上所述,峨眉道教图绘中既有具象化的绘制元素:道台、洞窟意象、仙人、道士塑像,也随着道教体系化的过程呈现出非具象化的倾向,这种非具象化指向了体系化与图像语言神秘化,“皇人之山”的形象建构是从“写仙山之景”到“绘真山之形”转换的关键环节。从神秘数字的角度,可以一窥山脉“真形”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对应,进而我们可以追问峨眉山道教图绘中蕴含和呈现了怎样的宇宙想象。
三、 身体·洞窟·宇宙:峨眉图像中的道教宇宙想象
“皇人之山”的形象在“授道台”“仙皇台”等景观和传说图绘中得以呈现和形塑,它展现了作为“洞天福地”的峨眉山是传授道法、符经的场所,神仙的降临、黄帝的求索是典型的图绘程式。而峨眉道教图像中更为常见的意象——“洞窟”——的绘制则体现了道教特殊的想象模式和宇宙意识。在《二十四治图》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到傅飞兰(Franciscus Verellen)指出的中国特殊的“关联宇宙论”(51)[法]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师道的空间与科仪结构》,《法国汉学》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0页。,而在峨眉洞窟图绘中可以发现这种关联宇宙论更具象的存在形式。山脉就是这种关联宇宙论中最核心的中介性存在,山脉在道教宇宙图式的形塑绘制过程中有着根基性的作用,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山脉想象脉络,同时也是地形地貌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山脉在社会稳定时期是求得长生之地,在社会动乱时期是躲避兵难之所。从蜀地兴起的天师道在扩散发展的过程中将这种山脉想象进一步传播到全国范围,洞窟的藏经、修炼功能是山脉得以道教化呈现的想象根基,道教想象脉络中,洞窟、洞庭和洞天的想象接续出现,成为这种“关联宇宙图式”的中介性存在,其核心功能是完成了人的身体和宇宙之间的连接转换,也就是说身体和宇宙都通过洞窟化得以达到“合一”的想象境界。同时,山脉的中介作用还体现在宇宙结构的建构之中,山脉是道教整体的宇宙想象图式中最核心的图像元素,天界的人鸟山图、地界的五岳真形图、天地宫符图、冥界的酆都山图共同构成了道教的宇宙图式组合,呈现出一种立体式的宇宙结构,峨眉的图绘既是这一宇宙结构的组成部分,又可以窥探出三重宇宙空间之间的关联。
(一)身体·洞窟·宇宙:经验性的想象模式
在峨眉山第一座道观——乾明观修建以前,峨眉山的修仙道士大多处于穴居状态,杜光庭在《神仙感遇记》中描绘峨眉山有七十二洞,洞穴景观是峨眉山的核心视觉要素。从 “仙山洞窟”到“名山洞天”,道教在图绘峨眉的过程中将洞窟作为山脉最重要的意象和指代符号,对洞穴景观的深度描绘与道教特殊的洞穴信仰有关,在道教峨眉图绘中可以一窥这种洞天宇宙观的形塑与呈现。
在道教观念中,“洞”即“通”,洞天即“通天”(52)姜生:《论道教的洞穴信仰》,《文史哲》2003年第5期。,洞穴与天(宇宙)是相连通的,峨眉山的洞穴图就绘有大量的“入山”/“入洞”的情节,白娘子入白龙洞中修炼,九老洞中有赵公明修炼的石床遗存,洞穴之所以可以成为修真之地就在于其通天的象征功能。另外,“洞”也被道家视为母体和子宫,复归母体是获得永恒的根本途径,这也是道教把握宇宙规律的根本方法(53)姜生:《论道教的洞穴信仰》,《文史哲》2003年第5期。。在峨眉道教图绘中,上山—入洞—成仙的过程是一个类似重生的过程,葛由飞仙、白蛇蜕变的想象根源就是“洞”与母体的象征性关联。洞窟具备了天地连接和生命转化的功能,进而也成为“道”的具象化呈现,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洞窟被提升到“道”的哲学高度,成为万物的来源及与宇宙的连接,那么在道教的峨眉山绘制中作为最突出表现的图像也就可以解释了,这是由道教根本性的对“道”的想象决定的。“洞”与“道”的连接体现出一种空无哲学,峨眉山“虚凌洞天”的命名就是描绘其作为一个无边无际、充盈灵气的修炼空间。
以上两种关联想象模式被三浦国雄总结为洞窟的“宇宙化”和“身体化”(54)[日]三浦国雄:《论洞天福地》,载《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7~356页。,西汉末年的浑天说促使道教将宇宙想象成一个封闭的洞窟,身体的孔窍与山脉的洞窟形成一种类比,可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想象模式,可以推测这种想象建立在道教对南方喀斯特地貌景观经验的基础上。另外,这种想象转换也是双向的,洞窟往往被视为“地肺”,“空洞”在道教文献中时常指代宇宙,洞窟的描绘往往是口小腹大,内涵万物。道教模仿盘古尸体化生传说叙述了老子的身体变形成为昆仑、星宿等世间万物的传说(55)[日]三浦国雄:《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第353页。;《云笈七笺》中记录盘古身体化成宇宙的神话:“垂死化身气成风云,身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56)(宋)张君房:《云笈七笺》卷二十七《洞天福地》,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16页。道教借鉴这一表述描绘了老子身体化为宇宙万物的场景:
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山;发为星宿,骨为龙,肉为狩,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毛为草木。心为华盖。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57)(唐)道宣:《广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52册,第144页。
道教这种将身体宇宙化的想象贯穿到洞天福地的形塑之中,身体入洞从而与宇宙相连。道教内丹著作《修真太极混元图》中的《人世七十二福地图》(图3)和《海中三岛十洲之图》(图4)就将人体穴位与洞天福地进行对应,这种观念影响下一些洞窟游记叙述仿佛是在人体中游览一样(58)李丰楙:《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3~238页。。洞窟与身体和宇宙的连接转换是道教洞天—宇宙观的核心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洞仙”观念和神仙位阶体系发展出了一个多层次的宇宙结构。

图3 《海中三岛十洲之图》(59)(宋)萧道存:《修真太极混元图》,取自《道藏》第3册,第96页。 图4 《人世七十二福地之图》(60)(宋)萧道存:《修真太极混元图》,取自《道藏》第3册,第96页。
(二)天界·地界·冥界:立体式的宇宙结构
《抱朴子》在描绘峨眉山时提到山中有“地仙”之人(61)(晋)葛洪:《抱朴子》卷四《金丹》,载《道藏要籍选刊》(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是谓名山,《天地宫符图》也描述了执掌洞天福地的不同位阶的神仙。这是和道教的宇宙想象紧密关联的,峨眉图绘中的“飞升”“降神”的情节展现出一个立体、垂直的宇宙结构,之所以会在山脉图绘中看到这样一种宇宙结构,在于道教的宇宙观建构就是以山脉为核心的。道教建构的中国本土神话宇宙观以“天人合一”为总特征,以山岳为核心,其基本结构是“天界—地界—冥界”的立体呈现,其想象模式是“身体—山岳—宇宙”三位一体的连接和转换。
中国古代对山的认知主要有“山中有神”和“山可通神”两种观念,道教承继了这一山岳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伦理化和体系化,使之成为宇宙观构建的核心和宇宙空间的象征区隔标志。山岳在道教核心的神仙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山为帝王封禅通神与民众修道成仙提供了条件,道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 “人—入山—成仙”这一离俗获得长生的思想(62)姜生:《论道教崇山的原因和实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山是道教哲学与实践的核心媒介,“入山”术语至今仍被用在道教仪式和法事中,道坛也被比拟为一个山形的微缩宇宙。山岳在宇宙观中的核心地位从道教所特有的各类《真形图》中得以呈现。道教所谓“真形图”既是“写真山之形”,又是“绘宇宙之像”,它是道教山水观和宇宙观的双重呈现。道教真形图主要有《玄览人鸟山经图》(图5)、《五岳真形图》(图1)、《酆都山真形图》(图6)三大类,这些道教特有的真形图体现出山岳在宇宙观中的核心地位。天界的“人鸟山”,地界的“五岳”,以及冥界的“酆都山”境构成了一个垂直、立体的宇宙结构。

图5 《玄览人鸟山经图》(63)取自《道藏》第6册,第697页。 图6 《酆都山真形图》(64)(南宋)蒋叔舆:《无上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取自《道藏》第9册,第609页。
人鸟山乃是天界诸多仙山的统称,其绘制和想象的传统来自昆仑这一宇宙神山。《玄览人鸟山经图》中的经文写道:“太上曰:人鸟山之性质,是天地人之生根,元气之所因,妙化之所用。”(65)《道藏》第6册,第696页。在此,天、地、人三才并列,“元气”与“妙化”展现了宇宙演化的内容,人鸟山被赋予了宇宙生成的意义。“人鸟山”的命名在经文中这样解释:“无数诸天各有人鸟之山,有人之象,有鸟之形。”(66)《道藏》第6册,第696页。人鸟山具有“一山七名”的特征,它的异名包含了须弥山、悬圃山、大地金根山、本无妙玄山、元气宝洞山、神玄七变七转观天山。“须弥”“悬圃”分别是佛教和中国传统的宇宙山,东晋《太上玉经隐注》中有“昆仑人鸟之山”这样的并称,道家发展了此说,将昆仑山与人鸟山相区分作为西王母和元始天王各自的治所,由此也可以一窥人鸟山是以昆仑这一传统宇宙神山为原型而被创造的宇宙山。经文记载了人鸟山所居神仙有“太上大道、十方天尊、元始真王、人鸟山元气生神、太帝君一”等,这些神仙皆属于道教天界尊神,对应着人鸟山在道教宇宙观中的“天界”层次。而与昆仑紧密关联的西王母则学道于元始天王,经文记载其学成归去“刻文于人鸟山”的情节母题在道教经典中普遍出现,也成为《玄览人鸟山经图》这一道教经典神圣性建构的重要环节。
五岳和诸洞天是作为地界和人间仙山存在的,是可以通达的仙境,《五岳真形图》应该是在东晋以前由道士绘制,葛洪《抱朴子》中记载:“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6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36页。《五岳真形图》为道士入山提供了辟邪和指引功能,所谓“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迎”(68)《道藏》第32册,第629~630页。,因其所具有的实践性功能,在绘制中呈现出道教神秘符图与地形图的结合特征。《正统道藏·洞玄部·灵图类》刊有五岳真形图以及霍山、潜山、青城山、庐山真形图,这四座山分别是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的佐命之山,南岳衡山“独孤峙无辅”。五岳本是帝王祭祀天地之所,是标示帝国疆界的重要山脉,道教在建构宇宙观时将其纳入洞天福地体系之中,使之成为道家人间仙境。
酆都山是冥都鬼神世界的象征,其绘制始于南宋,承继了《玄览人鸟山经图》与《五岳真形图》的绘法,反映了道教对死后生活和灵魂去向的想象,酆都山图像大多在道教超度仪式中被使用。从《玄览人鸟山经图》《五岳真形图》《酆都山真形图》的绘制和使用,可以看到道教宇宙观中山是沟通人间与天界和冥界的中介,也成为立体式的洞天宇宙结构建构的核心。
结 语
以“第七洞天”为主题的道教图绘植根于宗教普遍性想象与峨眉独特地文的双重形塑之中,峨眉洞天的图绘与想象背后是道教对“不老不死”的追求(69)[日]三浦国雄:《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第223页。。图像的绘制蕴含了深刻的宗教历史隐喻:峨眉的道教图绘展现了其形象从道家仙山到道教名山的流变过程,走向淡忘的景观图像也表征了峨眉在佛道之争中逐渐转变为佛教名山、“普贤道场”的历史本相。图像的绘制是人经验地方、想象地方的方式,也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70)Tim Cresswe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04页。的生成过程。
图像人类学将图像视为“心灵图像”与“物理图像”的结合,关注人的想象在图像生成和感知中的作用,峨眉的个案呈现出心图、景图、绘图的跨媒介图像体系,揭示出本土图像绘制中知识传统和想象传统的融合。图像—媒介—身体的理论视角确立了图像本身所具备的主体性,从而将其从艺术和文字的附属地位中释放出来;将图像视为一套囊括了观念、动机、行为模式等各种因素的实践模式(71)安琪:《文化遗产关键词:图像》,《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有助于挖掘更多“地方性图像”的价值,从而更全面地审视古往今来的图像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