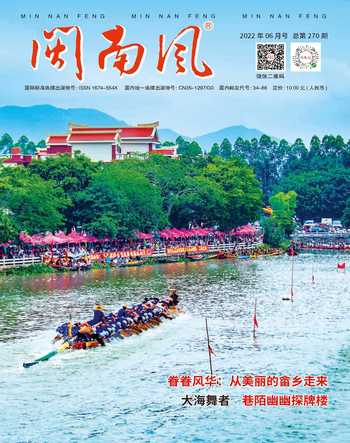“吃新”
2022-07-22张弓
张弓
在客家新泉镇,一直流传着一个特别的节日——“吃新”。这里是客家人聚居的古镇,“吃新节”是一年当中仅次于春节的一个节日。
俗话说:“牛歇谷雨马歇夏,人歇‘吃新’不要哇”。每當节日将临,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都要赶回家中过节。
“吃新”又叫“尝新”。在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吃新节”也许是唯一没有确定日期的节日。其时约在农历“小暑”到“大暑”之间,以早稻成熟为标志。
据考证,“吃新”习俗最早可追溯至黄河流域的周部落先民,并且在我国早期的古籍《诗经》《礼经》《淮南子》等中均有记述。“吃新节”的主要内容是贡奉新谷、祭拜谷神、祭祀祖先等礼仪程序。
每年春播之后,田野的稻谷进入抽穗期,人们为祈福耕种作物有个好收成,过了小暑,就会挑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在开镰收割之前,合家共聚“吃新”,以庆贺丰收,并祈祷神明,祝愿来年五谷丰登,百业兴旺。一家人欢聚一堂,过一个祥和的节日。
记得小时候,“吃新”那天,拂晓天不亮,母亲就早早起床,浸米、备馅,做一种叫捆粄的美食。当时的生活条件极其困难,一般常用的馅料是萝卜、青菜,或者南瓜。母亲从谷仓的瓷瓶里,拿出炸油之后的渣肉,跟刨成丝的萝卜一起切细,加入葱,炒熟备用。
这一天,母亲不去下地干活,算是她最休闲的一天了。然而,她要在家里忙碌,一刻也不闲。我跟姐姐早上起来,帮忙磨米浆。一个人双手推拉磨石,一个人用勺子打米。乳白色的米浆从石缝里溢出,流到石槽,汇入铝锅。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当年的场景,会被那些留在记忆中的往事触动心灵。那么朴实、鲜活的生活,呈现我脑际的许多细节,像陈酿多年的老酒,越久越馨香、陶醉……
捆粄是客家人用米浆制作的一种美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会做。我们从小吃到大,对捆粄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过节能吃上捆粄,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以至于在日后的生活中,远离家乡,捆粄像勾勒在记忆中的乡愁,经年累月,日思梦缠……
平时炒菜用油,都是比较节省的。做捆粄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炒馅料放的油,必须多一点,做的粄才好吃。而且还要加香葱、胡椒粉,这样做出来的馅料,味道棒极了。做捆粄还要精制粄皮油,加葱花、芝麻,用食用油炸一下。制作好的油,涂抹粄皮,做出来的捆粄味道,特别美味。一道朴实的小食,做出了家的味道。
母亲做好了捆粄,一般是最小的妹妹先吃,然后弟弟吃,一人一捆。等他们都吃了,才轮到我吃。之后,才安排姐姐和哥哥吃。一圈轮流下来,需要二十分钟。有时,弟弟、妹妹会赖皮,一圈没轮完,就抢着要吃第二捆,母亲就会劝我们,他们更小,先给弟妹吃饱了,再去吃。哥哥、姐姐知道争不过他们,都离开厨房,到别处去玩了。我守在厨房里,看着弟弟、妹妹吃,吞着口水,傻乎乎地等,心里很不服气,但又拿他们没办法。等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吃饱了,母亲总是最后吃。母亲虽一字不识、没文化,但是,她身上折射出来的,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善待儿女的优良美德。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从小培养出一种纯真、善良的品格,一直影响我的人生。
母亲在灶台前做捆粄,我帮忙烧柴火。时不时往灶台里添加木柴,并且要控制火候。火太旺了,要降下来;火太小了,要让它烧旺一点,这样才能保持,水一直是烧开的状态,做的捆粄皮才是均匀的。对母亲来说,“吃新”这一天,名义上是休息,但她从早上五点起来,做馅料、浸米、磨米浆,整个过程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到捆粄做好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吃饱了,母亲已忙碌了大半天,不比下地干活轻松,很辛苦的。但是,母亲毫无半句怨言,她总是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一个母亲的职责。
我们一边吃捆粄,一边喝温开水。每次,捆粄吃饱的时候,温开水也喝了两碗下去,肚子圆得跟西瓜一样,鼓鼓的。这时候的感觉,特别的好。母亲看着我们吃饱的样子,一脸微笑。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成人,该是她心里最幸福的事情了。
记得有一年“吃新”,几户人邀约,用刚刚收割的油菜仔,加工成菜油,用新鲜的菜油炸灯盏糕。米、油大家凑,炸了多少灯盏糕,几户人均分。剩下的油,也按份均分。那时的日子,虽然过得艰辛,大家聚在一起炸灯盏糕,却也不失为乐趣无穷。节过得简单、纯朴,却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丰富了我的童年。
这种过节的味道,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起来,就感到特别的温馨和幸福。这让我无论走到哪里,想起过节,想起家的味道,就会特别想念已经去世的母亲。
如今,时代不同了,大家都往城市发展,许多良田都荒了,没人耕种。现在的人,可能从小到大,都没过“吃新”节,没体验春播夏收的生活节奏,没人会记起,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有一个叫“吃新”的节日。这个代表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展望与祈福的传统节日,会因为人们都在追逐工业化社会的生活而失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