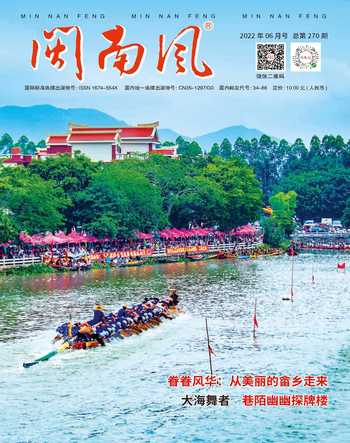在路上
2022-07-22许佩霖
许佩霖
她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高高瘦瘦,看起来虽然文文弱弱,但却有另一种豪气。
她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一旦有假期就走。一个人一个背包就远走他方。坐飞机到北京,再坐火车到新疆,徒步旅行。
当她拿着一张地图侃侃而谈时,我是很钦佩她的。这是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的画面:落日余晖,茫茫大漠中,一个人,一串脚印。她跟我说:“在夕阳下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喜欢上了在路上的感觉,但是我的旅行跟青春无关。我始终觉得我离青春甚远,自然不会因为青春就远行。我只是喜欢行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就想明白了一些事,有了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或者是为了摆脱只有“家——学校”这两点一线的生活,走出我那番狭隘的天地。
当我去到那些心仪的地方时,我总是报团。有人说出门旅行总跟着旅行团有什么意思,像赶鸭子一样。我从来都不否认这些。我只是爱听导游的解说,他们说的有的是书本上或者网上没有的,哪怕只是当地一个小小的故事,或者一个小小的民俗。好的地方去一次怎么够,待到疫情退去,带着这些我必然会重走那些路,那时我便能跟我身边的人说:“你知道吗?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莆田,一个小小的湄洲岛都震慑于那尊巨大的偶像,仿佛其他地方都黯然失色。从天后宫下来,我徒步走在一个不知名的渔村里,呼吸到的空气都带着点咸味。那时夕阳西下,阳光渐渐收敛,只落下粼粼微光在不远处的海上,一层层荡开去,竟有一种颇为耀眼的光芒。村子很静,很静,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出外打工,只有偶尔的狗吠。我知道那尊偶像是听不到我内心诉求的,自然也保佑不了我心想事成。倒是这个静静的渔村,让我暂时忘却了所谓的烦扰,有了片刻内心真正的平静,也成了我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
去云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也不是那些屡次被印上明信片的景点,那个地方我依然叫不出名字,甚至未能驻足观赏。我只是在前往香格里拉的途中,匆匆一瞥。透过车窗,我看到了那已经忘却了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花海,那时正有对新人在拍婚纱照。而我脑海中对于云南的记忆就定格在了这一个画面。
在路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去发现更多的美,而不是别人告诉你有多美。而这种美,有时只是在不经意间。
北岛说:“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当一个人还有能力行走时,就应该努力去拓展自己的世界。
当你远行回来时,你会发现你生活工作的地方并不是世界必须围着转的永恒轴心。这时候,有些曾经看似重要的人和事,开始渐渐淡出你的生活。每一次远行都可以是一次“遗忘”,又可以是另一次“重生”。旅行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拍了多少照片,又花了多少钱,而在于你改变了看问题的方式。
在《昨日的世界》中,面对着一战那种狂热的“爱国主义”,茨威格说他却特别冷静,这并不是他能把问题看得清楚,而是因为他长期行走于其他国家。“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像我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家园”。一战中,他和罗素一直在为和平事业奔走,也正是因为在身份认同上,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于“世界公民”,而非奥地利人。
有时候看问题的方式一旦改变,整个世界都会随之变化。在路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你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