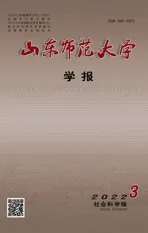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谭献与袁昶
——兼论“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分层*①
2022-07-21孙之梅
孙之梅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龚自珍逝后的第二年,魏源与龚橙合作完成的《定庵文录》《定庵外录》,开始了龚自珍诗文的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才有了王佩诤的全集本。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对龚自珍思想与文学的认识。本文从谭献、袁昶入手,考察同治、光绪年间人们对龚自珍的多元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理论。
一、谭献对龚自珍诗文的搜集与评价
谭献与龚自珍之子龚橙有深交,其文集中的重头传记文《哀亡友传》中有《龚橙传》,其中记述了自己与龚橙的关系:“献二十余岁兄事之。”后与龚橙之子仍有过往。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间,龚橙子谈及其父身后寥落,并示遗著《诗本谊》一种。龚自珍是谭献乡贤,谭又与龚氏有两世交往,对此焉有不关注之理。我们检阅《谭献集》与《复堂日记》,就会注意到谭献对龚自珍诗文的搜集和多处评价。龚自珍逝后的第二年,龚橙托魏源编过《定庵文录》12卷、《定庵外录》12卷,龚橙对此本进行了删削,存文9卷、诗词3卷。遗憾的是此本没有刊刻,仅留下了魏源的《定庵文录序》一文。直到同治七年(1868)才有了第一个刊本,即吴煦本。而谭献搜集编辑龚自珍诗文则始于同治二年(1863),《复堂日记》云:
付写人抄龚定庵文。龚文《初集》刻本予得之子高,写本数十篇得之林芗溪及《经世文编》,将合成一集,《初集》中有目无文者补之。此外子高欲名之《余集》,予以原目别有《余集》名,未知为何篇,不若定为《外集》,著吾辈所搜辑云尔。何时见孝拱,尽得先生遗文,勒成全集,以贶后人。(1)谭献著,范旭仑、牟小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子高,即浙江德清戴望(1837—1873),是谭献之友。林芗溪,即福建诗人林昌彝。谭献当时拥有的龚自珍文献,一部分来自戴望赠送的《初集》刻本;一部分来自林昌彝提供的数十篇文选;还有一部分来自贺长龄等编的《经世文编》所收文录。《初集》是龚自珍道光三年的自刻本,有上中下3卷,存文46篇。谭献请写手过录的是后二者,命名为《龚定盦外集》。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六日条云:
阅《龚定盦集外文》一卷,杭人谭献所传录者。定庵通经制训故之学,以奇士自许,其文学杜牧、孙樵而成,然自倔强可喜。此卷共五十六篇,雄诡杂出,亦多有关掌故。(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4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349-2350页。
谭献曾经把《外集》让李慈铭看过,存文56篇,多于《初集》10篇。同治九年(1870),《复堂日记》又记:
阅《定庵文集》七卷毕。定公文旧见于孝拱所及魏默深刺史案头者,稿本盈尺。游闽识林芗溪教授;教授客杭,曾假读全集,刺取若干篇。孝拱令写人录赠,即此本也。予借教授本传写一通。时江浙陷贼,孝拱踪迹不相闻,恐全集遂散失,欲存其略。德清戴子高来福州,又录一本去。会稽赵益甫避乱至,亦录一本。因各有搜讨之约。乱定,知孝拱流寓上海,楹书无恙,写本置行箧循诵而已。林抄本无目录,予从《定庵初集》刻本目录,补其未刻诸篇,佚者尚多,其他略仿《初集》义类次第之。戊辰五月出都,重见孝拱,则杭州有刻龚文者曹老人云。孝拱言:“曹老人者曾卖墨京师,为先君子食客,粗识字而已,谬托知交,所刻不知何本,贝也缪可想。”属予归访之。盖曹老人前自益甫得此本,懵不知流传端绪,写工又简略,怂吴晓帆方伯刻之,缪谓龚先生手定。刻既成,触手讹夺。龚先生一世班扬,传人有子,全书繁重,传世有待;刻百十篇,以厌学子先睹之心,未始非盛举。而曹老人谲觚荧眩,出自意外,要当备述以告读者。孝拱既怼此举,拮据料量,刻布全书,则曹老人实激成之,亦功臣矣。定庵先生收食客之报,在彼不在此。(3)谭献著,范旭仑、牟小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
《定庵文集》当是同治七年(1868)的吴煦本,除了龚自珍自刻3卷外,增加《定庵续集》4卷,存文105篇。综合谭献日记,可知吴煦本的来龙去脉:林昌彝是一大源头,一流向龚橙,一流向谭献。谭献找写手过录此本,在太平天国之乱中,与戴子高、赵益甫相约各自搜讨,他们二人又各自过录一本。由于这个本子没有目录,缺佚亦多,谭献补上目录,并按照初刻本的义例将搜集到的佚文次第编排。赵益甫过录的本子流转到曹老人手里,又由曹老人促成了吴煦本的问世。因此吴煦本最大的功臣首先是龚自珍的自刻本,其次是林昌彝和谭献的补充辑佚本。显然此本与谭献所掌握的仍有出入,且“触手讹夺”,《复堂日记》批评:“吴下新刻《定庵文补遗》,于已刻之文篇目不同,复见至六七首。似竟未寻检,可谓卤莽矣。”(4)谭献著,范旭仑、牟小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6-167页。因此,他从中刺取若干篇;同时也有他已经录入但吴本未收的,编成《外集》。谭献本最终没有刊刻,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因其与吴煦本的相似,其版本价值似乎也不被龚自珍集的整理者所重视。
同治、光绪时期,与搜集整理龚自珍诗文集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其诗文的评价,当时并非一边倒地肯定,不过谭献的评价却基本是正面的。《复堂文集》卷一《明诗》认为前50年之作者“智足以知微”的贤者只有汪容父(汪中)、龚定闇(龚自珍)、周保绪(周济)诸君子。(5)谭献著,罗仲鼎、俞浣萍点校:《谭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页。《复堂日记》所评更加具体入微,云:“读《定庵文集》。《平均篇》《著议》《农宗》《五经大义终始》《古史钩沉论》树义既高,文体迥出。《蒙古图志》诸叙、《西域》数文,制作之盛在此。其他序、记、志、传、杂文,则犹未湔唐习,甚者且有诙气,不及容甫先生之大雅矣。并世两贤,殆难鼎足,庶几周保绪乎?”(6)谭献著,范旭仑、牟小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页。于龚文褒贬互有,而于龚词则赏爱有加,《日记》比较其诗词:“诗佚宕旷邈,而豪不就律,终非当家。词绵丽沉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7)谭献著,范旭仑、牟小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页。《复堂文集·微波词叙》评价钱枚词云:“浙西词人,云属霞举,揭櫫六家,以为职志。先声同调,接武旁流,莫能尽也。乃有杳眇湘君之佩,苍凉成连之琴,屈刀为镜,唾地生珠,如钱吏部谢盦先生《微波亭词》,非朱、厉以来所能蓋也。先生高言令德,旷代逸才,遐举人海之中,托兴国风之体,玄微其思,锵洋其音,如谢朓、柳恽之诗,所谓芳兰竟体者已。同时龚定盦仪曹,横绝一世,目空千古。填词超超,有飞仙剑客之概,而倾倒先生,若同工而异曲。”(8)谭献著,罗仲鼎、俞浣萍点校:《谭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9-200页。龚自珍曾撰《钱吏部遗集序》,称赞钱枚词:“小乐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难言,疑涩于口而声音益飞,殆不可状。”(9)龚自珍著、王佩铮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在浙西词史中,以龚自珍词“横绝一世,目空千古”之“飞仙剑客之概”竟对钱枚“倾倒”,由此可见钱枚词之不凡。谭献借龚评来印证自己对钱词的肯定,并认为钱、龚乃六家之后发扬蹈厉、颉颃而同工的两位大家。
谭献对龚诗虽有“豪不就律,终非当家”的批评,但是他从福建归杭州时,做了一个《今人诗选》以遣日,其中选叶润臣《敦夙好斋诗》12卷100篇、吴西林《临江乡人诗》4卷87篇、符雪樵《卓峰草堂诗》14卷60篇、吴仲伦《初月楼诗》6卷56篇、龚定庵《破戒草》34篇、黄春谷《梦陔堂诗》32卷112篇。(10)谭献著,范旭仑、牟小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页。显然对龚诗还是青目相看的。
谭献对龚自珍诗文词的评价算不上充分,但是这在同治、光绪前期来看是可贵的。
二、袁昶接受龚自珍之纠结
袁昶与谭献同是浙江人;同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其座主是张之洞;袁昶是杭州太守薛时雨的侄女婿,谭献于同治八年(1869)入薛门执弟子礼;同治六年(1867),他们同为杭州诂经精舍编校。谭虽年长袁14岁,但多种交集,决定了他们是一生的好友。
从袁昶《毗耶台山散人日记》与其诗集看,同治六年六月开始出现关于龚自珍诗文的引文与评论。袁昶与谭献的学术祈向、文学趣味有较大不同,因此反映在对龚自珍的关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袁昶一生喜欢玄学、理学、佛学与道家学说,诸种学说归结到实践层面,就是全身远害、保养心性、隐逸市朝,文学上比较注意为文之法。《袁昶日记》里关于龚自珍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为文之法的。云:
魏默深评龚定庵《平均篇》《农宗》《古史钩沉》,论之言曰:“圣于文者,其文秃。曩者黄泥裹锐笋之谓也,其味闭;洞澈阴阳至精,笑之以为喜,迂之以为忧之谓也。”定庵当之矣。(11)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页。
光绪元年(1875)三月有云:
文必模范体格而后成,是谓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盖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而相寻于其迹,是执迹之所在,而以为是履也。博学属文,心通其意,近世惟实斋、龚定庵能知之。(12)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前者称赞龚自珍文为“圣于文者”;后者评价龚文尤其之高,同光时期,古文高涨,桐城文派、阳湖文派高手如云,袁昶认为章学诚之后,龚自珍一人而已。但是袁昶对龚自珍的推崇,不断受到质疑。首先是他的座主张之洞。张之洞在清末不仅是一个朝廷倚重、勤于进取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博学深思的学者、文人,对袁昶的人生宦途影响至深。同治十年(1871)三月,袁昶拜谒张之洞。《袁昶日记》云:“谒辞南皮座主,与师广论六艺之旨。言言平正通达,可以切实奉行,有益身心,不同外道。又论龚自珍之文,诡体遁词,无一可用。盖啜九流二氏而不返之五经四子书中,必致浮浪无归也。又戒予为文须去忼厉迫激之词,一归和平温厚,方为厚集其福。如此之类,倾谈甚快。”(13)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 86页。张之洞也许觉察到袁昶的思想与为文受到了龚自珍影响,因而直接针砭龚文“诡体遁词”“浮浪无归”,贬斥龚文悖离古文大道,文体文词均不称。袁昶在日记中未表达听了此论的感想,但是却记下了相类之语。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大署仁和龚礼部文集,始以礼部为文中之祅。又曰:‘定公富于狂慧,舞智以御道,而无忠信。五行无土,闰气浸淫,不足贵也。予惧后人为其所惑,故揭橥如此。’”(14)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9 页。从此,袁昶似乎接受了“文妖”之说。《袁昶日记》光绪三年(1877)五月一条载:“昨与张子忠论吾浙嘉道间贤大夫,黜龚定庵而进姚镜塘,以定庵文带妖气。”(15)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光绪八年(1882)十月中一条记载了他去拜谒前辈学者周寿昌时的对话:“先生斥言定盦龚氏制行之非,根器儇薄,误后生不浅。某答言:‘朱子称涑水之文如桑麻谷粟,窃谓为文得此意始有裨世教。定盦则失之太远,殆文中之妖,并不得与杨铁厓之诗同年而语乎。’”(16)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26页。显然此时他对龚也持“文妖”之说。“文妖”之号本是冠于元末诗人杨维桢,袁昶甚至认为龚自珍不可与杨维桢相提并论。
但是袁昶对龚自珍的接受有点纠结,情感上放不下,理智上越来越排斥。光绪元年(1875)他提到了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并解释说“天下之俗,靡然旋转如风,故谓之风然”。光绪二年(1876)年底,他去拜访江宁的汪梅村,看到其所居有三重门,立即联想到龚自珍“三重心” 之说。光绪四年(1878)二月,读到《左传》“明淫心疾”语,想到龚自珍《戒将归文》中所云“心疾之遘,光景聚兮”。光绪四年八月游访潭柘寺,形容胡僧为“蛆虫僧”,明言用的是龚自珍语。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他形容当世情形云:“乱世犹可望治,暗世不可望治,君子小人纷然在列,鲂鱼赪尾,四郊多垒,此乱世也。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上下雷同,是非相蔽,此暗世也。”其理路正出自龚氏“衰世说”。从袁昶对龚自珍诗文的信手拈来,不难看出他所下的功夫。不过他还是提醒自己不要陷进去。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确立为学家法:“村叟家法,无论自课及课子,勿务为龚、魏高远劳心之举,第遵守湘乡曾公家塾日程,以读、看、写、作四字为准,毋博爱致劳而少功。”(17)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643-644页。
袁昶这种纠结,当与龚自珍经典化的步伐有关。同治光绪时期,龚自珍诗文集各种版本纷纷面世,作者以他“独醒”之姿态与“知微”之见识,吸引了大变革前文人们敏感的心灵,加快了龚自珍经典化的节奏。袁昶的放不下正在于此。他本来可以义无反顾地去追逐时代潮流,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有两位人物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位是张之洞,另一位是郑孝胥。袁昶结识郑孝胥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冬。郑孝胥在光绪十一年应李鸿章幕之聘,由南京入津,冬随李鸿章入京,并准备参加丙戌年(1886)的会试,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报罢南下。其间他与京中文人广泛联系,其中就有袁昶。《袁昶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十二年(1886)四月有记载。前者云:“夜过郑苏龛孝胥、王旭庄中舍,谈闽中先辈蔡二希、雷翠庭、孟瓶庵诸公。苏龛言,陈恭甫先生寿祺为人颇不满于乡里,瓶庵先生则乡人皆敬重之。”王旭庄,即王仁东,福建闽侯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时在京中任职内阁中书。后者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云:“偶见闽中郑苏龛作半寸许真行书,结体疏而有法,兼具潇洒出尘之姿,一见神耸。其《报罢留别友人诗》云:‘门外春将暮,天涯绿尽生。’结句又云:‘再别青门道,沧江卧已成。’摆落语,亦甚可味。”郑孝胥的诗、书令他钦佩(18)《袁昶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观闽人孝胥所作八分书,疏逸得天然之趣,此君胸襟殊超淡,书诣当月有异境。”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与郑苏龛论文字利病。君极喜道园虞文靖公,予以为然。又谈黄老之学,大要在善审诎、信消长自然之数,世无常伸之时,人靡常伸之运。《孟子》言大任生于忧患,术智存乎疢疾。《老子》谓受国之垢,处众人之所恶,是为善损,损之又损,乃所以为益也。葛忠武《戒子言》:‘当忍诎信,去细碎,绝情欲,弃凝滞,广咨问,除嫌吝。’此皆丁宁善诎之义也。”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20、800页。,为以后的往来打下了基础。此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特别是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张之洞代署两江总督,郑孝胥为总督幕中红人,袁昶任安徽道台,因工作地缘关系他们的交往日多。袁昶曾主动示好,馈送郑孝胥银两。郑孝胥推辞,袁昶表示将来芜湖修筑纪念黄庭坚祠堂,请其撰写记文,此款不过是预订润例而已。(1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作书托爱苍,谢不受爽秋之馈,称海氛甚恶,将恐到沪折回,未能成行,敬以实辞。俄,爽秋回答爱苍,言非盗跖之粟,且于湖新修涪翁祠堂,他日将乞书记文,先以为润云云,乃受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74页。《袁昶日记》记载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某夜访郑孝胥的感想:“见洛中士大夫,与之语,昏昏白日欲寝。惟见苏龛则扫障翳、见青天,使人心开目明。君所论亦多平实切中利病。”
张之洞论龚自珍,上文已论。郑孝胥是同光体巨擘,闽地诗学传统转变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相与谈学术,谈文学,相识时谈话主题是“闽中先贤”,而后自然会涉及浙江先贤。光绪十五年(1889),二人交往较多,所谈多诗文利弊。此年二月某日,郑孝胥的一番话对袁昶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袁昶日记》所载如下:
苏龛评论江龙门、张亨甫,有叫嚣气,不免有犁靬眩人、吞刀吐火伎俩。又云:“龚定庵文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殆不及鲁通甫。”予谓“定庵挟其九流朱子之学,明阴洞阳,奥词赜意,辨者之囿,非通甫可望。惟过于陵暴驰骋,殆亦有独坐之功,而未造能适之境耳。至其论事实暗,不及通甫之切实透快也”。(20)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93页。
郑孝胥批评了近代的江开、张际亮、龚自珍和鲁一同,特别是文坛关注度日高的龚自珍,其批评的理论是“惊四筵”与“适独坐”。郑孝胥的评论在逻辑上存在递进关系,先说江开、张际亮和鲁一同,后说龚自珍,前者为“眩人吞刀吐火伎俩”,后者尚不及此,把龚自珍贬低到前者之下。袁昶不能全部赞成其说,但是“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激活了袁昶经年寻觅的理论核心。就在这一年十月,他与高白叔谈论杭州文派,其中有“近世不及乾嘉,乾嘉不及国初。国初染于石斋黄公大涤书院、蕺山刘公证人社之教,故声光气魄全不同。莫衰于龚氏,以后伪体多”(21)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834页。的观点,把龚文贬斥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归结于郑孝胥的影响。
三、“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
“惊四筵”“适独坐”源于《金史·文艺传·周昂传》:
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22)脱脱等撰:《金史·文艺传》(第126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30页。
周昂是金代有成就的学者、诗人,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有建树的理论家,《金史》本传将其文学理论概括为两点:一是“文章以意为主”的创作论。“文章以意为主”的理论始于杜牧(23)杜牧《答庄充书》云:“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2页。,杜牧认为文章之高低取决于意、气和辞采,三者之中意最为关键。周昂在继承其观念的同时,提出“内”与“外”、“工”与“拙”两对概念与之互文。“工”有时也表达为“巧”,云:“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甚,则失其本。”(24)王若虚:《滹南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7页。“巧”“拙”概念的引入使“文章以意为主”的理论削弱了杜牧儒家文以载道的倾向,偏向于道家的内敛与朴拙。这一理论深得清中期赵执信的赞赏,其《谈龙录》说到读《金史·周昂传》时不禁有异代知音之感觉,云:“余不觉俯首至地,盖自明代迄今,无限巨公,都不曾有此论到胸次。”(25)赵执信:《谈龙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二是“惊四筵”和“适独坐”、“取口称”和“得首肯”的文学审美论。“惊四筵”“取口称”的审美效果通俗地讲,就是吸引眼球,鼓动口水,容易被接受,容易激发接受者的情绪。那么是什么东西引动了受众的骚动?用郑孝胥的话说是“犁靬眩人、吞刀吐火伎俩”,用袁昶的话说就是“陵暴驰骋”,为了实现感染力、煽动性,“惊四筵”的作品会使用夸张惊悚的表现手法,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而“适独坐”“得首肯”显然是周昂、郑孝胥以及袁昶更为欣赏的审美论。这种审美论要求作者具备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品格,作品要有内涵,有深度,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更适合读者的潜心独悟,心领神会。
“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是中国诗学史上一直存在的现象,即审美的分层问题,例如诗歌,《诗经》中的国风与大小雅,汉代乐府与文人诗,两晋的民歌与玄言诗……但是这种审美理论的提出则要等待时机,金元时的周昂是创论者,但这一理论除了对王若虚有所影响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理论效应。晚清文学面临着两种惯性: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刍,使学人的思想力度进入一个较高的水平;一是社会问题太多,刺激读书人去学以致用。因为反刍的内容有所侧重,反刍后的反应、接受和产出也会不同。龚自珍的诗文应该是两种惯性的集结点,形成了一种文学对时代的冲击力,而这种冲击力既存在于接受者,也存在于不接受者。如梁启超等自然属于接受者,郑孝胥则属于不接受者,袁昶属于犹疑者,而龚自珍的“名噪”激发了审美分层论的被发现。
在郑、袁讨论龚自珍之前,袁昶已经关注“惊四筵”“适独坐”的理论,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在此之前曾四次提及。光绪八年(1882)二月谈读书体会,引周昂的话后云:“此至言也。哗嚣之美,君子耻之。”(26)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07页。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寄语子侄为人处世与读书治学之理,提出“处世作人要极平庸”“惟于读书作文时则取适独坐,要极不平庸,方可自辟规模堂庑”(27)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669页。。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回顾自己读书奉教的经历,总结为学门径以自警:“名,最损志招谤,知希澹泊为贵,但湛思孤往,求适独坐。”(28)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697页。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借用苏洵、苏辙的话评论欧阳修文之美:“颍滨言欧阳子文妙处,在不大声色。即文安赞欧文所谓‘纡馀委备’,特此四字,有妙悟耳。”接着以之阐释周昂的理论:“文章哗嚣之美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之意,作文之利病益于此辨之。”(29)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74页。这四处中袁昶对“惊四筵”“适独坐”的理解多集中于治学与修身养性,只有一次涉及文学批评。此时他所不喜欢的“哗嚣”只是类指,而没有具体所指,后来的“陵暴驰骋”才有了具体指向。
自郑、袁讨论龚自珍之后,“惊四筵”“适独坐”成为袁昶文学批评的核心理论,他在日记中频繁使用之,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30)袁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在庚子之乱中冒忤强诤,主张使馆不可攻、战事不可轻启而被清廷杀害。。他在有意识地进行理论构建,其意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治学为文需要下笨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方可下笔。云:“为文惊四筵不如能适独坐。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不若钝学累功,可期精熟,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多为少善,不如执一。”(31)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862页。其二,治学求有得,作文求自得之趣。何为自得之趣?苏轼答难说,吃龙肉不如吃猪肉适口;叶适说作文只是写自己心中所明,称量而出,不可借人家金银酒器以炫客;周昂说文章哗嚣之美可以惊四筵,不可以适独坐;钱大昕说作文不可苦思力索,深浅随其所得。四家之言的中心即“种学绩文,皆以优柔厌饫,有涵咏自得之趣”(32)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933页。。其三,文章不仅要表现事物的现象,还要揭示其中的理,具备理趣。袁昶读陈澧《东塾集》赞叹道:“他人务惊四筵,陈先生乃能适独坐耳。先生之文,一似姚惜抱七律诗,称心而谈,勃窣理窟,掇皮皆真也。”(33)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42页。“勃窣理窟,掇皮皆真”是“适独坐”的真谛。袁昶读李贺集,感慨的是杜牧叙文中的针砭语:“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从中领悟道:“造到茗柯勃窣、清转华妙之法界,是名适独坐。”(34)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939页。“适独坐”的关键是“适”,适就是“自得”“自然”“自娱”“自适”。《袁昶日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说到郑孝胥有“二适”:“苏龛年未四十,精神映澈,诗笔清丽。又日习英文,以为常课,令人企羡。顷语予,始衰之年,当自求二适:辟一静室,明窗净几,围以花竹,以便晏坐,一适也;聚二三素心人,近或望衡,远则数里,常获上下论议,当其兴惬,相对忘言,二适也。”郑孝胥的“二适”让袁昶于心有戚戚焉,曾自叙日常自得之境:“常收敛内景,微明自照,以适独坐”。(35)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34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袁昶整理出版其师张之洞的《广雅碎金集》,他的理论思考得到了一次阐述、发挥和提升的机会。云:
读香严师集,知公才性,向来一意孤行,不为利名所缠,不为世意所挠,穷不陨获,贵无充诎,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用心专密处,他人寻省不能憭。即以词章一艺而论,惟求适独坐之理趣,不逐惊四筵之浮誉。杨子云谓:“由于独智,入自圣门。”退之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周情孔思,日光玉洁。李翱识破古人创意造言,各不相师,故退之作语言,时到圣处;翱亦清巉曲折,一节独到。介甫云:“众然而然,小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后之读香严师集,勿执字句求之,乃能于形骸之外,时觏宗趣。(36)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182页。
这一段话先讲张之洞其人,再借题发挥,阐发自己所追寻的理想人格——独立不迁,荣宠不惊,大行其道,用心专密;表现在词章之道上,“惟求适独坐之理趣,不逐惊四筵之浮誉”。接着,梳理“适独坐之理趣”的渊源与内涵,他拈出历史上的扬雄、韩愈、李翱和王安石的相关议论来构建其理论。扬雄《法言》云:“天下有三好:众人好己从,贤人好己正,圣人好己师。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37)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4页。扬雄按照胸怀、境界把人分为众人、贤人和圣人三个层面,他们的行为准则、人生目标存在极大的差异,所谓“众人以其家之肥瘠为忧乐,故用家为占;贤者则推之于国,圣人则推之于天下也”(38)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页。。袁昶利用扬雄关于人的精神境界分层引申到文学的审美分层。“词必己出”“文从字顺”是韩愈关于古文的著名论断,其《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评价樊宗师的文学成就:“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39)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40-542页。。樊宗师的古文成就是否达到韩愈所评价的高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字表达了韩愈的古文理想,描述的是他个人的古文风貌。“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出自李汉《昌黎先生集序》(40)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序》第2页。,形容韩文传承儒家之道的精神品质。李翱早年师从古文家梁肃,后从韩愈游,其古文成就从宋代以来就与韩愈并称,明清有人将李翱、皇甫湜、孙樵并列为“唐三家”,韩愈、柳宗元、李翱、杜牧称为“唐四家”,还有在“八大家”之外另加李翱、孙樵为“唐宋十家”,由此可见李翱古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袁昶关注李翱集中于两点:“创意”与“造言”。清中期邵齐熊《李文公集补序》云:“从来古文家独推柳柳州与昌黎并称,不知李文公之文未尝不异曲而同工,俱雄而各峙者也。或谓李为韩门弟子,仅与张籍、皇甫湜辈竞,善鸣于一时。呜呼,此其说由来旧矣。今读其文,创意造言,戛然自立,绝不类韩子之文。惟其不类也,乃其所以为类。故不独子厚岭外之文,纵横争折不让昌黎,如公之义深理当,文词高简,夫宁不可鼎足于其间哉!”(41)李翱撰,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369页。袁昶之“创意”“造言”不知是否借用于邵文,然其意却由此更加明确,即强调李翱古文虽学自韩愈,但其意其言却另辟蹊径,在泱泱唐宋古文中别为一大家。介甫云云,出自王安石《送孙正之序》,为了表达完整,多引几句:“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42)王安石著,秦克、巩军标点:《王安石全集》(第3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王安石所谓的众人与君子,类似于扬雄的众人、贤人和圣人。袁昶解释道:“众然而然,俗士也,己然而然,豪杰也。”(43)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998页。众人会于时俯仰,而君子则守贞卫道,不惧茕茕独行。通过以上阐释,“适独坐”的理论内涵丰满起来:作者首先要具备丰厚的传统学问,在经史之学的基础之上精研“九流诸子之学”,达到“明阴阳,洞阳奥”;其次,应该具备独立不群、一意孤行的意志和不为得失宠辱而动摇的定性;其三,创新的品格。即如韩愈、李翱、王安石对文学的会解,达到文学的独创性。其四,文章的风格“妙处在不大声色”(44)袁昶著、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中):“颖川言,欧阳子文妙处在不大声色(即文安赞欧阳文所谓纡余委备。特此四字有妙悟耳)。此即《金史·文艺传》所云,文章哗嚣之美,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之意,作文之利病宜于此辨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774页。。“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理论从功用上看,一类是用来流播的,它面对众生,易读易懂,表达感情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和煽动性,描绘事物属于人人欲言的层面,一语既出,四筵哗然。袁昶概括这种诗歌的特点是“哗嚣”;一类是用来沉潜、理解、领悟的。它是面对宇宙人生的体悟、思考,表达一种深邃玄远的意涵,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抽象的逻辑思辨,需要读者具备相应的修养,方能灵犀相通。这样的审美论,代表着两极的审美境界,前者可以让作者获得“浮誉”,后者却可以让部分读者获得令人愉悦的情致道理。
这种关于作者、读者的层类分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袁昶把这种分流借助金代周昂的话表达出来,进行了合乎时代的理论构建,不啻让尘埋的理论命题焕发出光芒,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一大贡献。袁昶能有这样的理论贡献,首先要归结于他对周昂观点的熟悉和共鸣,而郑孝胥评龚,激活了他蓄积已久的理论意识。其次归功于他对龚自珍诗文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又受外力影响出现了“拧巴”状态,最后他“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竟然有了如此一个意外的收获。
四、余论
光绪后期,龚自珍经典化的节奏加剧。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写了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45)张之洞著、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3-154页。张之洞光绪七年(1881)出任山西巡抚,此后任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京,陛见后即奉旨同张百熙、荣庆商订大学章程与各省学堂章程。其谕旨云:“京师大学堂为学术人心之根本,关系重要。”(46)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8页。因此,他感慨离京后20余年间学术文风之变化,认为当时的情况比较糟糕:理乱、学术乖。此诗的价值在于比较敏锐地反映了光绪中后期的学风和文风,由此可知龚自珍在光绪后期被接受的程度。
龚自珍的经典化过程,光绪末民国初达到了高潮,但在同治、光绪初期,关注的人主要是浙江人。李慈铭在光绪时期是京城中的学术、文学巨擘,甲午年(1894)感愤中日战争国家战败呕血而死,其人性直好雌黄,但是对乡贤龚自珍则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书国朝文录后》统观有清一代古文,“顺治、康熙间则魏勺庭,雍正间则方望溪,嘉庆间则恽大云三家而已。其偏师之雄,顺康间则宁化李世熊《寒支集》,雍乾间则山阴胡天游《石笥山房集》,嘉道间则仁和龚自珍《定盦集》,皆奥如旷如,足以独立千载”(47)李慈铭著、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39页。。在李慈铭眼里,龚文在清代的地位可谓高矣。《越缦堂诗话》又说:“定庵文笔横霸,然学足副其才,其独至者往往警觉似子。”指出龚文“子”的特点。李慈铭对龚诗的评价颇有分寸:“诗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又好为释家语,每似偈赞。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然如《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歌》《常州高才篇》,亦一时之奇作也。”(48)李慈铭著、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84页。“霸才”“奇作”均非常才所能妄想,好用释家语而“似偈赞”,时为公安派体,均是“不成家”之表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李慈铭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上文论及袁昶接受龚自珍过程中有所谓“文妖”之说,而浙江革命党人章炳麟在《说林》中将这种意见发挥到了危言耸听的地步。云:
文辞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然佻达无骨体,视晚唐皮、陆且弗逮,以校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近实。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49)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1页。
章炳麟与龚自珍的学术家数有古文今文之别,龚文自然难入章氏之法眼。章炳麟对龚诗文语言、风格的形容描述,堪称为“文妖”的注解。他只知龚自珍文词特点,不知其思想见识所产生的启蒙作用,龚氏那种深得少年青睐的诗文有一种耸动听闻、发人深省的感染力和煽动力。梁启超感慨龚自珍的“杳眇之思”“倜诡连犿”文辞所具有的吸引力,“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50)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反清革命时期,南社以群体性的传播作用,把龚自珍推到了经典的位置,舆论、文学追求“惊四筵”的时代到来了。
在“惊四筵”“适独坐”理论被发现、阐释的过程中,郑孝胥不仅是袁昶理论意识的启蒙者,同时也是袁昶理论的阐释者。陈衍《海藏楼诗序》转述郑氏语:“君每言作诗无深抱远趣,所谓不可适独坐者固已。若处处不忘是作家,而不敢极其才思,诚作家矣,然终于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之境。”(51)郑孝胥著,黄坤、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海藏楼诗序》第3页。这里郑孝胥提出了与“适独坐”相关的两个概念——深抱远趣和深造自得,与袁昶的意思基本一致。其后,陈衍撰作《石遗室诗话》,“惊四筵”“适独坐”成为其批评武器,卷八开宗明义云:
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阔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下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非谓此数字不可用,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52)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与袁昶所说的“一意孤行”“用心专密”,词章上的“创意”“创言”,郑孝胥所说的“深抱远趣”“深造自得”大致相同。清末民初的诗坛重蹈了明末清初诗的覆辙,非刻意用空阔大字眼寻求大境界的复古派之门道,即“以寂寥言精炼,以寡约言清远,以俚浅言冲澹,以生涩言新裁”(53)沈春泽:《刻隐秀轩集序》,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1页。的竟陵派之取径。而近代陈衍用以批评的武器正是“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他希望用学术上的深造自得、思想上的深抱远趣指导诗歌走向康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