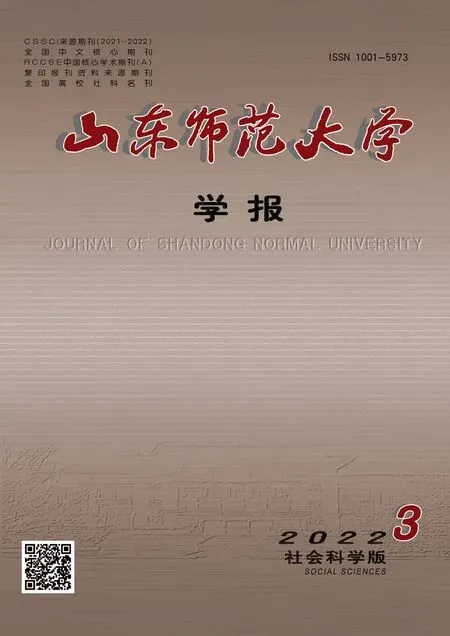《呐喊》《彷徨》的医学思维与诊治理路*①
2022-03-18黄健
黄 健
(浙江大学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
对国人的创伤描写,特别是心理和精神创伤的描写,是鲁迅《呐喊》《彷徨》创作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因为有在医学专门学校接受过现代医学的系统和专业的学习经历,鲁迅对国人的创伤,特别是心理和精神创伤的描写,是十分专业、细致和独到的。从表现方式来看,鲁迅采取的不是传统中医擅长的综合或曰整体认识与把握的诊治思维、理路和方式,而是采用现代医学分析型的诊治思维、理路和方式,对国人的精神和心理创伤进行了十分精细的诊断和描写,不仅发现了病症、病根、病源所在,而且深入剖析了病理,开出诊治和疗救的方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明确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坦陈在小说创作中采用了“医学上的知识”。(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同时,他还强调,这样做也是为了能够“改变他们(指国人——引者注)的精神”(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以践行他早年确立的“立人”思想主张和抱负。
一、由外而内:寻找与聚焦创伤背后的病源
以医生诊治思维和理路来对创伤进行描写,首先是要能够及时地发现创伤、聚焦创伤,以便能够迅速发现创伤的发病表象,为下一步确定如何医治奠定基础。以医者眼光来看,一般来说,创伤可分为外创伤和内创伤两种类型。外创伤较易发现,而内创伤的发现则要相对复杂一些。基于医学思维认知和诊治方式,鲁迅对国人创伤的发现,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看似一种常规医学思维和理路,但在鲁迅那里,却有着特殊之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及他去日本留学的目的时说,由于在南京求学时开始接触到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学知识,“便渐渐的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后来又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到日本留学后,“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以西医的现代医学思维和认知来发现创伤,其基本理路是在患者自诉(或代诉)的基础上,在发现创伤后聚焦创伤,由此作出初步判断,再进行相关的医学检查,从而得出相应的病情诊治的判断和结论,并开出治疗方案。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对国人创伤的描写,特别是精神创伤、心理创伤的描写,所遵循的就是这种现代医学思维和理路,而非用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思维和理路。《狂人日记》虽然是以“狂人”的日记方式呈现出“病情”,但实际上就是一本诊治的病历,是现代医学诊治程式的完整再现,其特点也就是由外而内地精准发现创伤、聚焦创伤的病情和病理的呈现。不同于肉体创伤的发现和聚焦,“狂人”的创伤是心理性的、精神性的,是全身心的。小说对此描写的是“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从病理上来说,这就是“狂人”的创伤,也是俗话说的“发疯”现象,属于外表性的创伤。小说就是先从这样的创伤发现和聚焦中,开始了由外而内的病情呈现过程,同时,也在开展对这种病情的诊治发现过程中,深入对国民心理和精神创伤的病理揭示过程,并最终发现了国民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内源性创伤,也即是“狂人”所说的: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用“吃人”来形容历史创伤的症结和国民创伤的源头,尽管不是医学术语,却是最形象、最直观,也是最深刻的一种病情和病源的呈现,是以最直接方式发现和聚焦创伤口的一种诊治表述。它让人们知道,国人既在肉体上“被吃”而形成创伤,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被吃”形成了心理创伤,所以,必须要正视这种创伤的事实,决不能讳疾忌医。这种病情的发现和聚焦,虽然是以“狂人”之口诉说出来,看似荒唐、疯癫、不正常,却深刻地揭示出历史的顽疾,揭示出国民心理和精神长期被残害的症结所在。尤其是发现了病症的源头在于“吃人”,并聚焦于此而展开分析,精准地找到病源,找到发病机理,进而由此开出诊治的药方——“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告诫和医嘱。这种用现代医学思维和诊治理路进行的创伤描写,可以说是高清晰度的,全方位地展示出国人的创伤部位和内源,让人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国人从肉体到精神上都是伤痕累累的病状事实,并告诉人们,如果再不对国人此类病情引起高度重视,继续在“瞒”和“骗”的路上逃避,自欺欺人,终将会加重病情,加速“堕落”,直到死亡。(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药》对华小栓患“痨病”(肺病)的创伤描写,也是十分详尽的。小栓的病状是“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且是“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拼命咳嗽”。从病象上来看,这是肺病的典型症状。对肺病的诊治,中西医的思维和理路完全不一样。小说写华老栓为儿子治病,信的是中医的路子,故相信“人血馒头”的功效,但在鲁迅看来,这不仅会贻误病情,而且更是精神的愚昧,终将导致小栓的直接死亡。事实也果真如此。无论小栓口服多么新鲜的“人血馒头”,其结果都只能是在堆堆的“丛冢”中,多添一座“新坟”而已。用现代医学批判传统中医的愚昧落后,从中展示国民从肉体到精神创伤的全过程,并由此找到真正的病根和病源所在,这也是鲁迅创作《药》的目的所在。在鲁迅看来,以医学思维和诊断来认知,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还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此时的国人都是病人,其身心都是创伤累累,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明天》中写寡妇单四嫂子为给儿子宝儿治病,信的也是中医的路子,结果自然也是与《药》里的华小栓一样。从病状上来看,宝儿的脸在“黑沉沉的灯光”映照下,“绯红里带一点青”,且“发烧”“气喘”,“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不住的挣扎”。用现代医学来进行诊治,一看便知宝儿患的是肺病,只要对症下药,应该很快就会好转起来。可是,闭塞的鲁镇如何会有这种认知?且不说当时鲁镇没有西医,即便有,单四嫂子真会带宝儿去找西医诊治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单四嫂子信的是中医,倒不如说她信的是迷信,她与华老栓的认知一样,本质上都是愚昧、无知、落后,其结果当然都是一样。
美国学者凯博文在谈到疾病的社会根源时指出:“我在研究中国的抑郁和神经衰弱上所做的努力,让我得以更好地理解一般意义上,文化是如何与情感、精神疾病,以及人类苦痛相互关联起来的,同时,尤其让我了解中国人的病痛体验。”(6)[美]凯博文:《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就人类疾病史而言,任何病理意义上的病症,其背后都有人类社会性的原因,有着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西医的诊治思维和理路,受到各自文化理念的规约,对创伤的诊治思维和理路不尽相同。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西医受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尤其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诊治思维、理路、方式、手段等方面有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从而代表了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而中医却还是传统一套,未能与时俱进。鲁迅到日本学医后,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愈发觉得中医的诊治思维和理路及其方式的落后,加之父亲就是因病而死于这种落后的医治,自己更是有着切肤之痛,故到了完全不信任中医的地步。所以,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人创伤的发现和聚焦,所依凭的现代医学思维与诊治理路,显示出深厚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与传统的中医相比,以西医为代表的由外而内的现代医学诊治思维和理路,不仅细致、精准,而且从中反映出先进与落后的鲜明对比,这更使鲁迅通过对国人创伤的发现、聚焦,能够深入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的诸多原因,并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和文化的寓意,让国人明白,在新的文明到来之际,国人其实并没有能够获得观念上的转变和更新,也没有在心理上作好接纳新文明的充分准备,依然是在闭塞、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没有出路,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如同他所描写的鲁镇那样,总是那么幽暗闭塞,那么死气沉沉,“没有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即便是旧历的年终,除了几声“送灶”的“爆竹”响,以及年复一年的所谓年终“祝福”大典,其他依然是旧的,没有更新的气息,也没有变革的活力。因此,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弱中国的子民”都已到了近于无法医治、无法拯救的地步。尽管在内心深处,鲁迅依然还抱着火一样的热情,依然要努力地去进行“疗救”。
二、由表及里:触及与诊断疼痛背后的病根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创伤,伴随而来的必然都是疼痛。肉体的疼痛是由创伤直接形成的,而心理上、精神上的疼痛,则有着诸多的因素,有的是直接由肉体疼痛而引发的,有的则是由心理和精神的原因如恐惧、忧郁、压抑等导致的,甚至也可以说,心理上或精神上的疼痛则是真正的病根所在。在小说创作中,鲁迅依据现代医学思维和诊治方式,对疼痛进行了由表及里的描写,力图诊断出疼痛的内外层的病状、病源,找到病根所在。
《阿Q正传》中对阿Q的疼痛描写,鲁迅就是从他的“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开始的。因为对阿Q来说,最令他懊恼的是“在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是他的疼痛点,虽然不是通常所说的急性发作的疾病,如外伤直接导致的伤口疼痛,却是伴随他一生都难以消除的疼痛。所以,阿Q最忌讳的是当着他的面说疮疤的事,对与此相关的词语也是十分警惕和排斥的。小说描写道:“他讳说‘癞’以及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人所患的癞疮疤,是一种顽固性皮肤病及其留下的印痕,医学上称为“疥癣(Mange)”。鲁迅在《书信集·致山上正义》中对此诊断说是“癞疮疤,即因疥癣而秃变处的痕迹”(7)鲁迅:《书信集·致山上正义》,《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按照现代医学诊治,此病基本上是可以治愈的,至少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且还可以通过现代医学美容的方式,使之恢复正常状态。然而,在阿Q所处的时代,现代医学尚未在中国普及,尤其是像鲁镇这样闭塞的江南小镇,不可能获得现代医学诊治,更何况对于像阿Q这样处于底层社会的人来说,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这种医治,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也不会相信现代医学的诊治方式。这样,癞疮疤就成为他永远的疼痛。然而,对于阿Q来说,这种疼痛不仅仅来自皮肉伤痕的疼痛,更是来自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心理疼痛、精神疼痛。鲁迅用现代医学思维和诊治方式,一层层地剥开阿Q这种由表及里的疼痛,找到了其疼痛的病源,也找到了他的种种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的总根源。他的忌讳、他的心理变异、他的精神胜利法,都是源自这种总病源、总病根的,换言之,也都是由这种源自内外的压迫而造成的心理病态和精神变异所引发的,其结果使阿Q变成了一个“非人”,尽管活着,但却不知道自已为何活着,已完全失去一个正常人活着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鲁迅说:“我之作此篇(指《阿Q正传》——引者注),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8)鲁迅:《书信集·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并一再强调,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9)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3、84页。,同时,也更“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10)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显然,这种由表及里的医学诊断,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其主旨是为了找到国人魂灵疼痛的病源和病根,以便制定“疗救”的医治方案。
《祝福》对祥林嫂疼痛的认识与诊断,也是沿着现代医学思维与理路来进行的。当年“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还是红的”祥林嫂,至少直观上并不见所谓的创伤,自然也不会有能看得见的疼痛。可是,两年之后,“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最后见到她时,则是“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11)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如果用中医的诊断来说,多半是说她气血不调、阴阳失衡之类的。事实上,这种笼而统之的表述,无法精准地发现和聚焦创伤,找到真正的疼痛点。鲁迅依据现代医学思维和诊治,在对祥林嫂前后三次出现的对比中,则很快地发现了祥林嫂的创伤及其疼痛点,认定是源自心灵的疼痛,是魂灵的疼痛。虽然有关“魂灵”有无问题,“我”也“说不清”,但以医生的眼光来观祥林嫂前后面色和神态的变化,特别是她向“我”询问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事情,就表明了她的疼痛是源自内心的纠葛、恐惧、失望,乃至绝望。这才是她的病根所在。小说中写她四处说自己犯傻,逢人就“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写她想到的是“地狱”,是在“地狱”里“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问题,是如何在“阴司”里,不被“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她,怎样不被“阎罗大王锯开”分给原先的两个男人的问题。实际上,透过这些表象的病情描述,鲁迅的目的就是要告知国人,祥林嫂自己是无解的,因为那些问题始终缠绕着她的魂灵,让她活着看不到希望,死了也无法摆脱纠缠,最终成为一个“木偶人”。这些都说明,祥林嫂的疼痛是挥之不去、无法消除的。除非对她而言,所有内外在的束缚都被解除,让她获得真正的自由,且她自身的观念也能由此获得现代意义的转变与更新,否则,所有的医治都是无效的,是无药可救的。
《孤独者》中对魏连殳的疼痛描写,是直接从他被视作“异样的”和被视为“异类”开始的。对于S城,特别是对于他的故乡——寒石山村的人来说,无论是他的行为举止,还是他的观念,都是被“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所以,当他回到寒石山村为祖母奔丧时,不论他怎样“听从”族人和村里规矩的安排,也不论他全然答应什么“都可以的”,却反而又被“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这种完全不被人接受,不被人理解的沉默、顺从的疼痛,才是魏连殳的真正疼痛,不然,怎会“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是怎样的一种病情?又是怎样的一种疼痛?特别是连他最觉得有希望的孩子们,曾经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天真”、看到了“好根苗”的孩子们,结果也开始“仇视”他了。从这开始,他的疼痛就更加深了一层。不过,造成他更大的疼痛,还有来自一连串的打击,迫使他不得不向现实、向命运低头,让他真正感到了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12)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看起来,他后来似乎找了一份差事,做顾问,当幕僚,实际上是苟活着,并不为人所理解,更不能减轻他的疼痛,而走向死亡,则是他的必然结局。《白光》中陈士成的疼痛,则直接来自心理。当他“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时,他的心就疼痛到了极点。“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从陈士成木讷的表情中,可见他内心疼痛的苦状:“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这回又完了!”屡次的失败,让他在持续不断的疼痛煎熬中走向了绝望。小说并没有在他如何选择死亡及其死亡过程上大做文章,而是用特写的镜头,把他由疼痛而引发的绝望放大和定格下来:“‘身中面白无须’,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且“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13)鲁迅:《白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5页。对于陈士成来说,或许他没有想过死,更不想自杀,也试图努力地挣扎,但这些对他来说都无济于事。无情的现实打击,沉重的精神压力,使他无法消除那种由表及里的疼痛,只有选择死。除了死,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消除这种疼痛呢?在鲁迅看来,这些才是国人疼痛的病根所在。不认识到这一点,即便是疼痛过后,他们也是依然如故,什么也记不得,什么也改变不了,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走向死亡。
尼采曾说:“人们烙进某些东西,让它留在记忆里:只有那些疼痛不止的,才留在记忆里。——这是从大地上最最古老(不幸也是最长久)的心理学中得到的一个基本法则。”(14)[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73页。鲁迅以现代医学思维和理路来描写国人的疼痛,特别是心理和精神的疼痛,由表及里,深入骨髓,深入心灵,旨在让国人永远地记住这种疼痛,使之刻骨铭心,并在疼痛中能够反思自己,反省历史和文化,从中萌发和生长新的希望,如同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自己曾经一度孤寂、绝望而获得体会时所指出的那样:“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1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441页。不像尼采那样追求遗世独立的“超人”,鲁迅始终还是怀有医者之心,希望能够给予国人以最终的拯救,即他反复强调的那样:“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6)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
三、由轻到重:审视与剖析呻吟背后的病理
从医学的认识角度来说,疼痛会带来呻吟,而呻吟声也会因为疼痛的大小而反映出病情的轻重。通过呻吟来审视与剖析其背后的病理,也是现代分析型的医学思维和诊治理路。相对中医注重综合、整体认知和把握病理而言,西医则多是选择对症分析型的认知与把握病理的思维和理路。鲁迅在日本学习的是西医的诊治方式,在《呐喊》《彷徨》创作中,他对呻吟的审视和剖析理路,除了“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就全凭他当年所学的“一点医学上的知识”(1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也即是说,鲁迅依据现代医学对呻吟作了深度的病理剖析和诊治。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18)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0页。无疑,深入细致地剖析呻吟背后的病理,是发现病源、诊治病根的现代医学之道。
《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的呻吟,显得有些特别,即不是写那种由皮肉疼痛而直接引发的呻吟,而写的是一种隐藏性的呻吟。在小说中,孔乙己即便常常是“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且不时地“添上新伤疤”,尤其是在偷举人家被“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写了“服辩”后,也没见他直接呻吟,只是恳求掌柜“不要取笑”“不要再提”,自己说是“跌断。跌,跌……”,以维持他那点最后的尊严。可见,就皮肉疼痛而言,他的呻吟是轻的,甚至是听不见、看不着的,表明他对皮肉的疼痛可以忍,可以不发出呻吟声,但是在被人嘲弄、被视为“偷窃”后,他就忍不住了,而是以争辩的方式来表示他的呻吟,虽然这有些古怪,与众不同,毕竟是“涨红了脸”“睁大了眼”“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嘴里发出一些让人听了“全是之乎者也之类”和“一些不懂”的话。显然,这是他的重呻吟声,是其内心的呻吟。孔乙己力图以这种呻吟方式来抵抗众人的嘲笑、嘲弄,为自己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然而,透过这沉重的呻吟声,人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他的穷愁潦倒,也不是由他自身的懒惰造成贫穷而导致生存的危机,而是他极力维护那个所谓“读书人”的体面,这就让人看清了他的迂腐,看清了他呻吟背后的病理。小说丝丝入扣地剖析了其病理的内在缘由:愚昧、无知与落后。同样,《药》在华老栓选择以“人血馒头”的方式为儿子治病的故事叙述中,透过华小栓“窸窸窣窣的响”和“一通咳嗽”的呻吟,鲁迅也是由轻到重地剖析出其真正的病理缘由。小栓的呻吟是轻的,华大妈(包括华老栓)“哭了一通”的呻吟则是重的。在这轻重转换之间,透露出来的便是那无尽的愚昧、无知与落后。《明天》也是在宝儿“喘不过气来”的呻吟中,由轻到重,层层深入,最终找到了其真正的病理机制。同样,宝儿的呻吟是轻的,而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的呻吟则是重的。在给儿子治痨病上,单四嫂子几乎什么法子都使过,求过神签,许过愿,吃过单方,但都不见效,只好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去找郎中何小仙为宝儿医治“痨病”。然而,这真的能够治好么?当然不能。因为其发病的病理恰恰就是她自身的愚昧、无知,以及落后的认知观念,再加上她所处的周边环境,即偏僻、闭塞的鲁镇及其看似古朴、其实是落后的风俗。对于这种状况,单四嫂子,其中也包括她周围的所有人,自身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也不会承认是神签、菩萨、单方、郎中何小仙等,治死了患痨病的宝儿,尤其是不会承认她自己实际上也是杀死宝儿的元凶和帮手。
对于被称为“狂人”“疯子”“孤独者”的呻吟,人们常常会认为是不正常的,无论他们的呻吟是轻还是重。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十分注重在这些看似不正常人的呻吟中,由轻到重地发掘出其“病理”的特殊性,以展示他们内在的清醒。《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被周围人都视作不正常的人,也即是“疯子”。他的呻吟特别处在于,当大人躲他,投以异样的眼光,都把他看作是疯子时,他不感到害怕而呻吟,而当小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时,“我”(狂人)则发出了呻吟:“这真叫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自然,这种呻吟也不来自皮肉之疼痛,而直接源自内心,是沉重的,而非轻声的。还有像大家都用“一模一样”的眼光看他时,他则有了一阵寒颤式的呻吟:“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这种源自内心的呻吟,促使他对“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道理体会得更深。可见,在狂人呻吟的背后,尤其是被看作“疯”的背后,其“病理”的真相,实际上是比任何人都清醒的那种内在的自觉,因此,狂人重呻吟的内核是对“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吃人”本质的揭露,是对有着“四千年文明”历史的深刻反省,也是他发出“救救孩子”的历史使命的一种责任担当。《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长嚎”般的呻吟,可谓是震撼心灵的,不然,“我”又如何会像他那样,“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魏连殳在压抑了许久之后的呻吟,一开始就是重声的,后来他死了,也是在看似“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但依然是“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这种死态的“呻吟”,可谓是表明了他心底里的彻底绝望,比活着时的重呻吟声还要可怕,还要沉重。对于他来说,不论是如何的转换,又是如何的挣扎、颓唐,都摆脱不了不被认同和理解的孤独、寂寞的命运缠绕,挥之不去,无可奈何,最后只能是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可见,从狂人、孤独者一类被视作异类人的呻吟中,不难发现,其病理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纯粹的生理意义,而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的内涵,那就是亘古不变的“超稳定”的社会重负和文化陋习,是千百年来习惯成自然的传统重压。
鲁迅当年与好友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时,曾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后来又发问道:“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19)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页。寻找国人种种病症,特别是蛰伏在心理、性格、精神背后的根源,反思历史和传统给予国人的精神负重,是鲁迅在《呐喊》《彷徨》创作的主题思路,也是他自觉地运用现代医学思维和诊治方式,进行精准、细致的诊断结果。虽然他对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有所失望,但他始终是怀有医者之心,依凭现代医学方式进行透视和诊治,从中写出国人病态背后的愚昧、无知、落后,触及内源、内核,入木三分,让人震撼,刻骨铭心。可以说,采用由外而内,寻找与聚焦创伤背后的病源,由表及里,触及与诊断疼痛背后的病根,以及由轻到重,审视与剖析呻吟背后的病理的方式,进行《呐喊》《彷徨》的创作,这些都表明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反思、反省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并为现代中国小说创作指引了价值方向,提供了写作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