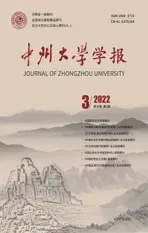成“物”与去“物”:受众本体存在的价值之问
2022-07-14陈文泰孙仲伯
陈文泰,孙仲伯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黑格尔经由对哲学自身的反思与阐释后如是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如今我们追溯对于受众的主体性研究仍犹如追寻“密涅瓦的猫头鹰”轨迹一般,厘清受众存在的价值发展脉络的同时并对其开展批判反思。援引“物化”概念去批判受众主体性缺失的同时也可以发现某些对“物”的先验界定在根植于“新受众”的思维范式里。如若将“物化”这一概念的主体性作用归之于受众本身来看,受众或许并非将“物化”看作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过程,而是不得已或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物化”这一转变,这与“物化”的体验密切相关。“物化”的生成无疑是对受众本体僵化的一种阐释,抛弃了传受间有机互动的交往可能,从而将传播学的受众研究分析推向了一个“死胡同”。因此,去“物”的迫切性就不仅在于重拾交往,更在于回归“此在”的存在价值。
一、受众的“物化”与“去物化”之辩
传播学中谈到受众的“物化”问题离不开对传者的目的性行为的探讨,受者相对于传者而为受者,这种相对概念的诠释或许我们可以从传者之于受者的建构出发,“物化”由此可以看作为一种建构的过程。所谓“物化”(Verdinglichung),平子友长认为是指“社会关系的位相本身消失,转移成物——属性(Eigenschaft)的内在关系的位相。某个对象=客体,当它所承载的各种关系规定都被想象成其对象的对象属性时,就被规定为物(Ding)”[2],物化的界定主体并非物本身,而是主体间所表现出的关系情况。
(一)受众“物化”:商业媒介运营的症候
由于商品经济下受众发生了物化转向,因此需经历一个“由受众到物再到传者”的关系传导(如图1),这成了商品受众论的经典诠释模型。

图1 受众“物化”(商品化)的关系指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之“商品”的物化隐喻为何?胡翼青认为“商业化媒体通过出售受众的注意力和闲暇时间以实现‘资本复制’”[3],这就将“商品”问题圈定到了“注意力”和“闲暇时间”上来,换言之,是将受众本体能动的表征加以商品化。但与此同时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颇深的斯迈思也指出,“所谓商品化的对象在于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相对劳动力的‘受众力’(audience power)”[4],这种“受众力”是研讨受众物化的重心。从受众到商品的转变即是“物化”的转变,这是商品化生产资料关系在传媒领域的体现,“物化”后的受众则是具有了某些量化症候,服务于传者的经营计算。值得一提的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更是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泛化理解,并未对时空适应性进行考量,而为“物化”问题探讨提供了扭曲的理论依据。这也要规避于对斯迈思理论本体的批判,应当重回对其行动理论的反思。卢卡奇指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5]。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确定了生产关系属性的同时规定了人的自身存在位置点,受众的“物化”即为生产位置的一种调试,这是基于既有的生产活动发生的对自身主体问题的变动。马克思直言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 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6]。物化批判指涉蕴含了生产关系的更迭。
其次追问受众的主体性就此完全丧失了吗?这要追回到受众本体价值去进行讨论。受众在传播网络上存在着自有的,或是说海德格尔提到的“此在”的性质,将受众研究归之于社会网络中去,时空下赋予的节点具有某些通约特质,这是我们探讨本体价值的关键所在。在此而言,受众商品论只是强调了受众作为“商品”(或者将其“物化”)的这一层面,由此自然会得到一个悲观的基调。整个传媒的庞大体系无法在商品化轨道下运行,或者说无法量化或直观显示出受众的“物化”情况,这是社会网络的复杂性所不允许的,就此来看,上述的“受者——商品(物化)——传者”传导路径仍是一个片面的、抽象的解释。
(二)连锁公众:自在“去物化”的逻辑
“去物化”是对受众本体价值的认同,也更加强调了对“物化”机械特质的反叛。比尔·科瓦奇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提到了“联锁公众理论”这一概念,他在阐述戴夫·伯金的多样性版面理论同时指出,“每个人都对某些事物感兴趣,甚至是这方面的专家。那种认为人民一无所知,或者另一些人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的观念只是神话”[7]。公众在不同事件中进行差异化分类是在“物化”关系中蕴藏了某些“去物化”的特质。“分类”显然是与“物化”紧密贴合的,但“分类”思想的另一重讨论是:受众是否可以被完全细分清楚?科瓦奇举例道,“底特律郊区的汽车厂工人不关心农业政策或外交事件,可能只是偶尔买张报纸或看看电视新闻。但是他会经常参加工人集体与资方的谈判,非常了解公司的官僚系统和工厂的安全情况”[7]。受众的细化分类是对自身关系属性的梳理,场域位置差异决定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看似精细的量化处理其实也并未解决本体(自身思维、自我精神等)层面的问题,“去物化”所要强调的便是对“人”本身的探讨。
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完善,其自带黑箱成了物化受众的盲点,而所谓“利基受众”则是基于一种资本划分的逻辑产物。从二八定理到长尾理论,分众化进程的逐步扩大或许使得科瓦奇看到了利基市场的弊端——对于特制节目的排他性,他宣告利基市场破产的隐喻就在于要对利基受众的数量和规模加以重视。算法的精准化就在于将公众的混合型身份验证工作由传统编辑人员让渡给了数据分析,实现了对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但由此也注意到,这种需求满足也同时是一种“圈定”,或者说是在设计者圈定的范畴下实现的满足。毋庸置疑,利基的前提是受众的个性选择,而应用于这种个性选择圈定更大的商品范畴则是商家的深度逻辑,这种需求认同或可以被认为是存在着虚假成分的。技术的理性逻辑无法和受众自在思维逻辑完全吻合,而偏差之处则是“去物化”可能发生的场域。所以,连锁公众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较为粗制的划分,但划分后的内容使用或满足心理是技术无法掌控的,所谓的“操控”也可视之为一种虚假认同,技术终究是海德格尔常谈的“座驾”。
仍需提到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物化”不等于“化物”。人们极容易混淆这样一组概念,在理解“物化”的同时夹杂了“化物”的观点。就如同强调“中国化”和“化中国”一般,贴近不等于成为,受众有了“物”的某些关系特征并不等于说受众成了“物”。“物化”之后令人反思的是“物化”所建构起的一套运作逻辑,之所以提到的是“运作”一词,这仍要将“物化”归置于操作者(或传播者)层面进行把量,“物化”且非受众自身的“物化”,而是上级操纵者通过媒介工具所建构起的一套关系法则,“物化”是形成法则的一种显性表征。
二、成“物”之思:“物”的先验
受众成“物”的原因本文归结于两种:一种是传者为其位置的调配确定,使之为“物”;另一种则是受众的“先验”体认,使之对规则进行认同。康德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一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尤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先验的(traszendental)[9]。借用康德的“先验”观念,受众成“物”即可当作为“先验”的,这里我们提到的并非是自然意义上“先天的知识”或者现象学意义上对存在经验设定的排除,而是强调受众在介入传媒场域之前已经确立了一种成“物”的身份并自身认同成“物”的可能。
(一)量化信息的先验假设
量化信息本身即为对受众“物化”价值的一种体现。卢卡奇批判道,“对于劳动过程的数字分析意味着放弃肉体器官的、不合理的、根据性质而决定的生产单位。只有通过把每一个复合体精确地分割成其组成成分,通过研究决定生产的特殊规律,才能获得作为能够以更大的精确性来预算所达到的全部结果意义上的合理性”[10]。本体价值的切割与分类无疑是就表征而言的,受众的量化信息并非针对具身的、灵韵的层面,这在“先验”中便是一个“残缺的设定”。
在新闻传播路径下,信息的“先验”首先在于对共同体范式的反馈,是一种基于时间与集体性的产物。对混合型公众的反思让科瓦奇意识到在某一具体场域下新闻自身应反映多数人生活和体验,这要将新闻的公共性进行前置,就此而言,量化的标准则在于对共同体利益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共同体”:一方面是媒介拟定的公众共同体;另一方面则是公众“想象的共同体”。前者是从媒介的角度出发,受经营生产因素、审查因素、法治因素等方面影响,进而可以将其看作是媒介主观意图和社会意识形态杂糅控制的产物;后者则是基于公众视角出发,借用安德森对民族属性讨论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一词来理解其共同体内核在于一种心理上的凝聚,这是沾染了迪尔凯姆主义色彩的成果。先验的情况也因此成了对拟定假设和“想象的共同体”问题的讨论,但毫无疑问,媒介拟定是对受众本体的剥离,通约性认同又会最大化地模糊掉受众的自我特质。媒体为“共同体”服务,也可以说是基于对后者公众“想象的共同体”服务,促进公众间相互理解,允许他们做出妥协,进而达到治理复杂连锁公众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妥协与理解也可归之于“先验”,模糊化与不确定性成了受众信息接触脱敏的前置因素。
媒介,作为联通人与人交流的工具,其程序“先验”则是对受众认知框架的规制。顺延上一节所提到的算法推荐机制,这种“先验”即是脱离了人的“先验”,当然在康德那里算不得“先验”,但也要看到媒介工具的规则设定之于传者和受者间本身就包含着“先验”,即进入规则前的“先验”。算法作为媒介控制的一种新型手段,本就成了联结受众生活的工具,例如当你重复点击同类型的内容之后算法会基于此进行相关推荐,而你了解了这一套推荐机制后则会应用这一套法则将APP贴上个人标签,让其进行不断学习和熟化,进而使其生活化,这也是受众接受量化信息并进行量化自我的一种体现。如若将算法置于传者的工具一层,那么“传——受”间的“先验”仍是包括了某种主体性思维。
(二)赛博格受众的内生悖论
基于后人类主义下传媒内在转型的展望,人机互动会消解“传——受”边界进而要关注“人——机”间新边界。人机边界的泛化是可怕的,技术理性的晕轮会遮蔽掉人伦的种种问题,这需要让研究者重拾对“人”的本体价值思考。
赛博格受众,作为一种新型的受众身份,随赛博格人所处社会关系下而转换得来。在承认“物”的先验观念下,赛博格受众的身份归属问题亟须阐明:是属于“物”的人?还是仍旧属于“人”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物”?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这里不能将“物”与“人”进行机械相加融合,以至于合成一种“机器+人”的人。由此可以设想,将自有的牙齿换成烤瓷的,这并不算作是机器人,将自有的四肢换成假肢,这也不算作是机器人,将五脏六腑换成机器装置,这还不算作是机器人,那如果将大脑、头颅换成机器的,这是否算作为机器人?肉身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机器变更会成为机器人?这种问题是无法用单一的量变知识来解决的,并且很难寻求一个“度”去进行判断,因此主体性问题反思成了后人类主义探讨的重要命题。乔纳森·克拉里认为赛博格的主体性是介于理性交流系统与信息网络之间的一道岌岌可危的界面[11],那么人的主体性思维与技术互嵌生成了影响整个社会的新型法则。可以说数据是人们交往行动的依据,交往行动又成了数据的来源,赛博格受众则是在交融了二者后于内部不断进行有机协调进而实现自身的产物。
技术具身在试图澄清这样一种“透明性”,即技术就好像融入我自身的“知觉——身体”经验中[12]。进而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技术之于人体脱离(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结果将反哺于人类交往或控制人类交往。赛博格受众面临的即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技术设计者控制背后夹杂了技术自身所带的逻辑法则,这是技术内生层面所要思考的。其内生悖论就是这样一重探讨——基于物的“先验”又反叛于量化更迭从而判断本我身份,机器的侵占注定会造成主体的迷思。顺延在探讨有机体与技术的交换,技术对于本体的完全更迭并不影响他者对其的情感赋予,或者说形貌、声音的复制会唤起某种记忆追寻。在2022年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中,邓丽君与周深的跨时空同台演唱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情,技术的复制演化成为一种媒介记忆,这又将使大众落入情感迷思。脱离肉身的技术呈现是在人格化赋能下完成的,赛博格受众同其他赛博格人一道所要考量的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嵌入身体”这一问题,进而面对有机物同无机物的交融来反思其间产生的内生悖论,寻求智能主体下的交往新路径。
三、去“物”之论:“人”的回归
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13],故而对“自我”的自觉确认,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者”[14]的把握。去“物”之论是对“物化”现象的批判,探讨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受众的成“物”必然是在传者逻辑影响下形成的,那么去“物”的关键就是在于回归探讨受众的本身。技术更迭无疑是隐蔽掉本体问题进而让受众达到“去本体化”,那么对受众本体的讨论就要复归到“人”的此在中去,这既是对传受复杂关系进行剥茧抽丝,又要将其重置于特殊场域中进行反思。
(一)思维与具身的不可复制性
我们往往将受众的反叛归置于“能动性”方面进行讨论,但这也造成了对分析主体特质的缺失。彼得斯认为人之为人的依据在于其不可复制性,能动性的强和弱以及是否使用能动性的问题也并不能在提出“能动性”一词后表述清楚,故而可以从“思维与具身的不可复制性”入手观察。自我确认与时空关系下的个体彰显是表达思维与具身不可复制性的核心要义。正如梅洛·庞蒂谈到“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15],就传受关系来看,受众思维依托于其关系属性而得以形成,受众内部成员思维差异又与在地位置紧密相连,受众间的个体差异决定了受众使用与满足的接受程度。
对身体的感知是人之所以脱离物的重要差别所在,具身传播回归于传统的身心交往,去媒介化的同时也构筑了再媒介化的新景观,身体媒介是区别于其他媒介物质性探讨的特例单元。由于技术介入,身体又可分为“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二者的重合与分割成了再思身体边界的标准。身体边界的确认直接关联到本体范畴,“表现的身体”是一切复制的原点,但复制又意味着对“灵韵”的剥夺,这是复制品之所以为复制品的体现。
受众的具身感知是与思维、精神紧密联结的,是从本体处寻求的一种共鸣。值得一提的是,共鸣不等于复制,不可复制是强调了对“物化”的反叛,共鸣则是仅在通约处位置存在的心灵交汇。近年来,广告界推崇的ESP理论(Emotion Selling Proposition)便是对受众本体的复归研究,以用户情感的凸显来区别于单纯产品暴露的本位思想。但用户本位并不代表着能够消除用户思维与具身感知的不确定性,用户间差异性及不可复制性仍是广告商难以逾越的鸿沟。
(二)重拾“此在”的关系性
“此在”是概括受众去“物”返归主体性的直接代名词,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16]。受众的“去存在”意义标注了自身追问与领悟的价值。正如费尔巴哈强调“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17],受众之所以为受众,无非是传受关系下的指称,但受众本体又不能局限于在传受关系规则下探讨,或者说受众是社会关系诸要素下的受众。受众的“此在”表征是由时空规则所建构的,从时间性来看,受众的接受行为并非是当下的一时之快,而是在于经验的累积。黑格尔曾谈到“这种持续存在的每一瞬刻都取决于一切过去的瞬刻,并将规定一切未来的瞬刻”[18],在历时性下探讨受众行为是在本真中寻求存在价值的途径。从空间性来看,受众的存在价值与其空间网络关系密切关联,意向主体与对象的相互接近的起因乃是此在生存的为何[19],受众的此在生存通过与传者对话实现统一,这在空间网络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为地理空间中的传播交往互动;另一方面为“共在”状态下想象的共同体。在俄乌战争话题下开启的云直播便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空间:场景自在建构的同时暗喻着传者的退场,受者以云平台为依托关注场景的细微变化,进而互动讨论形成一种新型公共领域。受者在“此在”关系网络与互动交往中逐步领悟自身存在,这一去“物”的渐进式转向是由本体价值追问演化而来的。
批判上述的先验论调是找回受众本体的基石。普里默兹克如是说“一个人总是身体——主体的存在,而永远不能是天上的自由缥缈的先验的自我”[20],厘清此在的生成逻辑需要对先验进行去蔽,这并不是将媒介技术作为去蔽的唯一手段,而是对存在的不断追问。
四、总结与反思
自在的人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异化的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自由的人[20]则以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和自由个性为基础,这是马克思著名的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论。探讨受众“物化”与“去物化”现象要依托于他所依赖的对象,但依赖不等于寄生,要考虑其去依附后的生存情况。历来学界对于受众主体性问题争论不休,从“靶子论”下的被动到有限效果论下的能动,再到强效果后的伪能动,这种争论可以复归到探讨本身的环境中去理解。是受众的主体性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还是探讨环境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笔者认为,从受者本体角度出发来看,受众自在价值是恒定的,但会随着传者策略与媒介更迭表现为一种离散与递归。受众价值的追问要对其物化进行去蔽,批判“物化”的同时也不可将受众完全等同于物来言说。所以,受众“物化”即为一种关系的确定,这种关系又同时被“此在”的“去存在”所解构,最重要的是要把受众本体价值纳入受众分析的研究视阈之中,进而观察受众的成“物”与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