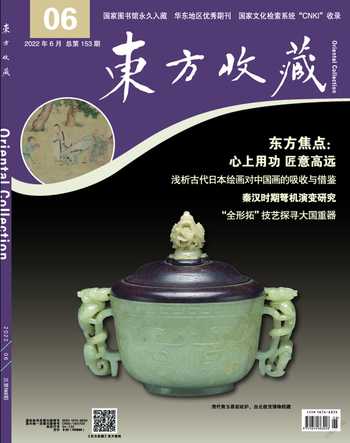浅析古代日本绘画对中国画的吸收与借鉴
2022-07-08于曦湲
摘要:中国与日本虽为不同的国度,但却因同属一个文化圈而很早就开始文化艺术的交流,绘画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古代日本绘画的诞生缘于中国移民带来的绘画艺术,其发展也深受中国画的影响,对中国画尤其是唐代的人物画和南宋的水墨画多有吸收和借鉴。正是在这吸收和借鉴的过程中,古代日本绘画实现了创新,逐渐产生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格。
关键词:日本绘画;中国画;人物画;水墨画
“同属东亚文化圈”[1]的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文化交流[2],而绘画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目前学界已经从多个角度对中日两国的绘画交流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部分课题上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从中国画对日本绘画诞生的影响、中国人物画和水墨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日本绘画对中国画的吸收与借鉴,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画对日本绘画诞生及发展的影响
专研日本绘画艺术的英国东方文化学者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曾指出:“日本的艺术史是这样的一部艺术史,它从中国取得了最初的灵感,逐步发展自己的性格,并且接受了新的题材。”[3]劳伦斯·比尼恩的这一观点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日本艺术之所以能够“逐步发展自己的性格”,是以从中国艺术中获得的灵感为前提,这就形象地揭示中国艺术对日本艺术诞生的影响;其次,日本艺术又有自己独特的“新的题材”,不完全同于中国艺术。
显然,日本逐步消化吸收了来自中国的艺术,并最终完成创新,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艺术,而这种创新只是“在华夏文明之上的衍生和发展”,根子上“始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精髓”[4],古代日本绘画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公元3至6世纪间,移民日本的中国人将中国绘画艺术带入日本,为日本绘画“撒下了第一批中国传统绘画的种子”[5]。可以说,正是在中国画的哺育之下,古代日本绘画才最终得以诞生,并从诞生之初就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绘画不断发展,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中国画对日本绘画两次大规模的影响:
第一次发生在唐朝,当时日本向中国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这种使团的随行人员中就有大量的画师和画工。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来中国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日本留学生,最有名的当属唐高宗时的日本僧人空海,他在回日本时带去了唐朝著名画家李真的名作《真言五祖像》,对日本绘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有大量的僧侣、文人等前往日本,最著名的当属天宝年间的鉴真东渡,鉴真大师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在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文化交流中,平安时代的日本袭仿唐代绘画而形成了著名的“唐绘”。
第二次发生在南宋时期,日本正处于镰仓时代。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武士阶层控制政权,甚至一度取代皇权政治。政治上的这种变化逐渐波及到艺术领域,变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此时在中国蔚成风气的饱含禅宗意味的水墨画,恰好迎合了包括禅宗僧侣在内的日本社会上层的审美趣味,于是,日本大量引入、移植牧溪、梁楷等南宋画家的作品并着意创新,形成了被称为“汉画”的日本水墨画[6]。
二、日本人物画对中国画的袭仿
唐朝绘画传入日本后所形成的“唐绘”,主要是以各色人物画为主[7],这些人物画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是对中国唐代画风进行吸收和借鉴的结果。关于这一点,1972年在奈良发掘的飞鸟时代后期贵族高松冢墓葬壁画,就是最好的例证。
高松冢墓的年代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相当于中国的盛唐时代,与初唐的永泰公主墓极为相似。将高松冢墓壁画(图1)与永泰公主墓壁画(图2)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高松冢墓西壁上画的四名侍女像基本是“八头等身比例”[8],与真人大小相同,且侍女们面部神情各不相同,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优雅,能看出明确的远近透视关系。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构图技法,高松冢墓壁画都与永泰公主墓壁画极其相似,显然是模仿了永泰公主墓。
另外,从侍女所持花伞的纹样中同样可以看到属于初唐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壁画(图3)的影子。将二者加以对比可以发现,高松冢墓壁画风格偏柔和婉丽,迥异于唐代壁画雄强茂密的风格,日本画风之源头当在于此。
高松冢墓所处时代之后的日本人物画作品,也有很多借鉴、吸收唐代绘画的痕迹。7世纪后期的奈良法隆寺金座壁画中,第六号壁画《阿弥陀净土变》的线条描法类似于中国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的“铁线描”[9]。壁画首先在15厘米厚的壁面上由白石灰粉刷三次,然后再用与敦煌发现的相同的“纸彩”贴在壁面,纸形背后涂上黑、红两种灰粉,将轮廓拓描在壁面上,按照描好的轮廓用尖笔描画成凹线,再按凹线描画,之后朱线上再覆以黑线。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赞张僧繇的线描画法是“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10],法隆寺金座壁画即是采用这种富有弹性的、有立体感的“铁线描”技法。
同高松冢墓壁画柔和婉丽的风格一脉相承,日本的这种“铁线描”技法同样十分柔和优雅,其后续发展为以“唐绘”为源头但又有较为明显差异的“大和绘”,这是一种无论题材、方式还是技法制作,都更富有日本特色的本土画种,“大和绘”的代表作品当属完成于11世纪的《源氏物语绘卷》(图4)。如果说前述高松冢墓壁画和法隆寺金座壁画还保留有中国古典题材的痕迹,那么《源氏物语绘卷》则明显区别于中国的唐画,是一幅具有浓郁日本风格的故事长卷,表现的完全是日本的风土人情。该画作构图视角独特,画面中园林风景、建筑和人物的排列采用的是“脱顶鸟瞰式”构图[11],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斜视角构图,能够充分表现主体空间感。值得注意的是,《源氏物語绘卷》中的建筑物均不画屋顶,就像是呈现于观者眼前的大舞台,又好像屋顶是被刻意掀掉的,室内贵族的私密生活一下子就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者的窥视心理与观看需求。
《源氏物语绘卷》既不见汉画的雄浑,也没有唐画的雍容,更缺乏宋画的崇高,展现出的是细腻华美的绘画形式,这是一种与日本风土环境相适应的“日本美”,成为江户时期表现世俗生活的浮世绘版画的先声。
三、日本水墨画的中国元素与民族趣味
如前所述,日本水墨画的源头是南宋的水墨画,因由禅林画僧移植而来,故又称为“禅画”。到室町时代(相当于中国明代),随着五山禅林的高僧倡导禅文学[12],日本水墨画趋于兴盛,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水与墨于纸上挥洒交融而形成的幻化图像,极好地契合了禅所要表达的境界,所以汉字书法在日本兴盛之后,水墨画又得以在日本生根开花”[13]。
当然,在中日水墨画的交流中,日本并没有全盘接受从中国传来的水墨技术,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充分表现出其民族特色。具体而言,北宋那种雄伟大气的水墨山水在当时并未引起日本画家的共鸣,反倒是南宋画僧牧溪那种有明确轮廓、多染少皴、带有禅意和朦胧的“没骨画法”[14],深受日本人追捧,被日本尊为“画圣”。
另外,被誉为“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圭的作品同样深受日本民众欢迎,尤其是师法李唐、并称“马夏”的马远和夏圭,二人均擅长“大斧劈皴”[15],这是一种与画家活动区域的实景山水关联极其密切的皴法。相对于多高山大川的北方,马、夏二人所在的临安城更多的是细碎的山石与杂草,多雨湿润的氛围成就了马、夏二人的风格特点,他们用书法意味很强的浓重墨线勾勒出山石,用“大斧劈皴”塑造结构,将画面收于一角或半边,表现出临安山水一片、烟雨迷蒙的景色。室町时代后期的狩野元信在师法马、夏二人作品的基础上,开创了日本水墨画中最具代表性的“狩野派”[16] 。
日本民众对于马、夏二人作品的喜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产生了共情。日本京都地区的地理环境、山水地貌与临安颇为相似,日本民众在欣赏马、夏二人的画作时,可以体会到“身临其境”之感,而不仅仅是欣赏“中国”的山水;同时,马、夏二人构图精简、笔墨直白的画风特点,有助于日本民众上手学习水墨画,其风俗性、社会性的画面易于在日本民众中产生共鸣。
不过,此时的日本画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中国画的简单袭仿和移植,而是着意创新,当然,他们也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正如开创水墨画现代化的著名画家横山操所言“日本水墨画始于雪舟(世界著名的日本“宋元派”水墨画家雪舟等杨——引者注)”[17],正是在雪舟等杨的努力之下,日本水墨画实现了“脱中国化”。“雪舟等杨这一画名的登场,标志了日本画家从亚洲画家群中独立出来的开端,自雪舟开始,日本开始脱离亚洲”[18],民族风格日益凸显。
日本水墨画的民族风格在雪舟等杨的《四季山水图》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特别是其中《夏景图》的设计。在《夏景图》中,除了矗立在中央的岩石与远景中隐隐约约的山峰呈直立状外,其他景物均呈微微歪斜之势。值得注意的是,右上方的大斜面弧度绝非一般,而衔接这一斜面的并非中央稍偏左的那一条细细的瀑布,而是中央下方五棵树的枝叶,用瀑布是中国的山水画法。雪舟等杨没用瀑布的一个有力佐证,就是坐在画面右方的男子姿势,瀑布虽在男子眼前,但他并不是在观赏瀑布。
应该说,雪舟等杨的画作在早先的中国是没有的,其有意识地导入了一种“动态的观点”,使得画面突破了二维纸面的限制。这种动态效果在他的《仿夏圭山水图》(图5)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个“仿”字似乎明白地告诉世人,该作品是对夏圭《山水图》的“模仿”。但就画作体现的内容来看,雪舟等杨并未完全模仿夏圭,而只是采用了夏圭画作中展示“动态”山水的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是中国画的一个显著特征——山水画中岩石、高山均透露出灵动的生机感。
在雪舟等杨的作品中,与《仿夏圭山水图》风格类似的还有《山水长卷》(图6)与《天桥立图》等,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雪舟等杨“取之中国而又跳出中国”的艺术风格和高深造诣。
考察雪舟等杨的经历就会发现,他这种艺术风格的确立发生在明成化三年至五年(1467—1469)的中国之行后。此次中国之行,雪舟等杨受到了明宪宗的热情款待,访问了明朝的宫廷画院,并向宗法夏圭、马远的宫廷画家李在和张友声等学习了“浙派”山水技法[19]。通过这次访问,雪舟等杨熟练地掌握了“传移模写”的画法,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山水画中有哪些因素可以借用,哪些因素又可以舍弃,之后将彼地的景色与此地的景色进行对比后再进行替换。雪舟等杨将这种绘画的“编辑”工作引入了山水画领域,从事实和形式中自由地导出形象,即制造出变化,改变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取并创造出新的意义。
日本是一个非常擅长这种“编辑”工作的民族,无论是最澄、道昭和空海等佛教界高僧,还是有“歌圣”“歌仙”美誉的柿本人麻吕、大伴加持、藤原定家和纪贯之等文艺界明星,均是深谙此道的高手。这种“引用与独创”的妙法是日本文化史蕴藏的独特方法,其与日本水墨画融汇在一起,使得画面展示出了日本的民族趣味。
四、总结
对于日本绘画与中国画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美术理论家、中国画研究专家伊势专一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恰好比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上更增一种地方色彩,这就成为日本美术。”[20]显然,古代日本绘画在中国画的影响之下诞生,然后对中国画进行持续的吸收和借鉴,通过“袭仿——移植——创新”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了“民族化”和“本土化”。
古代日本绘画的发展历程表明,一种新文化要产生与发展,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存另一种文化的简单模仿,而是要因地制宜,将具有本文化特色的关键元素融入其中。作为当下文化创造者的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果只是在画布上一味地模仿现有的艺术,那就永远都无法摆脱其束缚,要想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现有艺术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将具有时代色彩的内容融入其中。
参考文献:
[1]陈维东.中国漫画史[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89.
[2]王婷,韩雪.日本社会文化探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18.
[3](英)劳伦斯·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95-96.
[4]方志平.中国南宗绘画对日本绘画的影响——从董其昌到富冈铁斋[D].中国美术学院,2014:7.
[5][6]王莲.宋元时期中日绘画的传播与交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03):168-170.
[7]徐静波.解读日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83.
[8][13]赵文江.中国山水画与日本风景画构图研究[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1:50.
[9]余辉.秀骨清像——魏晋南北朝人物画[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77.
[10][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80.
[11]刘小羊.中国平面设计史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74.
[12]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515.
[14]杭州市文史委员会.杭州佛教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130.
[15]李乡状.山水画技法与欣赏[M].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6:60.
[16]仇贤峰.宁波丝路日本书画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18.
[17][18](日)松冈正刚著,韩立冬译.山水思想——“负”的想象力[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45.
[19]林士民,沈建國.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269.
[20]婴行.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J].东方杂志,1930,27(1).
作者简介:
于曦湲,女,2019级本科生,专业: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