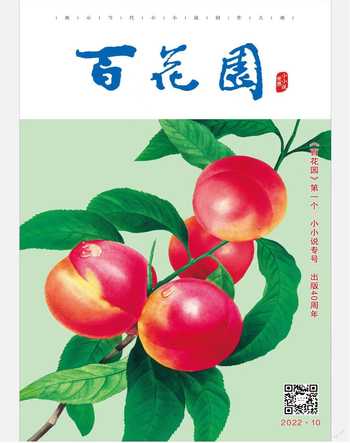薪火相传
2022-07-05李淑琴
李淑琴

在我们晋南,过继叫给人顶门,顶了门就跟原生家庭没有多大关系了。村里人都知道我从小过继给了二叔。
我家老院一共六间房。东为上。爷爷和奶奶住在最东边。我爹娘住在中间,西边的两间屋是二叔的。大概是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我爹让我搬进西屋自己住。西屋前面一棵瓦罐粗的桐树,掩得屋里头黑黢黢的。那时候流传着很多闹鬼的故事,我不敢一人住,晚上我爹趿拉一双泥鞋过来跟我住。只要我跑到娘屋里,就被他捉回去。爹的脸如死面团,他说我是给我二叔顶门的,西屋才是我的家。
自从给二叔顶了门,我跟弟弟的待遇大不一样。弟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上樹上房,下河下窖,统统来去自由;作业不写完就跟同学去田里套知了,我爹也就骂上几句“倒灶鬼”了事。我不一样啊,只要出门,我爹就追着问我去哪里、跟谁;作业写不完肯定不能出去,他杵在门口盯着,特务一样监视着。
有一回,铁钟喊我去河边看西瓜。铁钟的爹去镇上做手术了——腋下长了个瘤子。我满口答应铁钟陪一夜,田里的西瓜随便吃。我做梦都想去。脚丫子伸到河里,头上吹着夜风,手里捧着半个瓜,吃完瓜皮往脑壳儿一扣,星星不睡我不睡。可猫着腰路过我爹的窗户时就被捉住了,他大喝一声,开枪一样,吓得我全招了。我爹说:“河边蚊子下雪似的,河水涨潮淹不死你,河滩里的狼一口吃一个狗崽。”结果就是我被看得死死的,寸步难逃。直到我考上县城中学,铁钟都不搭理我,背地里骂我说话放屁一样。
大专毕业后我留在县二中教学,偶尔回老家,还是住在西房里。那年,我和弟弟都有了女儿。我爹抱着弟弟的女儿那叫一个亲,老胡子在小脸上死蹭,搞得弟媳妇夺过去死活不给他抱了。我媳妇是山里人,姐妹五个,她妈想生个男孩儿,到底没生出,给她起名“胜男”。轮到我这里,我爹丝毫不顾及胜男的感受,站得老远,一句一个“还得再生个男娃”,好像胜男生女儿对不起他似的。我媳妇蒙着被子狠狠地哭了一场,骂我爹封建。
第二年,女儿才一周岁,我爹就来了。他坐在沙发上闷着头,从怀里摸索出一包东西,往胜男手里塞。
胜男吓坏了:“这是啥呀?”
“一万块钱。你看,囡囡也一周岁了,你们再生个男娃吧。”我爹面团一样的脸泛红了,没见过他软口气说话。
“我有病啊?一个都管不过来。你咋不叫弟弟家再生一个?”我说。
“你再生一个男娃。”我爹低着头,倔倔的。
“现在都生一胎,男娃女娃都一样。”
“不一样。”
“生二胎你管啊?”
“我管。河滩里种花生卖的钱都给你。”
每年冬天,我爹怀揣卖花生的钱,骑着自行车,进门就把钱塞给胜男,好声好气地再三嘱咐:“再生一个,再生一个。”胜男回老家,我爹跟迎接皇后差不多,我娘让胜男帮着上屋顶翻晒枣子,被我爹骂了一通。儿子出生那天,我爹哭了,靠在产房外面的墙上哭。靠着靠着他就出溜下去了,捂着脸“呜呜呜”,坐在地上喃喃地说:“续上香火了。”
我爹一辈子还哭过一回。那是我儿子考上保定的军校,发回来一张穿军装军训的照片时。我爹瞅着瞅着,就开始擦眼睛。
我爹活老了,头脑清晰,耳朵有点儿背,一顿能吃一碗饺子。爷爷奶奶走后,他一直住在东房里,不肯跟我弟弟住。房子旧了,一下雨就漏,不适合挖下水道,也不适合接大暖。我和弟弟商量拆了重建个二层楼,还可以租出去。我爹说自己年岁大了,经不起折腾,屋顶用油毡补补就行,后来屋顶就白一块红一块的。
我爹九十岁那年秋天,差人喊我回家,说我爹回来了。我爹说:“你爹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
说话的爹是我的亲爹,他生了我养了我。他嘴里的“你爹”是我的二叔。
那一年,我爹和二叔站在槽子坡的月光下。二叔说:“你已成家,以后爹娘就归你管了。我一个人去哪里都是一样。”二叔去朝鲜半年就牺牲了。据说当时他冲出战壕,胸口中了一枪,滚下山坡,手里还紧握着爆破筒。那年我才两岁半,我爹给我改名叫“顶门”,让我顶二叔的门。
我爹是从新闻里知道二叔回国的。他坚持让我开证明,坐火车,接二叔回家。
二叔回家了,他躺在一只红红的木匣子里,躺在西房的炕头上。院子里都是人,我爹请红白理事会给二叔搭了灵棚,取了屋顶上的两片全瓦让我盖在二叔的棺木上。他从柜里取出麻衣孝服,让我和儿子穿上,递给我一只黑灰色的瓦罐。
“跪在灵前,磕九个头,把瓦罐使劲儿摔在地上。”我爹对我大声说。他被人搀扶着,不肯坐下。
在我老家,摔瓦罐就是继承死者家业。
二叔埋在槽子坡。
我爹坐在二叔的坟边,用拐杖点一下地,我就喊一声“爹”,磕一个头。从部队回来的儿子跪在我旁,跟着我喊一声“爷爷”,磕一下头。槽子坡的草随风摇摆,长尾巴的鸟从里面飞出,落到高高的老榆树上。
我爹拍拍坟头说:“你有后,有儿子,有孙子。往后年年有人给你上坟。”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