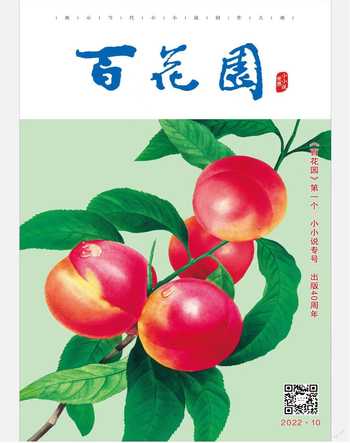兴安杜鹃
2022-07-05张港
张港
因海拔不同,兴安岭上草木花卉各有分层,白桦在下,落叶松在上,兴安杜鹃夹在当腰。进到四月,让雪捂了一冬的大山,杜鹃花开得旺盛,开得红火。花儿叫杜鹃,鸟儿叫杜鹃,女孩子也叫杜鹃。塔哈尔村的女孩儿,就有不少名叫杜鹃的。说实话,没几个闺女真见过杜鹃林——深山老林哪是大姑娘去的?倒是老赶山的,常常循着杜鹃树走山道,能采得着山货,找得到宝物。
一个达斡尔人,哪能不唱歌?一个达斡尔女孩儿哪能不唱歌?塔哈尔村老沃家那独生俊丫头,唱散山雾唱绿河唱肥牛羊唱谷黄的沃杜鹃,一股急火,忽地连句话都不能说了。你说说,这一家子人,日子可咋往下过?
求医问药找偏方,招儿用尽了。杜鹃爹说:“让搬山我就搬山,叫截河我就截河,只要闺女能说话就中。”
齐齐哈尔城来的老中医,望闻问切,上下相看了沃杜鹃,拉她爹的袖子,到外头说:“不是胎带来的,是毒火攻心,能治。”
“咋治?说!”
“那个啥,这个呀,找丫头最惦在心上的人,瞅冷子,使大劲儿,给她一个大嘴巴。这一激,她吐出心里的毒火,管保行。”
“啊——”杜鹃爹翻翻手巴掌,“那……那咋下得去手?”
“就是下得去手,你也不中。——丫头是不是有心上人?是哪个?叫他来才行。”
杜鹃爹唰地脸翻黑云:“唉——唉——病根儿真就在他身上。他这小子,上了北山里,两年了。”
上北山里,人人懂得,那是参加了抗联。
“哦——那个,回来没?能叫回来不?”
杜鹃爹一脚跺起沙尘:“还……还回……回个啥哟!——打日本,阵亡了呀!”
“那……那可是真?丫头,她知道不?”
杜鹃爹连点三下头。老中医摇了摇头。杜鹃爹说的那人叫墨尔根,抗联来人送信,戴着墨尔根的灰军帽,帽子上一个大枪眼儿。这事人人知道,杜鹃也看到了,打那时就出病了。
老中医听到这儿,说:“呀——是这个,那么的吧,我回城去,拿祖传天绝狠药。我去去就来。”
杜鹃姑娘上河沿儿,风就不刮了;杜鹃上草甸,百灵就不唱了。可怜啊可怜,这孩子可怜。人人宠着杜鹃,人人惯着杜鹃,杜鹃想干啥就干啥,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花红柳绿四月天,山上该是开出了杜鹃花。杜鹃姑娘穿了红,搽了粉,烧黑柳枝描了眉毛,一个人出了屯子,朝山里去了。屯里人说:“让她去吧,散散心也好。”
嫩枝扫脸,青草扯衣,泉水潺潺,白雾茫茫。春山是俊姑娘,俊姑娘是春山。杜鹃口不能语,心却在唱。她跟自个儿唱:“大松树刮不倒,墨尔根还扛着枪。雁去雁来,墨尔根就在山上。哥哥来,看我的新衣裳;哥哥来,杜鹃花红,红杜鹃唱……”
白桦林、落叶松之间,红杜鹃铺成宽宽的红花大道。杜鹃姑娘插了一满头红花儿,嘴唇微动,无声地唱着,顺着花路走。
杜鹃姑娘在心里念叨:“也就是打日本打累了,墨尔根睡着了,他们就说那个了。瞎说,胡说,瞎说,胡说。墨尔根哥哥就在前头,扛着枪在前头……”
太阳爷儿跟着杜鹃姑娘走。杜鹃姑娘累了,太阳爷儿也靠山头歇了。杜鹃姑娘坐在石头上,眼睛搜寻着,她要采一朵最大最红最好看的杜鹃花。她比画着,想象着把花插墨尔根军帽上,又插墨尔根胸脯上……
忽然,身后有响动,杜鹃一回头,我的妈呀!白桦树下,钢盔闪闪,黑枪筒子从榛柴棵里伸出来,啊——是日本人!
顺日本人枪管所指,杜鹃看到一个人:灰军帽,端大枪,站在大松树下。
啊——墨尔根!墨尔根?墨尔根咋这么瘦?墨尔根咋这么矮?墨尔根咋这么黑?啊——杜鹃使出全劲儿,可是,嘴喊不出声。

忽地,榛柴棵里起来一片黄衣鬼子,刺刀閃闪亮。
“墨尔根——墨尔根——有鬼子——”
杜鹃姑娘喊出来了,声震林海。
砰!砰!砰!枪声响了。
“墨尔根——墨尔根——有鬼子——”
大山中声音回荡,杜鹃姑娘躺在杜鹃花丛中。
杜鹃姑娘的喊声,救了抗联。
抗联安葬了杜鹃姑娘。那个哨兵很惊讶:“她为啥冲我喊出‘墨尔根这仨字?怪了!”
老中医打城里来了,将一包药塞给杜鹃爹。
杜鹃爹拿手挡了,说:“俺闺女没病,俺闺女嗓门儿亮得很。俺闺女还是抗联的人,戴着灰军帽。”
“啊——那个啥,你咋还哭了呢?”老中医惊疑了。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