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之歌
2022-07-05张定浩
张定浩
《诗大序》袭用《乐记》论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雅》里有一首《四月》,据传作于西周幽王时期,末句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这旧时君子所呼告出的哀歌,虽源自个人,却也正是为一个行将崩毁的帝国而作。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周代人使用历法,往往夏正与周正并用,这首诗用的历法是夏正,与我们今天农历一致。农历四月初,正是立夏时节。维,本义有联系的意思,“维者,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冬春之交,四隅之四维也”(参《素问·至真要大论》“其在四维”,张志聪集注)。前人多把此处的“维”视为语助词,一笔带过,但若联系起“四月维夏”与“六月徂暑”之间显然的对应关系,“徂”既为动词,表示“往”“至”之意,“维”至少也应该被视为一个曾经有意义的动词。春夏之交,往往是一年中最为敏感的时节,因为最美好的季节即将逝去。“欢乐极兮哀情多”,就比例而言,人生中幸福欢乐的日子总是少于悲愁困苦的日子,一个朝代的治世也每每短于乱世,正如春天只占据一年中的四分之一。这首诗从初夏写起,单用一个“维”字,让人隐约思及那不曾提到的春天。
“先祖匪人”,这句字面似有辱骂先祖之嫌疑,故历代注家多有曲辨,但最终是王夫之《诗经稗疏》的解释更受认可:“‘匪人者,犹非他人也。《頍弁》之诗曰‘兄弟匪他,义同此。自我而外,不与己亲者,或谓之他,或谓之人,皆疏远不相及之词,犹言‘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也。”
“胡宁忍予”,这句通常解释为“何忍使我遭此祸也”,或“忍受我久役在外不回去祭拜”,或“为何忍心使我受苦”,但这种解释中的“遭祸”“久役在外不回去祭拜”“受苦”,诸如此类,都是原诗句中所没有的,属于添字增释。考《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一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其中“愁予”一词,王逸和朱熹都解释为“使我发愁”。“愁”字作为心态动词,其跟随人称代词时做使动用法,是古文法常例;而“忍”字同为心态动词,“忍予”和“愁予”的词组构成也相似,若将“忍予”也视为使动用法,或许更简明。如此,忍受的主语就落在“我”的身上,而非先祖。“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的大意就是,先祖并非外人,如何会宁愿使我隐忍?这个意思,会比通行意思更深一点。
《四月》共八章,每章四句,除第七章一气贯注之外,大抵都是前二句借自然万物起兴,后二句自赋平生,兴和赋之间的关系似断实连,空灵跌宕,不可拘泥。《郑笺》:“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与人为恶亦有渐,非一朝一夕。”这是以暑热比拟恶政,将四月到六月的变迁比拟为恶政之渐成,可谓敏锐。但若结合后二句,似还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要点在一个“忍”字。《周易·坤卦》初爻爻辞:“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微知著,于乱世之初自当有所察觉,有所准备,或奋起反抗,或远走高飞。唯有普通民众,浑然不觉,自甘隐忍,同时,他们也缺乏想象他人痛苦的能力,会很轻易地去劝告那些置身苦难的人保持隐忍。作恶非一朝一夕之功,对恶的隐忍和默许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从四月之初夏至六月之酷暑,可以说是愈演愈烈,而我之先祖倘若在天有灵,他如何会像那些庸众一样,还一味地劝我忍受呢?“胡宁忍予”,在这里遂有一丝“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然而,当酷政已至顶峰,此时痛苦的反倒是那些不愿继续忍受的觉醒者,因为他们会发现无处可去。腓通痱,风病也。秋风一起,草木渐趋凋零,无从逃避。乱离,政乱民离;瘼,无名之病;爰,本义为援引,后借为发语词;其,高本汉认为在此处是一个表示未来和愿望的语气助词,并引《大雅·烝民》“式遄其归”为证;适归,往归。《说文解字》段注:“逝,徂,往,自发动言之;适,自所到言之。故女子嫁曰适人。”而这所到所归之处,具体又可细分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后世如《史记·伯夷列传》“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这是在时间长河中找不到归宿;如韩愈《上贾滑州书》“周流四方,无所适归”,则是在空间中无所归依。在此政乱民离的无可名状的国家之病中,觉醒者茫然四顾,于时间和空间中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此章与《蓼莪》第五章雷同。烈烈,凛冽。飘风,旋转之风。发发,迅疾的样子。冬日凛冽,比起秋日尚有残病之百卉,此时唯见大风肆虐横行于世间。“民莫不榖”一句,除《蓼莪》外,又见于《小弁》,或为当时惯用套语。榖,旧有几种解释,曰养,曰生,曰善好,曰福禄,各家争执不定。若从“善好”和“福禄”之义,似乎和前面“冬日烈烈,飘风发发”的乱世飘摇气息迥然不合,前人或解释为怨者绝望愤激之语,但在提及冬日风霜和自身苦难之间,插上一句“老百姓没有过得不好的”或“老百姓都在享福”,总觉得有违君子之情理。“我独何害”的“何”,旧解为“何故”“为何”,但这样解释,在“何”与“害”之间就要增加一个动词,否则于文法不合,因此郑玄解释为“我独何故睹此寒苦之害”,其后注家大多承繼此说进一步解释为“为何独独我遭逢这种灾害”,这种在文法不合之后的增字解经,尤其增加的是一个动词,显然并非善策。所以,今人高亨和裴学海遂将此处的“何”解释为“荷”,蒙受、负荷之意,这也是“何”字的古义之一,《诗经》中不乏其例,这样就通顺很多。但高亨和裴学海解释“榖”字,一取“善”之义,“他人都过得很好,独有我蒙受灾害”(高亨《诗经今注》);一取“福禄”之义,“他人莫无福禄,我独担负忧患”(裴学海《古书疑义举例四补》),如前所述,似仍有未尽之处。

《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诗毛氏传疏》(全三册)〔清〕陈奂著中国书店1984年版
榖者,谷也,本义为百谷之总名,引申为养育、生活、善好、福禄诸义,而在《诗经》中各义项都有对应之处,这也是容易造成混淆的原因。相较而言,养育和生活之义接近,表示一种动态;善好与福禄之义接近,表示一种状态。要明确“民莫不榖”的确切意思,需将《四月》《蓼莪》《小弁》三处“民莫不榖”合而观之,它们若为惯用句式,意思应当相仿才是。《蓼莪》为孝子思亲之辞,《小弁》是太子怨亲之辞,这两首诗中的“民莫不榖”,大多数注家都解释为养育、相养,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这是天下最为普遍的生活状态,《蓼莪》和《小弁》之作者却望之而不可即。而陈奂《诗毛氏传疏》释《小弁》之“民莫不榖,我独于罹”,引《诗经·王风·大车》“榖则异室,死则同穴”句,认为《小弁》的“榖”字也当如《大车》“榖则异室”之“榖”,当作“生”义解,“言人莫不有生聚相乐,我太子独处于忧”。随后,循照此例,陈奂将《四月》“民莫不榖”之“榖”,亦释为“生”,即“人无不贪生者”。此种解释,虽不曾通行,窃以为却比其他解释更得原诗之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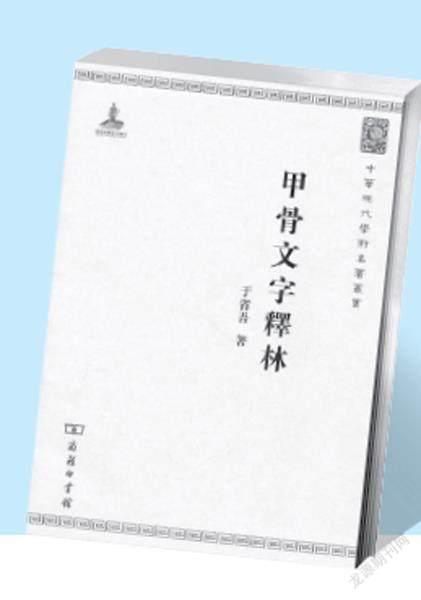
《甲骨文字释林》于省吾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民莫不榖”,意指老百姓最关心的永远是活着,能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愈近乱世愈是如此,忙忙碌碌,只为有一口饭吃。“我独何害”,或者“我独于罹”,讲的都是一个不同于“民”的君子,他的心思不单单在活着,因此也就要承担更多的忧患,并置身于更多的忧患中。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三闾大夫之慨叹几同于《四月》作者之慨叹。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侯,三家诗又作维,若用现代语法表示,大概接近于“乃”这样的副词,旧解多视为无意义的语助词,一笔带过。然而,要理解和欣赏诗歌,有一个基本认识前提就是,要相信一首好诗中的每一个词都是有作用的,尤其是语助词或副词,其幽微的语气转折和时态暗示往往能决定诗句的基调,这一点,古诗和新诗概莫能外。《诗经》中存在大量的语助词,若能细细体味其在具体语境中的选择,及其本义,每每会有意外的收获。
《小尔雅·广器》:“射有张布谓之侯。”“侯”字的本义,即箭靶,隐含有即将抵达的目标之义,但这个义项后来渐渐归属于“候”这个字,如守候,等候。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王侯之侯与时候之候初本同字,候为后起的分化字。……侯与候古通,典籍习见。”因此,“侯N侯N”,其实就是一个将来完成时的句法表达,即“等候着(成为)N和N”。此类句式,《诗经》中并不少见,若用将来完成时来解释,多可贯通。如《小雅·正月》:“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薪是粗大的柴火,蒸是细小的柴火,旧解多将“侯”作“是”解,再将“中林”与“薪蒸”对立,如君子之于小人,但说“看到树林里都是粗细不等的柴火”,这是很奇怪的说法,所以后来有些注家如陈子展索性将“薪蒸”译为灌木和草丛,然而,将“薪”译为灌木其实是有点牵强的,因为古书训诂中多次说过“大木为薪”,如《淮南子·主术》“冬伐薪蒸”,高诱注曰:“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而如果将“侯薪侯蒸”视为将来句法,即“看着这些树林里的林木,以后都会成为粗细不等的柴火”,就非常自然了,并且其中的悲凉恰与全诗基调相合。又如《大雅·生民》:“诞将嘉种,维秬维秠。”旧解为“天上降下好的种子,是秬与秠”,然而种子落在土里,是很难立刻具体辨别的,而“维”与“侯”古书中常可通,若视之为将来完成时态,即“天上降下好的种子,长出来将成为秬与秠”,似乎会更准确一点。

《香草校书》(全三册)〔清〕于鬯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废为残贼”,这句历代也是聚讼纷纭,涉及对“残贼”的理解,究竟是指残害他人还是指受到残害,旧解多倾向前者,即在位者慢慢变成残暴贼子,这个在句法上要自然一点,但需要处理“废”字,所以旧解就训“废”为“大”,为“忕”(惯于),为“变”,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废”的本义和“残贼”之间的矛盾。此种牵强,前人亦有所察觉,如于鬯《香草校书》就讲:“此‘废字依常解‘废弃义自通。《毛传》训‘忕、《朱传》训‘变者,殆疑于‘为残贼三字耳,故必谓在位者为残贼。其实上二句为被废者自言,固无不可。为残贼者,在废之者未有不以其为残贼而废之也,是废之者被以惡名,非真为残贼,与‘莫知其尤之义不妨害也。且正惟被以为残贼之名,而究无为残贼之罪状可案,故曰‘莫知其尤,则竟是无罪而遭废弃者矣。玩此诗之意,本无罪而遭废弃者所作。”这个解释,非常通达,且和前面一句“侯栗侯梅”的将来完成时表述恰可应和。
山中草木众多,诗人选择栗与梅起兴,并非随意。栗,是周代的族树,其木质坚实细密。《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梅,疑与《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之“梅”相同,即柟,现在所谓的楠木,与栗树同为高大乔木,优质木材。山中那些美好的草木,本来是要成为像栗树和楠树这样的可造之材,如同“我”本是要成为国之栋梁,没想到中途却惨遭废弃,沦为在位者眼中的残贼之人,竟不知罪在何处。“侯”字所暗示的巨大期望,与“废”字中所包含的无边绝望,一虚一实,字字千斤。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榖?
相,视也。载,则也。杜甫《佳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诗人的思绪从山林转向泉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郑玄释此章前二句,“我视彼泉水之流,一则清,一则浊。刺诸侯并为恶,曾无一善”,这大抵是受毛诗小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的影响,遂用泉水的清浊有别来反兴下国诸侯的善恶无异,并将“我日构祸”之“我”,解释为我等诸侯。但一首诗中的“我”,指代应该统一才合理,这首诗其他章句的“我”显然是指诗人自己,为什么这里的“我”偏偏指向诸侯呢?所以后来朱熹又有另一种解释,即把“构祸”解释为“遭遇祸患”,而非“制造祸患”。到了清代马瑞辰,甚至将“构”索性训为“遘”的通假,看起来字面自洽了,但一方面这种通假释经要慎用,另一方面,若将“构祸”解释为“遭遇祸患”,毛诗小序中的“下国构祸”又该如何解释?
反过来,我们可以说,毛诗小序的“下国构祸”说,其实也正来自于小序作者对“我日构祸”这句诗的理解。对小序作者和郑玄而言,“构祸”的本义就是制造祸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因此出现的矛盾就在于,祸患的制造者怎么就成了“我”?“我”不是受害者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只好把“我日构祸”之“我”,解释为下国或诸侯。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也会是制造禍害的人,而这种地方,恰恰是先秦古典诗学精神的核心。
《孟子·离娄》:“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渔父歌沧浪之谣,将自我之外的世界比作流水,无论世界清浊,我依然是我,或对之以缨,或对之以足;孔子闻沧浪之谣,视流水为己身,故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世界之清浊,就是我之清浊,而濯缨或濯足,恰是不同的我所需要承受的不同遭遇。“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是对世界和自我的判断;“我日构祸,曷云能榖”,则犹如“自作孽,不可活”,是一个被贬谪流放之臣痛彻心脾的反省。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败坏,身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若是为官者和读书人在平常时刻都只懂得投机和自保,每个人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言不发,自我阉割,坐等时局恶化,这种沉默和隐忍,日复一日,本身就是在参与制造更大的祸害。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宁莫我有”,即“宁莫有我”的倒装,《诗经》里不乏其例,这里的“有”可作“亲友”解,通“友”,与《王风·葛藟》“亦莫我有”相似,即善待或友爱。《说文解字》:“宁,愿词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补充道:“今人言宁可如此,是愿如此也。”然而,历代注家在处理《四月》中的两个“宁”字时(“胡宁忍予”和“宁莫我有”),几乎都忽略其作为愿辞的口吻,或训为“胡”,或训为“乃”,或反问或陈述。如此一来,“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在旧解中几乎都千篇一律地解释为诗人的哀叹,即我如此鞠躬尽瘁做事情,君王为何(还是)对我不理不睬。

《广雅疏证》〔清〕王念孙著钟字讯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
这种忠臣之怨,几千年来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然而《诗经》作者是在秦汉帝制形成之前的人类,他们身上自有一种迥异于后世的刚强明亮之气。而这种气息的微妙流荡,很多时候,就暗藏在那些被后世注家轻易忽略的语助词之中。“尽瘁以仕,宁莫我有”,按照“宁”字的愿辞本义就很好解释,即我尽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宁可(君王)不善待我。这显然是一种决断,而非哀怨。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长江和汉水,是南方两条最主要的河流,围绕它们遍布在南方的其他河流皆可视为这两条大河的支流,受其制约。旧解多以江汉喻王者,以江汉能纲纪南国反兴幽王不能纲纪诸侯和群臣。然而,周朝地处黄河流域,以当时属于蛮荒之地的江汉之水来比喻周王,似乎有点拟于不伦,或许也鉴于此,郑玄遂把江汉比喻做吴、楚之君,当然这样仍然有很多牵强,已为后世学者所驳,兹不赘述。而既然我们已经指出“宁莫我有”的决断,那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或许也能被这样的决断重新擦亮。
“纪”的本义,是找出散丝的头绪,引申为整理、综理。江汉滔滔,奔流向海,这不舍昼夜一往无前的力量本是水性使然,无须外力强迫,而就是在这样的本性激发中,它们客观上起到了一个经纪山川的作用。依旧是《孟子·离娄》,有一段对水德的赞美:“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水之本在其源泉,君子之本在自反自省,一切艰难困厄都要回到己心深处找原因,求解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被贬谪流放到南方的诗人既已痛定思痛,又被滔滔江水所激励,遂决心尽力尽责于当下在任之事,至于君王是否会再次重用,已不重要。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同为谪臣,东坡去世前不久所作自题诗,其中的沉痛、决绝与振作,浑然一体,堪为《四月》第六章的注脚。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
鹑,鸢,都是鹰、雕一类的凶猛大鸟,可以飞到很高的天空;鳣,鲔,又见《卫风·硕人》:“鳣鲔发发”,是大黄鱼和鲟鱼一类可洄游入江的海鱼,所谓“潜逃于渊”,即古人所见这些鱼类可以从江水中游入海洋的现象。《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本是万物各得其所之象。匪,非也,同首章“先祖匪人”之“匪”。朱熹《诗集传》:“鹑鸢则能翰飞戾天,鳣鲔则能潜逃于渊,我非是四者,则亦无所逃矣。”诗人借鸢、鱼各得其所之象,比喻自身不得其所。这种解释,历代本无异议,也相当合理,然而自从王念孙《广雅疏证》将“匪”字训为“彼”,王引之《经传释词》和陈奂《诗毛氏传疏》从之,歧义遂生。虽然前有王先谦、后有高本汉,都对“匪字训彼”之说予以明确反驳,理据均在,但当代通行的不少《诗经》注本译本却依旧将这里的“匪”字解释为“彼”,且罔顾与“先祖匪人”之“匪”的矛盾,不知何故。高邮王氏父子虽是清代训诂名家,因声求义,颇多创见,然好与人异,注解《诗经》往往只求字面通顺而搁置诗意,读诗者不可不慎。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隰,低湿之地。“山有……隰有……”为《诗经》惯用套语。蕨,薇,是山中常见野菜。《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所言风物与此处相似。杞,枸杞。桋,旧解通常人云亦云为一种名为赤栜的树木,丛生于山中,但究竟为何种树木,用在此处又有何意,皆语焉不详,所以后来又另有一种解释,认为这里的“桋”通“荑”,训为草木初生之嫩芽,这样似乎就可以像枸杞一样,作为一种可食之物来处理。但在原诗的对句中,“蕨薇”的草字头,显然和“杞桋”的木字旁相对应,若贸然将“杞桋”改作“杞荑”,如敦煌诗经写本那样,似乎也有牵强之处。
今人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鑒》,认为“桋”即今天的苦槠树,“古书上所说的‘槠‘杼‘桋等,均指当时北方常见的苦槠属植物……本篇‘蕨薇和‘杞桋并提,可见均为可食用的种类;‘蕨‘薇采食的是嫩芽幼叶部分,而‘杞桋中,若‘杞解为‘枸杞,则采食的是果实部分,则‘桋也应为采果,因此可解为苦槠。其种子俗称‘苦槠子,可磨作豆腐食之”。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并且早在此书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向熹主编出版的《诗经词典》,已将这里的“桋”解释为苦槠树,“桋,一种常绿乔木,又名赤栜,即苦槠树。果实为扁球形坚果”。苦槠果,和板栗有点相似,虽然味道偏苦,但淀粉含量高,饱腹感很强,在过去一直是山里人家的备用粮食。如此一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似乎可视为隐士的自白,如严粲《诗辑》所言,“遁迹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谪宦之身思归山林,虽为常情,但就全诗情思而言,似尚有未尽之处,尝申言之。

《诗经植物图鉴》潘富俊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诗经韵读》王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上一章说到飞鸟和鱼,虽令人向往,却非人所及。人只能生活在大地之上,甚至,就像植物一样,只能生活在那一小方属于自己的土壤中。蕨薇与杞桋,皆是寻常山野间毫不起眼的植物,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亦能给予饥饿者以能量。一个人身逢乱世,于国家于个人都看不到半点希望,种种有心无力,颓唐哀愁,《四月》作者自当了然于胸,这首诗也正肇端于这样的感情中,但诗人却没有耽溺于此,如前所述,他是在回望历史和审视当下之后,缓缓走向深刻的反省和勇敢的决断。
《四月》八章,每四句一章并换韵,其中四、六章同韵,二、八章同韵(据王力《诗经韵读》)。对诗人来讲,韵脚如同作曲家使用的音符,其间的呼应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文本内部的有意应答。如六章“尽瘁以仕,宁莫我有”的决断,就可视为对四章“废为残贼,莫知其尤”之遭遇的回答。同理,八章的“山有蕨薇,隰有杞桋”,不妨视为对二章“乱离瘼矣,爰其适归”的回答,是在目睹天崩地裂上下失序的拔根状态之后,重新扎根,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就在这个位置上求得安宁。“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作出这样的歌,正是诗人的职责,而“维以告哀”并非徒然的哀怨,而恰恰是属于诗人的清醒,如同克莱夫·詹姆斯在谈及策兰《死亡赋格》时所说:“这首歌以唯一可能的方式救赎了人类—承认这里没有救赎。”EB8FCC23-B861-458F-AFC9-A1D2962492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