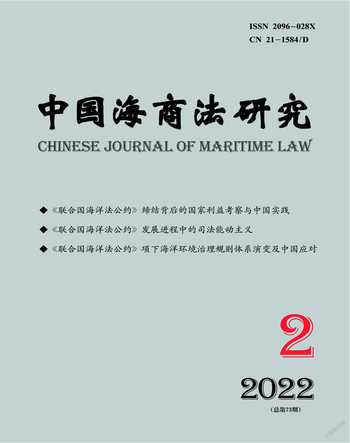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研究
2022-07-05唐尧夏立平
唐尧 夏立平
摘要:極地海冰消融的后果波及整个地球,并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人们。北极渔业资源就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影响。2018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极渔业资源治理是中国在北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一个世纪以来,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们表现出了三个特点:科学在国际机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机制的制定和实施的深度不断加强;通过不断加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来克服多边集体行动难题。中国的远洋渔业起步于1985年,且一直积极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为了更好地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制定、实施和完善过程,未来中国首先要加大对中北冰洋的科学考察力度,积累和分享关于渔业资源的知识;
其次要深入广泛地运用好非国家行为体;最后要加强和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北极;渔业资源;国际机制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2)02-0064-08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Arctic fishery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ANG Yao1,XIA Li-ping2
(1.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Shanghai 200136,China;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The consequence of melting of polar sea ice is affecting the entire planet and affecting people in many ways. Arctic fishery resourc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is change. The 2018 white paper of China’s Arctic Policy proposes to actively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governance of Arctic fishery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Arctic.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Arctic fishery resources have developed vigorously. They show three features: scienc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state actors in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difficulties of multilateral collective action can be overcome b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China’s distant-water fishery started in 1985 and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ance of Arctic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making, implementing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Arctic fishery resources, China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he first is to increase it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 and accumulate and share knowledge about fishery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to make in-depth and extensive use of non-state actors. The last is to strengthen and establish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r arrangements.
Key words: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rctic;fishery resources;international regimes
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2019年9月的报告指出,极地地区正在失去冰层,其海洋正在迅速变化。这种极地变迁的后果波及整个地球,并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人们参见IPCC:Special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访问网址: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3/2019/11/07_SROCC_Ch03_FINAL.pdf。北极鱼类就受到了极地变迁的影响。出于对已有和潜在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考虑,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渔业资源治理(governance)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既包括针对北极的区域性国际机制,也包括适用于北极的全球性国际机制,比如20世纪20年代制定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Spitsbergen Treaty)规定缔约方有在北极特定海域捕鱼的权利。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的范围包括次北极海域(sub-Arctic seas)和中北冰洋(central Arctic Ocean)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的地理范围大于通常所说的北纬66°34′北極圈以内的地区。目前,各国在北极的渔业活动集中在次北极海域。北极自然环境恶劣,鱼类的种类与热带海域相比较少,大约有200种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海水鱼类。[1]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的目标是解决或缓解北极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渔业资源枯竭的原因有过度捕捞,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以及副渔获和抛弃。那么,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发展脉络为何?其又表现出了哪些特点?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2]命运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2011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包括“四个必须”: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5]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性思维的体现,也是共时性思维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新中国外交战略理念、当代全球政治理念;[6]就后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诸多领域均有实践。比如,2017年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写入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和“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决议之中。2018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立场和方案。[7]海洋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法律基础,良好的海洋治理(good marine governance)就是其中之一。[8]北极渔业资源治理是海洋治理的内容之一,已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前沿议题。《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依法合理利用北极资源,其中就包括对于渔业等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利用。出于对经济和外交等因素的考虑,中国积极参与北冰洋渔业的治理、养护和资源开发。[9]特别是2018年以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作为原始缔约方签署的《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Agreement to Prevent Unregulated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简称《公海渔业协定》)使北极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区的地位日益显现。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再到海洋治理,北极渔业资源治理更像是一个交叉点,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上述背景与问题,笔者首先梳理分析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历史发展,进而归纳总结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特点,最后提出中国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制定、实施和完善过程的对策建议。
二、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历史发展
在梳理分析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历史发展之前有必要阐释治理和国际机制的概念。英语中的治理可追溯到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是指控制、指导或操纵。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流行起来。机制一词源于拉丁文regimen,意指规则、指导、指挥、管辖。国际机制的概念于1970年始用于政治经济分析。美国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指出,机制是一种治理资源。[10]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约翰·鲁杰(John Ruggie)、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围绕国际机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中斯蒂芬·克拉斯纳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得到了相对多的引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由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1]
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即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按照时间先后,相关国际机制包括《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区域性)、《保护太平洋大比目鱼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alibut Fishery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Ocean,双边)、《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区域性)、《渔业事务合作协议》(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shing Industry,双边)、《西北大西洋渔业未来多边合作公约》(Convention on Futur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 Atlantic Fisheries,区域性)、《东北大西洋渔业未来多边合作公约》(Convention on Futur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east Atlantic Fisheries,区域性)和《北大西洋鲑鱼养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almon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区域性)。
这些国际机制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次北极海域。根据2005年《北极气候影响评估》(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报告的内容,次北极海域涵盖四个区域,它们是北太平洋:白令海;东北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区域;东北大西洋:巴伦支海,挪威海;中北大西洋:冰岛/格陵兰区域。这一阶段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形成的原因在于解决或缓解已有北极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比如,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早在1502至1503年就在北美捕捞鳕鱼,直到20世纪中叶捕鱼国才认识到西北大西洋“取之不尽”的资源面临的主要威胁,从而在1950年建立了国际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Northwest Atlantic Fisheries),也就是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Northwest Atlantic Fisheries Organization)的前身。除《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以外,上述所有区域/双边机制都创设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与其他国际机制有所不同,它仅有个别条款涉及漁业问题。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即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公海渔业协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确立了专属经济区这一新制度,而全球绝大多数的渔业资源都位于各国专属经济区内,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直是北极渔业资源治理最重要的国际机制。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公海捕鱼自由同样适用于中北冰洋。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是,1995年通过的《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简称《鱼类种群协定》)规定了预防性做法,比如各国应广泛适用预防性做法以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和保全海洋环境,显然这是对“事后补救”做法的发展。在此阶段,全球性国际机制得到了全面发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有法律约束力和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渔业文件:前者如《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Agreement to Promote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by Fishing Vessels on the High Seas);后者如《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 on Responsible Fisheries)。区域和双边机制得到了同步发展。2000年签订的《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Migratory Fish Stock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建立了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Migratory Fish Stock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同时规定了应用预防性做法。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是极具特色的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它本身并不处理渔业问题,比如在2007年就没有接受美国关于在北极理事会讨论北冰洋渔业管理问题的提议,但它仍然通过发布涉及北极渔业资源的科学报告以及参与制定《公海渔业协定》的会议等方式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2013年5月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北冰洋考察总结报告》(Arctic Ocean Review Final Report)从范围、资源、相关国际文件、合作应对挑战、合作行动的机会几个方面阐述了北极渔业资源的相关问题,比如合作行动应当采取预防和生态系统方法。另外,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PAME)和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CAFF)参与了关于制定《公海渔业协定》的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
第三阶段是21世纪10年代至今,即从《公海渔业协定》至今。2018年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共十方签署了《公海渔业协定》,随着中国在2021年5月完成国内核准,该协定生效在即。《公海渔业协定》使得北极渔业资源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是首个针对中北冰洋的区域性机制,根据该协定,在未来16年内,此公海区域中禁止商业捕捞活动。这使得预防性做法从理念发展到机制中的个别条款,再发展到整个预防性机制。《公海渔业协定》是北极域内外国家合作解决北极地区问题的成功实践,也是对北极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12]在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问题上,《公海渔业协定》采取了“分步走”方法,即先为未来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积累科学数据,再建立正式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另外,2018年至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BBNJ)政府间会议已举行4次。BBNJ国际协定是国际社会通过订立专门补充协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善,而中北冰洋则是BBNJ国际协定最得以充分适用的区域。[13]由于渔业问题存在被纳入BBNJ国际协定的可能,该协定或将成为适用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的新全球性国际机制。
三、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特点
通过以上梳理分析可以归纳总结出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三个特点,第一,科学在国际机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北极周围边缘海域在历史上都曾遭遇过渔业管理危机。早在15世纪9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西北大西洋的鱼类资源,捕鱼活动也随后开始,但到1949年才签订了《国际西北大西洋渔业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Northwest Atlantic Fisheries)。同样,19世纪末随着更大更强的渔船、更好的渔具的出现以及更好的保存和销售渔获物的方法的发展,大规模商业捕鱼开始于巴伦支海。俄罗斯和挪威正是基于两国在巴伦支海的长期渔业活动而签订《渔业事务合作协议》。与此不同的是,直至今日人们对于中北冰洋渔业资源知之甚少。
在制定《公海渔业协定》过程中,有关各方召开了5次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2011年美国安克雷奇;2013年挪威特罗姆瑟;2015年美国西雅图;2016年挪威特罗姆瑟;2017年加拿大渥太华)。参与方包括北冰洋沿海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丹麦)、中国、日本、韩国、冰岛和欧盟,以及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次北极海域生态系统研究(ESSAS)、欧洲极地理事会(EPB)、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北极监测与评估工作组(AMAP)、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Inuit Circumpolar Council)、北极可持续观测网(SAON)、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PICES)、北极太平洋扇区工作组(PAG)。
其中,收集关于鱼类种群及其生态系统和迁徙模式的最新信息和数据是第一次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的任务之一,第五次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报告指出,中北冰洋公海区域被证实有12种鱼类,其中3种具有潜在商业利益参见NOAA Fisheries:Final Report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Scientific Experts on Fish Stock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访问网址:https://apps-afsc.fisheries.noaa.gov/documents/Arctic_fish_stocks_fourth_meeting/508_Documents/508_FourthFiSCAOreportfinalJan26_2017.pdf。,[14]但该报告仍然指出,当务之急是填补在中北冰洋公海关键区域鱼类分布方面的知识空白参见NOAA Fisheries:Final Report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Scientific Experts on Fish Stock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访问网址:https://apps-afsc.fisheries.noaa.gov/documents/Arctic_fish_stocks_fifth_meeting/508_Documents/508_Final_report_of_the_5th_FiSCAO_meeting.pdf。可见,关于中北冰洋渔业资源知识的匮乏贯穿《公海渔业协定》的制定过程。另外,在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or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和挪威-俄罗斯联合渔业委员会(Joint Norwegian-Russian Fisheries Commission)的实践中,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会为这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确定和制定鱼类种群的捕捞总额、季节、配额提供科学建议。《公海渔业协定》设计了针对科学合作的规定,即第4条“联合科学研究和监测计划”。因此,科学的作用从早期单一的提供建议发展到如今更广泛的引领指导。
第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机制的制定和实施的深度不断加强。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整个20世纪得到了蓬勃发展。与渔业资源治理关系密切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它们参与了国际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的建立。1949年1月26日至2月8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D.C.)召开了一次单独的会议,11个对北美东海岸渔业感兴趣的国家出席了会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还为签订于1994年的《中白令海狭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ollock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Bering Sea)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数据,促进不同群体参与建立和实施管理措施。
如上所述,参与制定《公海渔业协定》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有三类:国际组织如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国际论坛如北极理事会。具体来看,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就“气候变化对鱼类和渔业空间分布影响的全球评估”研讨会的结果在第二次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上进行了报告参见NOAA Fisheries:Report of 2nd Scientific Meeting on Arctic Fish Stocks,Troms 28-31 October 2013,访问网址:https://apps-afsc.fisheries.noaa.gov/documents/Arctic_fish_stocks_third_meeting/508_Documents/508_Report%20of%202nd%20Scientific%20Meeting%20on%20Arctic%20Fish%20Stocks%2028%2031%20October%202013_unlocked.pdf。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北极数据委员会主席彼得·普西弗(Peter Pulsifer)提供了一份独立的白皮书,其中就今后开展北极研究和监测常规清单的途径和方式提出了建议参见NOAA Fisheries:Final Report Third Meeting of Scientific Experts on Fish Stock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访问网址:https://apps-afsc.fisheries.noaa.gov/documents/Arctic_fish_stocks_third_meeting/508_Documents/Meeting-and-Breakout-Reports/508_3rd_Arctic_Fish_Final_Report_10_July_2015_final-unlocked.pdf。北極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和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更多以联合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方式参与完成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所列任务,比如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和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联合主持“中北冰洋综合生态系统评估工作组”参见NOAA Fisheries:Final Report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Scientific Experts on Fish Stock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访问网址:https://apps-afsc.fisheries.noaa.gov/documents/Arctic_fish_stocks_fourth_meeting/508_Documents/508_FourthFiSCAOreportfinalJan26_2017.pdf。与此同时,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参与了第二次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在2017年第五次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上,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还被认为可能提供相关信息,促进监测计划任务的完成。
与北极理事会关于北极海洋问题的基于科学的评估和建议不同,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和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进行的是原始科学研究。同时,北冰洋的大部分地区在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和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的工作范围之外(前者仅覆盖北冰洋的北大西洋部分;后者仅覆盖北纬30度以北的太平洋地区)。[15]因此,三者在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的合作是一种“强强联合”。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北极海洋科学组织(Arct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并赋予其强大的职能,比如制定和支持标准协议以加强实际合作,同时《公海渔业协定》的所有缔约方均应纳入其中。[16]另外,《公海渔业协定》规定,相关科学与技术组织、机构和项目可以参与有关数据的分享。综而观之,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机制的制定和实施超出了提供数据和建议的范畴。
第三,通过不断加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来克服多边集体行动难题。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的要求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鱼类种群协定》中均有体现。然而,美国学者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L. Goldsmith)和埃里克·波斯纳(Eric A. Posner)指出:“诸如保护渔场、减少大气污染以及维护和平等真正的国际性公共产品……属于多边囚徒困境,而非协调博弈。”“我们对真正的多边集体行动难题能够通过条约解决表示怀疑,尤其是在涉及众多国家的情况下。”[17]这一论断在《西北大西洋渔业未来多边合作公约》的实践中有所体现。《西北大西洋渔业未来多边合作公约》适用于“公约区域”和“管制区域”,其中“管制区域”限于“公约区域”的一部分(即公海)。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在其存在的前15年没有成功解决“公约区域”过度捕捞和资源枯竭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约区域”的渔业资源到了危险状态。同期欧盟和加拿大之间还爆发了“西北大西洋海洋渔业争端”。“公约区域”的很多资源直到2008年都没有得到恢复,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管理的20种资源中的10种在数年内被暂停捕捞。[18]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一度被认为是完全失效的组织。
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仍然不断加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是唯一涉及中北冰洋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它在渔业管理方面具有很多亮点,比如1998年通过了“对在国家管辖海域外的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管辖区渔船控制和执行计划”(Scheme of Control and Enforcement in Respect of Fishing Vessels Fishing in Ar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Fisheries Jurisdiction in the Convention Area),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行为的行动。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的北极渔业管理措施多样且全面,也体现了预防性措施等先进的管理理念。关于中北冰洋渔业资源治理的2014年努克(Nuuk)会议和2015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议等都提及并承认了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在中北冰洋的渔业管理职责。挪威-俄罗斯联合渔业委员会作为区域渔业管理安排同样发挥了作用,使《渔业事务合作协议》得到了较好的遵守。
《公海渔业协定》关于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的“分步走”方法是对传统做法的发展。根据《公海渔业协定》,未来可能启动谈判,为管理协定区域的捕鱼活动建立一个或多个新的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又对“联合科学研究和监测计划”条款的实施至关重要。
四、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北极环境变化增加了中国利用北极渔业资源的机遇。[19]中国的远洋渔业起步于1985年远洋渔业是指在公海或因签署协定获准在别国水域(主要是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从事的渔业活动,参见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47页。,目前的北极渔业活动涉及的区域有西北白令海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北太平洋公海、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渔业管辖海域。[20]中国分别在1925年和1996年加入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和《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尤其是通过签署《中白令海狭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明确了在高纬度北极海域的公海进行渔业捕捞与管理的权利。[21]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有在中北冰洋、次北极海域公海以及北冰洋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特定情况下)捕鱼的权利和义务。中国虽未批准《鱼类种群协定》,但并不拒绝参与养护机制变革,比如在《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框架下接受了他国的登临和检查。[22]在制定《公海渔业协定》过程中,中国先后三次参加北冰洋公海鱼类种群科学家会议。在会议上中国提出禁止商业捕鱼应是临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这使得禁令的期限最终定为16年。[23]同时,北冰洋公海渔业圆桌会议由中国发起,而该会议又促进了《公海渔业协定》文本的最终达成。如今,中国已是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国,并在特定议题上发挥了引领作用。
为了更好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制定、实施和完善过程,中国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加大对中北冰洋的科学考察力度,积累和分享关于渔业资源的知识。较之于次北极海域,中北冰洋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区域。中国已经具备了在中北冰洋科学考察的能力,比如2020年中国第11次北极科学考察中“雪龙2”号最高驶抵北纬86°。但中国的冰站考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观测局限于夏季,不能支撑完整冰季的观测,目前仅通过参与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冰站项目(Multidisciplinary drifting Observatory for the Study of Arctic Climate,简称MOSAiC)实现了对中北冰洋的冬季观测。MOSAiC由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启动,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暨亥姆霍兹极地海洋研究中心(Alfred Wegener Institute,Helmholtz Centre for Polar and Marine Research)组织实施,来自20个国家的400多人参加了该次考察。如今中国已有两艘极地科考破冰船,并且积累了20多年的北极科学考察经验,将来可以组织实施类似MOSAiC的活动,弥补现有科学考察的不足,不斷丰富对于北极渔业资源的认知。
与此同时,中国应在《公海渔业协定》框架下积极开展相关活动,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的联合科学考察。
韩国就有官员提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可以用他们的极地破冰船领导中北冰洋的渔业科学调查。[24]2018至2019年上海海洋大学依托中国“雪龙”号、日本“开洋”号(Kaiyo Maru)、新西兰“海神”号(Tangaroa)和澳大利亚“调查者”号(Investigator)科考船以及中国商业性磷虾渔船“福荣海”轮和“龙腾”轮等实现全球首次以南极磷虾资源为主要目标的环极调查,为北极渔业资源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基于获得的科学考察成果,中国应当参与甚至主持关于北极渔业资源的科学报告,为《公海渔业协定》的实施和完善贡献力量。另外,《公海渔业协定》规定:“本协定生效后,缔约方可邀请其他真正感兴趣的国家加入本协定。”因而不排除将来有更多国家加入《公海渔业协定》的可能,中国积累和分享关于北极渔业资源的知识正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
其次,深入广泛地运用好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面是要推动中国组织发起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北极渔业资源治理中发挥作用。如前所述,几乎没有中国组织发起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制定《公海渔业协定》,这就使得中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更多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同时可能对中国今后参与该协定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以北极理事会为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已形成了“知识型垄断”,[25]它在渔业资源治理等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极地科学亚洲论坛(Asian Forum for Polar Sciences )是中国组织发起的涉及北极的非政府组织,它的成立仅晚北极理事会八年,但其所发挥的作用相较之下极为有限。二者在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以及工作组等的设计上有相似之处。基于此,中国应当在极地科学亚洲论坛中加大研究力度,使其能够像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和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那样作出知识贡献。同时,极地科学亚洲论坛也可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2021年3月的极地科学亚洲论坛会议,在原有参会国家基础上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埃及的科学家参会,这表明其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要将极地科学亚洲论坛的作用提升到与其影响力相适应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要关注北极理事会的永久参与者,除前文提及的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以外,还有萨米人理事会(Sammi Council)、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阿留申国际协会(Aleu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北极阿萨巴斯卡理事会(Arctic Athabaskan Council)和哥威迅国际理事会(Gwich’in Council International)。较之于北极国家北极国家是指北冰洋沿海国、芬兰、冰岛和瑞典。
和观察员,中国对于永久参与者的关注相对不足,这同样可能导致在《公海渔业协定》的实施和完善中处于被动地位,该协定多处提及北极土著人民,比如“缔约方可建立分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包括北极土著人民在内的北极社区代表均可参加”。今后中国可在主办《公海渔业协定》或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相关国际会议时邀请永久参与者参会。与此同时,依据北极理事会规定,中国也可通过永久参与者提出项目参见Arctic Council:Observers,访问网址:https://arctic-council.org/about/observers。目前,阿留申国际协会是参与北极理事会项目最多的永久参与者,参与项目达到11个,而中国参与的项目仅有4个。中国可以围绕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相关的科学议题通过永久参与者提出项目。
最后,加强和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不论是次北极海域还是中北冰洋,中国都是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的远洋渔业国,而沿海国与远洋渔业国之间开展有效国际合作的平台之一就是区域性渔业组织。随着《公海渔业协定》的实施,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将基本实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全覆盖。特别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鱼类种群协定》对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肯定和鼓励,中国要在北极推进相关工作。就次北极海域而言,中国要与有关各方共同应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面临的挑战,包括捕捞能力过剩,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无法获得相关的数据用于完善自己的数据,在科学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养护与管理措施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来保证其执行的有效性,部分制度设计不合理的问题。[26]作为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的船旗国和港口国,中国要严格遵守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以及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委员会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规定,尤其避免与沿海国发生类似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下的“西北大西洋海洋渔业争端”的事件。
就中北冰洋而言,通过“分步走”方法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的做法为中国参与制定新的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提供了思路。中国应积极推动在《公海渔业协定》框架下建立一个或多个新的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根据《公海渔业协定》,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的基础包括来自联合科学研究和监测计划、国家科学计划和其他相关来源的科学信息等。这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中国与其他缔约方的合作;中国的国家科学计划;与可能提供科学信息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
基于此,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联合科学研究和监测计划”的实施;运用好国家科学计划;重点关注同参与制定《公海渔业协定》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在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的基础上,中国还要依据《鱼类种群协定》(第21条)等规定促进缔约方的遵守,[27]通过《公海渔业协定》实现有效治理。
五、结语
冷战结束后,北极迎来了国际合作的黄金时期,但好景不长,2007年北冰洋底“插旗事件”将北极推上了全球海洋治理的“风口浪尖”。当前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环境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更为复杂多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恰逢其时,使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拓展到了北极地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为北极海洋治理指明了方向。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历史发展综合了相关的区域性与全球性机制,它所表现出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特别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加强和《公海渔业协定》的制定,表现出了人们解决世界事务难题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应看到,参与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的制定、实施和完善涉及科技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北极渔业资源治理是中国在北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通过北极渔业资源治理国际机制加快建設海洋强国和科技强国。参考文献:
[1]王燕平,李励年,林龙山,等.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参与北极渔业的可行性分析[J].渔业信息与战略,2015,30(1):2.
[2]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2).
[3]何英.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5.
[4]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6.
[5]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N].人民日报,2015-03-29(1).
[6]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3):11-20.
[7]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J].当代法学,2019,33(5):143.
[8]CHANG Yen-chiang.On legal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toward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J].China Legal Science,2020,8(2):16-18.
[9]CHANG Yen-chiang,KHAN M I.May China fish in the Arctic Ocean?[J].Sustainability,2021,13(21):2.
[10]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陈玉刚,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11]KRASNER S D.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2,36(2):186.
[12]刘惠荣,齐雪薇.缔约方批准《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的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M]//刘惠荣.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07.
[13]桂静.中北冰洋国际治理进程检视及其协调[J].太平洋学报,2021,29(6):81.
[14]VANDERZWAAG D L.Governance of fisheries in the central Arctic Ocean:cooperative currents,foggy future[M]//LIU N Y,BROOKS C M,QIN T B.Governing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 the Polar Regions.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9:104.
[15]BAKER B.ICES,PICES,and the Arctic Council Task Force on Arctic marine cooperation[J].UC Irvine Law Review,2016,6(1):16.
[16]PELT T I V,HUNTINGTON H P,ROMANENKO O V,et al.The missing middle:central Arctic Ocean gaps in fishery research and science coordination[J].Marine Policy,2017,85:85.
[17]杰克·戈德史密斯,埃里克·波斯纳.国际法的局限性[M].龚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1.
[18]WEIDEMANN L.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Arctic marine environment: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high sea fisheries[M].Cham:Springer,2014:172-173.
[19]夏立平.北極环境变化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131.
[20]唐建业.北冰洋公海生物资源养护:沿海五国主张的法律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6,24(1):99.
[21]韩立新,王大鹏.中国在北极的国际海洋法律下的权利分析[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23(3):99.
[22]魏德才.公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变革的国际法考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54-155.
[23]LIU N Y,BROOKS C M.The future of governing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 the polar regions[M]//LIU N Y,BROOKS C M,QIN T B.Governing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in the Polar Regions.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9:228.
[24]KIM Y H,YOUNG O R,CORELL R W,et al.Overview:Arctic 2030 and beyond—pathways to the future[C]//CORELL R W,KIM J D,KIM Y H,et al.The Arctic in World Affairs:a North Pacific Dialogue on Arctic 2030 and Beyond—Pathways to the Future.Busan and Honolulu: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and East-West Center,2018:21.
[25]肖洋.北极科学合作:制度歧视与垄断生成[J].国际论坛,2019,21(1):105.
[26]魏德才.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国际规则变动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9:35.
[27]贾桂德,尹文强.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一些重要动向[M]//高之国,贾宇.海洋法动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