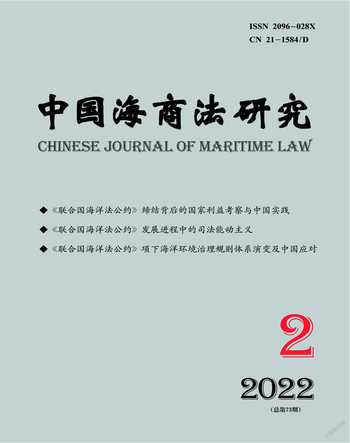《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背后的国家利益考察与中国实践
2022-07-05白佳玉
摘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结,是国际海洋法規则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缔约国提交的提案中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其提案的背后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其谈判过程中蕴含着对谈判尖锐问题的妥协、平衡与调和。中国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结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提案的背后显示出中国所秉持的“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当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维护的利益呈现出由国家利益向全人类共同利益演进的趋势。中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坚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努力成为基于国际法的国际海洋秩序的倡导者、建设者、贡献者,在气候变化共同应对、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公海生物多样性养护等与全人类共同利益联系密切的海洋法问题上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家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2)02-0003-11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hinas practic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AI Jia-yu
(School of Law,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The conclu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rules. During the Third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statements proposed by states parties were not aimless. Behind these proposals i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contains the compromise, balance and reconcili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contracting states to the sharp issues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clusion of UNCLOS and shows its consistent adherence to uphold justice and pursue shared interests. At present, the interests maintained by UNCLOS manifest a trend of evolution from national interests to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 In this Anthropocene era, China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ased 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tively strives to be an advocate, builder and contributor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based maritime order of the maritime community, and provides a “Chinese plan” on law of the sea issu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 such as the joint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seabed region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 se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 words:UNCLO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mankind; Chinas practice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的通过,是海洋法的重要里程碑。从此,国际社会拥有了一套相对全面的国际海洋法律规则体系。《公约》不仅对领海、专属经济区等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制度作出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规定,也对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简称“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域制度作出了一定的安排。事实上,《公约》是缔约国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相互妥协的结果。考虑到《公约》广泛的缔约国数量以及条款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其如何让如此众多的缔约国就诸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国家利益在各国提案的背后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通过对国家利益博弈和妥协的考察,笔者回顾了《公约》谈判期间利益博弈局面的形成,总结了影响《公约》达成妥协的尖锐问题,并分析了中国的参与。针对《公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解决新问题的不足和挑战,探讨了中国建设基于国际法的国际海洋秩序之角色与路径。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一、谈判过程中国家利益博弈局面的形成
國家利益包括生存、发展和荣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国家海洋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家利益的一切内涵,其外在表现为岛屿主权、海域及其中资源的主权、主权权利与相应的管辖权以及海上交通安全等,这些都与国家生存、发展和荣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产生联系。事实上,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缔约国的提案通常代表着以美苏英为代表的海洋大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以及包括77国集团成员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诉求。这些国家利益的交织导致了谈判过程中国家利益博弈局面的形成。
(一)国家主权、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内问题
1.领海
与领海制度相关的谈判焦点为领海宽度的问题,这也是联合国第二次海洋法会议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之一。其争议焦点在于,一些海洋大国主张窄领海制度以维护更大海域的海洋自由;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宽领海制度以扩大海域主权范围窄领海主张系指拥有不超过12海里领海宽度的领海主张,宽领海主张系指拥有超过12海里领海宽度的领海主张。虽然200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可使得沿海国获得超过10 000平方海里的海洋领土,但过宽的领海在使其获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不便,即本国船舶(含军舰)在其他沿海国相应水域航行时,受到其他沿海国基于无害通过制度的航行限制的几率远大于主张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宽度下的限制几率。有鉴于此,美英日三国主张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宽度参见UN Doc. A/CONF.62/C.2/L.3,3 July 1974。苏联考虑到过宽的领海将使其无法直接进入大西洋,从而减弱军事反应的灵活性,[2]227故而亦主张12海里的领海宽度参见UN Doc. A/CONF.62/C.2/L.26,29 July 1974。据此可知,谈判过程中上述国家基于军事航行自由以及商船航行自由等绝对航行自由的海洋战略利益,[3]69从而形成海洋大国有关窄领海宽度的主张。澳大利亚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继续巩固和加强二战后与美国建立的同盟关系,维护海上运输安全。澳大利亚虽然不属于海洋大国行列,但作为美国的盟友,同时又依赖其海军和海运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故而支持12海里的领海宽度。[2]227
肯尼亚虽然重视领海收益,但因其同时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故而只支持12海里领海宽度。智利则主张200海里领海宽度参见UN Doc. A/CONF.62/L.4,26 July 1974。这一主张可使得智利获得更为可观的海洋权益,因为相比较肯尼亚主张而言,此主张将使智利在200海里内海域的主权控制更为彻底。
2.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与专属经济区制度相关的谈判焦点为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开发问题。其争议焦点在于,以美苏英为代表的海洋大国既支持沿海国于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专属管辖权,也支持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开发优惠权(即在存有剩余渔获量的前提下,内陆国或其他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历史性捕鱼权的国家,在不损害鱼类资源繁殖的情况下可捕捞该区域内的渔获物)参见UN Doc. A/CONF.62/C.2/L.47,8 August 1974。,而发展中国家则只支持沿海国的专属管辖权。具体而言,美苏英等海洋大国由于拥有在自身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能力,因此支持沿海国于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专属管辖权,并且基于其远洋捕鱼船队的强大实力,其亦支持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开发优惠权。这种开发优惠权实质上为海洋大国进入他国沿海海域捕鱼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参见UN Doc. A/CONF.62/C.2/L.38,5 August 1974。而以智利、肯尼亚、牙买加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远洋捕鱼能力不足,因此只支持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专属管辖权参见UN Doc. A/CONF.62/C.2/L.35,1 August 1974;UN Doc. A/CONF.62/C.2/L.82,26 August 1974。
与大陆架制度相关的谈判焦点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的划定标准问题。其争议焦点在于,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优先考虑距离领海基线200海里标准,而不具有相关区域石油开发优势的国家倾向于选择200米等深线/距领海基线40海里标准或者大陆架边缘标准。具体而言,印度尼西亚参见UN Doc. A/CONF.62/C.2/L.42/Rev.1,13 August 1974。
、美国参见UN Doc. A/CONF.62/C.2/L.47,8 August 1974。主张适用距离领海基线200海里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标准。究其原因,这些国家作为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在200海里标准下更容易发展石油生产和出口业务,以满足其石油生产和出售的需要。罗马尼亚等国家主张200米等深线/距领海基线40海里标准,则是因为其在相关区域内的石油开采不具优势。[2]117
3.国际航行海峡
有关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谈判焦点为使用国在沿岸国领海海峡内的航行权问题。争议焦点在于,海洋大国倾向于主张绝对的航行自由,而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排除他国军舰在领海海峡的航行自由。具体而言,美英日出于海上贸易需求和海军力量部署需求而强调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内的航行自由参见UN Doc. A/CONF.62/C.2/L.3,3 July 1974。苏联则由于其军事战略部署中重要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都被对立国家所控制,从而需要通过支持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内的航行自由以满足其军事战略部署的需求参见UN Doc. A/CONF.62/C.2/L.11,17 July 1974。而对于智利与印度尼西亚而言,考虑到海峡邻接本国领土,外国船舶的自由通行可能对本土安全带来一定的潜在威胁,当发生军事威胁的情况时通常自身难以良好应对,故而支持无害通过制度以期减少因军舰的自由航行带来的潜在安全问题参见UN Doc. A/CONF.62/C.2/L.49,9 August 1974。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4.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问题
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环境管辖权的谈判焦点为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权问题。其争议焦点在于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倾向于制定国内法律与政策并执行,而海洋大国则倾向于制定国际统一的标准并由船旗国执行。具体而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肯尼亚参见UN Doc. A/CONF.62/C.3/L.2,23 July 1974。以及加拿大参见UN Doc. A/CONF.62/C.3/L.6,31 July 1974。等发达国家强调沿海国在国家管辖范围内有权根据本国的环境政策,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而美国和苏联等海洋大国则认为,应当适用国际统一的防污标准并赋予船旗国执行权参见UN Doc. A/CONF.62/C.3/L.4,23 July 1974。
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的谈判焦点表现为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加以一定的管制,而海洋大国则主张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科学研究自由。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主张沿海国有专属权利进行和管理科学研究,并且在沿海国主权和管辖区域内的科学研究在未得到该国明示同意前不得进行参见UN Doc. A/CONF.62/C.3/L.13,22 August 1974。而苏联等海洋大国则反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坚持各国可自由从事与勘探和开发区域内生物和矿物资源无关的科学研究工作。[4]480
(二)权利和管辖权未予明确归属的问题
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问题是权利和管辖权未予明确归属在《公约》拟定的海域制度中的主要体现。《公约》在扩大沿海国的管辖权和缩小公海自由间调整,于确立两种不同管辖海域制度的过程中留下了余地和空间,剩余权利问题由此而来。尤其是在专属经济区这一相对较新的海域制度的有关规定中,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专属管辖权与公海自由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划分自始就不十分确定。[5]由于专属经济区既非由沿海国完全控制,也不属于完全具备公共属性的公海,因而权利归属并不明确。对此,《公约》第59条给出了解决权利归属不明问题的方法,专门要求有关国家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虑及所涉利益于有关各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处理彼此利益关系,解决纠纷。为促成该条款,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有关集团和国家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在1975年的第三期会议上,现《公约》第59条《公约》第59条(解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的归属的冲突的基础)规定:“在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何其他一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的文本的前身首次出现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提交的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草案中。
会议上达成的《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第47条1975年《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第47条第3款规定:“如果本公约没有将专属经济区内权利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并且沿海国与任何其他一国或数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则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所有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创设了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归属冲突的解决方案,基本采纳了77国集团的提议参见UN Doc. A/CONF.62/WP.8/PartⅡ,7 May 1975。此后,这一条款的内容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在1976年的第四期会议上,新加坡代表认为“若公约明确地将唯一的资源管辖权赋予了沿海国,则该条款(此处的第三款与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达成的《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第47条第3款内容一致,笔者按)便是不必要的”,然而会议最终没有采纳其意见,会议达成的《订正的单一协商案文》不仅没有删除第3款,而且将其作为独立的第47条,其简略标题为“解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的归属的冲突的基础”参见UN Doc. A/CONF.62/WP.8/Rev.1/PartⅡ,6 May 1976。,这一标题沿用至今。1976年第五期会议达成的《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将其重新编号为第59条参见UN Doc. A/CONF.62/WP.10,15 July 1977。,并未采纳美国提出的修改意見。美国建议在“公平”后增加一个逗号,并将“意即”替换为“和”。这样的话,冲突解决的基本标准将成为“以公平为基础”,即可以描述成“参照一切有关情况……”。其同样提出了一个简略标题,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冲突的解决”。[6]519《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也未采纳内陆国及地理不利国家集团提出的“以一条新规定替换第47条,即冲突应依据公约在别处规定的争端的强制解决程序而解决”的建议。[6]520在1978年的第七期会议上,秘鲁提出“将‘其他国家的管辖权删除”的建议,乌拉圭则建议删除该条款,会议最终都未予采纳。至此,第59条的规定自1976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四期会议之后,内容上再未发生实质变动。[6]520
(三)国家主权、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外问题
从谈判过程的视角可洞悉,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表现为沿海国就相应海域内的权利向国际社会的一种让步。具体而言,沿海国通常倾向于不断扩张的海洋管辖权,但为了配合编制《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并达到上述条款所述的“公平”,沿海国则将部分前述权利向国际社会作出让步。[7]这种让步的结果是,原本带有主权色彩的主权权利变为“去主权色彩”的剩余权利。至于国家主权、主权权利以及管辖范围外的有关权利,则更加体现“去主权色彩”的效果。下文将针对国际海底开发制度以及公海自由的焦点问题予以梳理。
1.国际海底开发制度
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的谈判焦点为国际海底开发方式的问题。海洋大国倾向于自由且独立地开发“区域”资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选择单一开发制。智利等发展中国家根据“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主张应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管理,即通过“单一开发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机构对“区域”及其资源进行管理并由其勘探开发参见UN Doc. A/CONF.62/C.1/L.7,16 August 1974。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具备“区域”资源勘探与开发的能力,因此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获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因其雄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能力,主张对“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应由具有资金、掌握技术的国家、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进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主要职能限于发放勘探开发执照参见UN Doc. A/CONF.62/C.1/L.6,13 August 1974。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2.公海自由的具体内容
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公海自由的具体内容的谈判焦点为:是否应对所有国家在公海的自由进行适当管制?其争议焦点在于发展中国家主张对公海自由有必要进行适当管制;而海洋大国则认为公海自由应不受限制。因早期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公海自由谈判的提案及文件获取较为困难,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联合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侧面反映了其对该争议焦点的立场。例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勒比海国家认为,对于公海捕鱼应当用适当的条例加以规定;非洲国家也主张“公海内捕鱼必须加以管理”。而美国等海洋大国则在提案中明确强调“公海自由”,坚持尽量保留1958年《公海公约》的各项规定;法国则表明其从未同意对海洋自由的任何限制……除非通过条约或国际习惯法进行限制参见UN Doc. A/CONF.62/C.2/L.40 and Add.1,5 and 28 August 1974。
二、谈判过程中尖锐问题的妥协、平衡与调和解决 海洋大国基于资金、技术以及海军优势,通常倾向于维护相对开放的海域制度;而发展中国家则因其在上述方面的相对弱势,通常主张维护自身力所能及的海域利益,维护相对保守的海域制度。这些国家利益的对立导致了一系列尖锐问题的产生。《公约》最终落地前经历了谈判过程中尖锐问题的妥协、平衡与调和解决。
(一)沿海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与非沿海国航行权的妥协
针对宽领海与窄领海这一领海制度的谈判焦点,《公约》的正式案文通过第3条确定了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的界限为止。《公约》并没有排除沿海国在最大限度内规定不同的领海宽度,即沿海国可在12海里的限度内确定自身领海宽度。美英等海洋大国长期主张3海里的窄领海宽度,乃因其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便于进入他国海岸活动,实现海上霸权;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本国安全,抵制海上霸权,主张符合其利益的宽领海制度。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逐渐独立,主张更大海域主权范围的趋势不可逆,12海里领海宽度成为海洋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妥协的平衡点。[3]67海洋大国为减少其海军和贸易方面的航行自由受到的影响,给予发展中国家主张的宽领海制度一定的妥协,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主权海域一定范围的扩大。
针对专属经济区制度中的谈判焦点,即海洋大国既支持沿海国于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专属管辖权,也支持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开发优惠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只支持沿海国的专属管辖权。《公约》的正式案文支持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提议的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内的专属管辖权。事实上,美国放弃托管区提议、同意专属经济区概念对相关条款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谈判期间,发达海洋大国深明谈判形势的不可逆转,而沿海发展中国家深知发达海洋大国的分量,因此双方达成平衡后的结果,既体现了大国实力的作用,又体现了小国众志成城的力量。[8]
针对大陆架外部界限问题的谈判焦点,《公约》的正式案文采纳了折中的方案,支持沿海国大陆架包括领海以外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直至大陆边外缘的“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大陆边外缘不满200海里的则扩展至200海里的规定。对于超过200海里的大陆边外缘的具体划定方法,《公约》基本接受了爱尔兰方案中的两种方法爱尔兰方案中规定:“如果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边的外缘:(1)以最外缘各定点为基线划定界限,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百分之一;(2)以各定点为基线划定界限,各点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60海里。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公约》对于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并未单独采纳200米等深线/距离领海基线40海里标准、大陆架边缘标准和距離领海基线200海里标准中的其中一种,而是结合海底地理科学中的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原则,对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予以规定。至于《公约》对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具体的规定,既反映了对宽大陆架国家本身地理优势的认可,也反映了对窄大陆架国家的照顾,从而使沿海国可以选择最优的大陆架外部界限。这些规则也充分体现了《公约》对不同地理类型沿海国之间利益的平衡考量。[9]
针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制度中军舰通过问题的谈判焦点,《公约》的正式案文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规定确立了“过境通行制”,并没有采纳海洋大国主张的“自由通行”,而且还规定了海峡沿岸国对构成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领海水域享有主权和管辖权。有必要注意的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过境通行制不完全等同于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因为本质上,实行过境通行制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位于沿岸国领海范围内,这种海峡属于沿岸国的领海水域。《公约》针对这种情况下的海峡,规定了特别的航行制度,以区别于领海。“所有船舶和飞机”在这种海峡内“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因此,军舰和军用飞机也当然享有这种权利,而且海峡沿岸国对这种权利不得加以“阻碍”“防止”或“停止”,这实际体现了对海峡沿岸国主权的限制。
针对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管辖权的谈判焦点,《公约》的正式案文调和了相关利益,允许沿海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外交会议订立法律、规章或者国际标准,但明确了沿海国、船旗国与港口国将按照规定拥有一定的执行权。这平衡了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的权益以及其他国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利益。
针对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中的是否给予沿海国以同意权的谈判焦点,《公约》的正式案文体现出对二者的协调。一方面,《公约》通过设立同意制度对于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给予了比较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公约》通过在同意制度上增加条件,创设默示同意制度,对于开展研究活动主体的利益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0]
(二)利益对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重要性考量下的平衡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如前所述,《公约》谈判期间有关领海、专属经济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等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国家海洋管辖权不断扩张、作为国际公域的公海范围不断收缩的过程。随着《公约》所规制的海洋区域的范围逐渐由国家管辖范围内,再向国家管辖范围外扩展,沿海国对于海洋权利的主权色彩逐渐淡化。这一“色彩”的“浓淡”反映了有关提案背后的国家利益在该提案中的占比。这种“调色”的过程可视为一套谈判思维模型。对于相关“色彩”的解析有赖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而言,以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有关领海制度的谈判为例,鉴于领海制度中沿海国享有主权,主权色彩当然最为浓厚,因此在《公约》谈判过程中,凸显出的主色调为“主权色彩”。由此出现了美英日苏等海洋大国基于军事航行自由以及商船航行自由等绝对的航行自由的海洋战略利益而形成的有关窄领海宽度的主张,以及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基于扩大领海收益而提出的宽领海制度的主张。再如,由于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只享有涉及到专属经济区内的经济利益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主权色彩逐渐淡化,这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有关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归属冲突解决的提案基本获得大会采纳奠定了基础。
针对权利和管辖权未予明确归属的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问题,《公约》第59条采用“公平”措辞以解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的归属冲突,但“公平”一词的解释受到该条款后续表述的约束,即“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那么,如何“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通常认为,鉴于专属经济区功能的实质,即经济利益是主要关切的问题,因此涉及到专属经济区内的经济利益时,此条款将有益于沿海国,而当涉及与《公约》已规定的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航行自由等类似的未明文规定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涉及资源的勘探或开发)时,其他国家的利益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将被着重考虑。[6]520这种解释过程体现出《公约》第59条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即平衡沿海国权利和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以达到公平的结果的目的。据此安排,一部分专属经济区的剩余权利将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产生关联,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体现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并間接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因而,有关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的探讨,为后续有关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和公海自由原则的调和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空间,存在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和公海自由两大原则,其分别构成该海洋空间底土部分(区域)与上覆水域(公海)法律地位和制度的逻辑起点。海洋空间底土部分(区域)与上覆水域(公海)这一法律实践可以追溯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所发布的大陆架公告。不难看出,将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空间区分为底土与上覆水域,其主要目的为进一步挖掘海底资源并保证海洋自由,历史上各国的法律与开发实践均可证明这一点。[11]对于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的方式选择,《公约》的正式案文最终创设了介于单一开发制度与自由且独立地开发“区域”资源之间的平行开发制,以期更好地维护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事实上,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海底资源开发体制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美国提出了平行开发制以打破僵局,而发展中国家认为此提案有利于国际海底机构尽快独立地实施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制度,因此作出了妥协。[12]这一制度认可了申请者实施的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可使其享有对被申请矿区的排他性权利,从而顾及到发达国家所坚持的立场,同时通过设立国际海底管理局,回应了发展中国家有关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下“区域”由国际统一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诉求。
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是否应对所有国家在公海的自由进行适当管制这一谈判焦点,《公约》最终选择对所有国家在公海的自由进行适当限制。一方面,《公约》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管其是沿海国还是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强调了公海自由的普遍性原则;另一方面,《公约》也提出了自由行使中的“适当顾及”原则,强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是海洋大国还是别的国家,在行使公海自由的时候都是互相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优于其他国家享有权利。[]从不同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公海自由适用一定的限制条件,有利于“缩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13]
三、中国促进《公约》缔结的经验总结
在《公约》缔结所反映的国家利益博弈过程中,缔约国就尖锐问题进行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妥协、平衡与调和,最终促成了《公约》的达成。实际上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正式“回归”国际社会之后即参与了《公约》的缔约谈判过程,提出了“中国方案”,为《公约》达成作出了实质贡献。
(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期间的中国主张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12月21日,联大通过决议,决定增加中国为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成员国。自1973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14]中国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多次发言,利用《公约》提供的机会批评指责个别国家在全球海洋秩序中的霸权行径,支持77国集团有关提案,维护77国集团联盟的思想和政治完整性。
针对领海宽度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并没有明确提出支持具体海里的领海宽度,而是提出了划定领海宽度的原则参见柴树藩1974年7月2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上的发言、柯在铄1975年5月2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中第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支持厄瓜多尔提案的发言。针对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开发问题的谈判焦点,首先,中国主张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捕鱼活动属于沿海国的主权范畴,对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的开发,要顾及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的利益参见凌青1974年8月1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中第二委员会关于专属经济区问题的发言。;其次,中国主张要明确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享有主权和对经济区享有专属管辖权,外国渔船只有在沿海国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捕鱼参见张炳熹1975年4月28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中第二委员会关于经济区内渔业问题的发言。针对大陆架外部界限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主张根据“大陆架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原则确定一国的大陆架范围参见郭振西1979年4月20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八期会议中第六协商组会上关于大陆架问题的发言。针对领海海峡航行的谈判焦点,中国认为位于领海范围内的海峡属于沿海国领海主权范围内的一部分参见柴树藩1974年7月2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上的发言。,要求将军舰排除在“无害通过”制度之外参见凌青1974年7月23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中第二委员会关于海峡通行问题的发言、沈志成1975年5月1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中第二委员会“无害通过”小组会议上关于海峡通行问题的发言。针对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环境保护保全的管辖权问题之谈判焦点,中国主张沿海国有权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法律和规章(包括规则和标准)以防止船舶污染参见中国代表1976年8月11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五期会议中第三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关于防止船舶污染问题的发言。针对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则支持沿海国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科学研究享有专属管辖权参见中国代表1976年9月14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五期会议中第三委员会全会上关于科研问题的发言。以及同意权参见罗钰如1974年7月19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中第三委员会关于海洋科学研究问题的发言。的主张。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对于专属经济区内剩余权利的问题,中国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并没有提及,但针对国家主权、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外的问题,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提案。首先,针对国际海底开发方式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支持国际海底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参见柴树藩1974年7月2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上的发言、柯在铄1974年7月17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中第一委员会关于国际制度和机构问题的发言、欧阳楚屏1974年8月16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中第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关于开发条件的发言。,主张国际海底资源必须由国际机构直接进行开发,或者以国际机构完全控制下的其他方式进行开发参见沈韦良1977年6月10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中第一委员会工作组会议上的发言、沈韦良1977年6月28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中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柯在铄1978年4月21日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七期会议中第一协商组会议上的发言。其次,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是否应对各国于公海的自由进行适当管制的谈判焦点,中国主张关于公海的利用不得妨碍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以及在公海捕鱼应有适当管制等。[4]338
通过上述中国的提案情况可见,中国提案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尽管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国际造法会议,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在态度上以及行动上十分积极,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尽管中国暂未对专属经济区内剩余权利的问题提出提案,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在《公约》的原则下对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进行解读,以维护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安全,从法理上支撑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15]在提案内容的背后,体现出了中国所坚持的正确义利观,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惟利是图、斤斤计较。[16]
(二)中国主张背后的义利观
总覽《公约》谈判过程,不难得知,针对《公约》所规定的海域制度,拥有经济、技术与军事优势的海洋大国的提案经常反映出“利益至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国家利益观,坚持零和思维,具有狭隘性、短视性和惟利性的特点。例如坚持领海海峡军舰的无害通过,坚持基于公海自由理念下“区域”资源开发区块的排他权利等。而中国则坚持“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主张摒弃义利对立的二元思维,反对唯利是图,鼓励国家之间的互利和共利,谋求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幸福参见汪琼枝:《坚持正确义利观,应对“逆全球化”思潮》,访问网址:http://edu.people.com.cn/n1/2019/0605/c1006-31120917.html。例如,中国坚定地和77国集团站在一起,考虑到子孙后代,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事实上,党的十九大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扩大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秉持正确义利观,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其内涵不仅阐明了中国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正确义利观的应有之意,[17]也喻示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不同领导集体的正确义利观可能各有重心,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形成一种一脉相承的体系。
(三)中国主张对《公约》缔结的积极贡献
梳理与上述《公约》缔结中尖锐问题有关的中国提案是否被纳入《公约》条款,有助于分析中国在《公约》缔结过程中的积极贡献。
围绕国家主权、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内的有关问题,针对领海宽度的谈判焦点,中国有关适当设置领海宽度的意见被部分采纳进《公约》,其第3条允许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领海宽度;针对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开发问题的谈判焦点,《公约》第56条支持了中国有关专属经济区内捕鱼权应属于沿海国行使主权的范畴的意见,赋予了沿海国在该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的主权权利,这一主权权利自然包括捕鱼权;针对大陆架外部界限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主张的自然延伸原则及该原则下的计算方法被采纳进《公约》第76条;针对专属经济区内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所主张的由沿海国制定环境政策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被部分吸纳进《公约》,其第216条允许包括沿海国在内的有关主体制定相应法律和规章,并允许沿海国在法定条件下执行这些规定。这些被实质吸纳进《公约》的提案,一方面体现着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提案,促进了一些新海洋法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展现出中国积极与其他缔约国合作,参加各协商组讨论,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推进了海洋法立法进程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实现。
围绕国家主权、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外的有关问题,针对国际海底开发方式问题的谈判焦点,中国有关国际海底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的观点反映在了《公约》第136条中;中国对于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由国际机构直接进行或以国际机构完全控制下的方式进行的主张得到了《公约》第153条的部分支持,该条款规定了“区域”内活动由企业部独立进行或由符合条件的主体与管理局协作进行的平行开发制。针对“区域”内的科学研究问题的谈判焦点,《公约》第143条规定管理局可进行有关“区域”及其资源的海洋科学研究,并可为此目的订立合同。这一规定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科学研究应受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管理的中国提案相吻合。这些被采纳或部分采纳的中国提案,体现着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海洋法制度建立的实践态度。事实上,不论是针对国际海底开发方式问题,还是“区域”内的科学研究问题,中国相关提案所反映的内容都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在“区域”的具体表现,体现出中国坚持“区域”在和平使用的前提下由全人类所有、由全人类使用、由全人类共享的理念。
四、从国家利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演进下的《公约》发展趋势与中国机遇
经过多年谈判,《公约》作为首部专门针对海洋的综合性国际条约,终于得以通过。《公约》通过建立法律秩序来保障人类在海洋中的利益,为海洋综合治理提供了基石。有必要指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能够触及的海洋范围不断扩大,气候变化共同应对、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公海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与人类命运的联系愈发密切,呈现出一种从国家利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演进下的《公约》发展基调。《公约》作为“二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重建海洋秩序的妥协产物,受自身有效性不足的限制,无法完全解决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因此存在完善的空间。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一)海洋公域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
海洋公域的许多新生问题都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首先,在海洋公域生物多样性养护领域,为有效实现《公约》规定的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目标,联合国于2015年5月发布决议,要求各国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鉴于生物多样性养护被《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是全人类共同关注事项,而联合国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的需求,因此缔约国参与造法活动显然应当出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目的。有鉴于此,以BBNJ为代表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利用国际法律规则发展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良好融入的重要场所。其次,在海洋公域资源可持续开发领域,随着《公约》被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所接受,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逐渐发展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具体涵盖共同共有、共同管理、共同参与和共同获益这四大特征。具有全球海洋公域性质的“区域”法律地位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切入点。[18]最后,在气候变化共同应对领域,鉴于同样被公认为是全人类共同关注事项的气候变化共同应对问题能够引发海洋的剧烈变化,尤其是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等,有理由认为,气候变化共同应对问题作为全球性环境问题,涉及全人类的海洋环境利益。这些新生问题的解决为《公约》的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提供了机遇。
(二)《公约》相关附件谈判与实施趋势
为了进一步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目标,联合国决定根据《公约》的规定就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BBNJ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需充分考虑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世界各国海洋利益之间以及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利用之间的协调关系。截至2022年3月,BBNJ已经经历了四轮政府间谈判,但目前谈判的结果仍不足以推动该条约越过终点线参见Ocean Care:UN High Seas Treaty:Progress but not There yet,访问网址:https://www.oceancare.org/en/un-high-seas-treaty-progress-but-not-there-yet。各方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尚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重大挑战。例如,“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之争,环境影响评估是否应该“国际化”之争,BBNJ争端解决机制是否应该“比照适用”《公约》第十五部分或《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第八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之争,以及“一揽子交易”中的相關要素在谈判中面临不均衡发展和难以同步推进的挑战。各方在谈判中能否化解这些挑战,将直接决定BBNJ国际协定能否成功达成。[19]
在海洋公域资源可持续开发领域,“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承包者在勘探开发“区域”资源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实现“区域”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面对“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开发阶段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为了确保“区域”海洋环境免受开发活动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国际海底管理局正在抓紧制定“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在2017年8月第23届会议上,国际海底管理局审议并公布了《“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草案》。2021年6月25日,瑙鲁正式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商业开采,触发了1994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1节第15段的“两年规则”,即要求国际海底管理局尽快通过该草案以促进自申请两年内批准开发的工作计划,但显然这项繁重的工作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存在巨大挑战。
在气候变化共同应对领域,根据《公约》官网的电子资料,早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海洋与海洋法专题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就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共同应对的问题,认为“《公约》强调需要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更显示了海洋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以及控制和调节世界气候包括‘温室效应的影响等方面的重要性,这种作用还受到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承认”参见UN Doc. A/44/461,18 September 1989。2017年联合国大会海洋和海洋法会议产生了主题为“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的秘书长报告,系统梳理了气候变化影响海洋的主要因素、海洋变暖和酸化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气候变化的应对,以及进一步合作及协调的必要性参见UN Doc. A/72/70,6 March 2017。可见,在联合国层面对气候变化下的海洋应对有着长期的关注,意识到了“世界海洋退化状况令人震惊,必须在各方面采取行动,恢复海洋环境的健康和复原力,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保护和保全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地利用其资源”参见UN Doc. A/77/68,28 March 2022。2021年10月15日,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与国防特别委员会启动一项名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否同21世纪的基本目标相适应?”(UNCLOS:Fit for Purpose in the 21st Century?)的质询,就包括气候变化等在内的新问题给履约带来的新挑战等议题召开了10余场听证会。[20]质询所形成的文件认为,《公约》未能预见到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岛礁淹没及领海基线位置改变而给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带来的潜在改变,主张联合国机制和有关机构应发挥更大作用,促进国际海事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对海事活动的影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参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fence Committee:UNCLOS: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访问网址: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5802/ldselect/ldintrel/159/15902.htm。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
(三)《公约》发展趋势下的中国角色和机遇
中国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变迁,逐渐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自“回归”国际社会以来,便带着“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加强国内立法与国际法的互动”的使命感,在制定和实施国内法律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造法特别是对外缔约活动,充分利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平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表达中国主张,通过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了解并定位不同国家的共同需求,推动国际治理规则向法治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参见《国际法与新中国成立70年立法实践》,访问网址:http://www.npc.gov.cn/npc/dzlfxzgcl70nlflc/202108/7e3aaf6b374f428881637ee92ab921f7.shtml。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争做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倡导者、建设者、贡献者,为其提供“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指的便是坚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思维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衡平思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推倒重构,而是要在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有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共处、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21]在海洋领域,则是要在《公约》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造福全人类。中国有必要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当今国际海洋法前沿领域的造法论证与后续的谈判协商及履约进程。
针对各方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尚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重大挑战的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争议的焦点从个体利益转向共同利益,以合作的方式协调和弥合分歧,追求共同利益,[22]促进多边协商中的利益攸关方之间达成共识,进而共同实现BBNJ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针对《“区域”内矿产资源开采规章草案》的生效问题,中国有必要深入参与该草案的后续制定过程,同时增进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密切联系,围绕“区域”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中关乎国家长远利益的重要议题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具体而言,中国有必要统筹考虑“区域”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避免因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方,争取实现二者的平衡。
针对气候变化共同应对问题,中国积极在国际海事组织层面提出了与缓解气候变化有关的提案。作为连续17次当选国际海事组织A类缔约国的中国,正在努力通过共享信息和积极完成污染预防与应对小组委员会工作组的工作为国际海事组织规制黑碳排放的规则进行立法准备。根据2019年第74届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指示和2020年第七届污染预防与应对小组委员会沟通小组的要求,中国开展了与黑碳排放控制相关的研究,并于2021年通过MEPC 76/INF.43、MEPC 76/INF.44、MEPC 76/INF.45三份国际海事组织信息类型提案共享了正在进行的黑碳项目的信息。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3]这些积极的努力与承诺,彰显出中国对海洋事务的关注以及对《公约》发展趋势背景下造法时机的良好把握,体现出中国始终坚守公平正义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体制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倡导并以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五、结语
《公约》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同国家及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协商妥协所达成的一项海洋治理領域的瞩目成果。出于提案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公约》的缔约过程呈现出利益博弈的局面,而其正式案文的生成则体现着缔约国针对各项问题,尤其是针对某些焦点问题的妥协。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始终秉持着“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坚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约》从国家利益向全人类共同利益演进的趋势下,积极争做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倡导者、建设者、贡献者,在气候变化共同应对、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公海生物多样性等与全人类共同利益联系密切的问题上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以《公约》缔约为起点,正在为国际法治作出巨大贡献,着实为联合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中国烙印,影响深远,历久弥新。
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为深入参与国际造法活动,坚决维护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为世界永续的和平发展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0.
[2]SHYAM M.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a predictive model[D].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74.
[3]齐尚才.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1945年以后的航行自由规范[J].国际政治研究,2018,39(1).
[4]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5]周忠海.论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J].政法论坛,2004(5):174.
[6]萨切雅·南丹,沙卜泰·罗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二卷)[M].吕文正,毛彬,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7]白佳玉.《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公平制度体系下的适用争论及其应对[J].当代法学,2021,35(6):145.
[8]吴少杰.专属经济区概念的提出与美国的反应(1970—1983)[J].世界历史,2016(2):52.
[9]张湘兰,田辽.大陆架外部边界规则研究[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23(3):94.
[10]邵津.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研制度[J].法学研究,1995(2):71.
[11]孙书贤.国际海洋法的历史演进和海洋法公约存在的问题及其争议[J].中国法学,1989(2):107.
[12]金永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制度研究[J].社会科学,2006(3):113.
[13]梁源.论公海自由的相对性[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1):83.
[14]邹克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施中的若干新问题[J].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3,11(2):4.
[15]章成.论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法律边界与中国应策[J].学习与实践,2017(10):31.
[16]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N].人民日报,2013-09-10(7).
[17]白佳玉.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法战略[J].政法论坛,2017,35(6):143.
[18]白佳玉,隋佳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域中的国际海洋法治演进与发展[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4):90.
[19]施余兵.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挑战与中国方案——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研究视角[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1):50.
[20]叶强.英国议会质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履行情况[J].世界知识,2022(2):57.
[21]黄惠康.国际海洋法前沿值得关注的十大问题[J].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4(1):6.
[22]薛桂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共识性话语到制度性安排——以BBNJ协定的磋商为契机[J].法学杂志,2021,42(9):61.
[23]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1).212EC8D5-9D81-4019-B1A6-BCA6F5BCA0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