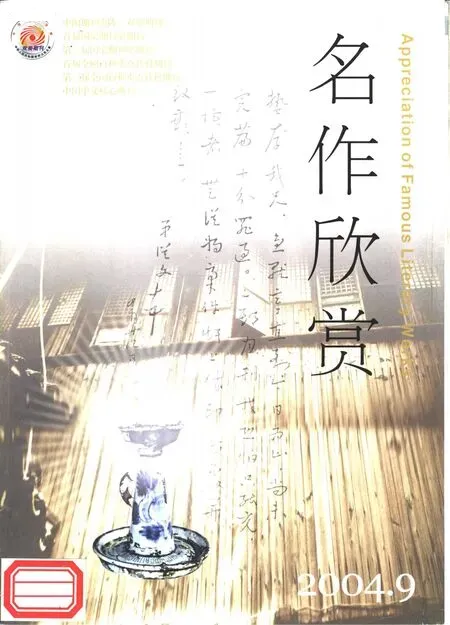李健吾集外佚文考述
2022-07-04戚慧
戚慧
关键词:李健吾 集外文 戏剧 考释
2016年5月,《李健吾文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十一卷囊括了李健吾先生所著的各类作品,可以说较为完整、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他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成果”。在文集之外,还有不少篇什散见于各类报章杂志,值得挖掘整理。笔者近来搜集资料时,在民国时期报刊上辑获李健吾佚文数十篇,均未收录于《李健吾文集》及其他文集,亦为《李健吾作品原刊目录索引》《李健吾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等所失收,是研究李健吾生平事迹、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现将这批佚文披露出来,并略作梳理考释,以期还原历史,裨助于李健吾研究。
一
李健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剧坛健将,擅长改编外国剧本,曾改编过莎士比亚、萨尔度、萧伯纳、席勒、斯里克布、博马舍、费齐等人的剧作。日本占领上海后,英美影片被禁,影业萧条,却促进了话剧的繁荣,加之法国在沦陷时期不像英美成为日本的敌对国,因而推进了法国剧本改编的盛行。1943年至1945年间,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李健吾改编了法国19世纪著名剧作家萨尔度的四部剧本,即《菲尔南德》《菲多拉》《赛拉菲娜》和《托斯卡》,并分别为它们取了中文名《花信风》《喜相逢》《风流债》和《金小玉》。他说:“我和萨尔度遇在一起,也只是时间、环境和机会的巧合,为了争取观众,为了情节容易吸纳观众,为了企图尝试萨尔度在剧院造成的营业记录,萨尔度便由朋友建议,由我接受下来这份礼物。……我不是萨尔度的信徒,当然不够资格有所是非,因为即使贬斥,必须曾经焚香礼拜,分量才能够正确。”李健吾深谙萨尔度艺术的得失,“只借重原著的骨骼,完全以中国的风土,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氛围和意境”,在改编中加深了人生忧患的蕴涵,使作品成为沦陷区现实巧妙而真切的隐喻性写照,以期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在创作和改编戏剧的同时,李健吾还为自己的剧作撰写附告(言、记、志)、序、前言、跋、后记等类文字,其中既有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亦可见他的戏剧观点。《〈花信风〉之罪言》《〈花信风〉——恋爱悲喜剧》《艺术成长在委曲中》《论历史和现时(致俞苹)》《〈喜临门〉的人物及其他》等文皆属于这一类文字,为李健吾的戏剧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
1943年2月3日、4日,李健吾相继在《海报》上发表了《〈花信风〉上之罪言》和《〈花信风〉——恋爱悲喜剧》。同年2月5日起,他改编的四幕悲喜剧《花信风》在上海金都大戏院上演,由吴仞之导演,演员有翟宇、沙莉、蓝兰、林彬、沈浩、梅真等人。这两篇文章均写于《花信风》演出前,当是为宣传演出而作的。在《〈花信风〉之罪言》中,他引经据典说明剧名的由来,带有鸳鸯蝴蝶派的气息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出戏不仅描写上流社会的黑暗,也揭露下流社会的罪恶。文末,他坦言《花信风》虽是一出三角恋爱的小戏,若干地方有着无巧不成书的毛病,而他也意识到这些“情节未免过于无巧不成书,失却了一切人性的真实的根据”(《〈花信风〉跋》),因而写下此文作为改编者的“罪言”。而《〈花信风〉——恋爱悲喜剧》则主要介绍了这出戏的剧情及人物形象。演出前,导演吴仞之撰写了《担心与放心——〈花信风〉导演者言》,他说“一出戏的演出,‘担心的应该不止导演一个。仅凭导演,并换不到完全的‘放心”,“担心,也在戏的本身。放心,也在戏的本身”,而导演要对得起编剧、演员与舞台工作者。《花信风》上演之前,编剧李健吾和导演吴仞之相继撰文表达“罪言”及“担心与放心”,足见他们对这部戏的重视。
1943年6月4日,《喜相逢》在金都大戏院上演,由上海联艺剧团演出,这是李健吾与吴仞之的第三度合作。演出前,李健吾撰写了《艺术成长在委曲中》(《海报》1943年6月3日第4版)。文中,他说明《喜相逢》和原作大有出入,对于剧本修改这一工作,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感觉自己和自己的制作一无是处。因而也就越发不敢冒昧从事”。待完全脱稿后,永远在等待指正,也“永远给自己保留一个最后的壁垒”。他说“《喜相逢》和我早年的《这不过是春天》相仿,比较起来,更其多了冲突和不幸。调子是单纯的。然而舞台的成分却浓厚了许多”,“富于‘哲理的‘文艺的气息”的语言是自己的。他曾考虑将《喜相逢》处理成“惊奇剧”或“侦探戏”,但观点在不断改变,因而感叹“艺术在委曲之中逐渐成长。所谓委曲,是一切;所谓一切,用一个时髦的词儿罢,就算是耳目的濡染”,“戏是要上的,幕是要揭的,但是最重的戏却在舞台以外,眼睛不敢看,心灵不敢接触的角落。《喜相逢》是一出悲剧,因为它上演的命运是悲剧的”。对于《喜相逢》的演出,李健吾的内心有些复杂,改编时思考了很多。《喜相逢》演出前曾在《申报》上打出广告语:“以《花信风》的盛况来证明《喜相逢》的成就。”珠玉在前,对于改编者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李健吾向来对自己的改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人属于一种有遗憾的动物,喜欢做的不一定能够做,时间不允许,环境不允许,尤其是,说也可怜,机会不允许。……我要写的戏永远没有写,我要改编的戏永远没有改编”,改编并非本志,但对待每个剧本,他都是努力经营,使之尽可能完美。这不仅是演出的需要,亦是一位艺术家的职责与良心。
1946年5月15日,李健吾在《世界晨报》上读到俞苹所作《影剧短评:金小玉》一文,随即写下《论历史和现时(致俞苹)》,5月17日发表在《世界晨报》第3版。早在1944年9月,《金小玉》便由苦干剧团在上海巴黎大戏院上演,黄佐临担任导演,石挥、丹尼任男、女主角,李健吾饰总参议一角,演出长达三个月,轰动了整个上海。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10日,《金小玉》再次演出。俞苹的《影剧短评:金小玉》正是在观看这次演出之后而作,他认为:“李健吾先生对于北伐时期几乎有了一种癖爱,同时几乎成了他对现实的挡箭牌,他爱把他的精神世界和现实拉开一条距离,在这所府第里他可以赏玩他的明珠珍宝。法国沙度(笔者注:即萨尔度)的剧本也躲不开这个命运,他不但给他换了衣冠并且也换了谈吐,换了一片古老中国的环境。他这改编的才能使我们惊叹,心折;但他这种在四面围墙中玩弄珠玉的写作态度我们却不能满足,并且也为他的才能惋惜。”接着,他评论黄佐临导演的《金小玉》“似乎忽略了这出戏所特有的‘卖弄(MELO)的精神,他排这个戏太‘规矩,或者说太拘谨”,整体上有“拘泥之感”。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理论中最为复杂的关系之一,李健吾曾多次撰文讨论现实主义。在《论历史和现时》中,他首先回应俞苹所说的“爱把他的精神世界和现实拉开一条距离,在这所府第里他可以赏玩他的明珠珍宝”,接着对历史、现实和现时进行阐述,他认为“现实建筑在现时之上,但是含有理想,并不就是现时”,“历史同样有现实,现时同样有现实,因为历史和现时仅仅是过去和现在之分,本质原来没有两样”。他以福楼拜的创作为例,既写现实小说《包法利夫人》,也写历史小说《萨朗宝》。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小说的一大缺陷在于时间的距离,虽然它努力把逼近理想的现实给我们,但读者缺乏故纸堆的经验,自然感到相当的隔膜,因而“历史小说往往不及现时小说那样单刀直入,那样切近读者的生命”,更不像“现时小说根据的是读者的活生生的经验”,容易传达作者理想,对读者产生感染作用。接着又以郭沫若和茅盾的创作为例,前者用熟习的历史做材料,后者则用熟习的现时做材料,路虽不同,方向却是一个,都是为现实服务。通过这些例子,李健吾解释将《金小玉》的改编背景安排在北伐时期,也是出于现实和自身的安全考虑。因《金小玉》的上演,被指影射日伪迫害革命党人,他被日本宪兵队拘捕,饱受酷刑之苦k。5月19日,俞苹发表《谢李健吾先生》进行回应,他称文中所指的“现实”是“今日我们血淋淋,黑甸甸的生活”,也是李健吾所谓的“现时”,希望李健吾在“遭受着太多的苦难与迫害,生活如在梦魇之中”的今日,“和现时拥抱得更緊一些”,用他锋利的笔刺向那些无耻的豺狼。俞苹承认自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金小玉》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认为《金小玉》“是一出佳构剧,它以紧张的情节见长。但从这情节里我们未能见到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历史的真实,退一步来讲,范永立在如此血淋(淋)的现实教训之下应该有所觉醒,这觉醒正是对观众的一个启示(所谓它的现实意义),但在这里也未能令人感受到这一点”。实际上,1945年4月28日,李健吾曾将《金小玉》进一步改编为《不夜天》,由中电剧团在重庆银社公演,把背景北伐时期的北京改为抗战时期的北平,将不问政治的考古学家范永立改成重庆方面派遣营救被捕的莫同。可见,囿于政治环境的考虑,李健吾对《金小玉》背景的选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了灵活的改编策略。《金小玉》在上海沦陷区取得了成功,《不夜天》在重庆上演却成绩平平,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众多,在此不作赘述。文末,李健吾所说当“另文检讨现实主义”,当是指收入其《咀华二集》“附录”部分的专门谈现实主义的《关于现实》一文。
1944年5月27日和6月10日,昆明版《扫荡报·戏剧电影》第7期和第9期刊登署名刘西渭的两篇文章,即《〈喜临门〉的人物及其他》和《〈喜临门〉后记》。从标题来看,这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喜临门》的,但其内容却不曾提及《喜临门》,而是评论李健吾于1936年发表并出版的三幕喜剧《以身作则》,《〈喜临门〉后记》更是与《〈以身作则〉后记》内容一致,显然这个刘西渭即李健吾。《扫荡报·戏剧电影》第9期上开辟了“《喜临门》述评专页”,同时刊登了白梅的《从〈喜临门〉公演说起》、凌鹤的《试评〈喜临门〉演出》和范启新的《罪状的自供》等文。据此可知,《以身作则》于1944年6月7日曾化名《喜临门》在昆明上演。笔者推测李健吾很有可能不知《以身作则》剧名修改一事,而发表在《扫荡报》上的这两篇文章大概是编者在收到文章后为与即将上演的《喜临门》保持一致而做出的修改。《〈喜临门〉的人物及其他》一文开篇言明“喜剧是作者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加以无情的讽刺嘲弄,给予读者或观众感情上的刺激”,使人发笑的同时还会让人深思,而“李健吾先生以他涉世深微的体验,锐敏精细的观察,怀着对人类热烈的情爱,他把人类的弱点,各样的性格给予细微的分析和揭露,叫作品建立于一个人性的基础上”,并逐一介绍了他笔下的九位可爱又可怜的人物,他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熟人。而这部剧的“对话尤为漂亮,别是一种风格,正像李先生其他剧作一样,初看像是生硬不上口,但念不上两遍,便觉流利隽朗如石上泻下的泉水,那么有节奏有韵律,越念越有味,而嘲讽的地方幽默俏皮,常觉得意在言外,话后还有话,逗人笑,引人深思,如果说丁西林先生的喜剧讽刺像胡椒滋味,那末李先生的喜剧讽刺便是辣子,胡椒滋味自然美,然而辣子不更够味?”点评可谓精彩,妙语连珠。文末说“读了《以身作则》会叫人想起十七世纪法国莫里哀的剧作在中国”,这与李健吾在《关于〈以身作则〉事》一文中所说“《以身作则》借取《伪君子》《夫人学堂》和《悭吝人》的形式”,“属于莫里哀的作风”,“属于莫里哀的喜剧的范围”等语一致。1944年6月8日,导演范启新在《喜临门》演出后台作《罪状的自供》,说明“我之所以爱,之所以导《喜临门》的原因很简单:这是国人创作的最好的一个多幕喜剧,虽然有人说作者是仿莫里哀”,被认为不成熟,但他认为“这个戏在结构及剧情和人物的创造上,却已‘成型,合乎规矩”,“我更其喜爱的是作者的感情的真挚,那表现于作品中的明显的爱与憎”,“我咀嚼于作者敏锐的观察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及那特有的风格里,所以我百读此剧不厌”,加之“这戏景少人少花费少,正适合穷团体的要求,所以我又排演了《喜临门》”。对于《喜临门》的演出效果,范启新称“因为个人的和团体的方便与过失,这次《喜临门》的演出,却使作者受冤不少!我与作者虽无一面之缘,但是身同己受”,遂撰此文向李健吾请罪。
二
李健吾在戏剧创作的同时,写有大量评论。他的评论范围广泛,涉及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绘画等领域,重直觉感悟,属于印象式批评,意在抒发审美感受,有着一种随笔体的自由风格。《黑雾》《李维斯(Sincl air Lewis)》《孔雀东南飞》《〈委曲求全〉跋》《读〈少年游〉》《牧师·狗·瞎子》《看司徒喬的画》和《张一尊之画》等佚文当属此类。
李健吾为《华北日报》副刊撰稿多篇,《黑雾》《李维斯(Sinclair Lewis)》《孔雀东南飞》这三篇书评均刊于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委曲求全〉跋》则发表在“副叶”上。在《黑雾》(北平《华北日报·华北日报副刊》1931年1月14日第361号)中,他批评张资平的长篇小说《红雾》的“趣味是恶化的,技术是肤浅的”,写了一个时髦女性的堕落过程,作者对这类女性是同情的,因而没有办法往深处刻画,直言张资平不是写小说,而是做广告,态度是不忠诚的,缺乏真挚和道德心,“已然不是初年的作者”,“他成了一个速成小说家:写着人性的卑鄙的部分,为了满足人性的卑鄙的部分”。篇末认为小说虽名为《红雾》,实描写的是窒息的黑色。对于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李健吾认为是“作者另给了一种想象的解释”,跳出爱情的浪漫的悲剧,演变成母亲的悲剧,围绕母爱与情爱的冲突,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同时也指出作者写剧技术的幼稚,如对话与人物的身份不谐和。整体上,李健吾对此剧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对母亲形象的刻画,改变了传统的无理取闹的老太太的形象,成为悲剧的宏丽的主角,凸显了人性的挣扎。《李维斯(Sinclair Lewis)》(北平《华北日报·华北日报副刊》1931年1月26日第373期)一文主要从人物形象、情节、写作手法、小说主旨等方面评价了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李维斯的代表作《巴比德》(即刘易斯的《巴比特》)。李健吾认为巴比德是美国的中常人物的代表,是一个立体的、有灵魂的人物,是“近代的人性的模型”,采用写实主义手法进行解剖,揭示了小说的主旨“幸福在遵循一己的真正的动机,不在依仿群众的虚浮的习惯”。《巴比德》采用新颖的材料,每一章都充满了活泼的讽刺,读者可以畅适阅读。文末,他注明此文写作的缘由:“先艾命做此文,没有写完,忽然他告诉我《文学周刊》奉谕停办。我也就懒于把文章好好地结束。本意是要拿塞可瑞等和李维斯比较,索性不谈下去了。慧修夫子大量,想能恕我潦草。”《委曲求全》乃王文显在美国耶鲁大学期间用英文创作的戏剧,1932年7月,李健吾将此剧翻译成中文,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委曲求全〉跋》(《华北日报·副叶》1932年9月14日第64期)并未收入《委曲求全》中文本。文中,李健吾从中国现实谈起,他认为委曲求全是“我们今日的道德律”,喜剧便从这样的环境中产生。而王文显作为“建筑在这样深切的观察上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同他的工作都值得我们特殊的注意。这里每句话有每句话的意义,每场戏有每场戏的功效。这不是敷衍,是工作。而且这是我们的自己人,更是译者多年的先生,所以译者敢于介绍出来,做我们作家的榜样”。据李健吾所言,他翻译此剧的初衷是为了排演,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搁置。直至1935年2月,由他导演的《委曲求全》才在北平协和礼堂上演。
《读〈少年游〉》(上海《立报·言林》1945年10月12日)和《牧师·狗·瞎子》(上海《远风》1947年7月1日第4期,署名刘西渭)这两篇为剧评。《少年游》乃吴祖光在成都期间创作的三幕剧,是对其少年时代的一个追忆与怀念。这部剧使李健吾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及他没有创作完成的《草莽》。文中,李健吾认为吴祖光的这出三幕戏,“毕业前后,不出北平古城,形式怎样束紧了这奔放的内容!所谓‘游,直到闭幕之后才开始,然而我多愿意和这等男女人物在一起逃难,挨饿,害病,被扣,逃命呀!”“吴祖光给我一出谨严的戏,我要的乃是史诗。我唯一的满足是他让我重游我的少年时代的故乡,古老的北平……”李健吾希望有一天能写出自己的《少年游》,“不伟大,然而是我短短的生命之中最有意义的孤独的痕迹”。无疑,李健吾此处将“自我”作为他批评的参照与阐释的标准,寻求批评者与作者之间人生经验的遇合。《牧师·狗·瞎子》是一篇关于梅特林克戏剧《瞎子》(今译《盲人》)的解读,李健吾指出这是一出象征的短剧,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看法,外国人认为“一群瞎子好比是‘人世,在愚昧孤独之中希望有人搭救。但是‘教会老朽了,‘新生太小了,新旧联系不起来,于是‘人世彷徨不知所措了”。作为中国人的李健吾读了这出短剧想到的是眼前的现实,他认为“宗教在这里没有什么力量。但是,我相信每个中国人正如那些瞎子,无时不在盼望一位‘明眼人把他领到光明平安的道路”,善堂的那条狗是“我们的习性,享受和一切物质的存在”,只能把我们引向死亡,因此要摒弃它。这篇解读可谓既言简意赅又具阐发性。
《看司徒乔的画》(上海《世界晨报》1946年6月8日第3版)与《张一尊之画》(上海《铁报》1946年9月17日第3版)是两篇画评。1946年,画家司徒乔抱病赴粤桂湘鄂豫五省画灾情写生,历时四个月,走过十多个县,画了《义民图》《水图》《荒村》等近百幅作品,先后在南京、上海举办了灾情画展。6月7日至10日,在南京国际联欢社展出,7月1日至14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画展,广获好评,这些血泪交织的画作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冲击。李健吾赞赏司徒乔用他的画笔描绘出时代的苦难,“他寻找绘画的灵魂,不从过去的传统,而是从一个更结实的传统,那活着受罪的人们的缄默的面貌。他以颜色和线条来为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服务。他的伟大的用意为他换来艺术最高的境界,不是空洞的学院派的理想,但是深深获有一切伟大艺术生成的根据”,他“所画的流民的种种病苦的形象,是一种控诉,也就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良心的控诉”。这些画作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试图以无声的语言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的灵魂,并对现实做忠实的报道。司徒乔一直被看作“是一位风景画家,长于捕捉光影和运用彩色”,而这次抗战灾区画展让人看到了他另外的一面,正如李健吾所说:“他扩张自己的世界,正是扩张艺术的领域。”李健吾曾言自己“不懂得画”,却以作家生动细腻的文学笔触写下了观画感受。他还为张一尊画展撰写了《湖南张一尊先生》和《张一尊之画》。张一尊(1902—1972)系湖南吉首人,曾名铁湘、也军,号太虚樵者,室称一心草堂。年轻时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军,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少将。自幼嗜画,尤爱画马,抗战胜利后获准退役,投身繪画,在南京、上海、杭州、重庆、武汉、桂林长沙等地举办过展览,与徐悲鸿、沈逸千、梁鼎铭一起被誉为中国画马四杰,代表作有《百骏图》《八骏图》《三奔图》等。1946年9月15日至21日,张一尊在上海威海卫路同孚路口新生活俱乐部举行山水画展,展出画作一百余幅。《湖南张一尊先生》一文已被披露,且多为研究者所引用,详细介绍了张一尊的生平和学画的经历,李健吾称赞他“不卖弄”“有艺术的良心”。《张一尊之画》则对其人其画做了简短扼要的介绍,内容如下:“太虚樵者张一尊先生,湖南人,过了几十年戎马生活,治军之暇,一直作画,曾在桂林开过画展,在大后方被誉为现代画马四杰之一。最近来到上海,接受友好的怂恿,举行近作个展,从月之十五日开始,地点在新生活俱乐部二楼。一位军人作画,不唯不俗,而且直追宋元,笔是笔,墨是墨,的确值得海上艺林结识。他第一次来上海,一切陌生,我这个外行人给他做介绍,分外觉得光荣。”除了撰文推介外,李健吾还推荐老友熊佛西等人前往观画。
三
抗战时期,李健吾还写有不少杂文,或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或抒发忧国忧民的愤慨,或怒斥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或倾诉孤岛生活的压抑与痛苦,这些都是他在战争年代真实的内心写照。《山西的症结》和《空当》这两篇杂文,同样关注着现实。
《山西的症结》发表在汉口《大时代》1937年12月21日第1期,署名刘西渭,此文是他在阅读上海《大公报》上刊登的徐盈的《请看今日之山西》一文后所作的。《请看今日之山西》是在日本大举侵略山西之际,徐盈以记者身份前往山西实地考察后写下的一篇战地通讯,引起李健吾“无限的牢骚”。李健吾认为徐盈的文章是“实录”,披露的是山西的“病象”,他自己的这篇文章则“鞭辟近里,推论病原”。“病原”有四点:一是山西人不大相信外省人,导致山西文化比较落后,虽然交通方便,但学生外出求学不多,以致人才缺乏;二是山西人排斥山西人,主要表现在“新旧的不合作”和“区域的不合作”;三是山西当局虽竭力表示以诚相见,但他们“头脑大部分不外孔孟的政治或者旧式的教训,小部分加以自身个别的经验(一种官场生活的经验)”,形成“自以为是的执拗脾气”和“心有所畏的周旋本领”,由于“私人道德不足以为标率”,缺乏政敌的刺激和磋磨以及地理上的错觉,导致政治当局“无所作为”,虽然“他们很想挽回山西的颓运,可惜他们除不掉各自的旧我,所谓诚者,也就有心无力”;四是山西人的性格,并称这是最可怕的病原,表现在“精神上的近视”,“没有创始的活泼精神,缺乏新式的知识和技巧”,导致他们“苟且因循安分守己”“切实和驯良”“自私和懦弱”,而这应当归罪于政治当局缺乏对老百姓心理的培植。文末,他总结到,日本侵略山西,各省军队联合抗战,希望“大家认识自己不仅是山西的山西人,还是中国的山西人”,抛却狭隘的乡土观念。李健吾并非一位冷静的“客观”分析者,他的笔端常带着情感,关于“病原”的四点分析,实际上是他作为山西人的一份子所提出的殷切期望。
《空当》#0刊于上海《导报》1946年2月15日第6期、7期合刊。1945年11月10日,《导报》在上海创刊,由上海日侨管理处宣导科编辑、上海日侨管理处发行,该刊关注日本的社会、政治动向,同时还注重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刊登一些文艺作品,撰稿者有丰子恺、赵景深、熊佛西、汤恩伯、郑逸梅、顾仲彝、郑振铎等人。文中,李健吾以在日本宪兵队司令部被关的两次亲身经历为例,记述了被拘期间他对横地藏行和萩原大旭、一个矮家伙这三个日本人的印象,虽然与他们有接触,但却“揣摸不出他们的用意”,在作者看来,他们是“非常地有礼貌”“非常地野蛮”“缺少个性”的“矛盾”的综合体。李健吾将敏锐的心灵感受流露于文字中,因为接触过“黑暗圈”,才能更加体会“我就是没有看见思想”这句評价,可谓是对日本侵略者最好的讽刺。
纵观李健吾一生的文学创作,涉猎甚广,与他的小说、戏剧、散文创作相比,诗歌仅占了很小的部分,但他始终保持对诗歌的热爱。据统计,他在《晨报副镌》《清华周刊》《清华文艺》《骆驼草》《北平晨报·诗与批评》《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了近30首新诗,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诗人的作品和诗论。此外,尚有诗歌《永生》和译诗《黑猎人》。《永生》一诗作于1931年,1936年7月10日刊于天津《人生与文学》第2卷第2期。全文如下:“我在忧郁之中/往往想起你来/仿佛春风/吹澈晚寒的堡寨/仿佛午阳/溶却墙阴的积雪/仿佛破晓/窗外流泻的音籁/在沉沉的云空/唤起我的长梦/你宇宙的宇宙/你昼夜的音奏/因为永生的情爱/出现你我的存在/从尘世的罗网/从失水的浅港/哦幽禁的灵魂/巨舟的焦唇/驶入你的明镜/沐浴你的光荣/仿佛秋泓/映着万盏的星文/仿佛蜜蜂/飞向唯一的蔷薇/诧异它这样红/喜爱它的微濛/维护它的花瓣/有一日要消散/恍惚水中明月/幻梦的音节/零落的花瓣/象征未来的黑暗/过去的消逝/中间却有你的恩誓/哦青春的青春/长青的松林/红颜的红颜/出水的红莲/让我为你歌颂/那永生的永生/伴着流泉的琤琮/树梢的吟咏/因为你的幸福/我的幸福。”整首诗清新自然,语言明快。作者于“附记”中写道:“一恍首已然五年了。偶然检出这首旧作,虽说稚嫩,还算朗朗上口,因而破羞披露,聊供同好者一笑。”李健吾颇为珍视自己的诗作。
《黑猎人》译自雨果的诗集《惩罚集》,1946年8月12日发表在臧克家主编的《侨声报·星河》上。黑猎人原是德国莱茵地区民间故事中流传的人物,在这首诗里,黑猎人象征着诗人、人民等正义的力量,表达人民反对拿破仑三世罪恶统治的愤怒心声。李健吾在“附记”中表白他的心迹:“今天我译出这首诗,百感交集。一八四八年,法国又是一度革命,雨果暂时放开诗人的桂冠,参加政治,充当国会代表。不久他就发见他和他的民主理想被总统拿破仑的后裔所出卖,犹如袁世凯,然而比袁世凯幸运,发动复辟,恢复帝国,推翻第二共和国。雨果便被放逐了,他足足有十八年度着流亡的生涯,关切祖国,然而没有方法和他心爱的同胞拥抱,他写下他著名的《惩罚》诗集。他诅咒一切缢杀祖国的恶魔,内在的,外在的,一切不顾人民福利的暴君,尤其是拿破仑和他的子孙。”《黑猎人》让李健吾深有感触,他说:“读着这首诗,我想到久已苦难的中国,在胜利之后反被自己的手所缢窒。借酒浇愁,酒更愁人。然而我不绝望,正如雨果所歌‘天亮了!魔障终于会消失的。”可见,李健吾借雨果的诗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虽然抗战胜利后中国仍面临苦难的局面,但他坚信光明终将到来。
此外,李健吾的佚文还有独幕剧《恐慌——讽刺的对话》(天津《庸报·庸报副刊》1928年11月19日、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第9版,署名李健吾)、《关于剧评》(北平《新晨报·戏剧》1930年6月12日第124期,署名健吾)、《北平小剧院第一次的公演》载北平《新晨报·新晨报副刊》1930年6月30第648号、1930年7月1第649号,署名李健吾)、《对话三折》(汉口《大时代》1938年2月1日第4期,署名刘西渭)、《职业妇女笔谈会》(上海《世界文化》1940年8月第3期,署名西渭)、演讲《略谈戏剧》(上海《中华时报》1947年4月1日、4月2日第3版,李健吾讲,王耕夫记)、《感谢母校》#3(《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1948年4月29日第11—12期“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署名李健吾)、独幕剧《蛮子的心思》(载上海《新人旬刊》1948年9月21日第2卷第1期,署名李健吾)等,囿于篇幅的原因,在此仅存目。以上是笔者在查阅报刊时陆续见到的李健吾集外佚文,除诗歌《永生》译诗《黑猎人》以外,大都是短小精悍且精彩纷呈的评论、杂文,希望它们能够对李健吾研究有所助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抗战时期社会动荡,兵燹不断,文学作品与报纸杂志的散佚情况比较严重,因而李健吾在这一阶段的著述尚有可辑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