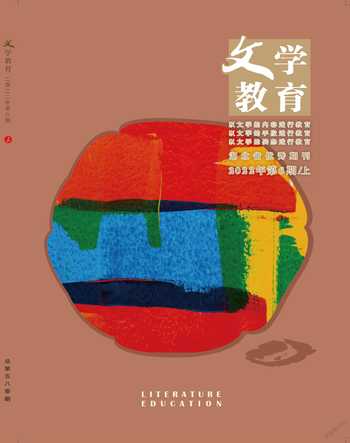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地下室人》:在凝视中存在与终结
2022-06-30王兆玮
王兆玮
内容摘要:本文以拉康、萨特和福柯的“凝视理论”为主要工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室人”的形象进行系统分析,勾勒出其内心变化的基本线索:首先,“地下室人”在自我的“镜像”幻想与他者的凝视中确立自己的存在,而后又在外界凝视所施加的权力压迫之下走向异化,最后在反凝视的努力中失败并走向终结。本文不仅通过“凝视”理论深入观察了“地下室人”的建构与变化、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深刻反思,更重要的是使其成为人们不断反思主体与他者、集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桥梁,让文学研究本身更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人》 “凝视理论” 凝视 异化 反凝视 俄罗斯文学
“凝视”,译自英文单词“gaze”,汉语中也常译作“注视” “盯视”,其基本理论来自于萨特、拉康、福柯三人的精神分析学及哲学著作。现代文化批评中将其定义为“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1],国内文学批评界对该词汇的界定如下:“凝视是携带着权利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她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the gazer)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the gazed)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2]由此可见,“凝视”一词除却“看”这一动作本身以外,已然被赋予了与权力和欲望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意义。
回归到《地下室手记》这部作品本身,百年之中它不断地以多样化的角度被解读和阐释。如1822年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论文《残酷的天才》中将陀氏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即侧重描写羊被狼吞食时的感受和狼吞食羊的感受。他认为《地下室手记》就是作家详尽描写狼吞羊时感受阶段的开端。但是笔者的看法稍有不同,《地下室手记》恰恰是将这两种感受杂糅在了一起——“狼”和“羊”正是在凝视与反凝视的过程中发生了位置互换,而这一点在地下室人和丽莎的对话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进入20世纪以后,对该作品的分析逐渐转向了哲学和诗学层面,舍斯托夫将其视为“一篇反理性的宣言式作品”,美国哲学家考夫曼则将小说的第一章定义为“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在巴赫金重获重视的60年代,他对小说主人公的独白话语进行细致分析后指出:“地下人在同自己、同他人、同世界进行交谈。……地下人是陀氏塑造的第一个思想者的形象,这是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内容集中于一种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3]弗里德连杰尔认为:“地下室人在敌视他的社会为他准备下的无数灾难和屈辱中生长……”,在马尔科姆·琼斯看来:“《地下室手记》写作上那种自我暴露的风格正是解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上保持着一种不断颠覆的状态……”[4]综合以上不同侧面的信息及笔者本人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地下室手记》涉及了存在与本质、理性与自由、个人意志和集体意识等存在主义经典命题;2.“地下室人”的独白中包含着一系列杂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他者(此处既包括幻想中的“小他者”,也包括实际存在的“大他者”)进行的对话;3.“地下室人”渴望获得他者(此处指周围的人群和社会环境)的认同但是始终无法得到理解,从而转向了自我折磨以及对相同处境的“同貌人”(此处指丽莎)的折磨。
“凝视”理论常被用于探讨和分析女性问题、种族问题、殖民问题等等文化领域的重要命题。但本文却以他者的“凝视”中自我确立与异化问题为主线,通过对“地下室人”形象的剖析,厘清其在他者的凝视中寻找自我、迷失自我、奋力抗争的过程。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开篇就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里的枷锁原指契约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自由虽然是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和权利,但现实中的人却不得不像“地下室人”一样在集体的凝视中徘徊思索、彳亍前行。
一.从“镜像”到“他人即地狱”——“地下室人”的存在与异化
首先,谈到主体这一概念,就无法绕开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他认为“注视”使得主体与他人之间建立关系,两者都在彼此的目光中确认存在。但是与此同时,被凝视的一方往往处于“凝视”的包围之中,产生羞耻、骄傲乃至虚荣的情感感受,即“我在我的活动之中把别人的注视当作我自己的可能性的物化和异化”[5]。这无疑会造成一种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权力压迫,同时迫使被凝视者作出改变去迎合“凝视”所反映出来的取向。
很多学者认为“地下室人”是自我意识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注重反思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这当然是这个形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侧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地下室人”时刻处于一种担忧、恐惧和愤恨之中,其中的大部分来自于对他者“凝视”的一种揣测和畏惧,小说第二章描写“地下室人”过去的生活经历时就曾写出他隐秘的内心活动:“我也十分清楚地发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当作怪人,而且——我一直覺得就是这样——似乎还用某种厌恶的目光在看我。……我甚至可以承认脸上的表情下流无耻,只要别人同时认为我的脸聪明绝顶就行。……我生怕自己显得可笑,甚至害怕到病态的程度,因此我奴性十足地崇拜有关仪态举止的一切成规惯例。……没有一个人与我相似,我也不与任何人相像。‘我只是唯一,而他们是全体’。”[6]除了这段典型的“凝视”描写之外,小说全篇都处于一种和暗含的读者以及内心矛盾的对话之中,且这种对话主要是建立在主人公对外界“凝视”的反应之上。“地下室人”在开篇对自己的定义即是:“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而他在和军官较劲、努力挤进“朋友”西蒙诺夫的小团体的过程也就是试图通过他者对自己的“凝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但最后他发现自己“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甚至连他所畏惧的他者和社会的“凝视”都已经消失了,别人把他当做“整个世界的一只苍蝇”,彻底忽视了他的存在,否定了他的价值。关于注视和见证萨特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由于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上,于是便产生了繁复的关系,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的联系……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7]可以说,见证是存在的见证,人的存在需要他者的见证。“地下室人”在他者的“凝视”之中畏缩、惶恐,他者凝视中带来的并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他始终未能得到一只渴求的对存在价值的“见证”,他人也终成地狱。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是从萨特的主体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窥淫癖理论继续延伸出来的,这一理论原指六个月左右的婴儿能够在第一次目睹自己镜像时辨认出自己的形象,拉康认为这种情景认识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关键一步,本质上也是确认自我存在、获得自我认识的第一步。但与此同时,拉康也指出,镜中形象尽管给主体带来了肯定自我存在的喜悦,但它实质上却是一种虚无的、异化的幻象。这种幻像便是拉康所说的与自我幻象相对应的“小他者”(即“地下室人”幻想中的正直、无私、有尊严的自己),而与真正主体相对的“大他者”(即“地下室人”周围的环境和环境中的各色人物)才是将主体确立下来的必要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主人公窥视着军官的一举一动,通过各种方法试图为自己受到的羞辱讨回一个公道,最后通過撞一下肩膀(军官甚至并未注意到这一撞)“达到了目的,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与他处于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其实,主人公的这一行为是颇具“阿Q精神”的一种自我安慰,他在一种实现目标的虚幻满足中给自己建构出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以这个“小他者”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当然,这里并不是对“地下室人”形象的彻底否定,毕竟正如主人公所说:“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目光如豆。”即使只是一种幻想,“地下室人”也望向了镜子中,试图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周围的“大他者”仍然处于蒙昧的迷雾之中,他们顺从于社会凝视所形成的权力威压,而后凭此在集体之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尊严,再把这种凝视投向于任何一个试图反抗的“地下室人”。
这也就涉及到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释的一种内涵于“凝视”目光中的知识与权力的运作。医生有权以治疗疾病、驯服疯癫的名义,通过自己的专业医学知识和技能对病人进行单向度的观察。《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狱的构想也给出了一个更具启发性的解读方式,即社会并不是一个公开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的社会。高位者通过全景敞视的结构来监管所有下位者,但是所谓的“高位”也只是相对的,最终必然会形成一个监视的循环。在福柯的理论中,“凝视”的主要内涵在于“监视”,这也是知识和权力运作的必然结果。而当人沦为各类凝视、社会常态化监视下的产物时,人已成为客体,成为毫无主体性可言的对象——他人,因此福柯得出结论:“人死了”,“真正的自我已经被他者化了”[8]。“地下室人”正是不服从于这种权力监视的人,他独立而自由的反思使其无法盲目地参与到这个大循环之中,因此他虽然在双重“他者”中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永远无法站到“凝视”链条的更高一层。那么,在各种努力都失败了以后,他又是如何进行“反凝视”的呢?
二.反凝视的失败——“地下室人”的终结
“凝视”是一个双向的动作,凝视者与被凝视者是可逆的,他们的位置拥有互相转换的可能性,这就是“反凝视”一词得以出现的原因。“地下室人”也多次做出类似尝试,从对军官的“报复”、到努力加入西蒙诺夫的小团体,他都试图通过一些行动获取他人的尊重,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平等,以求瓦解“凝视”行为中的二元对立。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对于这种行为又是极其鄙视和不屑的,在内心的这种矛盾之中他的“反凝视”行动常常以失败告终。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失败便是“地下室人”和丽莎之间的交往经历。从“女性凝视”的角度来看,这段故事首先来自于男性对待女性时的一种欲望,将女性他者化、对象化、客体化,他们在女性身上看到了这种欲望的匮乏,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这时男性会采取以下两种做法:1.妖魔化女性;2.物化女性[9],这两种贬低行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站在凝视者的高位上“教训”女性。“地下室人”在受到西蒙诺夫小团体的无视和侮辱后,开始对妓女丽莎进行道德训诫,他表示“男人和女人根本不能相比。完全是两回事;我虽然自暴自弃,糟践自己,可我却并非任何人的奴隶……可拿你来说吧,从一开始就是个奴隶。”由此可见:主人公此时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凝视者的立场上,通过语言将丽莎从想象界带入象征界(拉康语),试图掌控丽莎的敏感善良的心灵,最后在看到丽莎“可怜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的时候他感觉到了片刻的胜利。只可惜小说结尾丽莎来拜访他的时候正看到他受辱,因而他为自己建立的凝视者之高位迅速转变成了被丽莎所“凝视”的低位。
“地下室人”反凝视的失败并不在于缺乏反抗精神和反思意识,而在于社会凝视所形成的权力压迫本身就非常强大,他试图反凝视的意志又是不坚定的、左右摇摆的、充满怀疑的。或者说,他始终无法从来自于他者的“凝视”目光中挣脱出来,“忙于无尽无休地尊重自己”,时时刻刻感到“我被注视”,不断体验到“我的为他的存在”,所以他无法完成对“凝视”的最终解构。叔本华早早就对此问题有过经典的解答:“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地下室人”试图在他者的“凝视”中确立自己的存在,导致了个性的异化,最后尝试以“反凝视”的方式恢复尊严,结局却是否定了个人的存在价值。
本文以“凝视”理论探究的“地下室人”形象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在文学分析本身。而是“地下室人”作为个体面对“集体凝视”的一个折射,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揭示出一种自我反思和社会反思的必要性——个人在集体的“凝视”中如何自处?“凝视”中如何确立自我的存在意义?“反凝视”的意义何在?无论是在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中,被凝视的“地下室人”的现实意义才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7.
[2]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3]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马尔克姆·琼斯著.赵亚莉,陈红薇,魏玉杰译.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80-90.
[5]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331.
[6]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伦,曾思艺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07[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6.440.该作品引文都出自此处,以下不再另作注.
[7]柳鸣久选编.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3.
[8]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4.
[9]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82-95.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