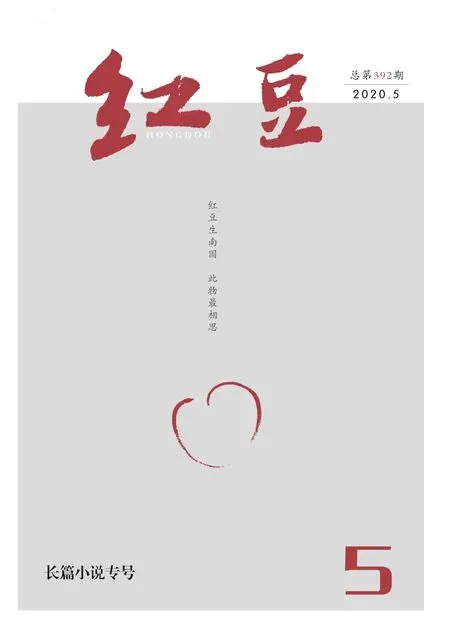城镇化是所有人的张灯结彩
2022-06-28余述平
余述平
我曾无数次构想自己理想的生活,一个人守着一只羊,像绝壁守着一条清澈的溪流,或者像一只鸟在天空孤傲地飞翔。我甚至假想过,自己是包装过的沉默的烟火,一生只为一根火柴献身,孤独和愤怒都是为了那一秒的彻底燃烧。我所构想的这种极致的生活,按现在的实际,永远只是一种奢望,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不是绝对绝望的人是不可能实现的。河流是狂妄的,无论它奔袭多久和多远,它最后还是屈从于路径和方向;鸟飞得再高,也要回到鸟巢。上海崇明岛海滩摇曳的芦苇荡里,生活着一种叫震旦鸦雀的鸟,它们在风雨飘摇中把爱巢筑在危机四伏的芦苇丛中。崇明岛海滩的芦苇荡每年都有海水冲进来,许多震旦鸦雀的家就被淹没了,但震旦鸦雀依然在崇明岛海滩的芦苇荡里精心设计着自己的生活。在震旦鸦雀眼里,或许那个毕生为之奋斗的渺小的窝,就是比天都大的城郭。
由此看来,一处居所,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它就是一个天体,在抵御突如其来的黑洞。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孤独和个体。一块被遗弃的石头和一滴独自飘落的雨,它们依然和广阔的宇宙发生着无穷无尽的联系。我们看似绝对的孤独其实是以另一种形式与广大的事物和世俗的现实群居着、共生着。一颗美丽的钻石,或许大半生都在一堆废墟之中。这废墟中的钻石曾经孤独过,钻石在废墟中脱颖而出,就是它璀璨的开始。
废墟和钻石,一直都在相互照耀,当然,也在相互损毁。没有一根草能独自抵抗风雨,草和草相互慰藉,就成了草原,一片无比蔚蓝和诗意的自然之源。人类的陌上,天然之城,就在我们相互的模仿和传导中形成了。孤独的个体,一定会以轮回的方式,最后握手、相聚。
天体进入黑洞的结局不是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态拥抱更大的天体。
蚂蚁在所有人眼里一定是渺小的,但正是这些看似卑微的生灵,在巢穴中建立了一个个秩序井然的王国。有一种蚂蚁叫瑞士红褐林蚁。在绵延一百多公里的森林里,只有红褐林蚁才认识路。全世界有人的地方都有蚂蚁,许多没人的地方也有蚂蚁。平时我们不把蚂蚁放在眼里,有时还会用脚踩死它们,但我们不知道蚂蚁活在这个星球,已经一亿多年了。它们吃云杉树脂,吃松毛虫、松叶蜂、松尺蠖、落叶松隐条斑螟,吃云杉黄卷蛾。它们用针叶、树皮和树枝修筑城堡,在森林里,瑞士红褐林蚁修建了很多座城堡。城堡和城堡间暗道相连,蚂蚁和睦地来来往往,像机器一样自律。没有谁能摧毁它们,它们的城市比我们的城市还要生机勃勃。以前我失落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比喻成蚂蚁,但现在看了瑞士红褐林蚁后,我脸红了,每一只红褐林蚁都是勇敢的承担者、承受者。这辈子我连蚂蚁都做不成了,但我努力向蚂蚁学习。我也常问自己,我们人类和自然中的万物,谁在城镇化的路上走得更坚决更持久更早。
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城镇化,是新生事物,还是早就已是我们进化的脐带?现在我多少有些明白了,其实人类从洞穴里走出来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只是人类的城镇化进程极其缓慢,游牧文明和长期的农耕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制衡着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城镇化的想象空间一下子被打开了,到了现在,世界正由农耕文明朝工业文明飞奔而去。这个文明形态的重要标志就是社区文化的崛起,而社区文化的中心词就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站在历史的节点,大踏步开始了城镇化进程,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之林。现在你到中国的每一寸沃土上走一走,处处都是城镇化的足迹,北京、上海、广州成为国际大都市,一批大城市崛起,一些区域性城市体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财富的积累和日益扩张的城市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现实问题,城市给人带来的压迫感造成了人们不同程度的焦虑,很多人不幸成为这喧嚣城市里的孤岛。我同时也看到,中国的城镇化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近年来,国家因势利导,大力发展乡村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建设在中国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这么多元化、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景象,值得每一个作家拥抱和抒写。漠视和缺席都是对写作的一种背叛。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一直认为我生活的小区是没有多少故事和兴奋点的,每一个人住在自己家里,大家不认识,时间久了,也装作不认识,因为这样省去了很多人际间的麻烦。我居住的小区比较特殊,每一户都有家属在机关工作,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彬彬有礼、谈吐严谨。时间长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小区里大部分人即使喝醉了,也不会说一句错话。通过这个细节,我高兴地发现这波澜不惊的小区里,其实暗藏了巨大的文学浪花。于是,我像一個“帕帕拉奇”学会窥视和观察了,这小区的一只鸟都变得有故事了。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小区,有不少装修公司临时进驻。我注意到了一个卖窗帘的女人,这女人像她家的窗帘一样花哨,小区的许多男人有事没事就爱往她店里跑。我老婆看得很紧,她先知先觉地警告我远离这个店。刚开始我认为我老婆过于敏感,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因为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把刀,把这窗帘店的老板娘追得鸡飞狗跳,我们小区的成年人都知道原因。城镇化或者社区化,确实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我又不知不觉地注意上了一个清洁工老男人,他有点话痨,不是自言自语,就是拉人唠嗑。他的这一点,我们小区的人是不喜欢的,我们小区的人喜欢物业的人安守本分、安安静静、不问东问西。刚开始这男人穿得比较邋遢,但几年后,他突然变得有点样子了,他在椅子上坐着,戴着眼镜看报纸,拿着收音机听新闻,走路也变得像老板的步伐了。我常问自己,这算不算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我们每个人该怎么进入城镇化?城镇化其实没有一处死角,它是所有人的张灯结彩,连偶然闯进来的空气也是。
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水乡小镇,我父亲是湖北人,母亲是广西宁明壮族人。小时候,我在小集市上屁颠屁颠穿行在人群中,眼里没有大城市和大工厂,我的注意力都在大人们的脚下。隔三岔五,我总是能在地上捡到几枚硬币,捡到硬币就是我的快乐。七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农村,七年之后回到小镇,后来考上技校到了油田。在油田,我先后干过电工、新闻报道员、宣传科临时职员、职工学校教员,上干部学校拿到了中专文凭,毕业后没当上干部。后来我又当了机务工、电台操作员,去了山东,闯荡两年。回到湖北后,当上了警察,我现在最高的学历就是刑事侦查大专。五年之后,我到了油田文联工作,有模有样地主编一本纯文学内刊。再之后,因为写小说写出了一点名堂,于 二〇〇二年调到省城武汉工作,就职于省文联的电影家协会。我之所以罗列我的经历,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摆脱无所不在的城镇化,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于城镇化。
二〇〇四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参加第三期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深造学习。有一天,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发,我叫了声师傅,师傅不理我。我想小时候在小地方,我们把理发的叫剃头匠,而在武汉,我们把理发的叫师傅,已经文明了一大步。但在北京,我喊理发的叫师傅,师傅却不理睬我。后来,理发师告诉我,我们这的理发师,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我又一次长见识了,城镇化就是让人不断地文明起来,让人获得身份上的尊重。
我的经历让我像一个孢子流动在各个城市之中,它落在哪,哪就是我的故乡。它与城市的大小无关,只与个人的生长有关,但城市会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在云南的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里,太平洋的风吹过高黎贡山的大风口,古老的杜鹃树长到二十多米高。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雷斯特来到云南把杜鹃的种子带到了英国,通过不断培育,杜鹃花开满全世界。只是现在的杜鹃不再挺拔,而是成了矮小的植物,这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杜鹃一定更有传播力了。这是否可以暗示,放下自己的身段和某些狂妄自大,也能走上另一种城镇化之路?
以上的种种思考,还有很多很多的假设,构成了我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电影小镇》的缘由。写这部小说是我这个受益于中国这场深刻城镇化运动的人的一次还愿,也是向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致敬。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