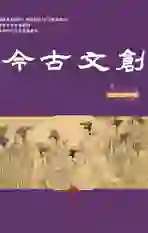蒙古族古代翻译史蒙汉互译研究初探
2022-06-22尹崇嘉
【摘要】 蒙古族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蒙汉互译活动及蒙汉互译内容在蒙古族翻译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促进蒙汉各方面交流、蒙汉文化习俗互通、蒙汉民族融合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不同历史时期蒙古族进行的蒙汉互译活动、蒙汉互译内容,其目标定位及受众群体也有所区别,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在蒙汉互译内容方面,不同时期蒙汉互译的互译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包含有政治性官方文件翻译、儒家经典著作翻译、蒙汉词典辞书与蒙汉双语教材编撰翻译,以及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翻译;在蒙汉互译目标受众群体方面,不同历史时期蒙汉互译的互译目标受众群体也有较大区别,上至蒙古族统治阶级与王公贵族,后又逐渐下移至蒙古族与汉族商贾群体及专门为两个民族间通商贸易往来进行翻译的民间翻译人员群体,最终及至广大蒙古族人民群众以及迁移至蒙古族聚居管辖地域的汉族普通农民群体。纵观不同时期蒙汉互译的翻译历史,不论是对于翻译特定内容还是目标受众群体,其在整体上呈现出由上至下、由官方到民间的趋势。本文从元、明、清三个不同时期蒙汉互译的活动及其内容入手,经过综合研究与思考过程后选取一些典型案例,对其进行分析探究,以简要论述不同历史时期蒙古族翻译史中蒙汉互译的特征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
【关键词】 蒙古族翻译史;蒙汉互译;翻譯活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0-01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0.037
蒙古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为适应其不断变化的发展需要而与其他民族、各个国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互通活动,因此在蒙古族的发展历史上,其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十分活跃并且持续不断。目前,学界在蒙古族翻译史方面所开展和进行的研究比较多集中于蒙藏互译、满蒙互译、蒙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例如畏兀儿文、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等)或外语(例如英语、俄语、拉丁语、波斯语等)互译等方面,并且研究者们尤其强调蒙藏佛经翻译在蒙古族翻译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而对于蒙汉互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总体特征及其所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与归纳相对缺少,故而本文对蒙古族翻译史中蒙汉互译在元、明、清三个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发展特征情况以及其各自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简要论述与归纳。
一、元代蒙汉互译以政治性文件以及儒家经典翻译为主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作为其统治者阶层的蒙古族本为北方游牧民族,该民族长久以来有着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并据此而形成豪放爽朗、自由不羁的民族个性,且主要是采用部落划分及汗王统治制来延续其统治。而居于广袤中原大地上的汉族人民则是习惯于农业社会下安定平和、耕种收获的生活,并且受到长期封建统治主导下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因而逐渐产生及形成了独特的高度集权、中央集权的帝王统治集团及科举考试制度、官员任用制度。基于此种情境下,蒙古族统治者认识到了学习汉民族固有的文化意识、政治理念并在其中融入蒙古族统治之法的重要性,因而蒙古族统治阶级在政治性文件及儒家经典的蒙汉互译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
元朝初期时,在官职设置方面即设有“怯里马赤”一职,其官职名汉译即为“译史”,而许多官衙中亦会配有专门的“怯里马赤”人员对蒙汉互译工作进行负责,这些“怯里马赤”人员便是通过翻译来实现政治性文件的上传下达、辅佐统治阶级发令、协助各方官员进言。随着翻译工作不断成熟、翻译职责分工逐渐明确完善,以及元朝整体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元代逐步正式设有并持续完善国家层面的翻译机构,这在其中就有专司负责儒家典籍经义翻译的分管机构,即艺文监和经筵译文官。研究学者阿拉坦巴根(2012)在其相关论文之中论及元代翻译机构时就表明,艺文监即为从事翻译和刻印儒学典籍的官署;而在艺文监供职之人,则多为蒙汉兼通的博学之士,并且艺文监也承担着组织人员对国子监所用汉文儒学经典进行翻译这一职责。阿拉坦巴根(2012)亦有论及经筵译文官一职,并在其相关研究文章中,简要表明了当时元代的朝廷开设这一官职,主要目的就是将其作为一个向皇帝翻译和进讲儒释两家经典文献及著述的专设高级翻译官职。
自元世祖忽必烈而始直至元朝终结,总计十一任皇帝中,仅有寥寥数位通晓汉文,其余则多不曾修习汉文。因而通过蒙汉互译的方式来帮助统治阶级颁布政令国策、了解研习汉族语言文化、掌握儒家经典著述,对于元代当时的历任统治者加强统治、巩固政权、更新优化政治理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明代蒙汉互译侧重蒙汉辞书以及双语教材方面翻译
元朝灭亡后及至明朝兴起时,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已经完成了由北方少数民族执政掌权回归至汉族当政统治的转换。学界诸多学者及研究者们对这一历史时期蒙古族的古代翻译史研究的关注重心几乎完全投入到了藏传佛经翻译、蒙藏互译的方面,相对而言则忽略了对蒙汉互译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发展、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方面进行更多探究以及深入发掘。
元王朝的衰败灭亡,虽然使得统治阶级产生了更替,原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整体退居漠北、完全淡出中原政治体系,但这一统治阶级层面的变更则并不代表着蒙古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也被一并切断。恰恰与之相反的是,在明朝时期蒙古族人民与中原地区民众的交流往来仍然较为密切,并且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商贸等各种层面(政治方面交往虽较元代时期有所减少,但也绝非是达到了全无往来的状态,而政治方面交往相较于经济、文化、商贸方面密切频繁的交流往来而言,则显得逊色不少)。贸易互市及使者往来,相对开放宽松的大环境为蒙汉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此而产生的蒙汉民族间大量的沟通交流,则自然少不了需要通过翻译来为两个民族架构起互通互联的桥梁。
据阿拉坦巴根(2012)撰写的相关研究论文中所论,蒙古族从十三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编写双语或多语对照辞典的传统。
明朝时,已经开设有专门培养包括蒙古语在内的多种语种翻译人才的专门学校,例如明永乐五年开设的四夷馆,就有专门开设的蒙古语翻译课程以训练蒙古语翻译人才,并在授课过程中使用特别选取及精编的专业教材。四夷馆所使用的高级教材包括有《蒙古秘史》,初级课本包括《华夷译语》。
《蒙古秘史》作为一部较为系统地叙述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以前的远祖时代起,蒙古族大约五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其所呈现出的宏伟的构思、雄浑的笔调、瑰丽的语言和丰富精彩的内容而闻名于世。据安柯钦夫(1984)相关研究论文中所论及,《蒙古秘史》目前的传世版本为汉文音译版本,即是一种将原文按照“纽切其字,谐其声音”的音译规则,由汉字拼写出蒙文,并且在蒙文单词右侧再附加汉意译文译成的版本,这一译本版本于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明朝洪武年间根据宫廷秘笈翻译印行,之后被全书载入明《永乐大典》。而《华夷译语》则涵盖了近千个单词,并且附有明朝廷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往来公文作为阅读材料,并且其所采用的分门别类的编排方法亦对后世所编著蒙汉辞书的编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阿拉坦巴根(2012)在其相关研究论文中亦有提及其他一些论述明朝边政的著述,例如通称的“北虏译语”,在这其中所出现的一些译语是采用了音译的方法,从而反映了明代蒙古语从汉语借词的实际情况。这些译语又是作为汉人学习蒙语的材料而流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当时汉族人学习蒙语的规范教材或参考学习资料,由此可见,明代蒙汉互译仍在翻译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汉蒙民族对彼此文化以及語言文字的学习探索从未停止,并且蒙汉互译广泛的受众群体已经有了逐渐从官方统治阶级往来而转移至民间群众交流互通的趋势。
明代蒙汉互译活动以及蒙汉互译的互译作品,或许是并不可作为蒙古族古代翻译史上一大主流翻译活动及内容而进行探究的;然而明朝时期蒙汉互译辞书及对于一些用作蒙汉双语教材书籍的翻译,则确实为当时的蒙古族人学习汉语语言文字、为汉族人学习蒙古族语言文字以及培养蒙汉双语翻译人才提供了较为标准且有效的学习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制定以及确立了当时蒙汉翻译学习的规范,并且在促进与提高蒙汉互译翻译质量以及准确性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有参考及借鉴意义的翻译方法,故而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和意义。
三、清代蒙汉互译重心转移至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
及至清代,由于统治阶级的再次更替,而这一时期蒙古族的各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蒙古族在其社会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是随着与满族、汉族关系的变化而产生了相应转变。与明代统治者相比,清代统治者对于蒙古族的政治态度和实行政策都有较大变化,清代统治者们不再将蒙古族边缘化,而是转为了较为明显地施行怀柔政策:一方面以蒙古族为尊,提高蒙古族的政治及社会地位,设立八旗并给予其优厚待遇,利用满蒙联姻笼络蒙古族王公贵族,用以巩固自身统治;另一方面仍然注重集权统治,设立蒙古衙门(后为理藩院)以专门司理蒙古事务。而与此同时,清廷统治者们也严格实行对蒙汉民族交往互通的管控,禁止蒙古族聘请汉族人教授汉文汉语,禁止汉族人擅自出关。在清前期实行的封禁政策几乎将汉蒙间文化交流全部阻断。依唐吉思相关研究论文中(2016)所论,清前期的蒙古文翻译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迎合、跟随清廷的翻译行为,其目的是给蒙古族王公贵族及其子女灌输儒家思想,以便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及至清代中晚期,随着汉族的农民大批量迁往蒙古地区并且移居于此,汉蒙民族文化交流又得以发展至一个全新的阶段,汉蒙两个民族间的融合互通及联系也愈加紧密。在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主体及翻译作品的受众群体亦是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以往朝代及时期的官方主导翻译活动、以政治性文件及儒教经典为主要翻译内容、翻译目标受众群体主要为统治阶级及官员外史等,完全过渡转变到由民间团体及民间人士自主自发进行翻译活动、以汉族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传奇故事作为主要的翻译内容、翻译受众目标群体主要为蒙古族及汉族人民群众等。
依据学者阿拉坦巴根的相关研究文章中(2012)所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文学名著,《西汉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东征》《罗通扫北》《列国志》等演义类小说和《大小八义》等侠义小说及《师公案》《彭公案》《济公传》等公案类小说相继被译成蒙古文,并以刻本、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这些文学名著及小说读本译本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并对促进加深蒙古族人民群众对汉族风土人情及文化传统的了解认知大有裨益,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蒙汉民族融合进程及文化交流。
而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的出现,更是在这一时期的蒙汉互译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依据安柯钦夫(1984)所述,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含义是自己酷爱文学工作,向他人提供精神文明。哈斯宝博览群卷、热爱文学、兼通蒙汉双语,这些因素都是其进行《红楼梦》翻译的有利条件。而哈斯宝本人也对这项自己选择的翻译事业及其热衷,投入大量心力。尽管最终成文只是节译文,使蒙古族读者不能从中窥得原作者曹雪芹意欲呈现出的当时清代社会全貌及作者本人意欲表达的全部所思所想,哈斯宝的译文也已为蒙古族广大民间读者提供了一个欣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之美、体味原作者曹雪芹情思之妙、深思社会变迁及人世无常道义的绝佳窗口,使蒙古族的民族文学创作也能够在借鉴吸取汉族古典文学精华及长处之后得以突破和提升。哈斯宝亦直接带动了当时的蒙古族文学翻译之风,在哈斯宝译作问世后蒙古族兴起了一波翻译汉族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翻译的高潮。通过当时如哈斯宝这样的蒙古族优秀民间翻译人士的翻译活动及译作传播,清代蒙汉互译活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蒙汉互译作品的民间传播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蒙汉民族融合进程。
本文纵观元、明、清三代蒙汉互译活动及蒙汉互译内容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进程,针对每一时期蒙汉互译特征及相关影响,以及各时期间整体间关联,可得如下三点总结概述:
其一,元代蒙汉互译多以政治性文件及儒家典籍翻译为主,翻译活动的主导及受众群体都较为局限,多以统治阶级与官员外史在政治上及国事外交方面往来交流、统治阶级王公贵族为更好适应统治需要而学习汉地儒家经典为主;这一阶段蒙汉互译的意义在于服务于统治阶级,通过翻译来巩固政权、实现政策传达及政治理念更新学习;元代蒙汉互译主体集中于蒙古族统治阶级官方层面,未有明显民间层面反馈。
其二,明代蒙汉互译偏重蒙汉辞书及蒙汉双语教材方面翻译,翻译活动的主导及受众群体有所变化,民间人士逐渐参与至翻译活动并逐渐增加其在翻译受众群体中所占比例;这一阶段蒙汉互译的意义在于更多为蒙汉民间交流提供了便利,确立并提供了一些较为实用且规范的翻译教材,翻译逐渐更多地倾向于服务于民众而非单纯局限于服务统治阶级;明代汉蒙互译处于一个由官方向民间的过渡阶段。
其三,清代蒙汉互译一大重心及亮点在于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的蒙译,翻译活动的主导及受众群体产生极大变化,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完全由官方主导掌控,而将主心骨转移至民间了。这一阶段蒙汉互译的意义集中于促进蒙汉民间文化交流及推动蒙汉民族融合,且清代蒙汉互译已完成了由官方向民间过渡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阿拉坦巴根.蒙古族古代翻译史概述[J].民族翻译,2012,(01).
[2]安柯钦夫.蒙古族文学翻译传统初探[J].中国翻译,1984,(05).
[3]唐吉思.蒙古族历代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特征[J].民族翻译,2016,(02).
作者简介:
尹崇嘉,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内蒙古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