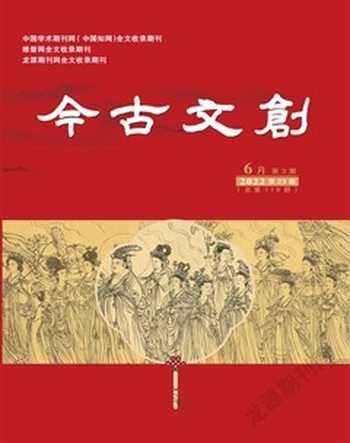孤独的传奇,苍凉的生命
2022-06-22郭亚男
郭亚男
【摘要】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张爱玲名噪一时。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童年以及成年后个人的独特经历对她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集中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历经浮华之后,其作品呈现出苍凉和凄怆之感,不断解构人性的卑鄙、扭曲与变形,由此形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本文将从张爱玲人格个性的形成原因以及创作心理在作品中的表现出发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 张爱玲;创作心理;孤独;荒凉;人性;悲剧;女性意识;中西融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3-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08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颗传奇般耀眼的流星,横空出世的才女张爱玲以其个性化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小说总是笼罩着一层荒凉之感,语言也极具特色,叙事手法融贯中西,其作品不断解构人性的卑鄙、扭曲与变形,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显然这位个性鲜明的女作家很难被某个潮流标签所定义,她传奇的人生经历,独特的个性气质促使她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自由畅游,抒写了一曲传奇苍凉的悲歌。
一、张爱玲的人格个性及形成原因
19岁的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句话叙述了她独特的生命体验,短短的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她的许多心理特质:聪慧、敏感、孤独。出生贵族,生来就带有天才的孤独,她的人生从亲情到爱情,从辉煌到破碎,都能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无常感,显示出她困顿挣扎的生命以及难以隐藏的抑郁气质。
(一)天才的孤独与伤痕的童年
张爱玲出生贵族之家,不可否认她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女。在3岁时能背诵唐诗,7岁时写作小说,12岁就发表《不幸的她》,19岁因《天才梦》斩获大奖。1944年拥有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此后也不断发表了很多小说、散文、随笔、议论等。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女,有人说天才就是异类,而异类注定不能被理解,注定是孤独的。这在张爱玲身上得到了验证,孤傲成了她此后生命的代言词。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受家族庇荫的没落贵族世家,虽然在她出生时家庭已然不像以前一样鼎盛,但是这个沉重的家庭背景带给张爱玲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她一出生就注定了她一生的不平凡。父亲张志沂是清末名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唯一的孩子,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纨绔遗少,继承了丰富的财产却吸食鸦片,游手好闲,挥霍无度。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同样也是门庭显赫,与她的父亲不同,张爱玲的母亲深受五四新潮流的影响,留学西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派女性。包办婚姻使张爱玲的父母结合,然而新派思想终与封建遗留格格不入,这样的结合带给这个家庭的是矛盾和无休止的争吵,最终张爱玲的父母离婚了。继母的到来又给她带来了更深重的伤痛,张爱玲厌恶继母的轻贱,厌恶她只顾沉沦贪欢,厌恶她对自己的残忍寻衅。家庭的种种不幸让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失望,也让她体会到了人性的残忍,使她成了一个长期沉默的人,一个性情孤僻的人。
张爱玲生于乱世,家族从往日的辉煌到没落,让她较早地体验到了人间的冷暖无常,个人的成长经历使得她的个性变得抑郁而孤寂。阅读她的作品总能有一种荒凉的独特体验 。
(二)创伤的爱情体验
除了早期家庭亲情的創伤体验,张爱玲的爱情经历也是非常坎坷。父爱的缺乏使她容易倾心于大龄男子,这样的她活得很寂寞,死得也很寂寞。
在她的爱情经历里读者比较熟悉的是胡兰成,这是一个比张爱玲大14岁的男人,不仅做了汉奸,而且风流成性,在这段感情里她卑微到了尘埃里也没有开出花儿来。在乱世中相识相爱,胡兰成给张爱玲的爱情体验让这个娇艳高冷的女人变得如此卑微,这种体验被深深压在潜意识之中,并且影响了她的创作。比如《小团圆》中,邵之雍就是胡兰成,而九莉则是张爱玲自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认为胡兰成懂她,所以明明受了伤也要忍着,这是一个女人生来带有的特质,柔情纯洁而善良。1956年张爱玲到了美国结识了赖雅,爱上了大她几十岁的男人,在他身上寻求安全感,这是原生家庭爱的缺失带给她的影响。她和赖雅幸福的日子并不多,他们在物质上也不宽裕,张爱玲总是需要不断写作获取收入去支付丈夫高昂的医疗费用。伴随着赖雅的离开,孤寂感又一次如同洪水一样侵袭着这个女人。
在爱情上终不圆满,种种爱与安全感的缺失成了她一生也甩不掉的影子。所以她的作品总是善于从两性关系婚姻的角度切入,揭示出生活的底蕴,叙述“家史性”故事。
张爱玲的人生是一场传奇的悲歌。虽然出身名门贵族,但是童年的生活却阴冷恶劣。父亲没有给她应该拥有的保护、安全感以及喜爱,带给她的只是惶惑的疤痕,母亲没有给她温和柔顺的关心,更多的是挑剔、灰心和背离。成年后的她经历战争、混乱、逃离。爱情的悲剧又增加了她身上忧郁孤傲的气质,她的创作被印上了灰色的底调。[1]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是她的个性。
二、从个性心理出发解读张爱玲的文学创作
(一)人性弱点的展现
张爱玲总是在她的创作中把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她剖析了人性的自私、残酷与无情等特质。在她的文学世界里,笔下的人物自私、虚伪、吝啬、贪婪……显示出了真实日常生活的阴暗和不堪,这种创作特色实际是的她心灵的反映。[2]
生于乱世,破碎的童年和爱情使张爱玲失去了对人生和未来的乐观想象,在她的笔下人性不是绝对完美的,而是丑恶复杂的。比如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是一个由于性的压抑而走向变态的人物。在黄金和情欲的枷锁之下她成了一个扭曲的女人,一个阴郁、狂躁、可憎、可怜、变态的女人。在张爱玲笔下同样也有一群男性形象,仔细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可以发现她笔下的男性大多都带有一种丑恶的特色,少有正派的男性形象。究其原因,或许与张爱玲的生活背景有关,张爱玲小时候时常会受到父亲的虐待,她的弟弟软弱无能,那个让张爱玲低到尘埃里的丈夫胡兰成,结婚后接二连三地与别的女人交好。在张爱玲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男性带给她的影响最终反映到了她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是个风流浪子,又如白三爷,他留恋于风流场所,抽食鸦片担不起作为父亲的责任。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无论亲情还是爱情仿佛都与自私变态的人性连接在一起。《琉璃瓦》中父母养女儿以钓金龟婿,却不管女儿的幸福。《心经》中许小寒和其父亲许峰仪之间惊魂动魄的不伦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对红玫瑰玩弄后遗弃,对白玫瑰无声折磨,表现出极度的偏私与软弱。除了这些,她笔下还有一些对命运逆来顺受的人,忍受命运度过一生。452F8187-7752-45FF-A17F-EB9E6F421547
总而言之,那些在正统文学中对美好人性的呈现,在张爱玲的笔下很少出现,反而被她拆解了,归根结底这与她个人传奇、孤独、忧郁的心理体验密不可分。
(二)荒凉感与失落者的悲剧表达
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我只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个人的成长背景以及爱情经历使她的作品有种无常感,失落者心态造成了其作品中笼罩着的世纪末的荒凉感和悲剧意味,给读者带来独特的体验。
以《倾城之恋》为例,从题目出发,就知道这描写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爱情,故事发生在香港,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在亲戚中备受欺辱,她离异后寄居在娘家,在偶然中她认识到了风流浪子范柳原,在谋生与谋爱之中,因为青春的消逝,因为旁人的白眼,白流苏选择去勇敢搏一次,她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两人最终因为战火成就一段倾城之恋。这看似是一个传奇,辉煌的香港沦陷从而成全了浪漫而激荡的爱情,故事最后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起了,她们结婚了。但是文本结局这样描述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她,一座大都市倾覆了。”“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 [3]结婚看来似乎是美好的结局,但一座城的毁灭换来的是一段情的延续,千千万万的人死去了痛苦着,这何尝有不是一种悲凉呢?后来的柳原再也不和她闹了,“他把俏皮的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3],白流苏得到了她想要的,但是她没有得到他全部的爱,这对她也是一种悲凉,一种怅惘。恋爱中对峙的双方都是有各自的欲望和功利心的,何尝不荒凉呢。小说的悲剧意味不止于此处,社会的丑恶,女性的生存困境在小说中同样刻画得淋漓尽致,男女的婚姻被金钱纠葛,女性沦为商品,为推销自己而厮杀,这也是悲剧。[4]流苏和柳原两个情场高手互相试探,不知道她们究竟有没有爱情,但是可以看到女性的挣扎,饱含荒凉之感,其创作心理得到充分展现。
(三)女性意识的体现
作为横空出世的才女,在张爱玲的创作中也表现了独特的女性意识。她笔下的各种女性人物栩栩如生,这和张爱玲本人就是一名女性作家以及她的创作心理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女性描写的痴迷其实也是对自我命运的映射。
以其小说为代表,在她的小说中拥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真实传递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张爱玲笔下也有很多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进行分类。第一类形象以《心经》中的许小寒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代表,大都有着变态的心理意识和强烈的人生欲望。第二类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以及《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为代表,显示出女性独立的生命姿态。第三类则是拘泥于当时社会旧有的准则不敢违抗的家庭妇女形象。[5]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例,她传统又开放,柔弱又强悍,败落的家,守旧的母亲,唯利是图的哥哥嫂嫂,所有的种种逼迫促使流苏强悍起来,她很有主见,丈夫对她不好,她毅然选择离婚。在谋生中,白流苏勇敢出击,成为一个为自己未来奋斗的骑士,作品中包含女性意识。
总之,张爱玲对其笔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地阐述,把男权社会对女性悲惨压迫的状况以及女性的相互杀戮描写出来,对笔下人物的心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把人物的情绪通过意象表达出来,她对女性的描写有批评也有赞美,其作品不再是男人为中心,具有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
(四)中西融会的内心积淀
出生在没落的贵族世家,张爱玲在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为她安排了中式私塾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香港教会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毕业之后,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接受了教育,西方的文化培养以及母亲带给她的影响还有生活国外的经历,又让她的作品有西方的韵味,形成了中西融会的内心积淀。集中表现在她的创作风格技巧、语言特色以及思想倾向等方面。
首先,从叙事来说,张爱玲在现代文学的作家队伍中,是极会讲故事的一位。她的叙述带有中西融合的特色,她的小说既保留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又对西方的叙述视角、结构以及风格都加以借鉴。她喜欢运用讲故事的叙述结构,让文章明白晓畅思路清晰,娓娓道来。例如《倾城之恋》是典型的讲故事的叙述。把白流苏离婚寄住在娘家作为开端,与范柳原的爱情纠葛作为小说的发展,最后因为一座城的陷落成就一段情为结局,娓娓道来,故事完整动人。
其次,张爱玲的语言文白相济雅俗结合,她的语言生活化,其中也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色彩底蕴,很有一些的《红楼梦》笔致,充斥着浓郁的《红楼梦》语言氛围。比如《倾城之恋》中的古典韵味就十分浓厚,作品经常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笔触色彩。[6]白流苏端详自己的那段描写“脸庞很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的清水眼……”这样的语言描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使得作品饱含古典气息。在《倾城之恋》开头还体现了古典的音乐美,“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本就带有东方色彩,流动的文字同时富含音乐之美,扣人心弦又不脱离创作的悲凉基调。
再次,中西融合的背景也影响了她对人物的设置,她笔下的人物有两种文化的交融趋势。《倾城之恋》中一半是土一半是洋的范柳原,他吃喝嫖赌,这是洋化的一面,但是其思想中又透露出封建的一面,他是两种文化的典型结合体;又如半新半旧的白流苏,她谈恋爱勇敢做自己人生的女骑士,这是她现代的一面,另一方面,她又是传统的对男性依赖。人物呈现非善非恶的“不彻底”也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对照。
最后,从思想风格出发,虽然张爱玲是中国文坛的作家,但是其作品仍然带有西方色调,比如张爱玲的《沉香屑》的风格与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十分相似,她本人也对此表示赞同。作为优秀的上海世情描绘者,她的小说中有大量以上海为背景的创作。有在租界没落大户人家的故事,比如《花雕》中的郑家、《倾城之恋》的白公馆等等。小说在内容上,或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中国都市男女的情感爱情状况,暴露人性之中的阴暗一面,或是从两性关系出发描述传奇,富有悲凉的意味。西方作家诸如王尔德、毛姆等的作品都流露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怀疑,表现出一种幻灭感,张爱玲结合其自身的生命体验,对这样的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有不由自主的认同[7],她作品中荒凉和悲剧意识的表现就是最好的印证。
三、结语
张爱玲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传奇。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得她的个性带有难以隐藏的抑郁和孤寂,人性的弱点、生命的苍凉在她的创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她的人生好像包装华丽的胭脂粉,被狠狠砸在地上,留下破碎的盒子和满屋的浓香,孤独或许就是她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1]倪金艳.从心理创伤看张爱玲及其文学创作[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3(04):50-66.
[2]赵春蓉.張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2): 81-83.
[3]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柳亚飞.论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爱情悲剧[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3(11):23-24.
[5]姚昌美.张爱玲小说中的几种女性形象剖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01):230-231.
[6]王岩.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语言艺术的文化解析[J].小说评论,2010,(02):72-75.
[7]王源.从其个性心理结构解读张爱玲的文学创作[J].山东社会科学,2009,(10):117-123.452F8187-7752-45FF-A17F-EB9E6F421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