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的一年
2022-05-30冬至
冬至

病中的她
这一年的寻常日子,就像一场梦。我想用第三人称讲述。
梦是镜像碎裂,缤纷闪烁;梦是语焉不详,雷声大作;梦是蝴蝶扇动翅膀,花粉飘落。
夜读
晚饭后,生病的她早早睡去。他抱着一摞书穿过门厅,来到远离卧室的厨房,打开油烟机的照明灯,沉浸于夜读时光。
厨房狭促。一张木制折叠餐桌紧贴一侧墙壁。杏色墙砖上并排装着两个电源插座。某一年,他用黑色记号笔在插孔上勾了两张嘴——笑的是他,哭的是她。
马克杯里,白天的咖啡残渣释放出浓郁的焦糖香;窗外,蝉鸣不再,蟋蟀的叫声变得短促不安;只有孩子的吵闹声在干爽的空气中显得愈发嘹亮。夏日进入尾声,秋天悄然降临。
他的思绪不时从书中飘离。
灶台上的器皿泛着幽幽清辉。昔日光彩照人的墙砖、厨柜、碗碟……经过岁月的洗涤,变得光泽内敛。如同莫兰迪的画,淡雅,浑然。事物一旦变得寻常,就会被忽视。时间令万物回归无名。
威士忌酒瓶里插着几株枯玫瑰,窗外的车灯不时将其划亮。那是年初她生病时,他为她买的。他把一捧花分成两束:一束摆在床头,一束放在客厅。玫瑰枯萎后,他把几株残枝拿到厨房阳台,插在翡翠色的空酒瓶里。现在,枝头花蕾红色褪尽,花瓣皱成旧纸颜色,呈现出清寂的衰败之美。
他以极慢的速度阅读。在一些句子或段落间停顿,试图理解背后的深意。今晚,他被理查德·弗兰纳根的小说《行过地狱之路》中的一句话触动:“人生只能被展现,无法被解释。不直接指涉事物的字眼反而才是最真实的。”

19 颗黑枣

一杯拿铁
蒲公英
“活一天少一天。”
“活一天多一天。”
“死亡是一种牵引力,多活一天就离它更近一步。”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悲观?”
“不是悲观,是真相。”
“生命不生不灭,增益与减损同时发生。”
无数个夜晚,他们在客厅席地而坐,促膝长谈。他们格格不入,游离于人群之外。他们相信,置身边缘才能看清内部,认清自己。
客厅亮着疏懒的灯光。在明亮、自然、轻松三种照明模式间,他们常年使用后者。有一年秋天,因忘记关灯,他们远行归来,才发现灯已长明半月。
他们把客厅改成书房。书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爱德华·霍珀的画册立在书架醒目位置。他着迷于霍珀画中营造的神秘氛围。尤其是那些表现都市男女的画作:孤寂、冷漠、疏离、不安。鲜有画家能像霍珀那样,敏锐地捕捉到看似稳固的生活背后潜藏的危机。
他深情且困惑地凝视她——这个容颜不再的清瘦女人,这个一度有着常人不及的理解力与洞察力的女人,这个喜欢独处的女人。
一枚蒲公英种子莫名出现在地板上,像个游魂徐徐滚动。他的目光追随着它,眼前浮现出那年秋天他们在西部旅行的画面:他们驾车行驶在荒凉的公路上,赶在落日前露营戈壁,在寒风与血色夕阳中携手漫游……
“秋那边应该很凉了。”她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她早就习惯了山里生活。”他盯着蒲公英说。
她转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乔治·夏勒的野外考察手记。译者是秋。
秋是个物质清贫、精神富足的女人,她个子矮小,精力旺盛,至今未婚。一个人常年住在北京郊外的山村,靠零散的翻译过活。攒够一两年的生活费后,她就停止工作,把时间投入到拍摄蜂和蛇。她经常带着帐篷,只身一人露营荒野。
一周前,秋坐了三个小时的公交车来看她。给她带来自己采摘的酸枣芽,说是可以安神助眠。她们聊了聊共同认识的人和事。话题比想象中的少,她们的生活都很简单。
秋在客厅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回到百公里外的村庄。临别前,秋借走了《树的秘密》。她泪湿双颊,秋说会再来看她。秋是她唯一保持联系的大学同学。
蒲公英不见了。躲进房间的某个角落。他知道,某一天,它还會出现。
电影《永恒与一天》的配乐在播放器里低徊。他喜欢希腊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电影配乐。艾莲妮几乎包揽了安哲的所有电影配乐。悠远的手风琴长音衬托着黑管的低沉与小提琴的欢快,仿佛海浪拍击礁石,层层递进,时而气势磅礴,时而隐匿无声。即使没看过这部讲述临终老人追忆往昔的电影,也会在沉郁与轻盈间哀婉与喜悦之间,感受到音乐中流淌的诗意。
他关掉音乐。静默顿时充盈房间,仿佛任何声音都无法侵入。
极光
他合上书,在厨房的黑暗中呆坐了一会儿,似乎想起什么。他起身打开冰箱,从冷藏室端出一早揉的面团。揭开凝着水珠的保鲜膜,面团在长大变轻。他轻轻闻了闻,凉丝丝的黄油麦香被吸入他的鼻腔。他感到心满意足。冷藏发酵烤制的面包口感更佳。
他蹑手蹑脚来到客厅。绕过某处会吱扭作响的地板。这些橡树即使被切割成地板依然活着。在不同的季节,它们会收缩、膨胀。在某一刻——有时是半夜——突然发出一声犹如关节错位的嘎巴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
他站在飘窗前,拉开纱帘。浑蒙的夜空挂着半轮西行的弦月。非必要不出京。今年他站在窗前向外张望的时候格外多。有时他看着街景,听楼下人闲聊。更多的时候他一脸茫然,心里空落落的,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期待什么,他也不清楚。
生命在黑暗中孕育,在阳光中成长。窗台上的花盆里,枇杷、荔枝、柑橘……他埋下的果核长成绿植。这些南方物种,无法适应北方气候,即便枝叶挺阔,也不会开花结果。他更喜欢那盆春天从野地里带回的夹杂着蚯蚓粪的干土,浇过几次水后,长出了马齿苋、萝藦、泥胡和纤细的狗尾草。
对面5楼的灯亮了。一个谢顶的男人,挺着肚腩挥舞苍蝇拍。他看着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他们都穿着本命年的红内裤。
一阵阵艾草味飘进窗内,又有人在深夜艾灸了。也许是楼下独居的老先生,他的老伴去世二十多年了。老先生仿佛活在时间之外,不论做什么都慢悠悠的,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路口的红绿灯不停变换,像悬在半空的两只眼睛,注视着夜晚冷清的街道。
杜仲在风中摇晃,叶子还绿着就落了。它的叶脉与茎皮内藏着丝丝秘密。
他关上窗,走进卧室。
她睡得很轻,像是漂浮在水面上,浅浅的呼吸声。
注意力在哪儿,世界就在哪儿。他闭上眼睛,无法入眠,眼睑内极光闪耀。
他突然笑了。

雾中秋夜

二月雪
记忆
他独自走在河岸,弯腰捡起一粒石子,地上出现一个浅凹。他把石子丢入河中,河水上涨一丁点儿,却难以察觉。
人类发明时间概念,希望藉此框定无限,令无常显得有序。事物有了时间坐标,便有迹可循,同时也产生流年易逝的错觉。
从前,她是个理性坚忍的人,有着锚一般的稳固性格,从不担忧未来。她信奉饥饿带来食物,疾病带来医药。他们曾是工作搭档。有一年早春,他们在湖北潜江采访,两人走在大雨滂沱的泥泞乡路上,浑身湿透。他不停咒骂天气,抱怨湿冷。她则一语不发,默默忍受。
现在,她步入更年期,变得敏感而脆弱。一种看不见的暗物质扰乱了她的生物钟。她时常幽闭在自己的世界中,仿佛坠入虚无的罗网。她成了自己的陌生人。书中的某句话;天上的一朵云;雨后蜗牛的爬行轨迹;乃至一阵微风拂过脸庞,都会引起她伤感甚至恸哭。一天上午,她被《天使望故乡》里的一句话击中,一瞬间泪水夺眶:“我们赤裸裸孤单单流亡至此。在母亲黑暗的子宫内,我们不知道她的长相;我们从她肉体的牢笼来到世间这个不可诉说、不可言传的牢狱。”
今年,她写了近千首短诗。此前,工作之外她几乎只字不写。在她固有的认知里,这个世界无法用语言描述。
现在,她试图借助文字,摆脱脑海中记忆之浪的狂暴冲击——
48年后/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谜
瑰丽的形而上/可疑的/命运
被遗忘的/橄榄树/静如死亡
每一天/都是/同一天
她想归还自己/却找不到/失主
她不怕黑暗/因为/她就是/黑暗
痛苦只是影子/转过身/即是阳光
一片落叶/神的/信件
她睡觉时/听到/枕头的心跳
他牵着一匹斑马/穿越/斑马线
一架飞机/划过/她的指甲
酩酊的金龟子/穿过海滩/繁华不远
他拥有/绝版的/车、电脑/女人
他们的婚姻/没有重量/只有色彩
美/在/你不在的地方
爱,像只惊鸟,振翅而飞。我,假装局外人,若无其事。每个人终将独自走完最后的旅程。此刻之前的与现在之后的都已过去,所有描述永远无法抵达正在发生的。

他们——夏末的影子

残荷与锦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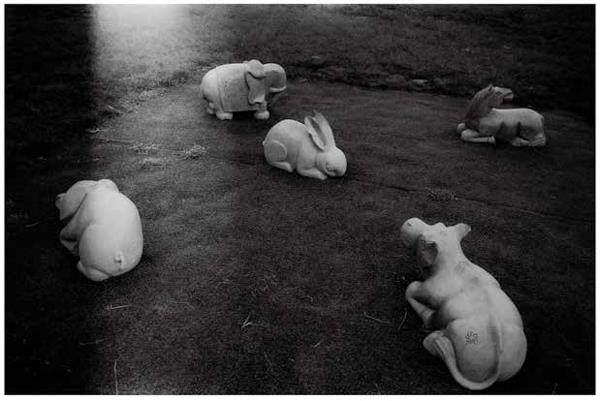
黄昏的公园

戈壁寒秋

晚霞中的一架飛机

冬日卧室

那年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