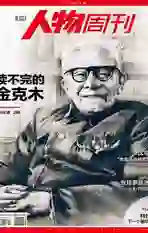与大都会博物馆的奇幻爱恋
2022-05-30孙凌宇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厅。图/视觉中国
“美术馆着火了,一幅名画和一只猫,只能救一个,你救谁?”这个问题在克里斯蒂娜·库尔森(Christine Coulson)听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无需思索、犹豫,如果你也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近三十年,估计会以一样的神情脱口而出:“ I would definitely choose the painting”。
她在2022年出版的《挑选缪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奇幻故事集》中详细阐释了这个观念。《藏品课》里艺术品纷纷发声:“但我们会继续活着。我们是证据,是迟迟不肯离去的、沉默的证人,挂在墙壁上,站在底座上。人们存在过的证据。”她在回复采访的邮件里进一步说明:“所有与之相关的人——艺术家、收藏家、管理员、博物馆参观者——最终都会死去。但艺术永存。”
保安是博物馆里“最伟大的英雄”
艺术会永存,艺术品也是。不出意外的话。
2002年10月6日,有着500年历史的亚当雕像在大都会展厅展出时突然倒下,整个头部掉落,身体碎成无数块。
亚当“遗体”被发现的那个早晨,成了许多亲历者难以忘怀的时刻。之后大都会耗时十几年对其进行修复,直到2016年才开设全新的展厅展出。但这个略显诡异的插曲在库尔森脑海中还远未结束。她忍不住要想,“这肯定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如果把亚当赋予灵魂,囿于石膏身体的灵魂是一定想要活动一下身体的,他准备迈出自己人生一小步的时候,就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她无意捕捉蛛丝马迹进行调查,而是决定将这种想象放入小说,这样的话,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亚当为什么神秘摔倒,一定会是有趣的故事。”
从亚当雕像的角度写的故事是她二十多年后下笔的开端,在这期间,她日复一日徘徊于博物馆的尘封小路和日常活动,带着新奇的眼光穿梭其间,工作、观察,在华丽深邃的艺术品点缀下,展厅间的水泥墙壁仿佛也变得松软,成了一处处值得欣赏的自然景观;博物馆内员工的语言和日常活动也同样令她着迷,她从不写日记或做笔记,仅凭记忆像采集蝴蝶一样收藏着这些无形的习惯。
“博物馆有一种非常像家庭的文化,鼓励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别人讲述同样的故事,这种重复创造了一种制度性的民间传说。为了捕捉大都会博物馆的幕后世界,小说必须既富有想象力又符合现实,而这些故事无疑为我的创作提供了真相内核。”
《捐赠人》里描述的为了答谢某位一次性捐赠了近百件珍稀藏品的大人物而邀请他来馆内拍照的事情确有发生,库尔森在书里用夸张的口吻还原那份隆重——著名摄影师带着大批人马精心挑选拍摄地点,不仅从场景中挪走不宜入镜的摆设,“恐怕还为了让光线变得柔和而调整了云朵的位置”;《夜间行动》的灵感来源于一则大都会博物馆流传已久的八卦——两个保安在储物柜里做爱被抓。她从来不知道具体的人是谁,便创造了一对情侣警卫,Radish和Maira,作为她想象中的当事人。
陈丹青在《纽约琐记》开篇回忆道,“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是警卫,一色青灰制服,但行头简单,只是徒手,每座小馆至少派一位。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正好没有观众时,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文艺复兴馆、印象派馆、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馆,男女警卫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来回闲步。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他们是仅有的活人,会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识。”
当他瞥见哪位百无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偶尔会闪过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还没看够么?相较之下,在博物馆工作的库尔森仿佛拥有某种“特权”,当她心里冒出同样的疑问时,她可以毫不费劲地得到答案。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博物馆每周都会举办活动,让大家认识、了解不同的同事,库尔森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与他们紧密合作,甚至可以说是一起成长,那些在游客眼里默默无闻的人物对她而言是“最伟大的英雄”,“他们对博物馆的奉献和策展人没什么两样。”

克里斯蒂娜·库尔森。图/Jackie Neale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的值班人员。图/本刊记者 孙凌宇
她了解他们,视他们不仅如同事,更像家人。考虑到保安实际上花了最多时间在展厅,与艺术有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她在小说里温柔地“赋予”了Radish出众的能力,能让大都会的艺术品中的情感传递到自己灵魂深处。她在书里写道:“他对这些展品的感知与一般的策展人或参观者不同。他能感到提埃波羅笔下凯旋的罗马将军马略傲立于马车上的昂扬气势,好像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看到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他感到悲恸万分,仿佛苏格拉底大口咽下毒药后,他自己就站在那间屋子里。看到洛伦佐·巴尔托里尼的《德米多夫桌雕》上睡意昏沉的人物,他几乎要瘫倒在地,仿佛喝了安眠药,整个人都要失去知觉了。”
看似无奇、感知力却异常敏锐的保安,他的悸动、悲喜哪怕是面对一起巡逻的女友都难以获得共鸣,反倒是在一尊雕像的眼里看到了惺惺相惜。“他经常选择从单铎神庙附近的楼梯间进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整面墙的窗格和窗格前宏伟的庙宇,以及古老的历史遗迹与现代生活和中央公园的人流车流之间的碰撞。亚当和其他的艺术品不同,他始终能感受到这座雕像的欲望,倒不是针对那个苹果的欲望,而是针对另外某种乐事的欲望。感觉有点像饥饿,但比饥饿更加迫切。雕像和保安,二者都有一种经久不变、来自心底的痛苦。”
而五百多岁高龄的“亚当”也同样留意到了这位“个头格外高、身形格外瘦削”的保安,“他花在欣赏艺术品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而且他似乎能看得懂亚当内心翻江倒海般的渴望——对自由行动的渴望。”于是,他奋力挪动,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吸引视线,“省得这个一时纵乐的小保安在楼梯间被他领导撞见。”
艺术界翻天覆地,博物馆界变化很慢
光是一个人与一件展品之间,都能有如此辗转动情的关联,不难想象,库尔森口中“小城市”般的、占地13万平方米、拥有超过2.2万名全职员工和三百多万件展品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有着怎样“惊人的复杂性”。“这个地方像是一杯奇怪的鸡尾酒,酒里有充满了自信与优越感的天选之子,也有被宽容相待的怪咖;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来到了应许之地。”
馆内有962个陈列室,按照每个展馆至少一位保安的配置,光是保安队伍就有近千人。“新的招募标准要求所有保安必须有大学学历,这条标准剔除了近千人队伍里的老油子和像赌场掮客一样膀大腰圆的家伙,招进来一些表演艺术家、剧作家、音乐家和电子游戏设计师。”
书里除了详细描写保安、灯泡修理员、慈善会引导接待女孩等平日容易被忽略的人群,也不乏馆长、策展人、捐赠者这类有头有脸的人物。扉页上标明此书是为了纪念1977年至2008年的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菲利普·德·蒙特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在库尔森眼里,“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在他担任董事的31年里,他激励员工尽力工作。作为一名领导者,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既设定了高标准,又尊重他人的专业知识。”
小说的故事多发生于她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的前10年,“那是博物馆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时,大都会博物馆是由一小群古怪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经营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我们像是在一个完全模拟的世界,自行运转地工作,这意味着即使我很年轻,我也经常和这些资深人士在同一个房间里。这种接触教会了我所有的东西,也确实为这本书的某些章节提供了素材。”
大约在1996年,她负责传递一张备忘录,上面写着“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将带着缪斯女神出席与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会面”,这短短的一行字启发了日后小说集里的同名故事《挑选缪斯》。“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馆长带着他自己的缪斯来开会,会发生什么?再过20年,我才会在小说中探索这个想法。”
她照例让艺术品“活”过来,来自油画、素描、陶瓷、摄影作品中的“女神”们纷纷来到馆长办公室参加竞选。“《挑选缪斯》中的馆长角色并非照着菲利普完全还原,但不可避免会有他的影子(菲利普英俊又令人生畏)”。当她收到第一本印好的小说时,她第一时间便是亲自送去给菲利普。
“在小说发生的那个时期,大都会博物馆是非常正式的,所以人们非常重视作品的写作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大都会博物馆也有自己的内部语言,通常都是首字母缩略词,因此可能会让外人感到困惑,比如ESDA,代表欧洲雕塑和装饰艺术系,我们发音为‘Ez-dah(诶兹达);AAOA(Arts of Africa Oceania and the Americas),代表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艺术。各部门间传递专用的、上面有洞的黄色信封我们叫‘奶酪;餐厅是‘员工咖啡馆;图书馆则直接唤以捐赠者的名字‘沃森。在很多方面,学习这种简称是你快速融入博物馆员工文化的一部分”。
透过最后一个故事《纸雕》里负责整理纸袋的女孩Edith,读者可以看到新人的心路历程,这其中多少有库尔森本人当年的自我投射。她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一样拥有艺术史硕士学位,为了迎接新工作,她没有“借一双好鞋”,而是直接买了一双,“放在办公桌底下,只在博物馆里才会穿,这样它们才会更耐穿。我还把奶奶的西装裙改短了,穿去上班。”
1991年,她在大都会博物馆欧洲绘画部做暑期实习生,参与来年哈夫迈耶收藏展的准备工作,负责整理美国印象派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和美国传奇艺术收藏家路易辛·哈夫迈耶(Louisine Havemeyer)之间的信件。那次奇妙的早期经历让她第一次看到了博物馆背后的世界,那时她便确知自己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过去30年,艺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博物馆界的变化要慢得多。当我开始在博物馆实习时,我马上就知道我想长期呆在那里。我周围的人都在那里工作了20年、30年,甚至40年,所以这个机构的员工文化使你在那里生活的想法成为常态。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真正离开。”
“我和大都会博物馆的关系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库尔森从小在纽约长大,很早便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常客,但被允许参与到观赏之外的工作中,感觉还是很不同。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她在1994年初回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受雇于发展办公室,负责撰写展览描述,这是她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作生涯的开始;接着她先后担任总监首席顾问和高级写手,分别负责撰写演讲稿以及为英国艺术新画廊的所有艺术作品起草墙上的标签。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走廊。图/视觉中国
“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那么容易,我一直都能写,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读书太多的缘故。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约翰·契弗、格雷厄姆·格林、多萝西·帕克、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朱利安·巴恩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声音,能够从第一句话就把你拉进他们的故事中。我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了25年各种形式的文章。2016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我写的关于博物馆幕后生活的文章。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九个月后,她获批一年学术休假,开始动笔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奇幻故事集》。身为作家期间,她相当自律,每天从早上10点写到下午3点,除了在谢尔德岛朋友儿子的房间借住几星期,其余时间都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固定驻地。“我会在下午修改我的草稿。因为我想写这本书已经很久了,所以写作对我来說非常容易。把它写在纸上就像是一种解脱。我没有使用任何图书馆的资料,因为这本书是虚构的。在那一年里,我偶尔会回到大都会寻找灵感;例如,在写《肉与奶酪》这一篇之前,我特意让建筑部门的负责人带我去博物馆下面的隧道看看。”
2019年4月,库尔森离开大都会博物馆,开始全职写作。近日她刚刚完成了下一部小说的初稿,内容仍与她在博物馆的经历直接相关。这座建筑无疑是个取之不尽的素材库,连同置身其间的一切耐人寻味,就像她总结的,“生与死、性与爱、战争与宗教、权力与金钱。不仅仅是在大都会门内啊,坐在大都会门前的台阶上就能看到这些。”
她在大都会博物馆度过了大半辈子,如今又持续写着与之相关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我和大都会博物馆的关系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读者在感受奇幻世界之余,同样也能体会到这般深情。有人评论道,“翻开这本《挑选缪斯》仿佛手握一把打开大都会博物馆不为人知幕后角落的钥匙,带我们深入博物馆那些不对游客开放的神奇角落。这不仅是一个个关于藏品的奇幻故事,也是作者本人无数的生命瞬间,爱和时间造就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