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村”的日与夜
2022-05-30郑立颖
郑立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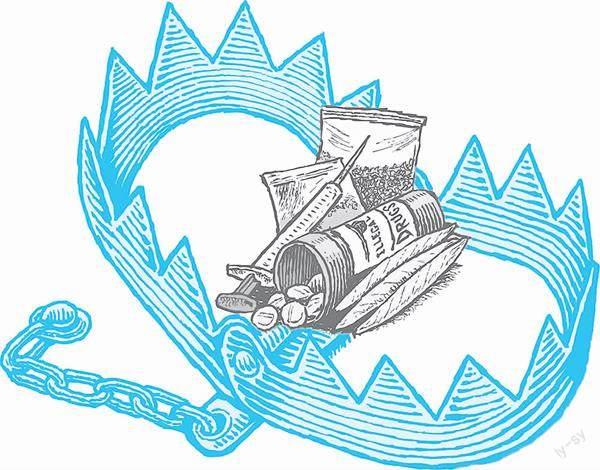
阿红看起来平和而安静,她脸上的皮肤很光亮,短发整理得一丝不苟,走在广州拥挤的街头,没人会想到她的大半生都在与毒瘾纠缠。
阿紅今年55岁,她至今记得,人生中的第一口白粉是在嘈杂的酒吧里吸食的,那一年,她不满20岁。之后在毒品的深渊中,阿红度过了25年生不如死的日子。她后来丢了工作,也离了婚,“家人的心都已经被我伤透了。”
阿红四次被送进戒毒所,在里面度过了八年的时光,但总是陷入戒毒复吸的过程中,反反复复。“后悔,自责,厌恶自己,但就是戒不掉。”阿红说,就连怀孕的时候,她还是坚持每天出门找毒品。
直到2012年,阿红在位于广州市郊的女性戒毒互助会戒毒成功,她的人生出现分水岭。后来,她又选择留下来,帮助更多的人摆脱毒瘾。在这里,被毒品打上烙印的姐妹们互相陪伴,一起逃离不堪的人生。
“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我都是不配的。”阿红这样总结自己过去的生活,这些年,她和家人的关系正慢慢修复,“她们觉得我不但能戒毒,还帮助其他人戒毒,做了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白粉,我什么都不能做”
阿红出生在广州市,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企业高管。在16岁那一年,经父亲的朋友推荐,她去广州一家国企工作,后来又去深圳开展新的业务,阿红还被合作的香港老板选中,兼职做验货组长。“86年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工资每月也就是几十块,但我的工资加上验货组长的收入能有好几百,因为跟着企业过来的,吃住都不要钱,还雇了洗衣工。”
那时候,阿红经常去香港买名牌手表,衣柜里挂满了名牌衣服。阿红还和一些年轻人经常出入酒吧,并开始慢慢接触“白粉”。
阿红不知不觉中上了瘾,每天下班回到租住的房间,她会把烟丝倒出去,将白粉灌在里面,抽上两口。
有一次,公司组织泡温泉,阿红身上没有带白粉,整个人开始不对劲了,她赶紧提前回到深圳,找人拿到了货。“吸毒的人,饭可以不吃,但没有白粉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做。”阿红说,一旦卖白粉的被抓进去,找不到货,那一天她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全部心思都在白粉上。
“我必须抽完才能出门,有时候我拿不到粉,那就没办法去工作。”阿红说,有好几次,老板从香港到深圳码头验货,她人在深圳,却为了找白粉比老板到的还晚,最后两份工作都丢了。
于是,阿红又从深圳回到广州,后来经人介绍结了婚。刚开始,家人和男朋友还不知道她吸毒,他们知情后就将阿红送到医院里的戒毒科,“一个疗程两个星期,费用就是一万多,家里人不知道为我花过多少钱。”阿红一直陷入戒毒、复吸的过程中,她也厌恶自己,但就是戒不掉。
1994年,阿红在医院生下女儿,女儿刚出生就有抽搐等毒瘾的症状。阿红家人把她的女儿送到中山医院做了全身检查,万幸的是,女儿在毒瘾戒断后,没有留下其他后遗症。
这之后,阿红四度被送进戒毒所,一次待两年,前后在戒毒所待了八年。“毒瘾好像已经腐蚀了我的心,每次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还是找白粉。”阿红说,她能理解家人,一次两次复吸,他们能原谅,但前后二十多年,反反复复,每当家人得到自己的消息时,不是要钱,就是被关起来了。
她们有相似的经历
阿红第一次走进女性戒毒互助会是在2012年,它就坐落在广州市区10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村子前面是一片水塘。
姐妹们都称之为“戒毒村”,她们也都是“过来人”,年纪轻轻就开始吸毒。阿红当时已经45岁,家里的积蓄快被她败光了。那段时间,她和家人的关系很糟糕,女儿和前夫一起生活。
像是一个疲惫的灵魂找到了归处,阿红告诉自己,再也不要过那样的生活了,她再次鼓起勇气戒毒。
在戒毒村,最初两周到一个月是戒断期,戒毒者刚进来的时候要把手机交出去,和过去的社会关系剥离。“刚开始毒瘾发作的时候,我每天呕吐、腹泻、抽搐,被毒瘾折磨得痛苦不堪,说度日如年,一点都不过分。”阿红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除了难熬的身体反应,最难受的是心瘾,当时谁能给一口白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阿红说,“犯毒瘾的那一刻,人是没有尊严的。”
但在戒毒村,很多人理解这种感受,并给予细心的照料与陪伴。毒瘾戒断期后,阿红开始慢慢融入这里的生活。她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洗漱,吃早餐,然后读经唱歌,劳动,吃午饭,下午也有活动,晚上10点钟睡觉,周而复始。
每一天,阿红和村里的姐妹们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她们也轮流做饭,还会学习弹琴、手工、刺绣等技能。她们在院子里养起了鸡鸭,赚取一点生活费用,冬天的时候,她们还会自己做腊肠和腊肉。
麦麦到戒毒村时30岁刚出头,但她已经是吸毒十几年的“老手”。“我15岁开始吸毒,19岁就去‘上大学(戒毒所),一共进了五次,前后十年,里面的管教都认识我了。”麦麦自嘲道。
麦麦记得,最后一次从戒毒所出来,“妈妈拎了一个大箱子来接我,我当时想出来需要换一套衣服,但不用这么多。”可还没等回家,麦麦就被母亲送到了戒毒村。
“姐妹们像家人一样对待我。”麦麦没想到,这里的人更加友好,吃的也更好些。“她们会特意给我留些瘦肉,上厕所也不用打报告。”除此之外,麦麦觉得这里的人理解她,不把她当犯人来管束。
阿红也记得,她刚来时手臂因过量注射毒品发炎、肿痛,流出的脓又臭又腥。但姐妹们并不嫌弃,反而悉心为她清洗伤口、换药。
她说着说着,伸出手臂展示了一下,上面布满疤痕,“吸毒者一天要注射很多次,胳膊很容易结疤,吸毒的老手还会在大腿根处的静脉上注射,因为那样感觉来得更快。很多吸毒者都会反复用一个注射器,他们基本不会花心思给针管消毒,把白粉兑矿泉水打到身体里都算是讲究的人了。”
从吸毒,到劝人戒毒fv
“毒瘾是非常狡诈的,它甚至能裹挟了人性。”阿红说,“只有我们过来人才能理解这种感觉,复吸是非常常见的,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就算是戒了毒的人,看见别人吸毒不可能没有反应,只能说反应大还是小,你一定会想起那种感觉。”
在戒毒村,她们并不建议没有吸毒经历的人去帮助人戒毒,因为很难理解吸毒者所想。“比如我们之前劝导一位吸毒者,加上了微信。半夜她给我发信息,说家里孩子病了,需要500块钱,一般人会想她确实有个孩子,500块钱也不是大数。”但凭直觉,阿红并没有贸然借钱给她。
半夜12点多,阿红还是带着自己的银行卡去找这位吸毒者,孩子在家里,她却不见人影。“那时候,我甚至希望她的孩子真的病了,但没有。”阿红有些失望。
“为什么这样不断让人失望的人,还要去帮助她,不心痛吗?”阿懵是最年轻的志愿者,也是唯一一位没有吸毒经历的人,她以前是一名独立摄影师。在戒毒村,她常常会问华姐和紅姐这样的问题,她们都是资深志愿者。
“没关系,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过来的,这也是我们的功课,看到人的丑陋还要报以热情,学会宽恕,也要学会用爱和智慧帮助别人。”华姐和红姐总是笑着回复,阿懵在村里做了5年志愿者,她深深感受到姐妹们对彼此的信任和爱,“我们曾经送一个姐妹回归生活,她嫁了人,在婚礼上,大家哭做一团。”
“劝说和帮助吸毒者戒毒,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阿红说,这些人曾经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很有钱,社会地位也高,而现在,他们连份工作都没有,既自卑又自负。
每当看见这些人时,阿红就想起过去的自己。
一个终身烙印
在戒毒村,大多数人从一二十岁开始吸毒,错过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忙于吸毒,找白粉,没有时间学习、工作,甚至谈恋爱结婚。”麦麦说。
麦麦从戒毒所出来后,家里人给她介绍过几次相亲,但很多人一听说她有吸毒的经历,马上就摆摆手跑掉了。
“对于吸过毒的人,社会的接纳度是很低的,尤其是女性。”阿红说,戒毒者回到社会一直非常困难,在戒毒村,姐妹们会学习一些手工,但这些简单的技能还不足以让她们在社会上立足。
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姐妹们还一起手工缝制口罩,“本来社区答应一天给100元的费用,但几个姐妹都不愿意收钱。”阿懵说,她们将做好的口罩捐出去,街道派出所还写了感谢信。她们回想起以前被警察到处追,现在却能收到警察的感谢,这也是一个奇妙的经历。
从戒毒村出去的姐妹也有找到工作的,不过她们能做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比如看门或者停车场收费员。让她们感到恐慌的是周围人的眼光。每当公司要上五险一金时,身份证信息就显示她们吸过毒。有时候,领导会质问,“为什么一开始不交代过去吸过毒?”
阿红已经戒毒十年了,但每次出门依旧感到紧张。“戒毒后有一次陪妈妈去贵州旅行,那时是五月,我们在贵州的一家酒店登记,没过一个小时,警察就来敲门,让我配合尿检。”她说。
去过戒毒所的人都是有案底的,这么多年来,阿红都不敢离开广州市,“每次老同学邀请我去旅行,我都找借口不去,事实上,我是害怕住酒店,害怕耽误大家行程。一旦警方要求配合尿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没有理由不去。”
阿红有时候会想,“吸毒者会成为我们终身洗刷不掉的烙印。”
据《2020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截至2020年底,我国现有180万名吸毒人员。“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字,但我们更知道这是一个个灵魂,和一个个破碎的家庭。”阿红激动地说,社会上很多人不了解这一底层群体,一些人甚至觉得让其自生自灭就好了,但在她们看来,每个灵魂都值得被拯救。
2022年5月20日,麦麦结婚了,对方也是一名“过来人”。麦麦第一次感到如此轻松,她再也不用谨小慎微地扒开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在婚礼上,阿懵穿着淡紫色裙子来当伴娘,戒毒村的姐妹们忍不住拥抱在一起,流下感动的泪水。麦麦穿着白色婚纱,一路笑盈盈地走向圣洁的舞台,舞台背景上写着“爱是恒久忍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吴嘉运荐自《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