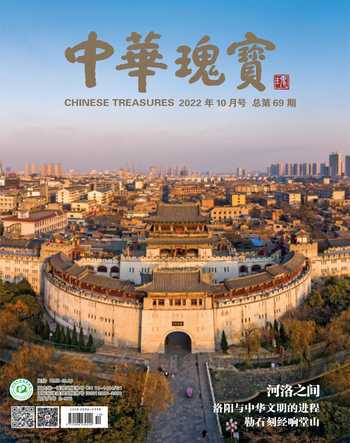夏代都城遗址与河洛文化的形成
2022-05-30薛瑞泽



阳城、阳翟、斟鄩等夏代都城,均建在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之城池、青铜器和文字,在河洛文化形成伊始的夏代的相关都城遗址中都有所体现。
夏代早期都城并不固定,而是频繁迁移,甚至出现一位国君有多个都城的现象。《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去世后,禹即位之初,定都阳城,故有“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之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这说明禹即位之初的都城为阳城,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阳城、阳翟、平阳、安邑、晋阳等地都在河洛地区的范围之内,属于豫西、晋南的黄河中游地区。
禹都阳城
以禹都阳城而论,除史书记载外,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即大城)和城壕,这是城池的典型标志,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和重视,该遗址被认定为禹都阳城。
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发现了东、西并列两座城址,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的地势高于东城。东城因五渡河西移被冲毁,仅存南城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城的夯土轮廓基本清楚,四面城墙基础多有保存。西城城垣略呈正方形,周长约400米。西城南墙长约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东段因水冲损,残长约29米。整个西城为边长约90米的正方形,城内面积为1万平方米。城池的出现是河洛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显著标志,也是河洛文化发展的典型标志。
夏都阳翟
夏禹定都阳翟在古书中多有记载,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阳翟在阳城东南,是夏禹继阳城之后的另外一座都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颍水注》云:“颍水自堨东迳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除都城外,阳翟还有夏启宴享诸侯的附属设施钧台。《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在禹州瓦店发现有20余万平方米的古城址,瓦店西北台地发现了大型环壕,呈西北—东南走向。环壕的西壕南端与南壕西端呈直角,相交于西北台地西南部,形成的西南角保存完好。西北台地的北边和东边有颍河环绕。西壕和南壕构成的人工环壕与流经遗址北部和东部的颍河共同构成完备的防御体系,显示城池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当时的文化遗存除石器之外,还出土了精美的玉器,有玉鸟、玉铲、玉璧等,还有卜骨和酒器。学术界初步认定瓦店遗址为早期夏文化遗存,再依据史书中夏禹定都阳翟的记载,推测这里应该是阳翟之所在,是禹与启的都城。
夏启之居
位于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经过前后三次发掘,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过渡期的新砦期文化遗存。在新砦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城址,属于龙山晚期和新砦期两个不同时期。
新砦遗址有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分大城(外城)和小城(内城)两部分,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很可能是宫殿,抑或是宗庙建筑,面积比二里头遗址的宫殿面积还要大。新砦遗址呈正方形,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贴近城墙下的护城河,南边则以双洎河为天然屏障。新砦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末期,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早期的大型城址,具备了早期国家都城的形成条件,极有可能是建于夏启时代的都城。关于夏启都城问题,西周《穆天子传》卷五曰:“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黄室之丘,应该就是新砦遗址所在地。
禹都安邑
禹都安邑、平阳或晋阳没有发现考古遗存,但文献中尧、舜、禹相继在河东地区建都的传统相沿不断。如果尧都平阳是陶寺遗址,那禹都平阳应距此不远。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曾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唐代史學家张守节指出周成王分封的唐叔虞的地理位置“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即唐代的“晋州平阳县”,故而推测禹在河东地区的都城安邑或平阳应当是一处地方。
在晋南,有可以作为禹都安邑的考古学发现。1959年发现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经过数年的发掘,在第五期文化中区发现了一座城址,目前已查明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位置,在城墙底部两侧都有为保护城墙基部而特意夯筑的斜坡,城墙外侧有城壕。在城内的西南角已确知有20座圆形建筑,还有未做清理的,总数大约为50—60座。东下冯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夏文化在晋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认识夏文化的传播过程以及中国古代都城变化的规律。
夏都斟鄩
夏都斟鄩近年来作为学术热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史书记载,夏启之后,太康即位,都城由阳翟迁到斟鄩。太康在位时沉湎于酒食,导致失国,政权被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夺取,故有“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之说。后羿继续以斟鄩为都,夏代最后一位国君夏桀也以斟鄩为都,所以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调查“夏墟”,在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发现大型遗址,经过新中国考古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基本确认二里头为夏都斟鄩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否属于夏文化,在学术界虽然还存有争议,但其中一期、二期遗存属于夏文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中,没有发现城墙和外郭城,只有30处宫殿遗址,其中1号宫殿遗址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毁于四期。基址略成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2号宫殿位于1号宫殿东北约150米处,建于三期,四期继续使用。该宫殿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8米,由正殿、庭院、廊屋和门道等单体建筑组成,建于夯土台级上,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这种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具有重要的领先意义。
青铜器、卜骨和刻划符号
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青铜器,在夏文化遗址中逐步出现。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了1件铜爵,器表素面,合范之缝清晰可见,透露出制作工艺较为原始的状态。在新密新砦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1件铜容器残片,可能是鬶或盉的流部。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中发现有少量青铜器,出土了青铜刀、青铜铃和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三期文化层中所出土的青铜器更多,四期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新增加了斝。出土的青铜器的造型种类的增加和器皿制作工艺的复杂,都显现出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成熟。
作为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文字虽然在夏代早期尚未出现,但在夏代都城的相关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卜骨。在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一期出土卜骨2件,第二期出土卜骨8件,这些卜骨均为猪肩胛骨;第三期出土卜骨39件,主要是猪肩胛骨,牛与羊的肩胛骨出土较少;第四期出土卜骨57片,除上述三种动物的肩胛骨外,还有鹿肩胛骨;第五期出土卜骨39件,多以猪、牛、羊等动物的肩胛骨为主;第六期出土卜骨30片,骨料为牛肩胛骨与猪肩胛骨,其中牛肩胛骨经过火灼的背面均有清楚的卜兆,这其实是文字产生的前兆。在登封王城岗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出土卜骨5件,分别用牛、羊的肩胛骨灼制,骨面均有灼痕;第三期文化层中出土卜骨6件,骨料为猪、羊的肩胛骨,猪的肩胛骨上有5个圆形灼痕;第四期文化层中出土卜骨3件,分别由羊和猪的肩胛骨灼制而成。在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早期遗存中也发现有卜骨,均有灼痕,较大的为牛肩胛骨,较小的为鹿或羊肩胛骨。禹都阳翟瓦店遗址中龙山文化晚期所发现的8件卜骨,除了1件为牛卜骨,其余皆为羊卜骨,多有烧灼痕。虽然众多卜骨上未发现文字,但无疑为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陶器上出现了刻划符号,其中Ⅱ式杯腹部饰一周划纹,Ⅱ式豆柄部刻划有一个“///”形符号,Ⅲ式豆口沿刻划一个“/”符号,Ⅰ式瓮肩部刻有“\\”符号。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陶器上刻划符号逐渐复杂,Ⅲ式杯底外部在烧前刻划有一个文字,形似“共”字,Ⅱ式碗腹外壁烧制前刻划有“×”符号,Ⅰ式瓮肩部两侧亦各刻划一个“×”符号。在王城岗龙山文化四期陶器上亦有刻划符号,Ⅰ式陶纺轮器面刻有一個“十”字。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的陶纺轮器的一面亦刻有一个“十”字;另一个陶纺轮一面刻有“米”字,中间有一个圈,极有可能是“龟”的象形字。在瓦店遗址中还出土有2件刻符陶片与3件刻花纹陶片,刻符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一个弓箭刻符,显然代表射猎的意义。在二里头遗址陶器中也发现有20多种刻划符号,有的是数字,如一、二、三、五、六、八、十等,还有一些象形符号,这些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很可能为当时记事所用。
进入夏代之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最初的都城。这些从龙山文化传承下来的都城,表现出点状分布、区域多样的特点。从史书记载,到相关都城遗址的不断被发现、认定来看,夏代早期都城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一带,并最终在斟鄩安定下来。与迁都相伴随的是,青铜器在龙山文化后期的都城遗址中逐步出土,制作水平持续提高。虽然夏代没有出现成熟的文字,但使用卜骨占卜则为后来甲骨文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主要用于记事,个别已现文字的雏形。多个夏代都城遗址,展现了河洛文化形成阶段的初始形态。
薛瑞泽,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