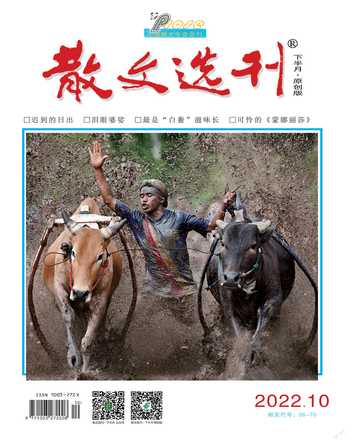那抹馒头香
2022-05-30沈杏
散文选刊·下半月 2022年10期
沈杏
我是南方人,可却偏爱吃北方的馒头。
小镇上有一家老字号的早点铺,每天清晨,里面总是坐满了人。我只要递上两毛钱,老板就会把热气腾腾的蒸笼打开,氤氲的雾气里,馒头雪白的身形一览无遗,清甜的香味扑鼻而来。竹夹子轻轻一捏,馒头腾空而起,落入一片巴掌大小的牛皮纸中。须臾,穿着外衣的雪白馒头就递到了我的小手中,内里往往还积蓄着蒸笼里的热气,有些烫手。我只好忙不迭地将馒头从左手换到右手,再从右手换到左手,口中还不停地“嚯嚯”着。诱人的甜香,丝丝绕绕钻进我的鼻孔,再也顾不上烫,我一口就啃了下去,松软绵长,又有嚼劲儿,淡淡的甜浅浅的香在口中蔓延。一个馒头,足以令小小的我快乐一整天。
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一年多,因为店主的儿子赌博,老店主只好卖了店面还债,离开了小镇。
读初中了。周末的下午,我正在书房温习功课,窗外传来了一阵阵“馒头,馒头”的吆喝声。我十分好奇,推开窗一看,院子里来了一个戴着浅棕色草帽、推着一辆高大黑色自行车的中年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半米高的白色泡沫箱子,旁边已经围了两三个邻居。我心中一动,也拿了两块钱,兴冲冲跑下楼。
馒头住在泡沫箱子里,还被一套雪白的棉布小心地包裹着,拿出来的时候,仍然是热气腾腾的。我轻轻闻了闻,忍不住直接咬了一口,竟然很熟悉,馒头在牙齿和舌頭之间翻滚,唤醒了幼时如云烟般远去的记忆。我抬头仔细端详了眼前这个卖馒头的人:黝黑又鼓实的脸上写满了饱经风霜,灰布衫的衣领和袖口已经磨出了裂痕,一双解放鞋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但他咧嘴呵呵笑的时候,淳厚的乡音,让人分外熟悉。没错,就是他,老店主的儿子!
再后来,我到外地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时,馒头老板儿子的车子摇身一变,成了一辆轻盈灵活的小三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