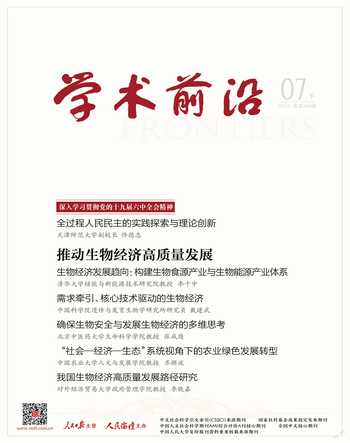确保生物安全与发展生物经济的多维思考
2022-05-30张成岗
【摘要】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快速发展,生物经济也迎来了迅猛的发展时期,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提供了有力的注解。然而,在看到生物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生物安全的问题。生物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健康发展,既需要确保环境生物安全即体外生物安全,同时也要确保体内生物安全即人体共生微生物系统的健康安全。因此,亟需以科技向善、为人类谋福祉的负责任创新发展理念为先导,在确保体外生物安全和体内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生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生物经济 生物安全 共生安全 科技向善 和合思想
【中图分类号】F42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4.004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在对人类社会科技进步欢呼之余,也为技术使人类形成的绑架性依赖隐隐担忧,尤其是当前已经能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遗传物质DNA进行精准调控、任意编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担心其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物种安全风险与生态灾难。因此,在通过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生物经济发展效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将生物安全放在首位,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2年5月10日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中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明确了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任务,指出要着力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目标之一是到2025年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生物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人类对自然界以及自身的探索精神,是人类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动力推动下,人类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后代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地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而前进。从地球到太空,人类不断拓展生产疆域,在彰显科技进步能力的同时,也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与生物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获得了长足进步,不仅进一步洞察自身的生命内涵,也在不断提升着对自我的发展与改造能力。
20世纪末,学术界提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命题,主要是由于20世纪人类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取得系列重要突破,例如DNA分子结构和功能的揭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哺乳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为21世纪生物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解决人口增长、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等诸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在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加速发展,从基因组计划、转录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代谢组计划、互作组计划等到精准医学,为生物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持久动力。通过优化遗传育种策略和发展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为解决农业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随着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地球上以DNA和RNA为代码的碳基生命的理解和掌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理论上已逐渐具备定向改造现有物种、甚至创造新物种的能力,因此,目前也已经有这样的说法,“21世纪不只是生物学的世纪,更是合成生物学的世纪”。随着人类对遗传代码从“读”到“写”能力的增强,在探索未知、创造未来的好奇心驱动下,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更加高级的生命体,这也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目前正在深入推进的课题,例如由我国科学家新近实现的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由此可见,生物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仍然处于高峰阶段,这是由人类的创新创造能力所决定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体现。
生物经济发展对生物安全的威胁和挑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如物理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样,基于质能公式(E=mc2)的质量和能量转换原理,既能够用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也能够用于研发原子弹。随着生物经济领域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由此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尤其大量涉及针对DNA和RNA等遗传物质的直接或间接操作,既能够成就人类,也有可能毁灭人类。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暴露在人类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忽视和摆脱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挑战,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制造出一个有可能毁灭人类的“怪胎”,因此必须第一时间确保生物安全的核心理念。
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没有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技术是否能够被掌握在可确保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手中,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很多问题一开始是技术问题,但随着技术问题的解决,就逐渐演化为一个伦理安全问题,从而与生物安全乃至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在生物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的趋利性很容易带来生物技术被误用、滥用甚至于被恶意利用的问题,这就要求将科技伦理、医学伦理、生物医学伦理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描述的场景为例,白血病患者因为特效药而看到生存机会,但高昂的药价又让希望变成绝望,价格相对低廉的仿制药让患者、警察、药贩子、医药公司等陷入巨大冲突。化解这些冲突的理想方法,当然是通过科技发展降低治疗成本,甚至消除此种病症。类似问题还有“罕见病药物”(也被称为“孤儿药”),同样呼唤通过生物医药科技发展研发出相应药物以惠及民众,这是社会公众对“科技向善”的现实期盼。
以器官移植為例,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因此通过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解决器官移植的痛点是刚性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显著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科学进步,例如如何解决不同个体之间器官移植之后的免疫排斥问题。此外,在人源性器官移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科学界将视线拓展到异种器官移植方面,例如,一名57岁的心脏病患者,面临“要么死亡,要么手术”的选择,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例移植基因编辑猪心病例。他于2022年3月8日去世,距离其接受手术约两个月。该次手术中的供体猪,在出生前曾接受过10处特异性基因改造,去除猪体内会引起急性排异反应的基因等,以便人体更好地接纳猪器官。相关案例说明需求驱动创新发展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从反向角度来思考,一旦有的人或者有的机构能够掌握将部分重要基因进一步优化、修饰的技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就有可能形成生物技术滥用的安全风险。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推动技术发展,更何况在生物经济领域,有的技术本身也会被作为引导(消费)需求而被设计出来。在需要技术的地方,就会有专利、产品,就必然会被赋予资本属性,并很容易被资本自我增殖的天性所放大,进而很容易越过生物安全的底线。如果这种能力被个别超级大国所掌控甚至垄断,例如掌握和操控基因,就很可能带来对他国的技术歧视,更可能导致全球性生物安全风险的显著增加。此类研究在早期阶段,往往会与减少疾病、抵抗衰老以及解决学习障碍等患者的现实需求有关,但如果生物医药技术研究获得突破,就完全有可能将技术用于正常人的能力提升,从而形成新的生物经济技术壁垒,引发生物安全危机。
基因编辑技术尤其具有形成此类风险的可能性。曾经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贺建奎事件,就是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两个人类胚胎进行了基因修改,触动了禁区,违背了科学伦理,触犯了法律。2021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人类基因编辑管治框架》和《人类基因组编辑建议》,从技术、道德、安全等多个领域对人类基因组编辑的治理和监管提出建议。涉及生物经济发展与生物安全的典型案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涉及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很容易引发道德危机和伦理挑战,例如,在技术上可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将蛋白质进行表达纯化并用于提高人造肉的品质(如成分、口感、外觀),但是,如果其中表达的是和人类蛋白质序列高度相似或一致的成分,将其用于人造肉并作为食物使用,那么,当这些人造肉被用户消费的时候,是否具有伦理风险,即摄入的是否为“人体成分”?这虽然并不存在技术障碍,但都需要通过医学伦理甚至道德法律来进行规范。如果遇到医学伦理的挑战,很容易引发严重舆情,导致社会和公众担忧,从而影响该领域健康发展。
就国际领域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生物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个别国家对生物技术霸权的控制意图所导致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风险问题,为全球带来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如果说20世纪之前引发人类烈性传染性疾病主要是天灾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的传染性疾病起因,则很有可能从天灾变成人祸,而其中生物经济推动下的基因编辑和遗传操控以及合成生物技术就有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更加凸显出必须同步甚至优先强调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因此,生物技术推动下的生物经济发展,为生物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亟需在发展、安全与健康之间把握好理想的平衡点。
发展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在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生物经济,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否则就会由于威胁人类安全而导致整体失控。
一是需要确保人类安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发展经济的第一原则,即在发展生物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严格禁止发展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甚至导致人类灭绝的生物技术,例如基因武器、生化武器、人种武器等。在个别国家单边主义思潮主导下,在资本逐利思想的驱动下,很容易在发展生物经济的外衣下将生物技术的能力无限放大、精心包装甚至伪装,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生物经济的名义,开展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研发活动,将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等非常隐秘地进行转移和控制,导致发展中国家形成潜在的人种危机。发展中国家应提高警惕,避免成为个别大国以技术霸权掠夺资源,并通过掠夺资源巩固技术霸权的牺牲品。
二是需要确保自然环境生物安全。这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安全,不仅包括工作场所、家居环境等,而且也包括人类生活环境的全部。应该避免通过生物技术的过度发展繁荣生物经济,却带来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环境安全的结果,例如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抗生素等,此方面教训深刻。
农药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农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生物技术成功应用的典范。然而,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微生态系统失衡,甚至一度在南极企鹅体内也发现了杀虫剂(DDT),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生态灾难。近年来,国内外对农药的使用作出了很多规定,既让农药发挥更好效果,也能够更好保护生态环境。此外,大量使用化肥固然能够提高产量,但是伴随的问题,例如土壤结块、肥力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容易导致生物安全问题,例如土壤微生物、土壤微生态失衡失控,最终反过来影响人类安全。因此,通过研发新技术,例如使用土壤微生态制剂,既能显著提高土壤活力,更好地提高农作物产量,也能够实现生物经济发展、更好地保障生物安全的目标。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抗生素,例如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拯救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受青霉素成功的启发,制药领域研发了更多的抗生素,为人类治疗感染性疾病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不论是人用抗生素、还是兽用抗生素,都会对环境中的微生物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兽用抗生素也会随着食物链的传播而走向餐桌,反过来影响人体健康。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导致超级耐药菌增加,反过来增加了新的疾病的风险。近年来各国陆续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我国也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之间平衡发展的典型例子,即以资本受益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却不能以付出生物安全为代价。
三是需要确保人体共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人类生活在地球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失衡必然会从外向内影响人体健康,同时,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也会自内而外地影响身心健康。在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经将人体内的共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即体内生物安全,简称为“内生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即由于人体不仅生活在充满微生物的自然环境中(即体外环境中的微生物安全,简称为“外生安全”),而且人体本身就在消化道、呼吸道等部位含有大量的共生微生物。健康的人体含有健康的共生微生物群体,罹患疾病的人体则含有大量与疾病相关的共生微生物群体。以容易导致胃炎和胃癌的细菌病原体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为例,60%~70%的正常人都带有该细菌,但并非所有人都发病。Hp诱发胃炎和胃癌主要与胃肠道菌群微生态体系是否失衡密切相关。临床上目前主要使用四联疗法(质子泵抑制剂、胶体铋剂联合两种抗生素如阿莫西林或克拉霉素或左氧氟沙星或四环素等)进行根治性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中,也会看到抗生素对胃肠道其他正常菌群的副作用,从而影响人体的“内生安全”,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如果在婴幼儿发育早期阶段,过度使用多种疫苗激活免疫系统,也会导致婴幼儿肠道菌群严重紊乱失调,从而诱发严重的人体“内生安全”问题,与自闭症、多动症、精神心理异常等密切相关,甚至还是导致这些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确保人体内的生物安全(尤指微生态安全)是保持健康、减少慢病的关键。前述导致生物安全问题的抗生素,不仅会影响体外的微生物,而且会影响体内的共生微生物,从而构成导致人体疾病的重要来源因素。尤其是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人体的慢病可能与体内的共生微生物失衡密切相关,更是将人体内的生物安全问题推进到生物经济的最前沿、甚至可能会成为发展生物经济不可或缺的前置条件,后文将详细讨论。
由此可见,必须在生物安全和生物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重要的平衡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充分说明在将生物经济发展做大做强的同时,一定要确保做好生物安全,不仅需要确保体外(环境中)的生物安全,而且更要把控好体内的生物安全,否则很容易导致生物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从人体与微生物的进化共存角度分析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的矛盾关系
通常意义上来说,发展与安全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安全,也需要发展。没有安全,发展就沒有意义。没有发展,安全也就没有价值。《规划》中指出,顺应“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新趋势,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医药,更好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对正确把握发展与安全关系的科学阐释。考虑到当前国内外仍处于与新冠肺炎疫情密切相关的生物安全的高风险状态,以及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等疾病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需要结合生物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密切关系进行分析。针对此问题进行科学研判,迫切需要从进化角度对人的存在与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因为只有从生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才有可能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经济发展与身心安全关系问题。
纵观国内外针对人的研究,无论是来自自然科学、生命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都是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的,通常不考虑人在结构上与功能上是否存在可分割性(此处指的并非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可分割性,而是指遗传角度上的可分割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新的研究指出,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角度而言,人体不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的人的存在,而是由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即“人微共生体”。其中的微生物可以被分为两类,最重要的一类是在卵细胞中就已经存在、并被受精过程激活、从受精卵到胚胎发育乃至从出生到死亡、并伴随肉体一起消失的微生物即线粒体(mitochondria)。该类微生物以细胞器的方式终生生活在人体细胞的细胞质中(除过成熟的红细胞之外),由16,569个DNA碱基对组成,仅编码37个基因。另一类微生物则是在婴儿出生后,从环境中向人体传递过来、并与人体共生共存直至人体消亡的微生物系统,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共生于人体的内外表面,包括皮肤、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生殖道等部位,正常情况下不进入人体细胞中(否则会导致人体感染而出现病理状态)。这些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构成了庞大的微生态体系,以肠道菌群数量为最多,可编码超过400万个微生物基因,是人类基因组所编码的2.5万个基因的150倍以上。这些与人体共生的微生物为人体提供促进营养物质分解消化吸收、合成维生素、激活免疫等功能,人体则为其提供共生环境。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发现,大量慢性病如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自闭症甚至阿尔茨海默症等都与肠道菌群异常密切相关,从而促使学术界对于人的研究不再只是局限于人本身,而是扩展到人作为由人体与共生微生物联合组成的“超级共生体”的新角度。在笔者实验室的研究中则发现,肠道菌群为人体提供了摄食所必须的信号源,即“饥饿源于菌群”,结合前述线粒体是人体细胞通过氧化磷酸化产生能量来源的动力工厂而形成“呼吸源于线粒体”的认识,尤其是在中医经典理论阴阳学说的启发下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菌粒阴阳学说”,从肠道菌群在人体相对主“阴”(简称为“菌脑主阴”)、线粒体相对主“阳”(简称为“粒脑主阳”)以及“人体主和”(即人体调控阴阳平衡)的角度进行了系统阐释,不仅为理解“全人”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为讨论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切入点。
众所周知,生物安全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人体是否接触到影响人体健康的病原微生物。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最有效的防控措施是隔离,避免新冠病毒与人体接触而致病,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考虑到人体本身就含有大量共生微生物,不仅包括细菌、真菌,而且还包括大量病毒(例如2021年2月有研究认为正常人肠道中有14万种病毒),说明人体与微生物之间需要具有良好的选择性,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微生物可以与人体共生共存,否则就会导致微生态失衡紊乱而引发慢病风险。因此,在讨论生物安全这一主题时,一定不能抛开人体共生微生物这个核心的角度而单纯讨论人体疾病的问题,否则就是孤立的、片面的、不完整的。事实上,种种迹象提示,在破解人体慢病难题的关键点方面,需要对“人微共生体”进行深入诠释与科学解读。只有当能够实现人体与共生微生物的共同健康即“人微同康”时,人类才有可能从慢病高发的困局中走出来,走向身心健康的新阶段。相反,如果仍像当前一样,只是局限于关注人体本身的健康,而忽视甚至破坏了人体共生微生物的健康,那么,就不可能实现《规划》中所指出的“身心健康”的目标。
之所以从“人微同康”角度讨论生物安全问题,是源于从生命起源与进化角度对“人”在地球上出现的重要思考,即自然界在形成“人”之前,已经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过程,首先在36亿年前出现细菌,于24亿年前进化出线粒体,逐步进化出植物、动物乃至人类。在此漫长的地球生命发展过程中,分别通过将线粒体内置于人体细胞向人体赋予有氧代谢的能力(即“呼吸源于线粒体”)、通过将肠道菌群在婴儿出生后接种于肠道向人体赋予因饥饿而摄食的能力(即“饥饿源于菌群”),从而形成以人体为依托、人体细胞与线粒体的“细胞内共生”、肠道与肠道菌群的“肠道内共生”的联合共生体,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人就是人、人只是人”的朴素认识。当然,除了这两种“内共生”形式之外,人类所在环境中的微生物以及动植物体系,可被认为属于与人体“外共生”的生态环境体系。
由此可见,在讨论生物安全即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方面,必须结合近年来的科学发现,认识并接纳人本身就是自然界使用作为宿主的人体和作为共生的微生物的联合进化的结果。只有确保人体内部的两套“内共生”微生物体系,人体外部即所在自然环境的一套“外共生”微生物体系和動植物生态体系的共同安全,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安全。通过实现人与共生微生物的联合安全与共生安全,即同时满足体内生物安全和体外生物安全的条件,突破以往只是以人为本、以人类为中心研究和应用的局限性,扩展到以人微共生体的协同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广域认识,在发展生物经济的时候,就能够有新的科学遵循,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这同时也是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的关键所在。
和合思想为生物经济的安全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现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思想同样也适合于本文讨论的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主题,这是因为就社会发展的主体要素与对象即“人”而言,也必须把握好“和合”的客观逻辑——“人”的出现、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自然界在地球碳基生命方面以“和合”方式而运行的特殊产物。
就“和合”而言,“和”演化出和谐、和睦、和平等意,“合”演化出汇合、结合、联合、融合、合作等意。这两个要素,在前述基于“人微共生体”理念对“什么是‘人”的科学解读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为人体提供能量来源、作为细胞器、共生于细胞质、本质上属于微生物的线粒体,需要与人体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人体通过呼吸系统为线粒体提供氧气,线粒体则通过生化反应将碳源中的能量以氧化磷酸化的方式释放。如果线粒体出现DNA突变和损伤,将引发人体细胞出现自噬、细胞凋亡、持续性炎症反应甚至诱发癌症,表现为线粒体与人体之间“和合”关系的破坏而导致“两败俱伤”。在高原缺氧、人体组织缺血缺氧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情况下,线粒体将无法通过人体呼吸系统获得充足氧气完成有氧代谢,无法为人体提供能量,从而导致人体出现严重损伤甚至死亡,表现为人体与共生线粒体(简称为“人粒”)的双双消亡,共生关系消失,肉体不复存在。由于线粒体只能通过母系遗传给子代,因此,一旦一个人自身的“人粒”共生关系结束,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体死亡、与其肉体共生的线粒体也同步死亡。新的线粒体则伴随着新的卵细胞被精子激活后,形成并启动另外一个新的个体的发育过程,从胚胎到出生,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开始一个新的“人粒”和合共生周期。
除了上述“人粒”之间存在从受精卵到肉体死亡而终生“(胞质)内共生”的典型“和合”关系之外,“人菌”之间所存在的“(肠道)内共生”显然也符合“和合”思想的客观逻辑,只不过区别在于“人粒”之间的“和合共生”关系是从卵细胞受精后启动个体生命的发育过程开始的、并持续人体终生;但“人菌”之间的“和合共生”关系,则是从婴儿出生后,自然界将以肠道菌群为主的微生物向肠道主动接种后启动个体生命的饥饿与摄食过程开始的、并持续人体终生。如果以肠道菌群为主的共生微生物群体处于正常、健康状态,就能够表现为“人菌”之间的“和合共生”关系的健康存在,两者之间也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状态。相反,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例如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使用抗生素等导致肠道菌群微生态系统出现失调、紊乱,就会导致大量不利于人体健康的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持续从肠道进入人体而导致出现慢病,与古人所说的“粪毒入血、百病蜂起”以及西方医学开创者希波克拉底所说“慢病源于肠道”是一致的,这也是慢病的重要根源。随着作为肠道菌群承载者的肉体逐渐出现慢病,免疫力逐渐下降,人体自愈能力降低,对肠道菌群紊乱失调的纠正能力也会持续下降,最终会导致“人菌”关系的破裂,即“人菌”之间“和合共生”关系遭破坏。当人体走向死亡之后,肠道菌群则从肠道内部开始分解肉体,并回归到自然界,为寻找下一个宿主、建立与新个体的共生关系、形成新的和合生命周期做准备。
由此可见,在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自然界本身就使用了“共生”与“和合”的内在科学逻辑,而不是直接通过一步登天的方式来形成人这样的个体。事实上,笔者在2021年年底发表的论文《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四元数矢量数学模型构想》中,从数学角度(超复数、四元数)进行了表述,指出对于完整的人的表述,可能必须从“肉体的人(标量)、线粒体的人(矢量)、肠道菌群的人(矢量)以及大脑和思想的人(矢量)”的角度,以联合存在和联立共生的方式进行解读,方才能够实现对于人的完整理解。这一点也是确保在生物安全前提下实现生物经济科学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将生物经济做大做强,而且同时也要将生物安全做好做稳,表现在人体这个层面,就是要实现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体共生微生物之间的均衡发展,这也是和合思想在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之间的自然体现,因为从人微共生这个新的角度来看,线粒体和以肠道菌群为主的共生微生物,本来就是自然界在形成人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天然的、自然而然的和合逻辑,从而形成了人的和合存在。人的出现源于和合,人的发展需要和合。只有确保内生安全,才能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的和合式生物安全发展。
生物经济的未来是确保生物安全前提下的和谐发展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铁器时代到蒸汽时代,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发展始终是主旋律。当前,人类正在走向生命科学时代,未来也必将迎来生物经济的更好发展,为人类发展带来更好的福祉。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诸如疾病等,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病实际上是以往在发展过程中对生物安全、尤其是人体内的共生生物安全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把控能力而导致的问题之后,就能够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纠正,例如通过噬菌体疗法对异常肠道菌群进行精准调控、通过将健康个体的肠道菌群向患者移植来替换慢病患者的异常菌群(即菌群移植),通过基因编辑等方式纠正导致人体炎症和癌症的人类基因DNA突变和线粒体DNA突变,通过研发更加高效的药物(化学药、中药、生物药)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诊断水平方面的显著提高,必将成为生物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确保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生物安全的关键,确保实现生物经济发展与生物安全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均衡发展,即实现生物经济的可控发展、安全发展。
在21世纪的生物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鼓励创新,但需要的是负责任的创新、尤其是将生物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的创新。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信息时代之前,尚未出现会严重影响人类安全的科技水平与能力;但是,到了信息时代之后,人们对信息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计算机、手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几乎对人们的日常活动形成了绑架性依赖,例如,当前大量使用的健康码已经成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管理技术,如无绿码则会为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从另一角度而言,当前民众所经历的社会变化过程,实际上体现的是“信息时代”与“生物时代”(或称生命科学时代)的交织与交替过程。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来看,如果不是来源于自然界,那么就有可能是人工(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而形成)的产物,毕竟在个别国家从事具有高度生物安全风险的研究过程中,存在失控和泄露的风险,从而很容易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灾难。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提高人类健康福祉无可厚非,但如果将该技术用于研发基因武器,就是严重的不负责任。人类越掌握与人类DNA密切相关的基因编辑技术,就越容易带来生物安全威胁,必须通过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努力进行防范。在此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能够惠及人类健康,而不是危及人类安全只顾实现自身霸权的不负责任的科技创新。科技向善不仅是发展生物经济过程中的重要遵循,而且也是负责任的科技创新的关键。
总结与展望
在发展生物经济过程中,需要把控好人体与共生微生物,即人微共生体的联合安全、共生安全,这不仅符合和合共生、和谐发展的理念,而且也是人体健康与慢病防控的关键。人类健康的未来并不一定是依靠药物就能实现的,正如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与治疗方面可见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才是关键,与《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拥有良好的人体与体外微生态以及体内微生态的共生生物安全、联合生物安全,在确保科技向善以及符合人类长期健康发展的医学伦理原则下,促进生物经济的可控发展,是未来健康发展之路。
(本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90011451310015)
参考文献
杨伊静,2022,《强化生物领域战略科技力量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中国科技产业》,第5期。
Green, E. D.; Watson, J. D.; Collins, F. S., 2015, "Human Genome Project: Twenty-five Years of Big Biology", Nature, 526(7571), pp. 29-31.
Portin, P., 2014,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NA Theory of Inheritance: Sixty Years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Journal of Genetics, 93(1), pp. 293-302.
曾(杰)邦哲、吳超,2008,《系统遗传学与合成生物学——21世纪的生物工程产业化》,《生物技术通报》,第5期。
《我国科学家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2021,《山西化工》,第5期。
李虎,2021,《从电影<我不是药神>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协调》,《法制博览》,第13期。
陈子梦、王丽、章浴、张曦文、路云,2022,《基于供应链理论的我国孤儿药可及性分析与建议》,《卫生经济研究》,第6期。
Griffith, B. P.; Goerlich, C. E.; Singh, A. K., et al., 2022, "Genetically Modified Porcine-to-Human Cardiac Xenotransplant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刘子奎,2020,《生化恐怖主义与冷战后美国防生化武器扩散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
黄鹏,2020,《“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中国卫生法制》,第6期。
Geisz, H. N.; Dickhut, R. M.; Cochran, M. A.; Fraser, W. R.; Ducklow, H. W., 2008, "Melting Glaciers: A Probable Source of DDT to the Antarctic Marine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2(11), pp. 3958-3962.
吕景海、朱海燕,2016,《农药安全问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现代农业科技》,第14期。
陈亚萍、李英芹、马文婷,2022,《基于复合生物优化剂的土壤改良技术》,《科学技术创新》,第18期。
薛闻俊、王颖,2008,《小议青霉素的发展历程与临床应用》,《黑龙江科技信息》,第7期。
薛宇、朱艳丽、张晨晨、高家福、谭雨薇,2021,《药物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及其多药耐药性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广东化工》,第7期。
张成岗,2020,《医学遗传学2.0:导致人类慢病的主因可能首先是人体共生微生物基因异常,其次才是人类基因异常》,《生物信息学》,第2期。
张成岗,2020,《从“菌脑主吃、人脑主思”分析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医学争鸣》,第4期。
张成岗、巩文静、李志慧、高大文、高艳,2018,《医学3.0与健康管理2.0将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早日实现》,《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第12期。
张成岗、巩文静、李志慧、高大文、高艳,2018,《菌心进化论:一种对于动物进化的新理解》,《生物信息学》,第4期。
张成岗、巩文静,2017,《基于饥饿源于菌群的新发现将引发慢病防控突破性进展》,《科技导报》,第21期。
张成岗,2022,《菌粒阴阳学说:基于“人微共生体”探讨中医阴阳学说的学术思考》,《中华中医药学刊》,5月12日。
Camarillo-Guerrero, L. F.; Almeida, A.; Rangel-Pineros, G.; Finn, R. D.; Lawley, T. D., 2021, "Massive Expansion of Human Gut Bacteriophage Diversity", Cell, 184(4), pp. 1098-1109.
张成岗,2020,《从人菌共生的角度探讨生物安全与传染病防控的新思路》,《科技导报》,第15期。
张成岗,2021,《动机进化论:关于自然界从生命起源进化到人类的学术思考》,《医学争鸣》,第5期。
张成岗,2021,《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四元数矢量模型的生物学意义与医学价值》,《实用临床医药杂志》,第16期。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