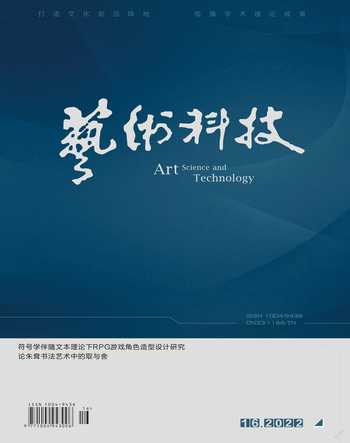论《马桥词典》中的“鲁迅传统”及其突破
2022-05-30黄伟涛
摘要: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通过对语言的读解,揭示了混沌的马桥文化压抑生命的本质,坚守了鲁迅的启蒙思想立场。同时,受20世纪90年代商品化潮流的影响,小说又流露出怀疑与悲观色彩。对启蒙的怀疑和对这种怀疑的突围,与鲁迅式的“反抗绝望”具有相似性。而在突围的过程中,韩少功所发现的民间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对“鲁迅传统”的一种突破。基于此,文章探究《马桥词典》中的“鲁迅传统”,以及该小说对“鲁迅传统”的突破。
关键词:《马桥词典》;“鲁迅传统”;怀疑精神;民间世界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6-0-03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景观中,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一部具有鲜明症候性的作品。韩少功以编撰地方词典的模式开启了“词典体小说”的叙述形式,以相对独立的方言词条为望镜,为偏僻蒙昧的马桥投去现代的眼光,透视马桥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理状态。小说的新奇形式为90年代的“长篇小说热”添了一把薪火,而在人文精神失落的社会中,韩少功在保持一贯的理想主义与文化批判的同时,由于心境的变化,又以民间的视角审视马桥的人与物,独到地发现了被灰暗的马桥秩序所遮蔽的民间世界。启蒙立场与民间立场在《马桥词典》中相互碰撞,构成了“后寻根小说”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厘清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关系,是进入马桥世界的重要前提。
1 乡土批判中的启蒙主题
启蒙是现当代思想史、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命题,它催生了现代文明,在不同的年代绵延反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构建了现当代文学的价值框架,并在“五四”和“新时期”处于主流位置[1]。启蒙主义贯穿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改革三大潮流,又在寻根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深广的阐释空间。寻根作家将笔触聚焦民族文化,探寻久远的民族传统与深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了认同与批判两种态度,而批判又往往与启蒙密切相关。“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2]277是寻根文学的指向之一,韩少功就是实践这一指向的代表作家,并把这一指向延续到《马桥词典》中。
同大多数寻根作家一样,韩少功将知青生活留下的乡土记忆纳入寻根创作,丰富了乡土题材的创作。“五四”时期,鲁迅最早将“国民性”审视的文化视角伸向乡土世界,以启蒙的目光照亮蒙昧的荒野乡场,开创了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同时以其“表现的深刻与格式的特别”,形成了独特的“鲁迅模式”,深刻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继承鲁迅的创作资源,将目光聚焦到马桥这一典型的乡土世界。韩少功并未抱着留恋、怀念的心态回望知青生活,而是冷静地对愚民进行精神审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韩少功延续“五四”的启蒙薪火,对民族劣根进行挖掘。
费孝通曾指出:“从基层上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宗法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大陆文化及农业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而传统乡土中国浓郁的村落群体文化色彩及其习俗风尚为主体社会结构,又使之本质上属于民俗社会。”[3]可见宗法制度与文化习俗是进入乡土世界的两大路径。《马桥词典》收录的词条大多带有浓郁的宗法制度色彩,记载了马桥的风俗、习惯、信仰,它们共同塑造着、制约着马桥人的精神世界。
“话份”是《马桥词典》中很显眼的一则词条,它是权力等级制度在方言中的生动显现。有了身份和权势,在马桥就有了“话份”,说话就有了分量与威慑,反之则人微言轻,说的话无人重视。本义是村里的党支书,也是马桥中最有“话份”的人物,他受人敬畏,不怒自威,是如同鲁迅小说中“赵老太爷”一般的存在,尊卑贵贱的宗法等级秩序由此可见一斑。在马桥,女性不仅没有“话份”,而且陷入无名的状态。她们没有独立的亲系称谓,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便是她们的指称,显露出浓厚的父权思想。同样,类似的思想也融入了马桥人的风俗习惯中。马桥的婚姻习俗忌讳“撞红”,即忌讳处女,在马桥人看来,女性的生育能力比贞操重要得多。“放锅”所指代的低俗婚闹、“不和气”所描写的女性过河要在脸上抹稀泥的习俗,更是对女性尊严的漠视。而“魂飘”“枫鬼”等词条则对马桥人的迷信观念、轮回观进行了揭示。
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流传民间的迷信思想相互交叠,戕害马桥人的灵魂,马桥人身陷封建文化的阴云之中却麻木而不自知。韩少功以词典编撰人的身份发掘出马桥人病态的思想观念,将之昭然示众。在文化批判的视野中,风俗人情、话语习惯都有了深刻的言说价值,作品中的启蒙意识也得以彰显。
2 “怀疑精神”与“悲观进取”
那么,这种理想主义的乡土启蒙行之有效吗?
在马桥,与封建文化同时存在的,是保守的文化心态。马桥位于湖南的偏僻山脉中,仿佛被世界所遗弃,然而马桥人有一种位居中心的自大感,将马桥以外的世界统称为“夷边”。马桥人认为城里人喝“颜茶”可怜、可笑,抗拒着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甚至走在县城的街市上会产生“晕街”的生理反应。而更有象征意味的是,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五四”的核心命题,在马桥人的观念中完全褪去了现代的色彩——追求科学等于偷懒,民主成了监狱里没有“牢霸”的牢房的代名词。这种对现代文明不假思索的否认或扭曲,对启蒙而言无疑是最坚固的壁垒。
当回忆起在马桥展开的启蒙活动时,韩少功说:“在农村当知青那幾年,我还办过农民夜校,自己掏钱编印教材,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让他们知道巴黎公社是怎么回事,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救世主,希望他们有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启蒙的成效很小。”[4]拥有启蒙者话语的知青们本可以为马桥带来嬗变,然而马桥没有留下知青的任何痕迹,“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5]301。难以攻破的马桥方言体系牢牢桎梏着马桥人的文化思维,留给启蒙者的只有深重的焦虑。
在这种强大的保守主义现实面前,韩少功在写作时不免陷入怀疑的漩涡:现实中的宣传倡导尚且收效甚微,笔杆下的几声呐喊又有多少令马桥人觉醒的力量呢?“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世界上各种仗说打就还是在打。崇拜歌德的纳粹照样杀人,热爱曹雪芹的政客和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不应该被过于夸大。”[5]395在此处,韩少功对自己的写作,对写作中的启蒙主义产生了怀疑。
除了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启蒙无效性,让韩少功陷入怀疑的还有马桥历史的停滞不前。《马桥词典》中的历史叙述上溯远古,下至21世纪初,而贯穿其间的是历史的循环论。“《马桥词典》将历史写成故事,讲述‘文化—历史的静止与循环。”[6]清末的“莲匪”之乱、抗战、军阀混战、“文革”,混乱、斗争在马桥轮番上演,生灵涂炭,苦难深重,但马桥人对此类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全不在意,甚至说不清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他们缺乏现代的时间意识,对历史保持置身事外般的冷漠,而历史的残酷与社会的糟粕便在这种冷漠中不断重现。于是,“有些老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大用了,现在又纷纷出笼卷土重来,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误以为是一些新词”[5]343。
“做脱”“牛头”“草鞋钱”……这些旧社会的词语重新进入现实生活,仿佛酝酿着历史的重演。
怀疑还体现在对语言本身的质疑上。语言的发展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它以符号的形式维持经验的交流与社会的运转。但当语言成为牢笼,束缚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的时候,语言的发展还可以与进步画等号吗?
这种对进步主义的怀疑,折射出韩少功深层的求索意识与思维特质,这与鲁迅的“怀疑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的“怀疑精神”贯穿其整个心路历程,是“鲁迅精神”中深层的意识存在。但鲁迅的怀疑并没有滑向悲观与绝望,而是不断地淬炼思想、坚守启蒙,形成了鲁迅式的“反抗绝望”:“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才构成鲁迅思想的真正特色。”[7]同这种“反抗绝望”一样,韩少功的“怀疑精神”同样走向了“悲观中的进取”。
据蒋子丹回忆,韩少功曾说,“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怀疑论者,连怀疑也怀疑”[8]。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对启蒙立场产生怀疑之后,又对这种怀疑进行二度怀疑。这种对怀疑本身的审视扩大了韩少功的认识范围,又转化成进取的姿态,最终使理想的启蒙主义得到强化。同时,在怀疑的过程中,韩少功发现,对启蒙主义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成立的——在沉默的马桥世界,还有一个长期被遮蔽、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这个世界对韩少功走出怀疑具有重要意义。
3 用以“反抗绝望”的民间世界
民间世界的发现,是韩少功在寻根文学创作中的突破。启蒙视角下的马桥布满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但民间视角下的马桥涌现出一些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爱恨情仇的人物。在《马桥词典》中,作为叙述者的知青“我”,在对马桥感到失望的同时,又不时被马桥人打动甚至“教育”。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人物大多闪现人性的光辉,令“我”流露出强烈的情感意绪,因而冲淡了“我”的失望。“我”既能以启蒙的立场俯视马桥,又能以民间视角平视甚至仰视马桥,这是对“鲁迅传统”的一种超越。
在等级森严的马桥,万玉、铁香、志煌等人是独特的存在。万玉热爱“发歌”,尽管他在马桥没有“话份”,但他坚持认为“发歌”应该是自由率性的,故而坚定地拒斥“大闹春耕”的革命艺术,宁愿被罚50斤谷,也不愿到县里参加演出。他常常以插科打诨的方式与本义逗笑,用喜剧性的方式消解本义的严肃威严。万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拒斥了马桥的权力秩序。在马桥女性中,铁香则显得格格不入,她与男性嬉笑、撒娇,展示自己的柔媚。她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女性无名的世界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后她逃离了万玉的控制,与三耳朵私奔,最终双双被炸死在山洞。铁香的行为无法被马桥人所理解,但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自我追求和渴望。“权力制度与民间同构的正常社会秩序,无法容忍民间生命力的自由生长,这些人只能在黑暗的空间表达和生长自己,在正常人的眼里他们乖戾无度不可理解,但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里,他们同样活得元气充沛、可歌可泣。”[2]374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曾表示自己对时局“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同时又表示,“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物事件,是有限得很,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9]。那些“没有见过的人物事件”包含希望,它们激励着鲁迅保持启蒙的动力。而在《马桥词典》中,这些没被注意到的人物事件便是韩少功挖掘出的元气淋漓的民间世界。麻木冷漠的马桥权力世界令韩少功失望,但这权力世界中还有一群拥有强烈爱恨与自我意识的人。因此启蒙并不是无效的、令人绝望的,启蒙有着一批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包含生命力的受众。“怀疑自己的失望”与民间世界的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使怀疑消退,使启蒙立场回归。
4 结语
在纵向的文学史脉络中考察《马桥词典》,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启蒙立场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启蒙大潮的余脉。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在创作中始终保持清醒理性的现代思维,对落后的土地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无论是《西望茅草地》中頭脑僵化的农场长张种田,还是《爸爸爸》中作为民族文化象征存在、丑陋而顽固的丙崽,都展现了韩少功迫切的启蒙呼吁。纵观韩少功的创作,其小说中的启蒙立场、阿Q式人物的塑造、归乡模式等均借鉴鲁迅。但在启蒙被解构的90年代语境中,《马桥词典》中的启蒙立场必然不是“五四”启蒙的机械复刻,甚至与韩少功本人于80年代创作的寻根小说也拉开了明显的审美距离。
20世纪90年代是滋生怀疑的年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导致消费文化、媚俗文化横行,崇高信仰与理想主义遭到侵蚀,不免令人陷入对理想信念的怀疑渊薮之中。这一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症候对韩少功创作中的启蒙立场也造成了冲击,而作为消解怀疑的一种方式,韩少功笔下的民间世界实现了对鲁迅笔下的农民世界的开拓。在“鲁迅传统”中该被启蒙、疗救的民众,在《马桥词典》中则拥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很深刻的意义上支撑着韩少功的启蒙坚守,故而民间立场最终强化了启蒙立场。
参考文献:
[1] 刘中树,许祖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
[2] 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77,374.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1.
[4] 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66.
[5] 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301,395,343.
[6] 金介甫.韩少功《马桥词典》中的回环观与文化悲观主义[J].张卓亚,译.国际汉学,2017(4):57.
[7] 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84.
[8] 蒋子丹.蒋子丹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61.
[9]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8.
作者简介:黄伟涛(2000—),男,江西九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