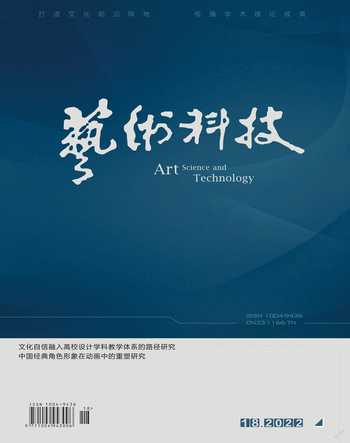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的私法保护研究
2022-05-30詹志杰
摘要:艺术体操赛事的直播利益属于无形财产的范畴,而对其直播利益的私法保护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特性。艺术体操赛事组织者对赛事直播利益的需求较其他主体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应受到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保护。将来可借《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的契机,设立一项排他性质的权利保护体育赛事直播利益,解决司法实践中赛事直播利益保护的困境。文章以艺术体操赛事相关利益中具有代表性的直播利益为基础进行概念分析,并提出体育赛事直播利益的保护方案,以期赛事直播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关键词:体育赛事直播利益;无形财产;体育法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8-0-0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的广播权不再只控制初始为无线方式的作品广播或者传播行为,其权能扩展至初始为有线方式的作品广播或者传播行为,广播组织的转播权也拓展至网络环境。上述变化使赛事节目著作权人、赛事传播者对赛事节目及其传播拥有排他性权利。这无疑平息了新《著作权法》颁布前有关艺术体操赛事节目能否归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的争议,但就赛事组织者对赛事本身应享有的利益,如授权直播、录像、周边产品等,我国立法尚未明确,既有研究、司法案例多以“体育赛事转播权”这一概念指代,但就其性质未达成共识。因此,为避免争议,本文以艺术体操赛事相关利益中具有代表性的直播利益为基础进行概念分析。
1 问题的提出
艺术体操赛事组织者面对未利用其节目信号的赛事直播者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赛事组织者依据其章程主张其为各项赛事所有权利的原始所有者,通过授权协议允许媒体机构在特定地区直播赛事。但赛事组织者章程并非不具有对世效力,如著名的奧林匹克委员会,其在性质上属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其章程亦不属于国际法渊源。同时,授权协议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导致被授权组织单独提起诉讼时会面临原告是否适格的质疑,法院只能将基于赛事本身所享有的直播利益视为一项财产性的民事利益,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但其是“行为规制法”,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而非以专有权利为中心形成主体、客体、内容、取得、行使、限制以及救济的规范体系[1],这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模式,只能在直播利益受到他人侵犯时被动地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的保护工作陷入僵局。
2 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的属性
2.1 赛事本身不是作品
在讨论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的私法保护前,应先分析赛事直播利益的属性,明确体育赛事本身是否具有作品属性。因赛事往往涉及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可吸引大批量线上线下的观众,其传播模式与艺术表演的传播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引起了体操赛事是否属于作品的讨论。若赛事本身就是著作权法中的作品,那么体育赛事直播利益的保护问题诉诸著作权中的各项财产权即可。
根据新《著作权法》的第三条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依照上述规定,虽然艺术体操赛事中包含着运动员对技术动作运用的智力思考活动,但其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从而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学界主流观点也对体育赛事是否属于作品持否定态度[2]。正如在NBA诉摩托罗拉案中法官的意见:“体育赛事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被授予版权保护,尽管在赛事准备中体现了专业水平,但这种准备是对某种无法预料的客观事实发生的期待。即使是参赛准备活动中最能体现创造性的项目——花样滑冰、体操、职业摔跤,运动员设计并做出优美而高难度的技术动作,若就此获得版权保护,将损害未来的比赛竞争;一种技术动作只允许特定运动员使用是毫无意义的。”
2.2 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属于无形财产
2.2.1 大陆法系财产概念的演进
大陆法系的财产概念随着对“物”这一概念的认识发展而演进。罗马法时期,财产和物的概念几乎是等同的,按照是否存在对应的物质实体,粗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前者指拥有物质实体的对象本身,后者指对象之上的权利[3]。罗马法中无体物概念的引入,是为了把与物质实体相关但又不是物质本身的他物权、继承权和通过合同产生的债权纳入物法的讨论范围,从而实现体系的自洽。
《法国民法典》时期已经存在主观权利的概念,认为财产之上应有主观上的权利,财产是权利的客体[4]。同时,《法国民法典》将罗马法的有体物与无体物的二分替代为动产与不动产的二分,并将“物”的概念限定为物质实体,把罗马法中的无体物依照其所依附物的属性、用途和使用目的不同划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然后将债、担保等归为财产的取得方式,从而避免陷入罗马法无体物概念中权利之上存在权利的怪圈。
德国民法理论则创造性地设计了债权和物权的二分,其民法中的物也仅指有体物,物与债共同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的保护“对象”,所有的保护“对象”都属于财产的组成部分。可见,在大陆法系传统中,“有体”概念在民法中即“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
随着以知识财产为代表的无体财产的涌现,“无体财产”概念在私法学界被广泛使用,多数学者习惯使用“无形财产”的用法,并且多认为“无形财产”和“无体财产”没有区别[4]。如曾世雄先生认为,财产权之有形或无形,并非指权利而言,而系权利控有之生活资源,即客体究竟有无外形;作为著作权,亦不产生有形无形问题,关键在于作品系智能之物,为非物质形态[5]。
2.2.2 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去除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章中关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表述,并规定“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表明我国在立法层面已经认可财产之上并不当然成立财产权,财产权是对财产进行有选择的保护。
艺术体操赛事是一种精神产品,承载着人类对健康体魄的精神向往,通过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活动取得外部直观的载体,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多样的精神体验。基于赛事衍生出的直播利益不具备物质形态,但蕴含着经济价值,在立法未对其采取专门权利保护之前,将其视为一种无形财产符合大陆法系传统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概念分析层面,有学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出发,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的客体是直播信号[6],但赛事信号并不是赛事本身,若媒体未经许可在现场直播赛事,基于直播信号的保护就不成立。究其原因,上述观点没有聚焦赛事直播利益属于无形财产的本质,而将视线投向直播信号这一客观外在实体,也自然无法构造出一条较全面的保护路径。
3 体育赛事直播利益的价值辩护
依照利益论的权利概念,权利由三方面构成:第一,存在某种利益;第二,该利益需要他人采取某种行动才能满足;第三,该利益是他人承担从事此行动义务的充足理由[7]。在前两点上,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体育赛事的直播授权费用成为一笔可观的收入,为赛事组织者带来了经济利益。赛事直播利益的维护,也需要赛事组织者以外的主体不出现侵害该利益的有关行为。但正如第三点强调的,某种利益的维护需要他人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时,并不意味着他人有义务如此,利益排他性保护的取得需要经过价值的辩护而获得实质性理由。
3.1 利益衡量的路径
按照利益论,只有当体育赛事组织者的赛事直播利益比他人因此被减损的利益更加重要时,他人利益的减损才是合理的,权利才是正当的。但利益的衡量没有具体标准的数字大小比较,尤其还是不同性质利益间的冲突。利益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需求和价值。利益首先直接表现为需求,如“我想吃饭”,同时作为利益的需求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目标,比如对食物的需求体现了生命的价值,这与出于盲目情绪的需求有所不同。不同价值目标之间并无绝对的主次之分,如生命价值不会永恒地高于自由价值,但需求是可以比较的,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获得解释。假设渔民捕到了一船鱼,其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多少作为自己的基本食物或者去换取基本的食物,然后考虑拿多少进行出售,维持日常开销。
3.2 体育赛事直播利益的重要性判定与比较
阿列克西认为,利益的抽象重要性和利益的干涉程度决定了利益自身的重要性。抽象重要性从利益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受公共利益的支持程度和利益是否明顯不道德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干涉程度体现为该利益的保护对各方需求的满足与抑制程度[8]。
在抽象的重要性上,对赛事组织者而言,赛事直播利益是其维持运作的主要财产来源之一。而对赛事组织者之外的民事主体而言,其可以在其他方向寻求发展。相对而言,体育赛事直播利益对体育赛事组织者是更为基础的利益,为其提供保护有利于财产秩序的维护,从而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效果。
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劳动者的个人劳动使某物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其原本所处的状态,进而排斥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共有的前提下,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其之外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从道德上而言,赛事直播呈现给观众前,赛事组织者需要开展策划宣传、对接场地等一系列前期投入工作,承担着投资失败的风险,这为其在体育赛事直播利益上排除他人的干扰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除赛事组织者之外的民事主体若出现盗播等“搭便车”行为,以“坐享其成”的方式来增加赛事组织者投资风险、攫取赛事组织者的利益,显然是不具有道义性的。
在对利益的干涉程度上,赛事直播利益的保护需要赛事组织者以外的民事主体消极的不作为,对其自由利益的干涉强度要远低于要求其积极的作为;而且赛事直播利益具有即时性,随着赛事的结束而消失,这意味着干涉并不具有持续性,所以赛事直播利益的保护对赛事组织者以外的民事主体的干涉程度是有限的。
4 体育赛事直播利益的保护方案设计
4.1 具体路径的选择
在《民法典》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我国将来可利用《体育法》修订的契机,在其中设立一项具有排他性质的权利,以此来保护体育赛事组织者对赛事的直播利益,这一路径具有以下合理性。
首先,从法律位阶上看,《体育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在效力位阶上要高于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由其设置一项排他性权利与我国《立法法》规定相符。其次,从法律内容上看,《体育法》尚未界定体育赛事组织者的相关权利,但其总则明确了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的立法目的,这与体育赛事组织者的理想利益契合。
此外,《体育法》中超过50%的法律条文都只具备宣示性和倡议性,不具备强制性,远高于学者估计的“国家立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软法条款占比21.3%”的水平[9]。而《体育法》第七章“法律责任”只有6条法律条文,这也导致《体育法》的司法适用频率极低。截至2022年9月7日,在裁判文书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作为法律依据检索,共检索到45个民事案件。而一项具有排他性质的权利安排可以降低《体育法》软法性法律条文偏高的占比,增强《体育法》的可适用性。以增强强制力来促进社会成员自律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增强其中倡议性条款的感召力,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实现。
4.2 法律条文的内容
在具体法律条文内容方面,本文聚焦于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但赛事利益不限于此。因此,具体条文的第一款可对体育赛事典型利益采取类似作品类型式的列举,最后一项再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以应对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型体育赛事利益,确保法律的弹性。此外,为防止体育赛事组织者对其绝对权的滥用,在条文第二款可明确体育赛事组织者行使该权利时不得违背宪法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仅以体育赛事直播利益为例,可参考如下。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对赛事拥有以下绝对性权利:(1)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举办的体育赛事,并获得报酬;(2)应当由体育赛事的组织者享有的其他赛事权利。体育赛事的组织者行使权利,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5 结语
我国学界对以赛事直播利益为代表的体育赛事利益定性研究尚存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保护面临困境。通过概念分析可以得出,艺术体操赛事直播利益属于无形财产,赛事组织者应对其享有绝对权。在保护方案的设计上,可借《体育法》修订的契机,为赛事组织者设立具有排他性效果的权利。
参考文献:
[1] 吴汉东.论反不正当竞争中的知识产权问题[J].现代法学,2013,35(1):37-43.
[2] 孙山.体育赛事节目的作品属性及其类型[J].法学杂志,2020,41(6):20-29.
[3] 孙山.财产法的体系演进[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36(4):70-88.
[4] 李国强.无体财产概念对现代所有权观念的影响[J].当代法学,2009,23(4):40-46.
[5]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台北:三民书局,1983:151.
[6] 吴汉东.财产权客体制度论:以无形财产权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0(4):45-58.
[7] 胡晶晶.“信号”抑或“画面”之保护:体育赛事实况转播保护路径研究[J].北方法学,2019,13(3):29-40.
[8] 于柏华.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J].法学家,2017(6):1-13,175.
[9] 马长山.互联网+时代“软法之治”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法学,2016,38(5):49-56.
作者简介:詹志杰(1997—),男,安徽安庆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