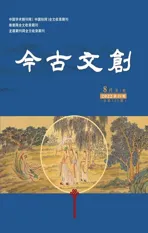从杜赞奇《文化 、 权力与国家》看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
2022-05-30王牵云
【摘要】 聚焦于清末国家政权的建设,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分析模型,提出其概念,同时通过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宗教网络、人际关系网络来分析乡村社会的权力生成过程,龙王祭祀仪式和封建国家对关羽的加封则表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功能在于沟通中央与地方,构建稳定的内外秩序,对于乡村治理中构建“治理性团结”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文化、权力与国家》;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9-005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9.017
杜赞奇,印度籍美国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他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建立对华北乡村社会的分析和研究模型,使用《惯调》作为研究材料,提出了有别于施坚雅的农村市场体系研究、弗里德曼的乡村宗族研究、黄宗智的农村经济研究范式。该书是杜赞奇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在国内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书中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清末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国家如何通过文化网络来影响乡村公共权力的实施。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
20世纪40年代,华北乡村社会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下,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联系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伴随着当时中国两个方面历史进程的发展。正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导言中提到的,“中国国家权力企图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始于清末新政”[1]1。1900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面临着巨额赔款,需要向广大乡村的农民进行摊款。此外,西方列强意图通过清政府加深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将控制范围从中心延伸至更为偏远的乡村地区。这两项历史进程的发展都围绕着权力向下层的渗透和控制,西方的学者如查尔斯·蒂利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国家政權的建设”。杜赞奇对比了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与18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差异,又进一步批判地吸收了当时学术界施坚雅、马若孟、黄宗智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出发构建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分析的模型。
文化网络是权威以及权力产生的基础,是乡村社会乃至更大范围内秩序构建的工具。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杜赞奇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进行了阐释。“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槽状组织类型。”[1]13在这些组织之外,基于人际、血缘关系建立的网络也属于文化网络。在这些松弛的网络之中,文化发挥着聚合的作用,促进各种网络的交织与联结。封建国家的权力借用文化的外衣,能够在广大的乡村社会构建秩序,以达成政治控制的目的。
杜赞奇吸收了施坚雅的三级市场体系理论,将市场体系纳入文化网络的概念之中。不过,他认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研究只能反映出乡村社会的市场结构,却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结构,市场体系也不是维系乡村社会的唯一体系,还存在着如村内的小卖铺、街坊邻里关系、牙人、宗族、水利协会等网络在发挥着维系乡村社会的功能。杜赞奇对于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所提出的婚姻圈是以集市为中心的观点持不同的看法,他通过对比吴店村、寺北柴村两村的婚姻嫁娶关系,认为“集市中心并不是婚姻圈的中心,联姻圈以嫁娶村庄之间的距离为准”[1]18-19。因此,文化网络并不完全等同于市场体系,文化网络包括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在“文法、法统与晚清政权”这一小节内容中,杜赞奇解释了权力是如何在他所提到的文化网络中产生的。正如恩泽所说,“社会上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尊重的需要”[2]37。乡村社会的领袖的产生并不是偶然与随机事件,而是某种文化赋予人们的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荣誉感成为乡村领袖追逐权力的动力,在血缘、宗族、地域关系上形成的乡村社会团体通过彼此之间对文化的争夺,来形成稳固的领导地位。因此,乡村领袖只会固定地产生在某种文化之中,且有迹可循。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寺北柴的村长总是在富有的村民或者某一宗族之中产生。
二、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构成
(一)政治网络
官僚机构与双重经纪制度。在阐释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之后,《文化、权力与国家》接着介绍了清末乡村社会中的两种经纪模型:赢利型国家经纪人和保护型国家经纪人。杜赞奇指出,“清朝鼎盛时期控制下层社会的最主要工具是治安用的保甲制和征赋用的里甲制”[1]37。在历史上,宋朝推行保甲制度,以户为单位,设立户长、甲长、保长维持一定地域内乡村社会的治安。明朝实行里甲制度和黄册制度,通过里长和甲首来管理和控制基层。到了19世纪末期,清政府在里甲和保甲两种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下层吏役来控制乡村社会,以达到征收赋税的目的。杜赞奇认为,这种通过中间人来构建权威的方式就是经纪人制度。中央与地方的中介人并不仅仅限于衙役,还包括社书、里书、保正和地方。经纪人根据为自身谋私利、收取礼物和维护社区利益划分为赢利型经纪人和保护型经纪人。但与宋朝、明朝不同的是,清政府将地方士绅排斥在外。
自卫型社区组织。河北省的昌黎县县衙与村庄之间四级组织:班、堡、社、牌。杜赞奇在书中讨论到,“半牌”是各村以合作的形式给地方发放酬劳而结成的组织,但它超越了原有的职能,有时也能发挥联庄自卫的功能。村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是“半牌”。例如,1893年官屠以强硬的态度向散屠征税,社区自卫组织的干涉使散屠免受官屠的欺压。因此,昌黎县“半牌”的组织是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构建的典型。
(二)经济网络
水利管理组织与祭祀体系。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之中以河北省水利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为例,介绍了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经济网络的构成过程。最初,农民在牛尾河和百泉河修建堤坝,设置闸门,形成了周围区域的农业灌溉渠道。之后,用水的村民联合起来形成闸会,掌握灌溉水源的控制权,水利体系之中也出现了称为“闸”的组织。后来,在更多的村庄和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出现了更多以闸会为核心的水利管理组织,出现了比闸会更大的管理单位,闸会联合与全河流域灌溉区。实力强大的村庄拥有闸会的控制权,村庄领袖拥有河正的任命权。每所闸会另有龙王庙供奉着象征闸会组织的龙王。逢新河正任命之日,闸会成员会举行龙王祭祀仪式。祭祀仪式赋予和强化了闸会的权威,它使闸会中的成员相信,如果做出损害闸会经济利益的事情将会受到龙王的惩罚。这样,成员就不敢私下向村民售水谋取私利。
(三)宗教网络
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的第五章“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中,杜赞奇详细地分析了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他认为“宗教的等级制度、联系网络、教义及仪式是构成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1]111。第一种类型的宗教是村庄范围内村民自愿组成的小规模组织,庙会是这一宗教组织的典型的代表,多为敬神和庆典而设,如顺义县河南村中举办的灯会、戏会、果供会、龙王会、药王会、虫王会。第二种类型的宗教是跨越村庄范围的横向联合组织,仍然以村民自愿参与组织原则,主要表现为地方的香社、会社、理教等组织。第三种类型的宗教是村庄非自愿组织,与第一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区别在于,所有的本村人都在无意识之中被卷入组织之中。在这种宗教组织中,村民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认为本村的守护神灵如土地爷、五道和地藏菩萨有着保护村庄的作用,因而供奉和祭祀关帝庙、城隍庙、地藏王庙。这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将外村人排斥在外。沙井村的求雨敬神仪式是全村人必须参加的公务,但是没有取得该村村民资格的寄居村民不允许参加该类祭祀仪式。第四种类型的宗教组织是超越村界的非自愿组织,中心设置在村外,例如河北省栾城县的红枪会以及灵寿县积善寺。
(四)人际关系网络
面子。关系是网络形成的基础,而权力说明了这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或者社会互动,而是充满了交往中的等级地位、权威及其张力。[3]在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中人”在借贷、租佃和买卖土地等契约关系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人”的面子越大,承担违约风险的人心理负担就会减轻,贷款人更容易借到资金。农民想要赎回自己的土地,一定程度取决于“中人”的面子。在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赢得优惠条件的过程中,“中人”的声望和地位也在不断扩大,权力也在增加。
三、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功能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杜赞奇并未对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功能作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但是他用了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龙王祭祀仪式与河北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一是封建国家对于关羽的加封。
(一)龙王祭祀仪式与河北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
杜赞奇认为,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这种体系是国家政权控制乡村的一个重要工具。各个区域的闸会通过龙王祭祀仪式使闸会组织神化,从而获取大众的认可。对于闸会外部而言,附近村庄的村民不会质疑闸会的用水控制权和分配权。对于闸会的内部而言,闸会成员遵守内部会规,不私自对外出卖自己的用水之权,不破坏闸会内部的秩序。这样,闸会的权威得以确立,内外秩序生成。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文化如何使自然的网络变成人为的权力网络。暂且将闸会这种组织看作一种经济组织,在没有龙王祭祀仪式之前,闸会只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自然产生的组织,每个区域的闸会自然地联系着周围的若干村庄。通过龙王祭祀后,闸会获得神的权威,对周围的村庄形成了控制能力,构建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闸会从自然的网络变成人为的网络,演变成权力网络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龙王—闸会—村庄的权力网络如何连接中央和地方呢?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呢?当越来越多的规模不一的闸会纷纷通过龙王祭祀仪式或者修建龙王庙来获得神的权威,龙王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权威也不断扩大,龙王能裁决的事情和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也就越多了。伴随着这种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权力的文化网络在乡村社会的影响范围也在扩大。当这种权力的文化网络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甚至能在民間获得大众共识的时候,朝廷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地通过敕封或旌表龙王使神披上国家的外衣,从民间的神转变为国家的神,权力的文化网络也完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与控制,从龙王—闸会—村庄转变为国家—龙王—闸会—村庄,获得了控制地方的权力。
(二)封建国家对于关羽的加封
关羽是华北地区乡村祭祀和供奉最多的神灵,村民认为关帝的神灵权威可以护佑全国的百姓,其地位远远高于专管一村事物的土地爷。因此,外村人不会祭祀其他村落的土地庙,但是却会给经过的任何一座关帝庙进香。对关帝作用的解读在不同的村落和村民之中具有差异性。村民认为关帝不仅是财神,还是文神或者守护神,能庇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杜赞奇认为关羽神话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愿望。关羽最初只是被视为佛教的护法神,在宋朝开始被神化。首先是关羽英勇故事从道观流传到坊间。据说在山西某一处村庄,上古时代凶恶的蚩尤之灵危害一方,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这时,被道观供奉的关羽突然出现,率领阴兵英勇作战,最终打败了蚩尤。到了元代,元剧剧本创作者将这一故事编写成剧本,四处巡演,关羽的英勇形象随着戏剧的传播而得到强化。当关羽的形象逐步神化的过程中,以关羽核心的英勇、忠义的文化也逐渐深入人心,但权力的文化网络还尚未形成,因为还尚未出现借用关羽文化来形成权威的集团。正如杜赞奇所言,“自宋一直到明末,封建国家一直在神化关羽,但却没有垄断关羽权力的企图”[1]129。明朝敕封北京地区的两座供奉关羽的白马寺和月城庙,在认可关羽英勇的形象之外还尊封他为财神,赋予关羽更多的文化含义。这一时期,封建国家和社会大众都拥有对关羽信仰的解释权。
到了清朝,关羽的形象的解释权转移到朝廷手中,朝廷试图垄断对关羽信仰的解释权力,社会大众被禁止对关羽形象进行随意的解读。在以关羽文化为核心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权力开始生成。清政府通过1693年《圣迹图志》编撰使关羽逐渐儒家化。这一《圣迹图志》也是源于一则故事。据说,有人曾在关羽的故乡水井中发现了记载他的宗谱,翻阅宗谱才发现原来关羽出自忠义之家,乃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官员后裔。此后,清政府通过加封关羽三代为公爵来强化关帝的忠义形象。因此,民间的关帝石碑多为颂扬他对朝廷忠诚的事迹,而原来社会大众所认可的武神、财神、庇护神的含义被弱化了。关帝这一权力文化网络的构建少不了乡村社会精英的参与。当地士绅阶层通过关帝圣像来取得与更高一级组织的联系。
通过杜赞奇所列举的龙王和关帝的例子,可以发现权力文化网络功能在于沟通中央与地方,构建稳定内外秩序。对内的秩序表现为形成村庄共同体,维持村庄的聚合性,对外表现为维护封建国家稳固的统治秩序。
四、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权力文化网络构建的重要内容是组织,各种组织如商人团体、庙会、闸会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发挥着联结的作用。乡村治理同样可以依托公司、村民合作小组、农村合作社、村委会、尖刀班等组织的来发挥积极作用。权力文化网络构建的核心是文化,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祭祀仪式等多样凝聚着村民。乡村治理中文化治理须先行,通过祖先崇拜、村规民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此外,乡村精英在权力文化网络构建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型经纪人会促进中央与地方的发展,赢利型经纪人则会带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外溢,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发挥乡贤在乡村社会中的積极作用,构建“治理性团结”,另一方面还需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恩泽.实现人生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3]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J].浙江学刊,2021,(05):53-64.
作者简介:
王牵云,女,汉族,湖北鄂州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