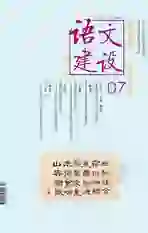送别诗的经典性:不可重复
2022-05-30孙绍振
孙绍振
一
对课文特别是文学文本的解读,不但是语文教学的难题,而且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难题;这个难题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尚待攻克的。西方文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涌现诸多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现象学到文化批评,从新历史主义到女权主义,旗号纷纭,均为攻打文本“城堡”而来。按学贯中西的李欧梵教授描述,诸多流派在城堡前混战数十年,旗帜乱而城堡安然无恙。英国文艺理论权威伊格尔顿直截了当地宣告文学这个范畴只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人群的建构,并不存在文学经典本身。美国理论大家乔纳森·卡勒宣称理论的任务并非是解决文学审美问题,而是质疑文学的存在:世界上既没有共同的文学这样一个实体,也没有文学性这样一个普遍理念。美国文学理论协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更是公然声言,理论并不能解决文本解读的问题,理论与阅读是不兼容的。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学理论界已经在文学文本解读方面坦承失败了,无能为力了。
在教育界却不然,美国诸多所谓阅读理论纷至沓来。近日有学者引进美国“三层级阅读”教学理论,颇具学术气象。然而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前卫文学理论大师的困惑,不是茫然无知,就是不屑一顾。推崇“三层级阅读”以“构建意义”,具体举例却是四层级。第一层级是读懂语言文字。第二层级是略读,快速把握重点。这两个层级看似轻松,但是没有提出问题,比如:怎样把握重点?把握不住重点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第三层级是分析性阅读,不限时间进行完整细致的阅读。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什么?如果是分析矛盾,而作品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分析從何着手?分析不了怎么办?第四层级是最高层级,比较阅读,不局限于单一文本,阅读多个文本,列出相关之处,提出“共同主题”。从理论上说,找出共同点是极其肤浅的。例如,提出《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牡丹亭》都属于爱情主题,能构建什么意义呢?这样肤浅归纳,就能保证阅读进入“最高层级”?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孤立的共同性是片面的。共同主题是普遍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分析的对象是矛盾,矛盾的特殊性才是研究的对象。从实践上来说,近半个世纪,在世界性的比赛中,美国青少年的阅读能力长期居于下游。对美国学界一知半解,抓住一鳞半爪,不经过反思,不加以任何批判,就将其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洋教条崇拜风气至今尚未引起国人之警惕。将这种所谓理论实施于课堂,面对的是微观个案文本,如何分析,如何比较,这才是关键的关键。
本文试以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为例,进行粗浅探讨。
二
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最基本的方法乃是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具体来说,是对语言文化的特殊性的还原。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安土重迁,世代定居。祖籍固定,然而学子赴考,将士出征,官员游宦,商贾出行,一去经年,国土辽阔,山河阻隔,回乡无期。故古代汉语中“生离与死别”并列为情感强烈之聚焦。《九歌》中有“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把别离之悲和相知之乐放在两极,实际上二者对立而统一,在诗歌中,表现别离之悲强于相知之乐。江淹(公元444-505年)《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说的是空间遥远;“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说的是岁月倏忽;“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最能表达激发悲情的往往在别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临行之际以诗送别,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高雅的文化风习,精品杰作汗牛充栋。
特殊性在于,送别诗多作于男性朋友之间,而很少有与妻告别之作。在此类母题中,友情高于爱情。《全唐诗》中有诗近四万九千首,作者两千二百多人,以“别内”为题的诗只有三首,皆为李白作于皇帝征召之时。究其原因,男权社会,送别往往是在公开场合,表现友情堂而皇之,表现对妻子的恋情则有所不便。诗人背井离乡,对妻子的思念为私密情感,然以“寄内”为题者(加上李商隐那首《夜雨寄北》,疑为“寄内”),也只有十五首。更奇特的是,对情人主要是歌妓之类的送别倒是很公开,特别是唐宋时期,杜牧、柳永都留下了杰作。乐妓、歌妓为官方所设,比公开表现夫妻之情更显风流。
李白诗作,除乐府古诗题目固定以外,白行命题者,人选《唐诗鉴赏辞典》的共六十首,其中标题注明送友者十九首,约占三分之一。随机抽样,即可说明朋友送别在唐诗中为突出的母题。
这样带着统计特色的还原,从逻辑上说是归纳,同时进行比较,揭示出送别诗在性别、友情和亲情上的差异,这还只是送别诗的普遍性。对课本所选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作具体分析的任务,乃是揭示其成为不朽经典的特殊性原因。能否揭示出其思想艺术之超越普遍性、唯一性,乃是课堂教学成败的关键。
这就要用上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品评。比较的基础是可比性。任意增加文本的阅读量,即使同类,也不能直接提供可比性;异类比较并非不可行,但要求具有比较高的抽象度。“列出相关之处,提出共同的主题”,这样的“共同性”就是普遍性,停留在普遍性上,不但有可能淹没文本的艺术创造的独特性,而且也不可能达到构建任何意义的目的。因为深刻的意义都是在对立统一中转化、运动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转,脱离创作实践,本来是西方文论的软肋。而中国古典诗论的优长乃是从创作实践出发。乔亿(公元1702-1788年)提出“句中有我在”,面临的问题是“景物万状,前人钩致无遗,称诗于今日大难”。乔亿提出“同题而异趣”。“节序同,景物同”,以景之真为准,则千人一面,以权威、流行之情为准,则于人为诚,于我为伪。真情不是公共的,因为“人心故白不同”,自我是私有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找到自我就是找到与他人之心的不同,“以不同接所同,斯同亦不同,而诗文之用无穷焉”。从阅读学的角度看,品评高下,拘于同则无个性,无艺术生命;艺术之生命在于独特,不可重复。因而,品评李白此诗当将其置于唐人同类送别诗中比较,贵在其异而不在其同。
唐人送别诗,一般双方同在现场,所见所感皆同,起兴直接共鸣,几乎成为模式。李白在这方面的杰作不胜枚举,留下了太多名句。例如:“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白兹去,萧萧班马鸣”(《送友人》),都是以共同的视觉激发情感之共享。
同题比较,特殊性显而易见,不难层层拓展深化。
李白寄王昌龄诗的特殊性在于,朋友并不在场,李白听到消息时,王昌龄已经在流放途中了。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怀念,聊解相思,如杜甫在李白遭难时,抒写梦见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故人人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朋友并不在场,所见景观不同,所思并不能共享,所作亦無从寄达,悲情白遣而已。
李白身在扬州,王昌龄白江宁丞被贬为龙标县尉,人已经到了现在的湖南省西部,过了五溪(武溪、巫溪、酉溪、沅溪、辰溪),二人距离遥远,李白不可能赶赴现场作诗赠别。在一般情况下,只能自我消愁。但是,李白此诗的特殊性却是不甘自我遣怀,题目标明“遥有此寄”。从江宁到湖南不下千里,李白所作并非公文,无法通过官方驿传送达。但是,李白还是要“遥寄”。这个“遥寄”,并非真的指望寄到王昌龄手中,而是虚指,明知无法送达,硬是想象王昌龄能够直接看到。“乐莫乐兮新相知”,李白与王昌龄并非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李白不在现场,不能分担朋友的痛苦,不能共享友情的温暖。
就是这种非现场性,成为这首送别诗在立意上的不可重复的特殊性。
三
立意只是起点,此诗成为经典,还得力于意象的情感内涵的特殊性。
“杨花落尽子规啼”,一个诗句,两个意象。春意消逝,不取桃李零落,而取“杨花”飘零。《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杨与柳合一,乃杨花柳絮通称,谢道韫言“未若柳絮因风起”,妙在飘落非直线下降,而是因风起降,全无方向感。而“子规”(又名杜鹃、布谷)呜叫,昼夜不止,声拟“不如归去”,呼唤回归故里。李白曾作《宣城见杜鹃花》日: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子规呼唤回归,而友人号称“左迁”,实际上无异于“流放”。用语明晓而寓意深沉。杨花意象隐含身不由己,远去荒僻异乡。“子规”,鸟鸣嘤嘤之美,反衬背井离乡之悲。
以两个意象建构一个诗句,于语法而言,“杨花落尽”是一个句子,“子规啼”又是一个句子,两个语法句浓缩为一个诗句。诗句大于语句,是古诗发展为近体诗之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在精练程度上超越了欧美古典诗歌。李白驾轻就熟,精练而不露痕迹,情意饱和。
第二句“闻道龙标过五溪”,以句法言,为连动式单句。然情感并不单纯。第一,听闻友人贬谪,已是伤感。第二,获得信息之时,友人已过“五溪”,从江宁去龙标是溯长江而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湖南西部,遥不可及。
此处,深入分析,无现成可比之诗句,只能直接作层次分析。表层句子为叙述性质,然而深层隐含双重情绪:第一,遗憾,握别无由,抚慰无方;第二,现实如此,无奈。表层意象群落有机统一,深层情感脉络隐性贯穿。
第三句,意脉一大转折:“我寄愁心与明月”,意脉由隐性转化为显性。情感不甘无奈,超越社会政治,诉诸想象,借助明月普照,跨越山河,缩短空间距离,化“遥寄”为直达。
明月意象构成意脉的跃进。不可轻易放过,须作诗学意象方面的宏观分析。借明月以怀远,是传统表现手法。如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汤惠休《怨诗行》:“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月光以其普照的自然属性,成为消解相思的意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古》)月光意象的功能不仅是空间的共在,而且是时间上的共时。但是,这些只是物理属性,月光作为诗的意象,还积淀着美好的意味。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明亮的月光与纯净的女性相得益彰。贾岛《题李凝幽居》借月构成意境:“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不强烈的月光与僧人的脱俗气质和谐统一。月亮不但明亮时是美好的,不明亮、朦胧的月光也是美好的。如“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苏东坡《春宵》),“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秦观《踏莎行》)。爱情的美好,就在花前月下。中国的爱情之神,不是长着翅膀的丘比特,而是月下老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情人幽会佳期。月下意象蕴含的意境传统,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古典诗歌被当作镣铐打碎以后,仍然生命不息,渗透到现代散文中。如朱白清的《荷塘月色》中写清华园朦胧的月下美景: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
之所以成为不朽的经典,就是因为现代散文语言与古典诗歌朦胧月色的意境水乳交融。
当然,完全没有月光,一片黑暗,情绪就不同了:“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就有军情紧急的氛围;而“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就很恐怖了。
展示如此众多的月光意象,目的在于提供大量的可比性,揭示李白此诗深刻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月色,不管是明亮的还是朦胧的,都是静态的,是视觉观赏性的。而在李白这里,“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题目上是“左迁龙标”,龙标还是个县名,很抽象,不成意象。诗里变成了“夜郎”,有名的蛮荒不毛之地,而且非常闭塞。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月光不是通常诗歌意象中的无处不在、静态的自然景观,而是动态的;不但是可以追随的,而且是听从李白差遣的。
以这样诗意的想象,李白消解了不能当面与王昌龄握别、赠诗的遗憾和无奈。
这个安慰王昌龄的使者,不是透明环境的背景,而是李白的“愁心”的载体.不但与王昌龄在地理上零距离,而且在心理上零距离。这就是李白这首诗最杰出的特殊性所在。
本来月光的意象,有时也带着诗人的忧愁,像曹操《短歌行》中有:“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明月是静态的喻体,解忧并不因明月,而是要借助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在李白这里,动态的明月携带着他的忧愁,不但送达对朋友的关切和安慰,而且也是自己遗憾和无奈的解脱。
四
此诗的特殊性分析到这里,还只是情感的特殊性。不可忽略的是:绝句的句法,内在的机制,统一而有微妙变化的特殊性。
开头第一句,“杨花落尽子规啼”,两个语句,结合成一个诗句,两个意象,有声有色,意象密度很大。從句意来说,是可以独立的。而第三句“我寄愁心与明月”,作为句子是完整的,只是动机,却并未表明目的。从逻辑上讲,并不完整;从情感的意脉上讲,并不能独立。只有与第四句“随君直到夜郎西”联系起来,目的、动机才不至于空悬,逻辑才能完整,意脉才能统一。这叫“流水句”。凭着这样的流水句,诗人的友情就不再潜在于意象群落之中,而是借助动态的意象抒发了出来。
这首绝句本来四句都是七言,难免单调,故除句中平仄交替,句间平仄相对以外,句法隐性变化不着痕迹。意象疏密交替,句法单纯而有变化,把绝句的技巧驾驭得出神人化。
为了彻底地解开李白此诗的艺术奥秘,比较还可进一步深化到李白和王昌龄同样写送别诗的特殊性。
王吕龄在当时号称“诗家天子”,绝句成就最高。立意的出奇、意象的疏密、意脉的流动,王昌龄也是得心应手的。在水准上,他与李白旗鼓相当,某种程度上可能还要略胜一筹。以王昌龄的送别之作《送柴侍御》为例: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该诗为王昌龄被贬于龙标时所作,这位柴侍御要离开,王昌龄以诗送行。在立意上,似乎与李白唱反调。李白说朋友远行,自己的忧愁之心不得解脱,要寄明月追赶,伴随在朋友身边。而王昌龄却说,“送君不觉有离伤”。这不是无情薄义吗?还写什么赠别的诗呢?但是,后面两句揭示原因:“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此去不是离开,因为青山相连,云雨相同,特别是,明月不用作李白式的追赶,也是所去与共,因而不改情感相通。
事物的可比性是无限制的,一般举例难以周全,深入到同样的主题群落中去,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古典诗人伟大的艺术奥秘。古典诗歌中离别因山川相隔而忧伤。这已经有了许多名作,如王勃的《秋江送别》:
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
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眼前尽是他人的归舟、归骑,都是回乡,而自己却是离乡。虽然此行水路,虽说他乡与此乡一水相通,一脉相连,可是才一出发,还没有到达他乡,友情的伤感已如此强烈,使得此乡变成他乡。与王昌龄的立意恰恰相反:王昌龄说,不管山遥水远,友情永恒不变,山川并不是相隔,而是相连,友情使得他乡变成此乡。而王勃却说,友情如此深厚,才开始出发,此乡就变成了他乡。
从手法上比较:这类诗作都是借意象来抒发情感的,因为情感的、抽象的意象可感,借其可感性表现情感。就抒情的方法而言,这是间接抒情。间接抒情并不是抒情的唯一方法,与之相反的是直接抒情。再看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里的情感的核心“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没有借助意象的可感性,而是直接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因为情感上是知己,所以不管你在天涯海角,都如在身边。这就不是间接抒情,而是直接抒情。这样的直接抒情,还成为格言。为什么没有可感性的意象也能流传千古呢?因为这里的逻辑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从客观上说,天涯海角之遥远,并不因情感上亲切而改变。但是,这是理性逻辑,因知己而变得亲近,这是情感逻辑,情感与理性是对立的,越是超越理性,情感越是强烈。这在中国古典诗话中,叫作“无理而妙”。此类诗歌中,经典之作也是海量的,如课本所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要把直接抒情讲透,还请耐心等待我的另外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