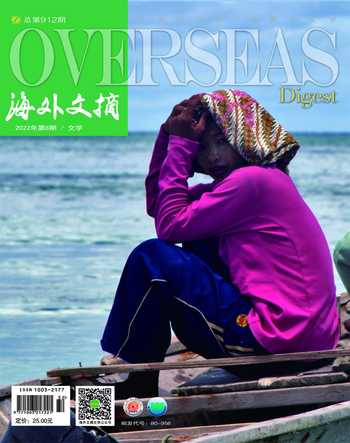遥远的筒子楼
2022-05-30夏鲁平
夏鲁平

一
我努力想象罗强的形象,是因为他打来的几个电话。我不认识他,又不能说完全不认识,起码小时候我们两家是邻居,经常见面。他那双晃动的大眼睛,极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由此我的眼前很快浮现出一群人的影像,虽然年代久远,却画面清晰。
影像的主人公无疑是罗强的父亲罗叔叔,他是我父母常挂在嘴边的人物。有一段时间,我父母在厨房做饭时讲,在饭桌上讲,上床睡觉前也讲。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罗叔叔的名字罗志贤,就会从他们嘴里溜达出来,铺展开去,信马由缰,最终落在罗叔叔炒菜这件事情上。我母亲说,男人下厨房跟女人不一样,他总是把锅碗瓢盆随手乱放,每次做饭,都能看到他家的铲子、勺子扔到我家灶台这边儿到处都是,我不得不帮他收拾起来,涮干净了放回原处。我母亲不得不承认,罗叔叔干活虽然邋遢,但炒菜味道在筒子楼是一流的。在我印象中,罗叔叔炒菜不仅香,还特别,别人都是左手握大勺把柄,右手挥舞菜铲,而罗叔叔却是反着来的,左手挥铲,右手握大勺,那动作怎么都让人看不惯。
其实罗叔叔炒菜的香味,完全来自油锅里的一种食材——辣椒。罗叔叔一家是湖南人,辣椒是必不可少的作料,他家经常炒的是大头菜或菠菜。菜放进大勺,他便大把大把地往里投放辣椒,那横冲直撞的辣味总是灌满了整个走廊,呛得人不住咳嗽,流眼泪,然后又努力回味那刚刚飘散的辣香,荡气回肠的。
那时,我们家住在我父亲单位分配的筒子楼里,十几户人家,都是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把那筒子楼带动得极为扎眼。筒子楼的特点是,每家每户共用一条走廊、一个厕所,生火做饭的厨灶全搭建在走廊里,厨具铁架子挤占了走廊的半个空间。这样一来,过道就过于狭窄、逼仄了。有人在那里做饭,身后屁股时常蹭到过路人的身上。这时,不管手头多么要紧,都要直起身,缩紧屁股避让行人,嘴里还要打一声招呼:“回来了?”“做饭哪!”或是“出门啊!”也有不打招呼,直接走过去的人。
筒子楼里的人说话南腔北调,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什么事情都好奇,说话也吵吵嚷嚷。一到做饭时间,走廊里挤满了一群系着围裙、个头高矮不齐、穿着花花绿绿拥挤忙碌的身影。这些人有的默不作声,有的有说有笑。一通热闹之后,饭菜做好了,端起盛有饭菜的碗回到自家屋里,人流散去,欢喜的日子就包裹进了自家的房间里。
我们这座城市很早就有了煤气,筒子楼更不例外。每次打开煤气灶,那蓝色的焰火,会让那些楼外住平房的人家好生羡慕。那些人家用的全是煤烟炉,也有烧木柈的。漆黑的油毡纸房顶,常年歪歪斜斜地竖立起一根又一根烟囱,袅袅炊烟从烟囱里钻出来,在天空指引着风的去向。
筒子楼顶没有烟囱,这显得平房屋顶的烟囱也格外突出。这些平房里的人家,为保持室内的温度,冬天晚上从不弄灭炉火,睡觉前往炉火中添加一层湿煤,闷住炉火,一不小心,就造成煤气中毒事件。那些住在平房里的人不仅羡慕筒子楼里的煤气,更羡慕暖气,而我们筒子楼里的人羡慕的,与他们不同,是罗叔叔炒菜的香气。据我母亲讲,罗叔叔炒菜除了用葱花、花椒面、味素、酱油、辣椒这些作料外,很可能得力于对煤气的火力控制。可以调控的煤气灶,加上罗叔叔的左撇子,炒出的菜自然卓尔不群。
有一段时间,我母亲把罗叔叔左撇子看成是干活不得要领,她曾尝试加以纠正,手把手教他如何使用大勺,如何挥动炒菜铲。罗叔叔很是虚心,及时采纳了我母亲的意见,几次操作后,竟然满脑门是汗,不但左撇子毛病没有改过来,反而两手不知如何使用,也不会炒菜了。
后来得知,罗叔叔只是照顾我母亲的面子,才不得不临时改正一下原有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
那时在筒子楼里,每个楼层只有两个厕所,男女各一个,且紧紧相连。厕所每天安排一户人家值日打扫,门口挂着小牌,写着户主的名字。有的人家打扫不及时,就有人操起扫把顺手收拾几下。干这活最多的,女厕所这边是我母亲,男厕所那边是罗叔叔。因为打扫厕所,我母亲和罗叔叔就有了很多次交集。每每打扫完厕所,两人磕磕扫把,都会给对方一个敬佩的目光。
有了这层关系,我母亲每提出一个建议,罗叔叔都虚心采纳,照搬不误。细心的我母亲后来发现,罗叔叔的毛病不但没改过来,反而增添了新毛病——他往大勺里放酱油时,也是反着来的,握有酱油瓶的手总是往外翻,这一翻,手背朝下,手心朝上。当一股细流涓涓溢出瓶口的时候,罗叔叔对酱油拿捏的准确程度叫人十分惊讶,我母亲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炒菜发出的香味,完全出自奇特的思维。
二
我家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如一块整砖那样大小,镶有蓝白相间的塑料壳,里面放两节一号电池。每晚吃饭时,我母亲把这金贵的玩意儿移到餐桌上,我们边吃饭边听半导体收音机,那里面好听的声音常让我忘记对饭菜的吞咽。
在半导体收音机之前,我家使用的电匣子,也叫戏匣子,体积如同现在的微波炉大小,固定在一处,用插销通电。由于使用年头过长,电匣子一天比一天老化,像上岁数的人不可避免生病,不住咳嗽。每当电匣子出现吱吱啦啦或咳嗽声,我便使劲儿拍打其外壳,说不定哪股寸劲儿,里面的声音又完好如初。
不管是收听电匣子还是半导体收音机,都是我了解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我們家的精神食粮。那里面的风声、雨声、雷鸣声,常常把我们带入流连忘返的神奇境地。我还能从播音员甜甜的声音里,猜测他们长的样子。想象是有力量的,能够生出美丽的翅膀,在我脑子里长久萦回飞翔。那男播音员,我会把他安装在罗叔叔身上;那女播音员呢,我自然会想起罗婶。这样一来,那虚幻的美也就落到了实处。
罗叔叔家没有电匣子,也没有半导体收音机,他所知道的国内外大事,多数来自这台半导体收音机。罗叔叔在走廊做饭、炒菜时,总是支棱起耳朵收听我家里的广播。听到关键处,他停下手里的菜铲,得寸进尺地歪起头,将耳朵凑到我家门口,听得如醉如痴。知道罗叔叔有这一爱好,我母亲就把屋门打开,让收音机音量顺畅地跑到走廊,跑到罗叔叔的耳朵里。我家遮挡屋门的半截布帘,会随着半导体的音量,一鼓一荡,我也时常看到帘外立着的一双腿,如施了定身术般一动不动,久久不肯离去。
我母亲说,多亏那时没有电视,要是我家屋里播放电视新闻,罗叔叔脑袋非探进屋里不可,那样,我家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罗叔叔只是在门帘外面听,无论如何也不越雷池半步,他严格遵守这一规矩,从没打破。听了广播的罗叔叔,对于全国各地的大事小情如数家珍,嘴里也时常挂着北京、武汉、南京、重庆,还有我记不住的城市名字。他身处东北长春,却眼望着全中国,视野大开着。
罗叔叔家屋门也挂着半个门帘,是个蓝花布。有时我跑出家门,跑到罗叔叔家门口,从那半个门帘下面往罗叔叔家看。那屋里跟我家不一样,床宽,书桌子比我家的大,有一堆书从地面摞到屋顶,上面夹着一个个零乱的字条。他家棚顶有木杆滑道,从上面坠下一扇布帘,偌大的床铺就被一隔两段。床上盘腿坐着一个老奶奶,她对小孩很不友好,看见我张望,嘴一抿,吐出一口假牙,红乎乎一团,吓得我撒腿跑掉,她借机鬼魂一般消失在布帘后面。
老奶奶是罗婶的母亲,严格讲我应叫她姥姥,但我们习惯对所有老太太称之为奶奶,就像现在我这一把年纪的人走在街上,总有年轻者称我为爷爷一样。老奶奶户口在湖南乡下,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证,她来这里,等于挤占了罗叔叔家的口粮,所以他家的日子比谁家都拮据。据我母亲讲,罗叔叔每月会抽出一个星期天,将自己乔装打扮成工人或农民模样,鬼祟地走出家门,去黑市上购买粮票。再用粮票为家里添补粗粮。有一次,罗叔叔在黑市上进行交易,让人盯上了,被扭送到公安机关。遣返回单位那天,他衣服上一只袖子从肩膀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脖颈上有明显的抓挠血痕,别提有多狼狈了。
罗叔叔活得窩囊,三天两头跟罗婶打架。他俩打架很特别,总是事先压抑着声音关好门,然后低声吵,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加大了嗓门,随之噼里啪啦打斗起来,乱了阵脚,有碗盆摔在地上,四周灰尘腾空而起。罗婶是典型的辣妹子,动起手丝毫不怯懦,从力气上较量不过罗叔叔,就使用惯常的招数,一头撞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其裆部,拉、扯、拧、撴,罗叔叔立马老实了,脸色煞白,冷汗涔涔,呼救着我父亲前去拉架。他们每次打架,我父母的原则是,能装听不见就装听不见,实在听得不能忍受,才去咚咚敲响罗叔叔家的屋门。我父亲在隔壁苦口婆心相劝,我母亲这边也没闲着,她拿起家里利用率极高的搪瓷茶缸,轻轻扣向墙壁,歪起头,耳朵贴向搪瓷茶缸底部。
茶缸有扩音和拢音的效果,落到茶缸底部的耳朵,如同探进了罗叔叔屋里,什么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我母亲离开屋子去走廊拎暖水瓶,我趁机拿起搪瓷茶缸也扣在墙上,耳朵贴上去,里面不知怎么突然炸开一声巨响,震得脑子嗡嗡生疼。
在厮打最为惨烈的时候,屋里那位老奶奶什么话也不说,拽起她的孙子罗强往屋外跑,紧迈碎步来到街上,肌肉扭曲的脸冲向空旷天空,嘴里发出愤怒的叫喊,那声音里分明是对罗叔叔不满。罗强年龄和我差不了几岁,我们在走廊里相见,也不说话,只是彼此用眼睛看,静静看,没有敌意,也没有友好。他的眼睛又大又圆,像刚刚从水中捞出来的黑葡萄,晶莹剔透,会勾起我想从上面摘取一粒的欲望。
不管罗叔叔和罗婶打得如何,一旦休战,两人关系立马逆转,似乎比以往更加亲密。在这种亲密期里,罗叔叔像打了鸡血,乐颠颠地跑到走廊炒菜、做饭,罗婶也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配角,跟在罗叔叔背后,手忙脚乱摘辣椒,准备葱姜蒜。那副样子,看着有点让人肉麻,我母亲为此不知偷笑过多少回。罗婶很会与外人相处,全楼暂停煤气的日子,她会从家里端出半盆玉米面,走出筒子楼,一溜烟儿消失在胡同平房里,不到一个小时,又端回一盆油亮亮、黄澄澄的玉米饼。撞见我母亲,脸上羞涩地一笑,不由分说掀开盆帘,塞过来两片玉米饼。我母亲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她知道罗叔叔家粮食不够吃,这些玉米饼来之不易。两个女人像打架一样撕撕扯扯好一阵儿,最终我母亲还是强行把塞到怀里的玉米饼送回到罗婶的盆里,彼此又都心无羁绊地分开了。
三
腊月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咔吧脆响,做什么事容不得怠慢和犹豫,于是这里的人性子急,做事直截了当,来不得含糊拖延。而对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温和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不同,他们做事三思而后行,极为含蓄,也极为隐蔽,就像那时许多单位需要保密。保密单位都是用数字代替的,比方说,长春航空液压厂,叫133 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叫652 厂;厂办小学叫652 小学,中学叫652中学。652 厂职工住着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家属宿舍,冬天从生产车间流出的余热,顺着暖气管道注入每家暖气片里,屋里热得需要将窗户四敞大开,热气腾腾的白雾会冲破室外寒冷,缥缈地散开。
这些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性质也都是保密的,所以做事含蓄、隐蔽十分必要。我觉得我父亲的工作没什么可保密,看上去他也极为平庸,但每年年终他会准时捧回家一个印有“先进工作者”的竹篾罩保温瓶,或者带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我又认为我父亲不平庸,只是他对工作上的事守口如瓶,我就以为他平庸罢了。我父亲和罗叔叔在同一科研单位,同一个科室,两家又同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筒子楼,这样的关系很是微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
筒子楼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过春节。春节是大节日,楼里人平时可以很少来往,过春节就不同了,大家同处在一条大走廊,需要在这时间走动走动,表明彼此友好。这种表达方式是相互送饺子。过年我家煮出的头一锅饺子,要盛出一碗又一碗,然后庄重地端给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同样送来一碗碗刚出锅的饺子。饺子在走廊里端来端去,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烘托起节日热烈的气氛,很是温暖人心,其乐融融。每家的饺子各不相同,吃到不同人家包的不同味道的饺子,无论咸淡、浓厚还是清爽,心里还是欢喜的。我们家给邻居家送去的饺子常常是单独和馅,这馅里的肉比自家吃的饺子肉多,这是个脸面问题,也是为人品德问题,必须这样做。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罗叔叔家异常尴尬了,罗婶不会包饺子,他们家过春节从不包饺子,但办法还是有的,就是把东家送来的饺子送给西家,西家的饺子送给东家。有一次,罗叔叔端起一碗饺子刚出门,脚跟不稳,猛地被门槛绊了一跤,整个人摔出门外,碗打碎了,饺子散落一地,人狼狈得趴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
那碗饺子很有可能是送给我家的,我们都这么认为。不久,罗叔叔果然敲响了我家房门,是轻声,像特务接头暗号那样见不得人。我们正在吃自己包的饺子,母亲手攥着筷子去开门。罗叔叔手里拎着一只网兜,没等说上一句话,便自作主张往屋里挤。网兜里装有三条冻鲤鱼,我们全家知道罗叔叔是送鱼来了,以补偿那次没有送来饺子的尴尬,热烈的情绪随之高涨起来。
我母亲嘴里发出:“哎呀呀,啧啧!”
我父亲马上撂下筷子跑向门口,同样回应:“哎呀呀,哎呀呀……”他们只能用“哎呀呀”代替千言万语的感谢之情。
罗叔叔闷声拎着网兜,没工夫回应我父母的热情,执意往屋里闯,很害怕我父母这时把他拒之门外,他说:“进屋再说。”
我父亲,包括我母亲怎么好意思让罗叔叔顺顺当当进屋呢,罗叔叔要是轻易进来,显得我父母太不知深沉,太那个了。两人就极力向外阻拦,不管怎么阻拦,罗叔叔还是没费多少力气挤进屋来,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总不能让罗叔叔一直拎着鱼,我母亲从书桌底下抽出一只盆,接过罗叔叔手里的网兜,将三条鲤鱼倒进去。再客气就絮烦了,我父亲从桌底拉出一个板凳,拉扯罗叔叔衣袖,亲热而实在地让他坐下,一只手紧紧握住罗叔叔的手,半天不肯撒开。
我母亲嘴里不停地说:“你看这事,这事,你们留着吃多好。”
罗叔叔很为自己的得逞而得意,他坐在板凳上,挣脱出我父亲紧握的那只手,使劲搓着带有腥味的两手掌心说:“这鱼刚从水库打捞上来,出水不到两个小时,吃着新鲜。我看你家总也不吃鱼,给你们拿来三条。”
我父亲脸上堆积着膨胀的笑容,说:“真是真是,我家总也想不起来吃。”
罗叔叔忽然说:“三条鱼,我也不多算,给我四块五毛钱就行。”
母亲的脸咯噔怔住了,手僵在了那里。我父亲脸继续膨胀着笑,但那笑已凝固成一块硬团儿,别提有多难看了。原来罗叔叔这三条鱼不是白送,是卖给我家。我母亲缓过神儿,为自己找台阶说:“好,好,我现在给你拿钱。”回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铝饭盒,掀开盖,找出四块五毛钱。可能钱币之间有所粘连,不愿离开,我母亲用食指和拇指对每张纸币强行挤捻几下,递给罗叔叔,不受控制的手簌簌抖动起来。
罗叔叔的行为,搞得我父母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条鱼被收下了,收得勉为其难。送走罗叔叔,我母亲认真端详三条鱼,心里掂量着这到底值不值四块五毛钱。我父亲大大咧咧地说:“四块五毛钱,不贵,咱家的确应该吃一顿鱼了。”
当天晚上,我母亲收拾出三条鲤鱼,拿到走廊炖在大铝锅里。
我母亲说,就是这次炖鱼,险些与邻居发生矛盾,酿成事故。也不知罗志贤安的什么心,好事都他做了,反倒显得我们里外不是人。
原来是我母亲炖鱼时间过长。只有长时间煮炖,鱼才能好吃,有一句老话叫千炖豆腐万炖鱼。这平平常常的炖鱼,暴露出厨房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煤气的使用。因为一层楼所有人家使用一个煤气表,到月底用掉多少煤气,平均分摊费用。这样一来,有的人家做饭简单,使用煤气有限,月底拿出的煤气费却不比别人家的少,吃了哑巴亏,又不好意思声张,只能暗自较劲儿、生气、制造事端。
我母亲炖鱼是悄无声息的,也是低调的,等鱼香飘满了整个走廊,就有人提起鼻子往走廊里嗅,看谁家做这么好吃的东西。三条鱼炖了一个多小时,我母亲觉得时间不够劲儿,要继续炖下去,这时,住在靠近厕所的那家女人,出门朝我家这边看了两眼,也打开炉灶,烧上一大铝锅水。这户人家平时做饭比较简单,爱干净,炉灶无论什么时候都擦得油光锃亮。这家女人还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烧上一大铝锅开水,端进屋里,去洗澡。春夏秋冬从不间断。那哗哗啦啦的撩水声,清脆而响亮。那家男主人为了不让木桶里的热气散发得太快,特意用一大块塑料布制作了一个木桶罩,女主人钻进木桶,男主人把塑料罩扣上,不管女主人在木桶里怎么撩水、擦洗,水珠都不会溅到桶外。这样一来,塑料罩表层往往蒙上一层迷雾,女主人晃动的朦胧身影,如同在演一场皮影戏。
虽然这户人家做饭简单,但女主人每天烧水用去了不少煤气,也不算吃亏。在我母亲炖鱼的时候,那边却不这么想,而是把她家的煤气灶也点燃了,比平时烧洗澡水提前了两个多小时。据我母亲讲,罗叔叔那天晚上,特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掀开那家铝锅盖,发现那里面除了水,还有一块石头。罗叔叔说:“我过高估计了他的科学精神,原以为那家男人在做什么实验,其实不是的,纯属是为了赌气。”因为煮过石头的水,很快被那家女人倒进了下水道。这种赌气方式,使这层楼煤气使用量明显超标。
面对用锅煮石头女人的不满,是罗叔叔前去解的围。他也炖上了鱼,炖的时间不长,炖鱼的香味从锅盖缝处飘出来,丝丝缕缕弥漫到走廊时,他关掉灶火,端起炖鱼锅,送到煮石头的女人面前。对于慷慨的罗叔叔,那家女人无话可说,她关掉了炉灶,跟罗叔叔你推我搡谦让一阵,不得不接过两条炖好的鱼,直夸奖罗叔叔的鱼炖得好香。
这期间,我母亲与罗叔叔之间发生了一件极为秘密的事,我是当事者,只是年纪太小,一直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出了那件事后,我有好长时间没看見罗叔叔,他也没脸面再见我母亲了。
没过两个月,罗叔叔去南京出了一趟差,回来时,他身穿一套崭新的西装,衬衫领口打了个歪歪扭扭的领带。罗叔叔要调走了。没过几天,筒子楼下开来一辆大解放车,跳下一群工人,帮罗叔叔搬家了。那是一个早晨,罗叔叔和罗婶早早起床,罗婶身穿一件我从没见她穿过的真丝旗袍,整个人显得焕然一新。罗叔叔还穿他那件崭新的西装,手握一把木梳,反反复复梳理头发。他的头发平时很不规整,罗叔叔就不断往木梳齿上吐上口水,再梳在头上,湿润的头发成绺地贴向头皮。有一只飞虫落入发丝,怎么也不肯离开,他头顶着那只飞虫,浑然不知地跟人打着招呼,然后走出楼道,走下楼梯,来到楼门外,一头钻进那辆装满他家物品的大解放汽车里。车缓缓开走了,整个筒子楼里的人的心好像一下被抽空,而我看见罗叔叔头上还顶着那只一动不动的飞虫,不停地挥手与大家道别。
四
很多人不知道罗叔叔调走的真正原因,我母亲敏感地意识到,羅叔叔这次调动绝非偶然,他是因为与我母亲之间那个秘密而毅然决然调走的。那是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他必须离开。
前面讲过,罗叔叔家因为吃饭问题总跟罗婶打架,自从他当了科室小领导,一切风波都消失了。罗叔叔变了,看上去格外刚毅,还有点鬼鬼祟祟。那些日子他是怎样从困境中走出来,安抚住罗婶,稳固住他的家庭的,不得而知,但他在单位带领大家奋勇攻关,获得两大科研成果奖励,尽人皆知。
有一天,我母亲点燃了走廊里的炉灶火,淘米下锅,加水熬粥,回身进屋给我扎辫子,两条辫子。我母亲喜欢女孩,就把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当女孩打扮。她给我买花衣裳,穿裙子,扎小辫,由着性子任意摆布,简直不可理喻。
我头上小辫子扎完一条,准备扎第二条时,我母亲想起了走廊里的一锅粥。她手握着我一条辫子打开房门,看见粥已经开锅了,热气鼓动着锅盖叭叭作响,浓密的米汤溢出来,顺着锅沿汩汩流淌,浇得蓝色的灶火一惊一乍。我母亲掀开锅盖,放小了灶火,手握我头上的小辫回屋,继续编织,编完了,还在辫梢扎了两根大红绳。我母亲又想起屋外那锅粥,她拉着我的手打开屋门,准备再看一眼锅里的粥,也就在这时,她猛地定住了,牢牢定在那里,因为罗叔叔那只左撇子手,正握着一把大勺子从我家的锅里出米粒,投放在自家锅里。他家的锅也在灶上烧着火,里面同样翻滚着清爽的米汤。看样子,他从我家锅里出米粒不止这一勺,那左撇子动作如行云流水,顺畅无比,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时我母亲会出现。
惊诧地定在那里的我母亲,表现出少有的机智,赶紧撤身说:“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她还试图从脸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可最终没有笑出来。罗叔叔那只左撇子手,就那么握着勺子,不会动了。隔了几秒,他慢慢转身回过眼神,目光软软地看向我母亲。我母亲极力退缩,加了个摇摆的手势,嘴里不停地说:“我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那时的罗叔叔,我父亲的领导罗志贤,眼里忽然布满了哀伤,他努力地看向我母亲,可我母亲根本不看他,她想的是怎样快速退缩、退缩。罗叔叔眼神猛然低落下来,落到我母亲的膝下,他把目光投向了我,投向了我的眼睛,随之身子矮下去。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不懂他的肢体语言,一个劲儿往我母亲身后躲,试图让母亲遮挡住我。罗叔叔就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两手揪起自己的头发,痛哭。他的哭,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母亲终于缩身退回到屋里,她关上门的工夫,一下把我扯倒了,随之,她的手扣住我的嘴巴,没让我发出一点哭声。
对于这事,我母亲后来极为愧疚,甚至是痛苦,这痛苦一点不亚于罗叔叔当时的痛苦。她说:“千不该万不该我在那时出门,鬼使神差地撞见罗志贤,见到他,又千不该万不该反应过激,我们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谁还没个难处,没个缺吃少穿的时候。”
我母亲因为没机会跟罗叔叔说上这些话,总像藏着一块心病,一直到晚年,她还念念不忘。
五
上世纪80 年代,也就是罗叔叔调走没两年,我父亲单位盖了几幢家属楼,那个让我们骄傲的筒子楼早已光环不在。我们家搬进了新楼三室房子里,我父母时常想起罗叔叔,认定他没能住上这样的新宿舍,真是可惜,亏大了。但据去过南京回来的人讲,罗叔叔在那家单位发展得很好,已成为声名显赫的大领导,大得让人可望而不可即,有时报纸、广播里都能出现他的名字。
这几天我连续接到罗强打来的几个电话,他说他出差来东北,参加一个医药会议,受罗婶嘱托来看看我父母。我告诉他,我父亲去世十年了,我母亲前年冬天也离世了。罗强在电话里沉吟起来,我问,罗叔叔身体可好吧?他说,上个月去世了。
那一代人很快过去了,我们后辈也进入了人生下半场。
我提出在我家楼下附近咖啡馆里见个面,罗强很高兴地应允,随即我们加了微信,我给他发了个位置图。一个小时后,罗强乘坐出租车过来。那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人,陌生得不敢相认,但他那一双晃动的大眼睛,又恍惚唤起我的记忆,小时候我们是时常见面的。罗强说,他有很多话要跟我说。
他说,他在整理罗叔叔的遗物时,发现了两个厚厚的日记本,里面零零碎碎记录着我们两家的来往,似乎有许多只有当事人可以看懂的暗语。他想知道他父亲当年经历了什么,受到了什么刺激。罗强说罗叔叔晚年脾气一直不好,发作起来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段时间他对父亲失去了耐心,厌倦透顶。
经过窒息般的沉默,罗强回身拽过身边的兜子,打开拉锁,他说他父亲留下的日记也不全晦涩,有些页码能看懂,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他手颤抖着拿出两本发黄的日记本,一股陈年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掺杂着刺鼻的辣味,萦绕开来。他说:“我原准备把这些日记全部烧掉,虽然里面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隐私,但我还是留了下来。”
我接过日记本,一页页地打开,停留在一则记录上:
今天腊月小年,室外大雪飘飞,我与朋友Z 去水库打鱼。年关刚过,那里管理很严,也许是大雪天的缘故,冰面不见一人,几米之外视线极差,这正是捕鱼的好天气。我与Z 在冰面开凿一个大窟窿,由于冰底缺氧,无数条鱼向窟窿涌来,我们捞得十余条,各分一半。回到家中,想着这鱼自家吃掉有些可惜,遂想到邻居夏家,春节过后送去三条。那一家人见到鱼,高兴得不得了。我随即改变主意,向他们索要四块五毛钱,场面虽有些尴尬,但夏家欣然接受。其实之前我做过调查,那三条鱼在副食商店里顶多卖三块五毛钱,我多卖出一块钱,夏家竟然不知,老夏聪明只是小聪明,实则愚也!四块五毛钱虽然不多,却解决了生活大问题。可是,我又觉得老夏没那么愚蠢,他很可能看出问题,只是留有情面,不想捅破罢了。每念及此,我心生悔恨,恨不得拿起刀来,将自己的这只手剁掉,剁掉那沾有污秽不堪的手。
蓝色的钢笔字体已经浅淡,那一笔一画蝇头小楷浸染在黄色易碎的纸张里,在我的眼前剧烈跳动。我的脑子里再次出现一幅黑白画面,生动而活泼,那是罗叔叔炒菜做饭时的身影,是他扒在我家屋门外偷听收音机的模样,也是他拎鱼敲门强行挤进我家的情形。在日记的后半部分,有半页搬家的描述:
……今年春早,室外树叶婆娑扶疏。调离东北,是我个人急迫需要,也是組织的需要,我必须抓紧实施,离开这个单位。正如一张白纸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重新开始吧,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后来,我父亲知道了我母亲与罗叔叔之间发生的事,他觉得有必要跟罗志贤把话说开,只有话说开了,我们家和罗叔叔家关系才如同从前。但罗叔叔始终躲避着我母亲,而且匆忙调走,一直没给我母亲说话的机会。调到南京的罗叔叔,开始步步高升,已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物了。这样一来,我父亲觉得更有必要把话说开。那时,常有些人带着套近乎的心理前去南京拜访罗叔叔。这些人中,大多是东北的老同事,也有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对于那些人,罗叔叔没有全部拒绝,他会有选择地与那些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老同事见上一面。每次接见他们,罗叔叔说话都小心翼翼,显得有些矜持,生怕哪句话出现什么纰漏,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更重要的是,他像爱护羽毛一样爱护自己的形象,与人说话,总是不停地检查自己的西装前襟或衣袖,只要上面有一点不洁之物,他都要认真地摘掉。每当有人不知好歹想与他回忆往事,罗叔叔立马沉下脸来,长时间不语,或顾左右而言他,眼神里全是含混、迷离,魂儿也飞走了,飞到不为人所知的世界。
这期间,我父亲获得了一个去南方出差的机会,那是一个大夏天,他利用星期天绕道赶往南京,去拜访罗叔叔,或者是想跟罗叔叔把话说开。那时打电话很不方便,我父亲一路打听着摸到罗叔叔家,是罗婶开的房门,她见到我父亲,大呼小叫把他拉进屋里。罗婶告诉我父亲,罗叔叔刚出门,没说出门干什么。我父亲坐在他家的沙发上等,左等右等,也不见罗叔叔回来。这时,我父亲完全可以跟罗婶把话说开,让彼此不必心存芥蒂,可是我父亲觉得这事太小,怕在罗婶跟前越涂越黑,反倒解释不明白,所以我父亲一直没张开这个嘴。这时已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罗婶扔下我父亲去厨房做饭。我父亲是个屁股很沉的人,也有点死心眼,他非要等罗叔叔回来,说出心里计划好的那些话。我父亲就这么留下来吃饭了,他想边吃饭边等,等饭吃完了,罗叔叔还没回来。我父亲坐在沙发上,难受地抬手嘎吱嘎吱挠起头皮,内心的矛盾、煎熬可想而知。我父亲觉得再这样耗着,连自己都说不过去了,他不得不遗憾地离开,那些憋在肚子里的话最终没有说出来。
六
罗强坦诚地透露,其实那天罗叔叔并没有出门,而是坐在书房里看书,听到门口罗婶大呼小叫,知道是谁来了,他赶紧起身钻进身后的大衣柜里。他以为我父亲见不到他会很快走掉,想不到我父亲在他家里不仅长时间喝了茶,还留下来吃了饭,害得罗叔叔在大衣柜里整整蹲了两个多小时。要知道,那是个大热天,大衣柜里闷得密不透风,罗叔叔就那么狠心咬牙蹲在大衣柜里,一声不吭。等我父亲离开,罗婶打开大衣柜的门,看见浑身大汗淋漓的罗叔叔已经不会动了,罗婶强拉硬拽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罗叔叔从大衣柜里弄出来。他缓过来的第一句话竟问:“他走了吗?”
罗强说他准备将罗叔叔的日记整理出来,完成一段回忆录,所以,他与我这次见面很重要。我努力合上日记本厚厚的纸页,心情复杂得半天无语。罗强起身去室外吸起烟,隔着厚厚的茶色玻璃窗,我看见罗强点烟的动作很是特别。究竟特别在哪里?我恍然发现,他也是左撇子,他的动作竟与当年的罗叔叔如出一辙,又在某些地方与他的父亲有着脱胎换骨般的差异。
吸过一支烟,罗强重新坐到我对面。他说他父亲死得很蹊跷,本来在床上躺了半年,人轻得像一张纸片,有一天却非要从床上坐起来不可。他让罗强把他移动到床下的椅子上,他坐在上面,脸不自觉地朝向了东北方向。罗强几次帮他矫正坐姿,可他的脸还是转向了东北。罗叔叔就以这种姿势在椅子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从椅子上滑落的方向也是东北……
罗强提出要去看看筒子楼。
我说:“那楼早就拆掉了。”
罗强说:“我看看那个原址也好。”
我说:“那你更不必动身。”
他问:“为什么?”
我说:“就在你的脚下。”
我还对罗强讲,当年拆掉筒子楼时,发现地下有一个密室,据我母亲讲,我父亲和罗叔叔曾在密室里一举攻克两大科研项目。罗强怔怔地看着我,满眼全是惊奇、惊讶,还有些难以置信。他慢慢站起身,再次走出室外,眯着眼仰头冲着四周的楼群,恍惚间,他的眼睛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