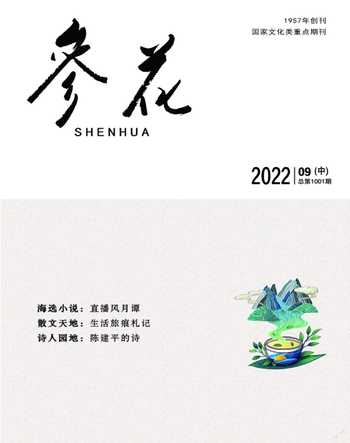欧洲近代的“伊利亚特”
2022-05-30戴诗涵
《浮士德》高度概括了恢宏的社会历史和实际现实,作者歌德通过对叙事节奏的把控和全景式的描摹,还原了欧洲近代的社会风貌,与《荷马史诗》带来的冲击与震撼感有异曲同工之妙,极具史诗性色彩,无愧“欧洲近代的‘伊利亚特”之称。此外,歌德在《浮士德》中刻画的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时代感,高度凝结了社会一般性,使得其主题意蕴能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焕发出独到的光芒,加深了作品的史诗性。
一、史诗性的呈现方式
(一)包罗万象的全景化构画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叙事诗,作为一种文体,它描述了人类在孩提时期有着重大影响的史实或者神话故事。《荷马史诗》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离不开它对人类幼年时代的自然、社会活动的广泛写照。在《浮士德》一书中,虽然浮士德的灵魂被作为赌注的故事是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但是歌德通过描写浮士德在五个时期的人生追求,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真实,给予了读者包罗万象的、全方位的体验。
浮士德的人生经历了五个主要时期,分别是对学识的渴求、对爱情的探索、对仕途的追求、对美的追寻以及对事业的探求这五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这一角色的成长,同时,也映射着整个时代的变迁。浮士德对知识的追求的悲剧,否定了守旧的书斋式的生活方式,使他实现了从精神到肉体的新生;爱情的悲剧使他领悟到在个人生活圈子里追求人生理想的局限性,使其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过渡;仕途悲剧则折射出当时理想的破碎;对美的追寻的悲剧和事业追求的失败,则使浮士德最终明白了某些含义。浮士德这一角色的成长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不断成熟与时代的变迁相辅相成,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回顾作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看,可以发现在歌德出生的那一段时间,欧洲的社会正处在一个旧时代;到了他的暮年,浪漫主义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作为欧洲巨大变革记忆的承载者,歌德用《浮士德》诠释了历史故事,并且答复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相关问题。歌德在年轻时,他强调追求自然的纯真,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浮士德》最初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他的主张在剧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比如对太阳、月亮、星星与精灵的描写。此后,他发觉他的作品与他所处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因此,他开始追求形式化与节制,这也标志着他向古典文学迈出了一步。《浮士德》就是在这样的转变中诞生的,可以说,他将自身的体验和经验汇入了时代的洪流中。这个故事不仅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欧洲的社会发展经历,而且还历史性地反思了诸多的社会思潮。既可以看到歌德对生命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探索,也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细致描摹。内容的广阔与深邃构成了《浮士德》史诗性的特点之一。
(二)宏大严整的结构体系
黑格尔曾将“客体的整体性”作为史诗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并且指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动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1]《伊利亚特》遵照着“客体的整体性”原则,整首诗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主线,人与神两条线索纵横交错、并行发展,在结构的安排上独运匠心。但这部叙事诗并没有对整个过程进行系统的描绘,而是交替运用概括归纳、画面布景、省略留白、适当停顿等手法,使结构实现了疏密结合、重点突出的效果,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加深了对主旨的表达。《浮士德》结构的宏大和严谨则体现在对分幕的安排上,这是因为该诗剧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如何分部、如何分场地亦不是容易之事。全剧没有首尾贯通的情节,歌德在此独具匠心地将这部剧作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作为线索,将作品分成了三层结构。通过这三层结构,读者能够对浮士德形象的固有特征有更符合实际的把握。
在内容上,可以看到浮士德一生的活动呈现出的在精神上发展的阶段性;在结构中还可以看出,歌德写作《浮士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和表达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每个独立存在的结构都被一条中心线贯穿起来——主人公浮士德的精神:永不自满,奋斗不止。在第一部第一幕中,浮士德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在中世纪的书斋中埋頭钻研,但他甚至一度迷失了自我,想要结束自己的一生,而当他听到钟声时,他回忆起了往昔的美好,因此,他下定决心,决定踏上探寻自我的道路,并以灵魂为赌注,他的心路转变过程体现了他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超越;在与格雷琴的恋情悲剧中,浮士德虽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但他仍明白这是诱惑,“蛇!你这条蛇!”“恶棍!从这儿快滚,不准提到那个美人!别让我这半疯的神志……生了邪心!”[2]在这一情节中,虽然他最终没有抵住诱惑,酿下了悲剧,但是他的疯狂是在保持理性下的选择;在最后一幕中,浮士德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明白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在于为大众,在生命的尽头能够对热烈的往昔释然,视人生的喜怒哀乐为蜉蝣,他在寻觅个人意义的过程中实现了生命价值的升华……由此可见,浮士德在各个阶段所体现出的浮士德精神都是动态的,是成长的,这作为线索贯穿了全剧的经络,歌德正是用浮士德的创作和对结构设计的巧思,借助浮士德的言语对历史的进程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三)富有时代精神的形象塑造
“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3]在史诗性作品中,通常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英雄人物或主要人物,通过发生在英雄人物或主要人物身上的事迹来展现一个民族的特质。《伊利亚特》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公正不阿、能征善战的阿喀琉斯;唯利是图的阿伽门农;仁和善良的帕特洛克罗斯;忠诚勇敢的赫克托耳……复杂的人物特征构成了曲折的故事情节,反过来,曲折的故事情节又塑造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性。然而在这些极具矛盾特征的人物形象中,又有一个共性的精神体现。他们以激情与热忱,努力完成自我使命,实现个人价值的超越,体现出旺盛、不羁、顽强的生命意志。这就像被誉为“战神”的阿喀琉斯,他早已知晓“留下战斗”和“返回家园”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却仍为了那份“恒定与不朽”踏上战场。在这部史诗中,英雄形象被集中赋予了强大的时代精神。
《浮士德》则主要描绘了浮士德这一人物形象。浮士德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探索者,他的一生都在坚持实践,为了感受人生那短暂的、至善至美的瞬间,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即使他经历了在五个追求阶段中的悲剧,但他并没有流露出软弱与满足,最终还是投身于改造自然、为人类作贡献的伟大事业中。浮士德把个人的追求和造福人类的理想结合起来,如此才获得了人生真实的价值和至高的意义。这种浮士德精神正是当时精神风貌真实又生动的写照,与此同时,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举例来说,浮士德仍无可避免地沉溺于名声、财富、权力等欲望之中。由此可见,他的前进并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在不断战胜自我、排除万难、不断地与外界的阻挠做斗争中取得的,而这也正是浮士德形象具有的更高的含义。《浮士德》的史诗性由浮士德这一人物形象所具象化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史诗性的主题意蕴
黑格尔曾说:“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4]《伊利亚特》之所以使希腊民族“长久地感兴趣”,原因就在于它的中心主题深刻地反映了“一般人类的东西”,《伊利亚特》所反映的最为根本的,就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基本领域——尊严。在尊严与生死不可兼得的问题面前,英雄会斩钉截铁地选择前者。就像阿喀琉斯,明知道自己“注定的死期也便来临”,但他依然要为他的挚友复仇。
《浮士德》亦是如此。首先,主人公浮士德是一个高度具象化的人,他所亲历的百思不解与对生命方式的深刻探索,凝聚着“一般人类的东西”,而他所实践的事情,则是当时人类发展的标志。浮士德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观照,都有着现实的事实依据和时代精神发展作为基础。其次,在这部作品中,歌德把他对辩证法的解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人的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二元论”,体现为美与丑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等。在《浮士德》中,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作为戏剧冲突的对象,象征了某种对立,他们二人签订了一个赌约:梅菲斯特可以帮助浮士德去追求他想要的一切,但一旦浮士德获得满足,他的灵魂就会永远属于梅菲斯特。虽然梅菲斯特用种种方式引诱浮士德,但石浮士德都能够在探寻生命时不为沿途风光所惑,代表着一种奋发图强、勇猛精进、迎难而上的精神,他是“善”的化身。而梅菲斯特毋庸置疑是“恶”的代表,象征着诱惑与否定。单单这样看,这二者的关系似乎与原来的“二元论”大同小异,但从故事发展的角度看,能够发现这两个形象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换的,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总体上看,梅菲斯特的本意是想使浮士德走向自满、堕落的结局,以取得他的灵魂,但事实脱离了他原本的預料,相反的是,他在对立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得浮士德开始了自己在人生探索路上五个阶段的追求,促成了他最终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恰恰可以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恶”是成就“善”的工具。梅菲斯特曾以皮囊相诱,但浮士德不甘束缚于“小我”,对“大世界”有着强烈的渴望;梅菲斯特曾把浮士德带到宫廷中,用权力去诱惑他,殊不知他只会痛恨宫廷生活;梅菲斯特曾带他去高山,让他放眼领略 “万国的荣华”,以财富与领土的荣耀诱惑他,殊不知浮士德毫不在意这些浮在表面的名利,甚至在探索的过程中寻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生的价值在于为大众,而不是为自我。梅菲斯特静静地潜伏在浮士德左右,时不时运用自己的魔力想引他走上邪路,反而使浮士德不断趋向崇高和完善,从“小我”中挣扎出来,走向广阔的“大我”。这种看似对立的行为,实则有内在的统一性,说明“恶”作为对立统一中的否定面,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歌德的这种思想还体现在浮士德与梅菲斯特这两个形象上,他们二者虽然分别为“善”“恶”的化身,但都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具有强烈的矛盾色彩。浮士德在梅菲斯特的各种诱惑面前,虽仍能坚守本心、迎难而上,但他也不免遭受灵与肉的折磨,在探索的过程中做出事与愿违的选择,譬如他甘愿充当君王的帮凶,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他的自私与利己在这一情节中一览无余;而梅菲斯特虽然作恶多端、阴险狡诈,但是也并非完全的十恶不赦,他的思想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作者通过大胆的设定,使得梅菲斯特以一个超前的批判者身份来展现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作者也利用这一形象的辩证性,通过其丑陋疯狂的外壳,道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对现实世界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三、结语
歌德的《浮士德》包含了事态与曲折,追寻与挫折,历史与恒定,倘若说《荷马史诗》的美具有某种古典主义的“崇高的纯粹和静谧的伟大”,那《浮士德》这部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史诗性的波澜壮阔和恢宏博大,无论用任何形式的体认来设限这部鸿篇巨著,都会削弱这部伟大史诗的意义。
参考文献:
[1][3][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德]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蒋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题再探[J].今古文创,2021(03):16-18.
(作者简介:戴诗涵,女,本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