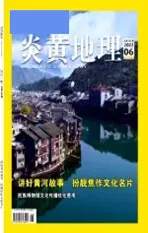羌族铠甲舞中肩铃的美学探析
2022-05-30张婷婷
张婷婷
羌族舞蹈中铠甲舞是比较常见的祭祀性舞蹈,而肩铃则是羌族人民在祭祀中用于祭祀神灵的道具,在铠甲舞中较为常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肩铃也逐渐成为羌族同胞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性道具,肩铃的划圆动律和胯部的S型动律形成了铠甲舞乃至羌族舞蹈中特有的美感。主要以羌族铠甲舞中的肩铃道具作为研究对象,并从肩铃的来源和律动延伸至羌族人的生命观、宇宙观、社会观,甚至有对女性崇拜的体语美学的探析,最终引申出对文化瑰宝的保护与传承。
羌族铠甲舞的概述
羌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泯江上游地区生产生活,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灿烂多彩的羌族文化。相传古羌族人为了躲避战乱,逃亡到半山腰避世而居,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家园,随着时间的推移,羌族同胞创造了许多别具情韵的舞蹈。而羌族舞蹈一般没有音乐,没有乐器伴奏,舞蹈的人边唱边跳,或是用舞步的声音来配合表演,舞蹈动作和舞步没有严格的规范,如此造型古拙,风格简洁典雅,有丰富的生活气息,也保留了原始舞蹈的粗犷和古朴的风格。
羌族铠甲舞就是其中一种古老的祭祀性舞蹈。此舞是为战死的羌族将士举行葬礼时或者敬奉神灵时跳的舞蹈,以此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敬,舞蹈大多在逝者灵柩前或出殡下葬的墓地进行。因此铠甲舞保留了人们祭祀时所使用的独具代表性的工具——肩铃。祭祀时舞者穿着生牛皮制成的铠甲,每件铠甲上都挂着一根牛骨、一顶皮制头盔和一根山鸡羽毛或稻草。他们手里拿着弩、长矛、短刀和武器,脚底踩着深皮靴,看上去像战士,而领头的巫师肩上则要挂着铃,手拿羊皮鼓等。舞蹈旋律经历了奇妙的变化,节奏紧迫,让人紧张和恐惧。羌族人民骁勇善战,以为民族捐躯为荣,铠甲舞的起源与战争舞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铠甲舞具有古代战争舞蹈的特点。其实舞蹈的起源大多都与战争相关,古文中也常常遇到“武”通“舞”的通假字,顾名思义也说明战争与舞蹈有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
羌族铠甲舞中肩铃的功能探析
征战与狩猎在原始时期的部落氏族生活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为了增强战斗的能力或庆祝凯旋,便将舞蹈内容融入战斗场景当中,形成了独特的战争舞蹈。古代的战争舞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临行前鼓舞士气,二是祭奠战争后死去的士兵或庆祝战争胜利,三是具有健身、习武、象功的功能。
羌族铠甲舞正是集合了以上三种功能的战争舞蹈。首先是在远征前用来鼓舞士气,领舞者身着铠甲,手拿皮鼓,肩上挂着铃。跳舞时,萨比打鼓和跳起,其余的舞者排成两排,手拿长矛和刀器,在跳跃之前,他们唱着象征胜利的歌谣。然后他们按照鼓的节奏和铃铛的响声对阵拼打。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呼喊声、铜铃的嗒嗒作响声、铠甲和肩头铃铛的撞击声,人们欢呼声音威武雄壮。它显示了羌族人民的士气和威严,让敌人产生畏惧。
同时羌族的铠甲舞也作为战争后的祭祀性舞蹈,它有一种形式称为“克西格拉”,意思是跳盔甲。用于战争后祭祀那些为民族捐躯的英雄将士。此舞蹈类型是为战死的羌族将士举行葬礼时候所跳,以表达人们对死者的怀念与哀悼。该舞蹈分别在祭灵前、出殡前后或者下葬的墓地旁边进行。后来一般的葬礼也会跳铠甲舞,祭祀时一般都没有乐器来伴奏,基本上以羊皮鼓、肩铃等打击道具发出的声音作为伴奏,以加深人民对死者的怀念和哀悼。
铠甲舞另一种不同的形式是“哈日”,意为带领士兵演习的意思。人们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得不学习熟练灵活地运用武器,而在学习或操练过程中,用肩铃发出的声响来统一动作的节奏,也可以更好地掌握武器要领。久而久之这些操练兵器的动作与姿态就被记录下来。
由于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使得“克西格拉”与葬礼祭祀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哈日”则多出现士兵操练演练以模拟战争的场面。当今社会远离了战争和杀戮,所以羌族铠甲舞的功能发生了较大改变,却仍然与丧葬祭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保留了过去祭祀时所用到的道具——肩铃,用祭祀表演时铃铛嗒嗒作响的声音,来提醒或强调羌族人民对先人的崇拜以及对死者的敬意。
女性舞蹈体语之美学探析
由于远古时期古羌人的语言能力还未发展成型,他们需要通过肢体语言来进行情感的交流。又因长期以狩猎、畜牧业为生,古羌人形成了以丰满、肥壮为美的意识,所以他们的舞蹈表演也特别注重曲线美,胯部夸张的转动,甩肩铃这一动作半保留了“轴转”这样一个主要的羌族舞蹈动作,而改变了转动的部位,用肩膀的转动代替了腰部的转动来带动铃铛。
肩膀是胳膊与身体躯干相连的部分,自古就有勇于或能夠承担的责任的指向。如曹禺《王昭君》第二幕就有“萧育严猛尚威,是个有决断、有肩膀的汉子。”以肩部的坚实有力体现萧育是个能够承担责任的男士。因而承担责任就需要强硬厚实的支架支撑,那这个强硬的支撑就是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肩膀就像高楼的立柱,与其所承担的体积相比微不足道,但缺了它万丈高楼崩于一夕之间,所以人们的肩膀作为支撑承担着身体的重量,承担这一切的象征,也是早期人们对于身体意识的朦胧启蒙。
而羌族肩铃舞蹈中女性肩上系着铜制或者木制的肩铃,把肩铃两个字拆开来看,就是肩膀上的铃铛。想要甩起肩铃也需要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同样还是肩膀,而肩膀并不像人的手或者脚那么灵活,想要甩起肩铃,肩膀的柔韧度和灵活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羌族女性每到闲暇的时候,就以甩肩铃为游戏,他们的肩膀经过不断的锻炼变得非常灵活柔软,用此间接表达出羌族女性的心灵手巧。古羌族人认为女性是非常高贵的,她们不仅可以繁衍生命,繁衍民族,而且可以统治整个民族。为了祈求丰收,古羌族人每年春耕时,一群生过孩子的妇女会在一个固定地点跳舞,以祈求来年的丰收如同繁衍子孙一样兴旺。
肩铃利用肩膀的运动较多,在身体语言的所指上也可能暗含了女性在舞动时向男性求爱,是她们想寻求一个爱的休息所的信号。作家舒婷《神女峰》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上痛哭一晚。在古代男权主义社会,女性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没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肩膀本来就有依靠的含义,而肩膀画圆转动的突出有可能就是呼吁广大女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依靠,用身体语言婉转含蓄地来向男士传达爱意。
圆的轨迹之文化探析
“轴转”是羌族舞蹈的一个主要动作,是指以腰、胯部位发力带动上身平面转动,并促使双肩随动画圆的动作。而肩铃的运动路线则是半保留了“轴转”这个主要的舞蹈动作律动,改变转动的部位,用肩膀代替了腰部的转动。随之肩膀成为主要发力点,跳舞时肩膀带上铜铃,从上往下顺时针快速绕肩,连续重复进行划圆,铃铛被绕肩这一划圆动作所控制,肩膀的运动轨迹是划圆,而铜铃在肩膀的动作控制和线的拉扯下成了另一个优美的圆的形态。圆中有圆心,由圆心向外等距离扩散生成无数个大圆,大圆等距离收缩可变成圆心,大圆小圆可复归于一。大圓生出小圆,小圆生出大圆,大圆等同于小圆,宇宙的发展规律亦是如此。肩膀和铃铛的轨迹路线的圆弧线中的一点是开始,运动一周回到起始位置,始就是终,终就是始,周而复始,无始无终。
生命轮回之“圆”
羌族舞蹈中肩铃使用的基本动律是从上往下顺时针轮回绕肩,形成圆的优美形态。圆从起点又回到起点,像从生到死,死而又生,生死轮回,永无止境。同时也引申为轮回的时空结构。轮回是宇宙中人生整体的生态系统与流程。只要我们还是凡夫俗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囚禁在生死循环中——也就是轮回之中。轮回的概念是人在死了之后,灵魂又轮回重新投胎成为另一个人,像车轮一样不停地转动、循环。其中也包含了对事物因果联系的解读,是对万物能量之间相互转换规律的把握,反映出了古人看待生命哲学命题的智慧与希冀。
从宗教与生死探索的角度来看,宇宙与人生又有着微妙的关联与映射。宇宙不仅仅是作为生命轮回循环结构中时间、空间的存续场,更是芸芸众生生活的舞台。因此,广义的传统的宗教宇宙观除了探讨“物理中的世界”的生成﹑堆叠﹑腐朽﹑毁灭等变化,还包括了生命个体﹑社会群体的内在精神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层面的“灵性世界”。我国自古就有天地轮回、因果轮回之说,羌族铠甲舞常用于部落首领和战死的将士祭祀,如此看来,祭祀舞蹈动作当中划圆的律动,就是轮回,其精神的崇高性不会因为世俗层面的毁灭而消亡,相反他们将在灵性的境界之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并长此往复。
圆融圆满的人生境界
古人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圆相对于缺而言的话就是不缺,不缺就是所谓的圆满,所以“圆”也有“满”的意思,中国古代唐朝发展到达顶峰,即圆满,圆满之时就是开始没落的表现,美好的事物忌讳十全十美,留有余地才能有回旋的空间,一个人追求圆满,是退而求其次,是懂得知足常乐,不断地追求圆满,但也趋近圆满,才能走得更远,这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人生哲学。
我们所说的“圆融”一词就是圆满过后的融合,就是完全的交融,不对立不冲突,大同不碍小异,各显其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比喻就是“月印万川”,这很好地体现了圆融的特点。这个比喻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江水婉转,月光普照,天底下千千万万的湖水没有一处不照映出月的圆影,但是上千万个圆都出自同一个圆月,一圆贯穿了万川之圆,散落在婉转的江水中,在湖水中连成一个整体,却只有一个生命。“随处充满,无稍欠缺。”就是说的充满、圆融之境界。第二个就是只此一个月亮就可看全月,由于散落的江湖水都是由一月所映照,所有皆可看到万千月亮的内在。即有一物可看万物,自一圆可达万圆。
而圆融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技巧,圆融就是圆满通融,和谐相处。有句古话说:“舌存常见齿亡,刚强终不胜柔弱;户朽未闻枢蠹,偏执岂能及圆融。”其意指偏执刚强终究胜不过婉转圆柔,我们应当有如常常转动的门轴一样灵活变通,破除固执的能力,必须要能屈能伸。圆融精神在当代社会也显得尤其重要,它不仅能影响人,也能影响社会,可以用于处理各种矛盾。为人处事,学会圆融,人生的路会更通达圆满;学会圆融,创造一个和谐美满的世界也并非难事。而羌族人民的主要动作就是轴转,就是划圆动律,不难看出,在羌族人的民族文化意识中同样蕴藏着对一种圆满圆融人生境界的追求。
羌族舞蹈的生态传承
中国羌族的主要地貌是高原、高山和峡谷。岷江上游、湔江、清漪江(平武西南)及其支流是羌族地区主要的河流。河流沿线形成了一些小型冲积平原坝和高山缓坡,那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适宜种植农作物。在高山向阳的一面,有大自然赐予的牧场,特别是在夏天和秋天,温暖如春,水草丰富,是牛羊放牧的好地方。
然而近年来大小地震频发,居住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北川、茂县、汶川等地的羌族人民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受此情况影响媒体对羌族进行多次报道,呼吁社会加强保护,加大救援力度,专家也多次讨论保护措施,有关单位收集整理资料组织展览或出版物,将羌族文化保护问题列为地震灾后重建精神家园的一个非常大的考虑项目,保护羌族文化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多方面的指示加强了各界保护羌族文化的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希望通过进一步挖掘羌族舞蹈的文化价值,在重建羌族人民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能对当地有所裨益,使羌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更好地延续下去。
羌族舞蹈反映了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宗教、历史以及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由于羌族有语言,却没有文字,所以在舞蹈的实际传承过程中,只能通过口头传播的形式代代相传。因此,羌族舞蹈的继承和传播,对羌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铠甲舞作为羌族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深深植根于羌族文化艺术的土壤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中肩铃独特的肢体语言艺术在本土传承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前,为了实现羌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我们在研究与保护时更应捍卫活态环境的文脉高地,使羌族民间舞蹈这朵云端上的花能更美地绽放,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也可以充分促进民族文化的当代发展。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正因如此,羌族铠甲舞不仅作为我国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更因其存在的特殊性丰富了世界艺术之林。
参考文献
[1]李征.羌族民歌的保护与羌族文化的传承[J].教育教学论坛,2012(21):127-128.
[2]白渝.羌族舞蹈传承性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5.
[3]马鲁.从“风俗”到“舞风”羌族风俗对羌族舞蹈风格特点的影响[J].青春岁月,2015(10):148.
[4]施小惠.云端上的舞蹈——《羌族肩铃舞》观后感[J].北方音乐,2013(02):89-90.
[5]冯瑶.羌族铠甲舞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6]史浩琳.羌族舞蹈的典型分类及传承路径探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7(05):135-136.
[7]高云鹏.轴转——羌族舞蹈顺边美探究[J].明日风尚,2016(21):160.
[8]朱良志.论中国艺术论中的“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04):390-4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