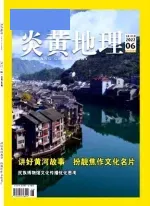《阿萨拉克齐史》之历代汗王与佛教关系初探
2022-05-30桂梁
桂梁
《阿萨拉克齐史》是一部史料价值浓厚的文献,着重记载了蒙古民族谱系的历史。作为一部编年史,书中不乏佛教经由吐蕃传入蒙古地区及其发展的相关史实。虽然学术界围绕《阿萨拉克齐史》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针对其佛教相关内容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还尚未出现。基于此,现以《阿萨拉克齐史》中所记述的历代蒙古汗王与佛教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该史书的佛教史学价值。
史书《阿萨拉克齐史》,成书于康熙六年(1667),作者系喀尔喀部人占巴。内容从孛儿帖赤那写起,讲述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史、元朝诸帝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以及元朝灭亡后的蒙古史,内有阿阑豁阿感光生子、铁木真诞生等诸多传说故事。
占巴其人其书
《阿萨拉克齐史》自1667年问世至今,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阿萨拉克齐史》已被多次刊印发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在少数,所以学者们就某些问题产生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譬如,针对《阿萨拉克齐史》的章节或段落划分方面,就有多位学者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下面从作者、版本和内容三个方面对《阿萨拉克齐史》进行叙述。
《阿萨拉克齐史》之作者
《阿萨拉克齐史》作者系喀尔喀赛音诺颜部贵族占巴(又名“阿萨拉克齐”),故《阿萨拉克齐史》也被称作《占巴书》。占巴生年不详,卒于1707年。“占巴”由藏文音译而来,蒙古文意为“阿萨拉克齐”。
占巴系成吉思汗后裔格埒森札札赉儿洪台吉的第三子诺诺和氏。占巴的曾祖是图蒙肯,其封号为昆都伦·楚忽忽儿·赛音诺颜[1]。占巴的祖父是图蒙肯的第二子丹津喇嘛,对此学术界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围绕丹津喇嘛的相关研究却有着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丹津喇嘛孩子的数量。蒙古国学者沙·比拉认为图蒙肯有十三子,其中第二子丹津喇嘛有四子。中国学者王梅花也指出,丹津喇嘛是图蒙肯的第二子,但是与沙·比拉所持观点不同的是,王梅花认为丹津喇嘛有十三子[2]。二是关于占巴之父塔斯希布是丹津喇嘛的第几位孩子。沙·比拉认为塔斯希布是丹津喇嘛的长子,王梅花则认为塔斯希布是丹津喇嘛的第八子。沙·比拉的观点可能与历史事实更为贴切,因为有多位学者认为占巴父亲塔斯希布是丹津喇嘛的长子。《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关于占巴祖先的记载与沙·比拉有着相同的观点。
此外,从占巴的个人生平事迹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亲满派,一直与清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1691年到1696年,占巴带领军队三次帮助康熙皇帝与卫拉特的噶尔丹进行征战。康熙皇帝也先后两次对占巴授予正式封号,最初封他为伊特更吉图·额也泰·额日和·岱青,后封他为札萨克亲王。除了上述两种封号外,占巴还获得了“赛音诺颜”的封号,但是这一封号并未得到康熙皇帝的正式诏书确认。
《阿萨拉克齐史》之内容
《阿萨拉克齐史》中主要记载的是从蒙古民族起源到乌哈汗图·妥欢帖木儿的蒙古历史。其中从成吉思汗到乌哈汗图·妥欢帖木儿的历史事件叙述得较为细致,成吉思汗之前的历史记载相对简略。书中认为蒙古民族的祖先源自印度,并与吐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该史书在写作形式上未进行段落划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占巴严格遵照古代蒙古史学家的史学写作风格[3],以编年史的体例形象化地记录历史。基于此,有不少学者依据《阿萨拉克齐史》的内容,试图对其进行段落划分。沙·比拉主张《阿萨拉克齐史》可分为四个部分,前言;蒙古古代史,主要是成吉思合罕史;从帝国崩溃到十七世纪中叶的蒙古史;后记。乔吉也认为可分为四个部分,前言;蒙古古代史,元朝诸帝及具所尊帝师和喇嘛、妥欢贴睦儿汗逃离大都及在应昌府逝世、关于明朝永樂帝仿佛是妥欢贴睦儿之子的传说;元亡以后的蒙古,从必里克图汗到达延汗为止的蒙古诸汗史、喀尔喀与卫拉特战争、达延汗诸子及其后裔世系、喀尔喀诸贵族谱系史,喇嘛教在喀尔喀的传播。王梅花则认为可以分为三个章节,即前言;蒙古古代史;结尾诗。
上述三位学者的章节划分均以《阿萨拉克齐史》的内容为主要依据,所以三位学者的划分方法大同小异,但是在划分形式上各有其特点。沙·比拉的划分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以《阿萨拉克齐史》内容为依托,围绕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轴,划分为四个段落。乔吉的划分则较为具体,围绕《阿萨拉克齐史》的内容,以每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为主要划分依据。较之沙·比拉和乔吉的划分,王梅花的段落划分显得更为简洁,除去前言和后记,将其余内容整体划分为一个段落。
《阿萨拉克齐史》之版本
依据目前所能够查阅到的文献资料,《阿萨拉克齐史》有蒙古文和汉文两种不同文字形式的版本。其中蒙古文版本曾多次刊印发行,汉文版本则只有两种,即鲍音和格日乐翻译的两个版本。
《阿萨拉克齐史》原是一部手抄本,今收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4]。该手抄本最初是由蒙古国著名学者贺·佩尔于1960年在乌兰巴托胶印刊行,成为国内外流传的唯一版本。1984年3月,巴·巴根对蒙古科学院内部发行的油印本《阿萨拉克齐史》进行校注,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2002年,由蒙古国学者沙格都尔苏隆与韩国学者李圣揆主持,在乌兰巴托对《阿萨拉克齐史》进行影印出版。
《阿萨拉克齐史》的两种汉文译本分别是由鲍音和格日乐翻译。鲍音译本是以系列专题形式将其所翻译的《阿萨拉克齐史》分成六个部分,于1891年在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分六期发表[5],其所参考的母本信息不详。格日乐译本是在2016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刊印发行的《新译简注蒙汉合璧〈阿萨拉克齐史〉》[6],所参考的是2002年乌兰巴托影印版本。两种译本虽然在内容方面差异甚微,但是在写作风格方面却截然不同。从结构层面分析,两种汉文本《阿萨拉克齐史》在章节划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鲍音译本对原本没有章节段落划分的《阿萨拉克齐史》,以其内容为主要依据,在汉译的过程中对该书进行段落划分。格日乐的译本则是严格按照所参考的乌兰巴托影印版本结构形式,未划分段落。从语言层面来看,两种版本的汉译本对专业术语的翻译方面有所差异。鲍音译本是将原有专用名词的意思直接翻译成汉文,格日乐译本则将原有的专用名词以其读音翻译成汉文。
蒙古汗王与佛教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后经吐蕃传入蒙古地区并兴盛至今。佛教之所以在蒙古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与作为中间者的历代蒙古汗王所采取的相关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在不同蒙古汗王时期,佛教的发展传播程度也有所不同,下文从《阿萨拉克齐史》中所提到的众多蒙古汗王中选取对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具有显著影响的窝阔台汗、忽必烈汗、赛音葛根汗和阿巴岱汗四位蒙古汗王。围绕其相关事迹,阐述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窝阔台汗与佛教
据《阿萨拉克齐史》记载,窝阔台汗时期佛教以官方形式正式传入蒙古地区。窝阔台于四十三岁即位,在位期间,窝阔台汗患足疾,派遣使臣命吐蕃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前来。窝阔台汗在额里伯之阔阔兀孙地方迎见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见窝阔台汗的足疾后言,“可汗前世为印度国王之子,因建庙破土伐木,土地神前来作祟,又因建庙有功,如今降生为成吉思汗之子”。便给四臂大黑天供奉食子,使其足疾立刻痊愈,随之窝阔台可汗与全体蒙古地区的民众敬仰萨迦班智达并皈依佛法。有学者指出,《阿萨拉克齐史》中所述窝阔台可汗迎请萨迦班智达一事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多个历史文献中记载,与吐蕃结成“实施者”与“国师”联盟的倡议者并非窝阔台,而是其子阔端。
忽必烈汗与佛教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有两次传播的高潮,分别是萨迦班智达与阔端时期和八思巴与忽必烈汗时期[7]。《阿萨拉克齐史》中并未记载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相关事迹,仅对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往来作了简单叙述。忽必烈汗三十岁时命十九岁的八思巴坐床,将名为库楞参丹城的柱子以白色石头筑成,同时让民众皈依佛法。至于为何将柱子用白色石头筑成,书中未作详细描述。
忽必烈汗与八思巴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供施关系,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八思巴自身的原因,八思巴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之人,为忽必烈汗的政治生涯提供了诸多方法策略;其次是忽必烈汗自身的原因,即忽必烈汗是一位尊重并且善用知识分子之人;最后是察必夫人的原因,即察必夫人自身皈依萨迦派之后,并劝说忽必烈汗接受萨迦派八思巴灌顶。虽然忽必烈汗接受八思巴的灌顶皈依佛法,但是在国家与佛法的关系上与八思巴形成了一种非常平和的共识。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结成供施关系之后,赐予八思巴“珍珠诏书”和玉印,予以八思巴崇高的地位。
此外,八思巴也忠实地执行忽必烈汗对西藏采取的政策,对蒙藏文化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即八思巴自身学识渊博和忽必烈的支持。忽必烈汗在政治方面给予八思巴宗教最大指挥权与西藏地区的“执行长官”地位。在经济方面,给予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在政策方面,应八思巴的请求,忽必烈汗为藏区减免赋税。在1276年,忽必烈为八思巴在大都举行送别仪式,自此以后元代诸帝均设置帝师一职,并且这一职位上的人选均出自萨迦派八思巴的宗亲。
赛音葛根汗与佛教
从完泽笃汗时期至林丹汗时期,佛教在蒙古地区自妥懽帖睦尔汗以来一直处于中断状态,《阿萨拉克齐史》中并未记载这一时期的佛教相关内容。直至赛音葛根汗时期开始,才对蒙古汗王与佛教的相关事迹再一次进行叙述。
赛音葛根汗萌发佛心,派遣使臣去往吐蕃延请索南嘉措并约定在青海会面。索南嘉措出发前往青海的路上,不断有信众前来奉献黄金等布施品,听灌顶法会或出家为僧。赛音葛根汗认为自己与索南嘉措是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转世,并互相赐予尊号。赛音葛根汗赐予索南嘉措“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索南嘉措尊奉赛音葛根汗“法王大梵天”的尊号。赛音葛根汗与索南嘉措时期,原先在蒙古族地区传播的萨迦派逐渐被格鲁派所取代,其影响程度极为广泛。与忽必烈汗相比较而言,赛音葛根汗接受佛教的程度是全部且彻底的。主要原因是忽必烈汗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西藏乃至全国宗教事务,赛音葛根汗则是利用格鲁派的势力达成蒙藏联合,消除战乱,统一蒙古诸部。
阿巴岱汗与佛教
据《阿萨拉克齐史》记载,阿巴岱汗会见三世达赖之前就已经与萨迦派的高僧有所接触,并在把萨迦派引入漠北喀尔喀的同时修建了喀尔喀地区第一座庙宇——额尔德尼昭。在该庙的第一座佛堂竣工时,他迎請达赖来喀尔喀为佛堂开光,达赖拒绝了他的邀请,但后来还是派了一名萨迦派喇嘛罗多宁布前往喀尔喀主持佛堂的开光仪式。
达赖未亲临喀尔喀,却派萨迦派喇嘛,可能与额尔德尼昭为萨迦派庙宇有关。额尔德尼昭第一任主持为著名的席捋图·班迪达·固始·却尔吉。据民间传闻,该庙席捋图·班迪达·固始·却尔吉之后的五任主持都为萨迦派喇嘛。1775年额尔德尼昭派人到西藏萨迦寺迎请了大量的佛经和佛像。额尔德尼昭建庙之后的一百年间一直是阿巴岱汗及其后裔封建主的家庙,后来才逐渐成为全喀尔喀地区著名的寺院。上述史实可以说明,阿巴岱汗在喀尔喀蒙古地区首先引进的是藏传佛教萨迦派。
《阿萨拉克齐史》虽然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但是也不乏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相关内容。从《阿萨拉克齐史》的内容出发,总结出如下几点佛教史学价值。首先,弥补历史资料的不足。《阿萨拉克齐史》中收入了关于佛教在喀尔喀蒙古开始传播的新材料,这可以弥补喀尔喀在阿巴岱汗时期与南部蒙古同时接受佛教这段时间历史资料的不足。此外,《阿萨拉克齐史》中所记述的喀尔喀台吉世系史,包含了十六世纪至作者占巴所处时代的喀尔喀有封地王公之间亲缘关系的最完整材料。其次,文化的传入。佛教经由吐蕃传入蒙古地区时,大量的吐蕃本土文化依托佛教渗入到蒙古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一特点在语言文字方面尤为突出,如《阿萨拉克齐史》中所涉及的部分蒙古族民众的名字就是藏文,而非蒙古文。再次,蒙古汗王利用佛教维护政权。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蒙古地区,除了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外,其主要因素是蒙古汗王维护政权的需要。古代蒙古地区,尤其是进入北元时期以后,处于频繁的战乱之中。这就需要统治者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以此来巩固政权。最后,历史记述不实。就作者占巴而言,其在某些方面歪曲历史事实。比如,即使早已有人指出贡嘎宁波与成吉思汗非同一时代的人物,但是占巴在《阿萨拉克齐史》中依旧说贡嘎宁波是成吉思汗的国师。
参考文献
[1]沙·比拉.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M].陈弘法,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王梅花.《阿萨拉克齐史》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巴·巴根.阿萨拉克齐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4]乔吉.蒙文历史文献要览(五)[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02):69-73.
[5]善巴,鲍音.阿萨拉格齐蒙古史[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87-96.
[6]格日乐.新译简注蒙汉合璧《阿萨拉克齐史》[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7]丁守璞,杨恩洪.蒙藏关系史大系·文化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