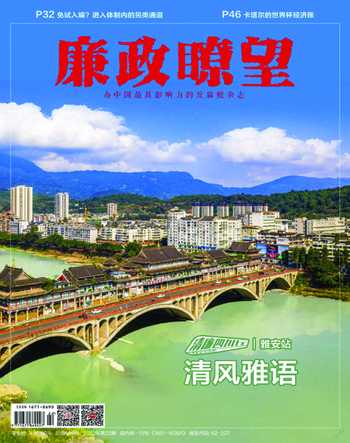从茶马古道到川藏公路的千年史诗
2022-05-30邓苗苗
邓苗苗


对雅安的初印象,是连绵群山间的缭绕云雾和江河蜿蜒处的水波微荡。对这番山川景色,清代光绪年间成书的《雅州府志》描述称,“雅地层峦叠嶂,镂罅嵌空,而平羌、青衣、大渡、泸河诸水星驶电激”,用“钟灵毓秀”“翠微杳霭”来描述,恰如其分。
雅安常年下雨,素有“雅州天漏”之称。宋代西蜀文人赵彦材在解释杜甫一诗中“天漏”二字时提到,“蜀有地名漏天,古诗‘地近漏天终岁雨”,应当就是对雅安一带多雨气候的记载。史籍中记载荥经县有八景,其一就是“古城烟雨”,据传唐代李德裕在此筑城,遇阴雨则烟雾浓笼、景色可掬。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征造就了雅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质,从茶叶到大熊猫,从茶马古道到川藏公路,一个个元素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雅安印象。
茶马功过
有一种说法是,北纬30度是产茶的黄金纬度带,拥有茶树生长的最佳自然环境。这条神秘的纬线经雅安的名山区和雨城区,再穿越天全县。也正是在这条纬线附近的蒙顶山上,被誉为“植茶始祖”的吴理真驯化野生茶树,成为世界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种茶第一人。
据说在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公元前50年),吴理真在蒙顶山发现野生茶的药用功能,于是在蒙顶山五峰之间的一块凹地上,移植下七株茶树。清代《名山县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被誉为“仙茶”。
吴理真植茶开启了人工培植茶树的新篇章,“由是而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商贾为之懋迁,闾阎为之衣食,上裕国赋,下裨民生”。当地人介绍说,每年谷雨前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制茶人、茶学家、茶商们都会到名山区“寻根祭祖”,纪念吴理真。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蒙顶山“每岁贡茶为蜀之最”,作为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明发祥地,雅安在四川乃至中国茶产业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且雅安地处藏汉结合的重要咽喉位置,产的茶大部分都用于边贸,茶马互市、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随着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唐人饮茶的习俗也传入吐蕃、回鹘等民族地区。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以高蛋白的食物为主,在饭后须饮茶以助消化,“宁可三日无盐(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来自雅安的茶叶从盛唐开始,就在高原扎下了根,成为连接藏汉民族的桥梁纽带。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后,宋朝实行榷茶博马政策,茶叶成为易马的重要物资,太子中舍李杞入川筹办茶马之政,并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茶马贸易机构,如都大提举茶马司、川陕路买卖茶厂、博马场等。熙宁年间,雅州境内先后在名山、宝兴、天全、汉源設立四个博马场。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鉴于茶马司在四川地区“治茶易马”的实效,宋神宗特诏“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方许籴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再次诏令,“以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名山茶从此成为中央王朝以茶易马、以茶睦边的专用茶。
茶马贸易为宋廷提供了大量可以用于边防的战马,但官府垄断茶叶销售、官员层层盘剥,令以茶为生的百姓苦不堪言。曾有思道、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六名官员先后上疏力陈茶马之政的不当之处,却反遭贬官流放。苏轼在《送周朝议守汉州》一诗中便提到,“茶为西南病,岷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二李”指的是李杞和李稷,李杞筹办茶马之政后,“岁增息为四十万”,而后李稷又掌管雅州茶马,“一岁之间,通课利及息耗至七十六万缗有奇”。思道等六人相继针对弊政直谏,被世人誉为“六君子”。还有说法称,后世流行的茶艺器具“茶道六君子”就是从思道等“六君子”衍生而来。
如今,茶马之政的功与过早已化作尘埃消散,留存下来的茶马司少之又少。就在名山区新店镇,一座赭红色的茶马司遗址仍立在108国道西侧,不起眼到即便有心去寻,也有可能错过。这座四合院式建筑于清道光年间重修,仅由大殿和左右两个厢房构成,面积不大却厚重古朴,无声诉说着往昔茶马互市的兴旺与繁荣。
古道悲歌
1939年的夏天,一名年轻的学者孙明经来到雅安,进行“茶马贾道”考察。这段考察历时160余天,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让这条在过去漫长时光里连结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多民族交流发展的重要古道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
川藏茶马古道“自碉门(今天全县始阳镇)、黎(今汉源县清溪镇)、雅(今雨城区)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以雅安为重要起点,这条古道从名山到雨城后分“大路”“小路”。“大路”又称官道,从荥经县翻大相岭,经黎州、泥头翻飞越岭,过泸定到康定;“小路”则相对近一些,从天全县翻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两路在康定会合后,再通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南亚、西亚各国。
在这条沧桑厚重的崎岖道路上,布有无数的窝坑,这样的窝坑当地人叫作“拐子窝”。背夫们背着少则几十斤、多则两三百斤的茶包在这条路上往返,由于茶包太重,休整时不方便将一捆捆的茶包取上取下,背夫们只好用一根“丁字拐”支在背架下撑着休息,行走时也可借力于“丁字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条路上便留下了一个个“拐子窝”。正如背夫们口中顺口溜所说,“一手提着丁字拐,拄路歇气全靠它。沿途拐窝酒杯大,挂在窝中才不滑”。孙明经考察时,当地背夫告诉他,识别一条路是不是“茶马贾道”,只要看那条路上是否有很多“拐子窝”就可以了。
除了用“拐子窝”识别道路,各地的背夫们口口相传的顺口溜也可以作为参考。如汉源当地相传的是“一出门来灯杆坝,关顶上坡坡最难爬。高桥过了三脚坪,三道桥上停一停”,“化林坪的号伙大,冷碛过了飞儿崖。甘露寺过了泸定桥,烹坝瓦斯日地坝。走进康定把茶交,急急忙忙把家转”。而天全则吆喝“一出禁门关,把命交给天。上得象鼻子,翻得马鞍山”。
“把命交给天”无疑是对背夫处境最残忍也是最真实的描述。而当地流传的民歌:“阳雀叫唤口朝天,小妹望郎一天天。白天黑夜望郎归,迟迟不见郎回转”,则唱出了家人对远行背夫的担忧。对于无数的背夫来说,这是一条血泪路,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拐子窝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背夫以生命搏得生计的悲壮。他们如此辛苦地在这条路上奔波,一趟下来却只“可买几斤玉米粑”。但勤劳坚韧的雅安背夫无怨无悔,有时甚至妇女和小孩子也会背上一段,接力般地将边茶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一个个佝偻的身子扛起了家庭的一片天空,虽然风雨不断,却总会雨后天晴。
开山筑路
如果说逶迤五千里的通天茶路因边茶而生,那么川藏公路则因时而生、因势而生,在“人类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1949年底成都解放后,为进一步解放西藏,恢复打通川康公路、康藏公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之前,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运输货物也全靠人背和畜驮,“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羊肠小道猴子路,云梯溜索独木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党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要求下,为解决补给问题,为西藏长远发展考虑,“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成为当时的最优选择。1950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雅甘工程处,4月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数万军民激情投入到筑路一线,掀起了一场抢时间、促通畅的筑路热潮。就在这一年的7月,一首名为《歌唱二郎山》的歌曲传遍了整个新中国,激励着筑路大军奋勇向前,让艰苦筑路的英雄事迹和“二郎山精神”广为流传。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二郎山是川藏线上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座高山,海拔3437米,气候恶劣,地势凶险。加之其山体地质结构复杂,有的是石岩地段,坚硬难攻;有的是泥沙混合,稀泥遍地。那时,战士们筑路只有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等简易工具。如今人们还能看到当年筑路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里,战士们在一面与地面几乎呈直角的绝壁上,仅靠着一根绳子作为安全保障,不禁让人为他们捏一把汗。这样的凶险在当年的筑路工程中数不胜数,据统计,在绵延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战士牺牲,而修建二郎山险峻路段时,平均每公里就有7名战士献出了生命。
以西南军区十八军为主的11万军民历经千辛万苦,艰难修建,川藏公路终于在1954年12月正式通車,为巩固祖国西南边防,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筑路更要养路、护路,川藏公路通车后,线路、路况也在不断调整与改进。60多年来,在川藏公路建设和运营维护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二郎山老川藏线起于龙胆溪,止于大垭口,在天全县境内总长17.8公里。位于天全县城厢镇的梅子坡道班,是目前川藏线上唯一留存的采用苏式结构的养护站房,这座苏式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历经了数十年的风吹日晒雨淋,仍保持原有风貌。据天全县公路养护段老段长王联邦回忆,以前大部分道班工人都是外地人,来到这里便在道班上工作、居住、生活,“以道班为家,以养路为业”,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来完成党和国家交负的重任。
梅子坡道班养护工人最多时有近20人,到现在只有3个工人,养护13公里的路段,人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精神的流失。王联邦说,现在工人少了,但“两路”精神在不断发扬,也有新的筑路人、养路人不断加入,在以新的形式传承这样的精神谱系。
从茶马古道到川藏公路,再到如今正在建设的川藏铁路,雅安人民用自己的坚韧与不屈,守护着祖国西南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