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灵山》中的空间意识
2022-05-29高彬
高彬
摘 要:高行健的《灵山》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部现代小说,《灵山》中的时空叙事支离破碎甚至颠三倒四。在空间方面,小说架构了“身游”和“神游”的二度空间,二者在并置的同时又展现出交集的关系,而房间、断墙、窗、街等空间意象对小说的内涵阐释起着重要作用。最后,《灵山》的创作技巧和空间哲学与高行健的海外漂泊经历密切相关,小说中表现出作者想要与过往隔断的迫切情感,而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空间对时间的剥夺已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高行健;《灵山》;空间意识;现代小说

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的《灵山》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除了内涵丰富的特点以外,这也是高行健在小说文体实验层面走得最远的一部作品。作者用人称代词“你”和“我”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名称:“你”来到南方小镇乌伊镇寻找“灵山”并邂逅“她”;而同时,“我”则在川贵高原一路沿长江漫游,近距离接触沿途的自然历史与边缘文化。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认知方式。在叙事学中,时间和空间又有着不同的叙事功能:“时间的本性是将事物组成一条无限行进的线,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是前与后的秩序;空间的本性,则让事物进入彼此共存的结构之中,事与事的关系是相互参照的形状、方位与广延……”因此形成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两者的存在都以克服对方使对方融化成自己的内容为前提,因此……空间观念亦将时间的历史次序转化为共时状态。”任何一部小说都离不开空间这一带有终极性的根本问题。空间引起现代小说家的重视,正说明了创作者对空间的自觉意识和差异体验。小说从外在的空间形式探究作者的空间哲学,旨在还原空间意识下作者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灵山》的形式和内涵解读在空间层面互为印证,更为丰富。
作为画家和剧作家的高行健,显然对空间有着极为敏锐的把握。空间对于小说情节的建构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就强调了时间和空间的有机组合对小说情节的意义。《灵山》中的空间不仅是构成事件本身所固有的场景,在“我”的叙述中,空间位移也成为故事情节的发展线。同时,小说中的空间意象影响着读者对作品含义的阐释。
一、“身游”和“神游”的并置空间
《灵山》由“我”和“你”分离出两条线路,形成两个并置空间,而作者对这两者采取了不同的时空叙事策略:“我”作为主要线索,从川贵一带的自然保护区开始,前往熊猫观察基地、探索原始森林、感受彝族山寨的民歌习俗、参观贵阳博物馆、亲临苗寨、去湖南寻找死去的外婆、到湖北神农架探寻野人、一路沿长江流域到达东海之滨的某个小镇,后经上海坐火车返回北京。这条故事线地点明确,线路清晰,叙事中常出现“从某地出来途经某地,而到达某地”这样的表述(如“我经过铜仁……到了一个叫玉屏的小车站”),这一连串的地点名称显示出极强的空间关联性;而“你”作为另一条线索,在山路、河边、村镇中穿行寻找灵山并遭遇“她”,人物所历经的“乌伊镇”“梦家村”和“灵岩”等地方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实指,叙述中充斥着大量的对话、独白、回忆和历史故事,有些章节全章以“你说”或“她说”开头,这条发展线中的空间维度是抽象模糊的,而时间维度却是紧凑的,比如作者在某些章节的开头就用“第二天”或者“过了一夜”来表明章节与章节之间时间上的连贯性。
那么,故事中的“我”和“你”到底有着怎样的时空关系呢?从空间上看,“我”和“你”处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二者在行走空间上并没有重合点;而从时间上,作者在小说第二章就说明了“我”和“你”存在的共时性——“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我正沿长江漫游,就找寻这种真实”。“我”和“你”的时空看似平行,一个在长江漫游,一个沿尤水找寻灵山,但作者通过叙事话语使“我”和“你”进行了潜在对话:“我”在漫游的同时,知道“你”正在寻找灵山。这种交流并没有从故事层面显现出来,却从话语层面成为叙述的前提,且这种潜在对话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多次出现。
第十五章,“你”在寻找灵山的途中看到了“灵岩”——“你倒是确认了这地方叫灵岩,想必就真有这么个灵异的去处,证明你奔灵山而来并没有错”;在第三十五章,“我”找到了灵岩——“这一道道崖缝里……我想这大概就是山里人之所谓灵岩吧,妇人家求子的地方”。
在第二章,“我”在羌族地区寻找懂得邪术的石老爷的“石老爷屋”;在第六十九章,“你”来到了“石老爷屋”并见到了石老爷。
在这里,“我”和“你”通过“灵岩”和“石老爷屋”等暗合的空间点产生关联,这种叙述上的呼应印证的正是“我”和“你”的对话关系。如作者所言,“这部小说不过是个长篇独白,只人称不断变化而已”,“我”和“你”都是作者的一部分,加上后面的“他”,其实是叙述者一分为三,呈现出的是一个非二元对立的多元世界。“这漫长的独白中,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我自己,你不过是我的影子”,作者在这里就明确了“我”和“你”的关系,指出“你”就是“我”的倾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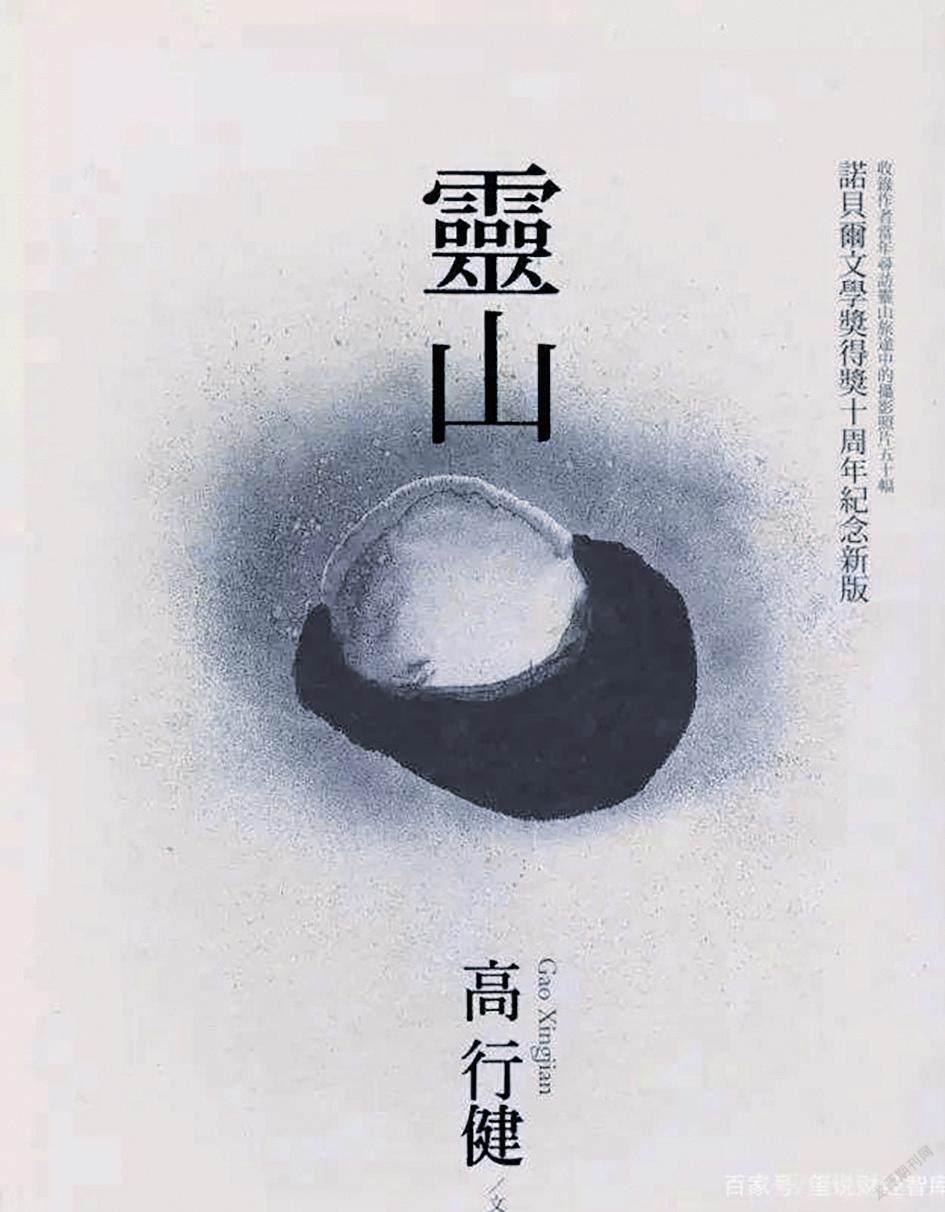
《灵山》中的自我分解为你、我、他,其对话就是自我的内部关系。高行健曾表示,“为了写这本书,我去长江流域做过三次旅行……我得到了这本书第一层结构: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前者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前者派生出的后者则在想象中神游”。事实上,笛卡尔在创立主客体二分的时候,就倾向于将空间性归属于物质世界,而将时间性归属于精神世界。所以,在物质世界漫游的我,是以“我”为中心的向外扩展,“我”作为一个异乡人来到一个新的空间,常常感到陌生:“我”经历着周遭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從自然生态到民间文化,从人性的反思到历史的意义。而在精神空间的“你”,则是以“你”为中心的向内审视,你似乎对这个空间再熟悉不过了:“你”在途中邂逅女人,你同女人交谈,同女人做爱,对女人讲当地人的故事……在男女情性的精神世界中,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名叫灵山的精神彼岸。
二、封闭与开放:房、窗、街
房间、窗户、街道,是《灵山》的重要空间意象。

房屋在小说中一方面指主人公现实的居住场所,一方面也寓意作者童年回忆中的家宅。房屋将人类的生存空间划分为自我和外在两个世界,房内的空间象征着隐私、稳定和安全,而这样的空间在小说中却是不存在的。在小说的第一章,“你”来到一家破旧的旅馆,躺在单人间的床上,清楚地听到隔壁吆五喝六的玩牌声,只一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缝里,“你”甚至可以看见虚虚晃晃的几个赤膊的汉子。从失去空间意义的房间中逃离出来的高行健曾多次表示:他“需要一个家并不是拥有个女人,要的首先是一个不透风雨的屋顶和四堵封闭而且隔音的墙”。从情感意义上说,房屋也意味着家园,意味着关爱。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认为:起童年庇护作用的家宅,有着把思想、回忆、梦境融合在一起的强大力量。
伴随着这种空间的丧失,“房间”对作者逐渐失去了封闭含义,破碎为没有完整墙壁的空间印象:“哪怕我在自己房里,墙的板壁木是没有撑到房顶,就是纸糊的墙皮破碎,或者有一面墙干脆倒了……”“断壁残垣”是《灵山》中较常出现的空间意象,“而我明白我此刻包围在一个死人的世界中,这断墙背后就有我死去的亲人”。“墙”意味着生存困境的障碍,也有着冰冷潮湿的质感,而“断墙”增加了破坏和残缺,这种往昔残存的断片之物往往能引起人们对过去时间的追忆。在《灵山》中,“断墙”可能指一种时间上的距离和空间上的隔阂,尤其象征着作者与父母、外婆等已故亲人之间生与死的阻隔,活着的人在梦境里透过断墙看死去的人的生活,却又永远无法轻易跨越。
窗”是自我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一方面,人可以从屋内向窗外看,另一方面,屋外的人也可以透过窗看向屋内。而在《灵山》中,“向窗外看”这个动作总是发生在主体“我”的身上,“我”注视窗外的阳光,“我”看到了窗外的雪地里的一只青蛙……这印证的正是漫游在现实生活中的“我”的向外扩展的过程,选择从窗看而不是走出门外,也表现出主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窗”在《灵山》中也有着情感内涵:在百无聊赖的山洞里,潮湿和寒冷的双重袭击下,主人公领悟到“我要的充其量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有灯光的窗口,里面有点温暖,有一个我爱的人,人也爱我,也就够了”。这里所指的“窗”,是走出家园漂泊在外的人,在夜晚看到有灯光的“窗”时对温情的渴望。巴什拉认为:因为所有发亮的东西都在看,所以窗前的灯象征着房屋的“眼睛”,而通过这双眼睛,房屋也像拥有人性一般地在等待,在守候。有灯光的窗口是房屋情感归属的象征,也是高行健情感需求的象征。
作为一部漫游小说,街道是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一方面,道路是相会或偶然邂逅的主要空间点,往往推动情节的发展。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就认为,“在道路中的一个时间或空间点上,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社会性隔阂在这里被克服,不同的命运在一处相遇并相互交织。所以《灵山》中的许多人物是以作者在街上偶然相遇的方式出场,如“你”在喧闹的街上再次遇到“她”,这种邂逅為“你”与“她”接近并同行创造了前提。又如“我”在街上邂逅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女孩,以此产生了一段交集。另一方面,街的空间概念还包括两旁有房屋或商店的比较宽阔的道路,街道上不仅人流密集,还可以充分展现当地人的生活情景,有着更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如夜晚的南方小镇的街道上,充斥着小商小贩、当地的妇女和儿童,而苗寨老街则是另一番场景。街道是完全开放的,作者作为空间的外来闯入者,可以自由地观察并体验所在地的生活和习俗。
但在《灵山》的结尾,“我”和“你”经历了外部世界的漫游后又都回归到了房间,“你”伴随着录音机的音乐在房间中写作,并在这种写作中得到重生;“我”从屋内看到窗外雪地里的青蛙,认为那就是上帝。在白茫茫的雪地中,雪覆盖了色彩,吸收了意念和含义,将外部的一切化为乌有,而雪把外部世界的存在消减,加强的是人物内心的精神空间。
三、结 语
通过梳理《灵山》的时空叙事脉络,我们可以发现:《灵山》在叙述上呈现出空间化的特点,作者在小说中取消了时间的序列性,架构出“我”和“你”的并置空间,小说时间由线性形态变为了立体化和空间化。高行健注重在《灵山》中展现空间,将人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和人物心理活动投射的想象空间并置混杂,同时在空间中融入人物的精神活动,成为感官化的空间,这些都是现代小说技巧的体现。
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强调时间和历史,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注重空间与并置,正如福柯所认为的:19世纪让人着魔的是历史,而20世纪则是空间的纪元。对空间的重视反映的正是现代社会中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混沌。然而这种时间感的丧失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福柯就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人们需要时间感,需要怀旧,人们需要这种意识,从而重新找到真正的处所。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文化教育学院)
基金项目:2021年河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黄河文化对眷村文学影响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2400410354
参考文献
[1] 薛毅.无词的言语[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235.
[2] 刘传.诺贝尔文学奖冲击波[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0:318.
[3]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19.
[4] 伊沙.高行健评说[M].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62-69.
[5] 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5.
[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44.
[7] 高行健.灵山[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
[8] 刘再复.高行健论[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
[9] 赵宪章.《灵山》文体分析[J].华文文学,2012(2).
[10] 黄丽华.高行健戏剧时空论[J].戏剧意识,19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