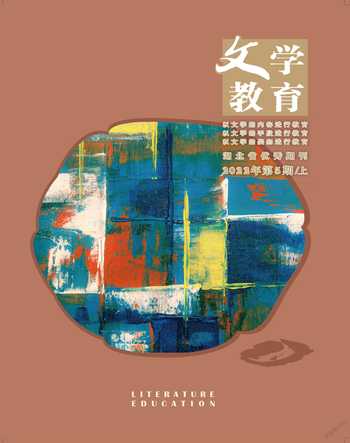卡佛《发烧》中的女性形象
2022-05-26刘丽
刘丽
内容摘要:从母性意识、女权主义、性别空间等角度,通过文本细读,对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发烧》中的女性形象深入剖析,揭示了韦伯斯特夫人和妻子艾琳這两位女性的主要人物特征及在凸显小说主题中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卡佛 《发烧》 极简主义 女性形象
雷蒙德·卡佛是近年来美国文坛涌现出的杰出短篇小说家,美国“极简主义”代表作家。他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卡佛于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美国的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高中毕业后,他未能继续大学学业,而是到锯木厂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二十岁之前卡佛就已经结婚生子,之后二十多年里,他辗转多个城市,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等,在养家糊口、艰难谋生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作,终有所成。卡佛的前半生充满了苦难与失望,经历了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等人生苦难,晚年罹患肺癌,于1988年8月2日因病去世。
卡佛的作品主要为短篇小说和诗歌,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大教堂》以及《何方来电》等。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如:锯木厂工人、餐馆招待、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他用浅显简洁的语言讲述着这些普通平民的生活: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卡佛将自己视为美国平民的代表,正如他所说,“自己归根结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1]。卡佛用词精简、笔法冷调,真正践行了他所说的“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1],其作品深受各国读者的好评。
一.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的数位译者先后翻译了雷蒙德·卡佛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国内研究者也对其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多个角度对他的多部作品进行了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分析了卡佛作品中的极简主义风格。如:王英杰从巨大的沉默、尖锐的疼痛和无言的结局三个方面分析了卡佛的短篇小说“少即是多”的创作特色[2];胡海青分析了卡佛《大教堂》中大量的留白技巧,指出这正是卡佛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3];卿深和曾繁健从源语文本的词汇和句法角度对卡佛的作品《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进行了英汉语言对比,发现该作品存在诸多极简主义的特征,并探讨了相关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4],等等。(二)、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卡佛作品的叙事特征。如:郭威总结出卡佛作品具有如下叙事特征:确定的人物形象与破碎的叙事结构相结合、白描式的不确定背景、极简的语言与无头绪的对话、留白的结尾[5];黄莉莉归纳了卡佛的短篇小说在叙事上的情境化、简约化和有限叙事的特点[6];朗晓娟分析了卡佛的早期作品《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在空白的语境下的大量重复现象[7];王中强认为卡佛在短篇小说中通过打破交流障碍、让人接触和亲历叙事疗法等手段,使人物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格和潜能的可能,体现了卡佛对底层社会民生的人文关怀[8];谢雅卿在叙事进程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视觉和触觉的隐喻式解读,从多维层次探析卡佛的短篇小说《大教堂》的叙事进程,反思作品中因视觉理性造成的封闭主体性[9];等等。(三)、运用精神生态批评的理论剖析卡佛小说的生态文学价值。如:张洁借助生态批评理论对卡佛的短篇小说《羽毛》进行解读,通过比较分析巴德夫妇和巴德夫妇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揭示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和谐观[10];江明瑶运用生态批评理论,探究了卡佛短篇小说中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11],等等。(四)、分析了卡佛小说中的文化因素。如:虞颖分析了卡佛小说中的电视文化[12];王中强对卡佛短篇小说中的“电视意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卡佛小说中的电视不同于消费研究或大众文化研究中电视的指涉意义,卡佛把电视作为当时社会蓝领阶层的符号,蓝领阶层沉迷于电视,反映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蓝领阶层的生存状态[13],等等。其中,分析卡佛小说的极简主义风格和叙事特征的研究成果占绝大多数。
目前,在国内还鲜有学者对卡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分析。虽然卡佛笔下的主人公多为男性,但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将从母性意识、女权主义、性别空间等角度,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卡佛的短篇小说《发烧》中的女性形象深入剖析,揭示其人物特征及其在凸显小说主题中的重大意义。
二.《发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短篇小说《发烧》选自卡佛于198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该小说入选了《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发烧》中,男主角卡莱尔是一名在高中教艺术史的教师。妻子艾琳抛下了卡莱尔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位男性同事离家出走。这个故事情节在卡佛的短篇小说中比较常见,很多时候,卡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面临类似婚姻危机的男性,如《小心》中的劳埃德、《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中售卖家具的男子、《取景框》中的男主角等。
妻子的出走给卡莱尔的生活带来了剧变。卡莱尔一边忙于工作,一边照料家中的两个小孩,简直疲于应付,需要马上请到一位保姆,而一时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后来幸好出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韦伯斯特夫人,使卡莱尔的生活重新走上了正轨。可惜没过多久,韦伯斯特夫人要去别处谋生,卡莱尔的生活再次陷入不确定中。小说到此结束。
在该小说中,有两位重要的女性角色——韦伯斯特夫人和卡莱尔的妻子艾琳。
韦伯斯特夫人显然扮演了母亲和救赎者的角色。
韦伯斯特夫人勤劳善良,是操持家务的好手,她把卡莱尔的两位孩子照料得无微不至,将房间打扫的干净、整洁,使卡莱尔重新感受到了来自女性的温暖,使他觉得身上的生活重担有所减轻。在卡莱尔身患重感冒、发高烧时,韦伯斯特夫人不仅亲手喂他吃药和喝麦片粥,还耐心地倾听卡莱尔讲述自己和妻子的故事,并不断地给予鼓励和安慰:“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继续讲,卡莱尔先生。有时,说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得说出来。再说,我爱听。讲出来,你就会感觉好些了。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像那件你正形容的事。爱情。就是它”。[1](P172)“很好,这样对你很好。”韦伯斯特夫人看见他讲完后,这样说,“你是好人。她也一样——卡莱尔夫人,也一样。别忘了,等这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没事的”。①(P173)
韦伯斯特夫人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经济状况很不好。她本人是一名保姆,以帮其他家庭做家务谋生;而她的丈夫六十多岁了,已经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她对待生活态度积极,充满热情和活力,對别人的痛苦充满同情,在卡莱尔最失意落魄时,韦伯斯特夫人给予了他毫无保留的帮助和鼓励。作为一位老者,韦伯斯特夫人的热情、积极和活力与男主角卡莱尔的无助、绝望和萎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韦伯斯特夫人不仅在生活上为卡莱尔提供了帮助,更在精神层面给予了卡莱尔鼓励和支持。在小说结尾,面对妻子离家出走的事实,卡莱尔变得更加平静和坦然。韦伯斯特夫人走后,卡莱尔决心告别过去:“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了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某种东西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和这之前的生活有关”。①(P172)卡莱尔站在窗边看着韦伯斯特夫人向他挥手告别,他感觉和妻子艾琳有关的旧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的心灵得到治愈。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一般扮演弱小的被保护者的角色,而在此小说中,韦伯斯特夫人却是个例外。韦伯斯特夫人对卡莱尔的帮助和鼓励表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成为救赎男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此可见卡佛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
而妻子艾琳属于另一类女性形象。
首先,艾琳在婚姻生活中对配偶不忠,这表明她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迷失了自己,伦理道德意识脆弱,内心空虚、无聊。在卡佛的小说中,类似的人物形象不胜枚举。他们信仰缺失、精神空虚,往往通过酗酒、寻求婚外情等方式来追求刺激,这是现代人共同的精神疾患。从这一点来说,艾琳体现的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负面的堕落女性的形象。她们大胆、放纵、自私,和美好的理想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卡佛并未忽视生活中负面的女性群体,她们身上虽有较多缺点,但却是当时美国现实生活中部分女性的真实写照,其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同样令人回味。
另一方面,艾琳梦想成为艺术家。在和卡莱尔的书信和电话聊天中她多次提到这点:“大学里,她的专业是艺术,就算答应嫁给他后,她还是说想做些和自己天赋相关的事。……就像她在信里面说的,她要去博一把”;①(P149)“告诉基思和莎拉,我爱他们。告诉他们,我会再给他们寄画的。告诉他们这个。我不想让他们忘了他们的妈妈是个艺术家。可能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那并不重要。但,你知道,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忘了这点”。①(P153)为此,艾琳抛弃了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离家出走,道德上的评判暂且不论,艾琳以她独特的方式探寻着“娜拉出走后怎样”这一命题的答案,展现了她的固执和倔强,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女性如何获得自由”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艾琳的出走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该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女权主义者的权利追求从最初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了工作和家庭等其他领域。卡佛通过对艾琳心理和语言的刻画,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女性地位仍然低下,女性仍从属于男性。艾琳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契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使在今日社会中,无论是在东西方国家,多数女性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生育和照顾子女,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她们的生活被束缚在家庭空间。“女性的身体被困在家中,她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婚姻成了限制她自身潜能发展的牢笼……正如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里奇所说,制度化的母性强调母性本能而非女性潜能;强调无私而非自我实现;强调自我同他人的联系而非自我的突破”。[14]任兵曾评述戴维·洛奇小说《换位》中的希拉里是“作为母亲而不是作为女人而存在,母亲成了她的身份,是一个和孩子、家庭相捆绑的存在,这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定位”[15],社会对艾琳的角色定位也原本如此。但艾琳不甘于这一角色定位,她不愿再做体贴和顺从的家庭主妇,而是通过和情人出走的方式对男权社会的桎梏发起挑战,独立勇敢地去追逐当艺术家的梦想。正如李钧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女性来说,“幸福的家庭主妇”是一个温柔的陷阱,“贤妻良母”的形象是一个“惬意的集中营”,诸多要求女性“适应环境”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必然断然否弃弗洛伊德“解剖学决定一切”之类“女性的奥秘”并看穿其虚伪性,努力战胜各种歧视与偏见,坚持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获得新生;这一突围的过程可能是持久、艰难而痛苦的,但女性按照个人内心召唤去努力的时代必将到来”。[16]事实上,女性要想得到和男性同等的权利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进程,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
卡佛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其形象范式却大多是被毁灭的女性。这些女性多数因为身处社会底层,因生活困顿而性格扭曲,有的脆弱,有的疯狂,有的堕落。短篇小说《发烧》中的韦伯斯特夫人却是个例外,这位年迈的老太太虽处于社会底层,生活贫困,但却坚强、乐观、乐于助人,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和人类的希望。韦伯斯特夫人的善良充满了人性主义的光辉,为卡莱尔摆脱精神困境提供了力量源泉。正如高熹微在评述《大教堂》时所说,“尽管生存现实仍然残酷,但他(卡佛)开始相信希望与奇迹的存在,试图通过呼唤传统人性中的善意来帮助人们找寻到精神的出口的可能性,在表现生存原态的同时点亮了理想主义和人性的光辉,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成为拯救与重生的力量”。[17]
而短篇小说《发烧》中的妻子艾琳虽然也存在伦理道德意识脆弱、精神空虚等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疾患,但她有了独立的女性意识和反抗精神,试图打破家庭空间的束缚,从家庭的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艾琳离家出走,将照顾子女这一传统的女性任务留给了丈夫,这本身就是对性别空间的一种颠覆与反抗。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卡佛.大教堂[M].肖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2]王英杰.论卡佛短篇创作中的“少即是多”[J].芒种,2014(22).
[3]胡海青.由《大教堂》看雷蒙德·卡佛的省略艺术[J].芒种,2014(11).
[4]卿深.曾繁健·《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的极简主义及其汉译策略[J].名作欣赏,2021(14).
[5]郭威.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卡佛叙事特征[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4).
[6]黄莉莉.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中的“电视意象”研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1).
[7]朗晓娟.空白与重复:评卡佛的《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的叙事手法[J].时代文学,2011(22).
[8]王中强.叙事疗法: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中的“人文关怀”[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1).
[9]谢雅卿.超越封闭的自我主体——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大教堂》的叙事进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2).
[10]张洁.雷蒙德·卡佛《羽毛》的生态主义解读[J].出版广角,2015(C1).
[11]江明瑶.现代人的危机——从生态批评视域看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J].安徽文学,2018(12).
[12]虞颖.卡佛小说中的美国电视文化——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为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19(2).
[13]王中强.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中的“电视意象”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3(3).
[14]翟文婧.价值的载体与欲望的对象——托尼·莫里森小说《爱》中的女性身体[J].国外文学,2011(1).
[15]任兵.戴维·洛奇小说《换位》中的性别空间[J].国外文学,2016(3).
[16]李钧.以“出走”反抗强权、以“书写”拒绝遗忘——论黄碧云《媚行者》女性主义叙事的经典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17]高熹微.浅析雷蒙德·卡佛《大教堂》中的不可靠叙述[J].学理论,2011(20).
(作者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