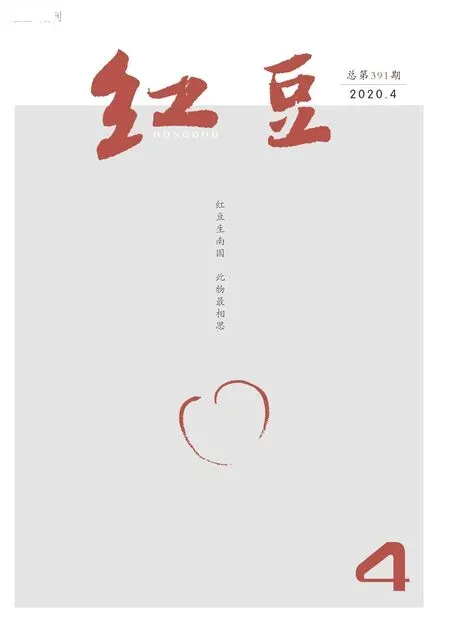我生长的地方
2022-05-26雷育斌
雷育斌
茉莉花开在春末,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季,花期进入尾声时已是十月。跨过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阳光最烈的季节,茉莉花美丽、洁白,香气浓郁,傲然立于枝头。这期间,花农的功劳居首位。
在我身边,有很多人的一生都与花田系在一起,像打了结的麻绳,缠绕、曲折。花农们一辈子泡在土地里,熟知茉莉花生长的规律。插枝、剪枝、施肥、除草……每一步都被花农记在心里,一年一年地去实践,慢慢地与血液融合,最终变成了身体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花农的一天是在花田里开始的,也是在花田里结束的。
当茉莉花苞的颜色介于黄白、青白间时,是最适合采摘的。早上六七时,已有零零星星的花农在花田间穿行采摘了。此时,花农无须戴草帽、穿长袖,就着清新的花香和微风,赤着脚一垄一垄地采摘和行走。他们长年走在熟悉的田垄间,脚早已习惯了土地的温度和松软度。对于花农来说,感应天气的变化,是从与土地零距离接触的脚开始的。雨天的田垄蓄着水,花田间一片泥泞,脚踩上去,再提起来,脚上沾着泥块,越踩泥块沾得越牢固,最后倒像是长在脚上的天然的鞋了。艳阳天摘花,随着时间推移,踩在花田间的脚渐渐升温,而后又慢慢降下去。多云的天气摘花最是舒适,脚踩在土地上,没有灼热感,亦无泥块牢牢沾上,赤裸的脚板踩在落于田垄间的花叶、花枝上面,感觉柔软、温润。
在農村,随处可见赤脚走村串巷的、下田干活的人,年纪越大的人越不喜穿鞋,孩童亦如是。他们将鞋放在挑担上,或将鞋置于田头间。土地是庄稼人的根,他们的一生与土地牢牢地系在一起,他们泡在土里、浸在地里,不分四季,百年后也将永远长眠于此。对于花农们来说,用脚去丈量土地、感受土地,是对土地的一种感恩。
午时的茉莉花质量最好,花骨朵大、白,透着晶亮。花农将纯白的茉莉花一一摘下放进腰间的小花袋中。一步步,花袋愈来愈沉,一垄茉莉花田也就走到了尽头了。
阳光渐渐西斜,花农们陆续收工。下午四时左右,花农们纷纷赶往横州市最大的茉莉花交易场所。这里有上百家收购茉莉花的摊点,浓郁的花香在整个花市弥漫。
横州茉莉鲜花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横州被原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横县茉莉花”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江,在百色被称为右江,在南宁被称为邕江,而流至横州,则被称为郁江。郁江孕育了小城的希望和生机,也赋予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别样的美食。鱼生成为横州最有名的美食。
鱼生的制作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工序。先是在鱼尾一寸处横切一刀,放血,去鳞后将鱼挂在钩上。然后是起肉,锋利的刀刃贴着鱼脊快、准、狠地割出两大块鱼肉。接着是剥皮,在鱼尾处轻轻划开一道口,一手抓鱼肉,一手抓鱼皮,用力一拉,肉与皮就分开了。剥出来的鱼肉用干净吸水的纸包着。最后是切片,鱼生片切得越薄越好。横州的鱼生片是艺术品,有的像花瓣,有的像蝴蝶,有的像鸟儿,让人不忍心动筷。
横州鱼生的配料非常讲究,将姜、香菜、紫苏、洋葱、酸萝卜丝、七彩椒、木瓜丁等切好和摆好,将一小撮配料放进盛有花生油、酱油等配料的小碟子里。夹上一块鱼肉,连同配料都放进嘴里,鱼片的鲜、脆、甜、嫩,与配料的香、咸、酸、辣在嘴里奏响美食交响曲。有人说,有了鱼生,桌面上的其他菜可以不用吃了。
据说吃鱼生有可能患上肝吸虫病,但鱼生的鲜美,仍让不少人视之为宴会佳肴。
我在这个小村庄生活了许多年,每一天都在村子里撒欢地跑。早上从村东头追着初升的太阳到村西头,傍晚从村西头随着夕阳余晖到村东头,一追一随间,一天也就过去了。村子里的一草一木,寄居在石板路缝隙下的蚂蚁,掉落在地上的野果子,果园里的蝈蝈、蟋蟀……都是我儿时的玩伴。那时我想,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个村子了。那时黑瓦黄泥墙的土房子特别多,衣服在土墙边摩擦,长年累月磨掉了一层层黄泥土屑,被磨掉泥屑的泥墙见证了一个村庄的变化。
那时村子热闹极了,到处是人。住在西边的陈婆和三婶子赶集要往东边走,在第二个路口转弯时,会撞见挑着剩菜、老叶子去池塘喂鱼的雷二叔。住在北边的是雷七叔,他们家种了几亩茉莉花,家门口就有几垄,经常能看到他在花田弯腰采摘的身影。七婶子从蛇皮袋中抓了几把玉米粉,拌着昨天的剩饭、剩菜倒在喂鸡槽里。住在南边的是收废品的十叔,他踩着一辆生锈掉漆的三轮车,晃着手中的铃铛去别的村收废品。
白天,小孩子成了村子的主人,他们绕着村子玩石子、跳格子、丢沙包。不知谁家的窗户被砸出了一条裂痕,哪家的小孩哭着鼻子走回家,哪个孩子在混战中取得了胜利。
傍晚,一大早就走出村子的村民从四面八方回来了。村子像平静的水面突然被投入了石子,波动了起来。炊烟最先在南边升起,一阵风将它吹散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各家屋顶的炊烟袅袅升起。菜香味飘出来时,太阳已落山,暖橘色的余晖笼罩着大地。
春天一到,村子周边的田地都热闹起来,嫩绿的野草铺满了整片黄土地。牛拉着犁耙,犁耙后边跟着人,嫩草被翻垦的土覆盖,成为农作物的肥料。村民将秧苗拉到稻田旁,开始插秧,或者抛秧。茉莉花枝上的黄叶子一片片落在田垄上,枝芽在疯长,被花农拿花剪齐齐剪掉,为茉莉花期做准备。一垄垄菜地上盖着厚厚的稻草,走进去翻看,菜籽已经发芽了。
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时期不一样。夏天,茉莉花是主调。七八月,花生开始收获了,水稻还在生长。当秋风吹着稻浪时,大地已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着稻秆,村民们拿着镰刀开始收割。一车车水稻被拉回来,堆放在晒谷场,堆起了村民的希望。趁着天气好,赶紧脱粒,一人放稻穗一人接谷粒,一人将脱掉的稻秆扒拉至一旁。小时候,整个村子只有两台脱粒机,二叔帮着七叔家放稻穗,七叔帮着六叔家接谷粒,你家、我家、他家成了一个家。
冬天的土地并不荒芜,在别的农作物被储存进粮仓时,果蔗成了土地的守护者。它们在土地上节节攀升,直指蓝天。这里的人爱吃果蔗,越是寒冷的天,在火堆旁啃得越欢。果蔗种多种少全凭个人意愿,多的砍了拉去集市卖,少的留着自家吃。这里的人不兴一根一根地买卖,而是五根、十根、二十根捆成一把买卖。
很多曾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离开了。有一段时间,我脑中无比清晰地记得那些刚离开的人。他们说话时的神情,微笑时嘴角的弧度,走路的姿势,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村西头住着雷四和阿东。阿东脑袋不灵光。从村子正门出去,有一条路必须经过他的房子,他房子的窗没有玻璃也没有糊纸,几根圆形木条在窗框里显得孤零零的。阿东常站在窗边看着,傻呵呵地笑。世人对他议论如何,阿东是不知道的,他生活在自己纯粹的世界里。
雷四早些年死了妻子,他带着儿子阿东一起生活。雷四每天早早出门干活,到饭点回家给儿子煮吃的,儿子吃完后他又下地去了。日复一日枯燥和艰辛的生活使得雷四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但大家没有听到雷四对命运的叹息和埋怨。他将阿东照顾得极好,他家的田地也打理得很好。
阿东是在一个冬天去世的,雷四是第二年的春天走的。他们在这个村子的痕迹慢慢消失,只留下无人居住、无人问津的土房子。院子里的荒草一年比一年长得茂密,取代了雷四和阿东,成了这个小院的主人。
对于一个村庄来说,有人来有人走,有人离开有人留下,是它亘古不变的规律,没有什么能陪伴它长久存在。村头古老的榕树也是如此,榕树在某一个雷雨夜被雷劈成了两半,一半被拦腰截断,另一半则枯萎了,只剩一个枯树桩。后来,枯树桩也不知被谁挖起了,等人们再记起来时,这里只剩下一个深坑。
小時候我自诩是最熟悉村庄的人。我爬过村头最高的那棵榕树,在它的顶端与一窝刚孵化的小鸟打了照面。我躲进过牛栏,牛的脾气与它的体型相当,但那天它喘着粗气看了我一眼,就自顾自地趴在角落里……
长大后,我明白了有些离开会如同雷四和阿东,有些离开是另一种方式——来来去去。过了年,在外打工的人扛着大包小包走了。在城市买房的人在某个吃完饭的午后带着妻儿坐上了汽车。有时候,我离开村子一去一个月,有时候,又一去半年。思乡就像一根藤蔓,延伸至五脏六腑。毕业后,在别的城市工作,我也成了来来去去村民中的一员。
村子渐渐陌生起来,我错过了它身上的每一次阵痛和欢愉。而总有一些人选择留守村子,比如我的祖父,不愿意跟他的儿子在一座城市生活,也不愿意跟他的孙子在另一座城市生活。每天天将亮时,他被自己的咳嗽声吵醒,再也无法入睡。他的床边有一把旧椅子和一张笨重且磨损严重的书桌,桌面上一只缺口的杯子装着半杯茶,杯子旁是白色塑料袋装的散烟和一沓方方正正的卷烟纸。他坐在椅子上,扯了烟丝放在纸上,卷上几卷。天亮后,他又移到院子里重复他的卷烟抽烟。一根烟慢慢卷慢慢抽,卷着抽着,他的生命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很久以前,年轻的他曾在雨天为了换粮食来回走六十公里,回到家已是半夜,鞋子走丢了一只。后来他跑货车,从南往北拉,又从北往南赶,一趟十天半个月是常事,跨越大半个中国。不开货车后,他打理家里的土地,种过大头菜、芋头、稻谷、花生……六十岁时他在集市开了一家早餐店,每天凌晨三点骑电车去十公里外的镇上拿米粉,返回时因天太黑常常错过拐回集市的路口。
如今他什么也干不动了,他抽完烟后就在村子里找老伙计玩。前几年隔壁家的老大去世了,住在西北边的爱陪他下棋的四叔公中风了,阿庆公去城里带小孙子了。一栋栋小洋楼取代了土瓦房,但他走了一圈又一圈,谁也没有遇到,甚至看家的狗也没有了。他又回到他的院子,坐在龙眼树下,慢慢地卷他的烟丝。
现在,村子一天比一天安静了。以前,村子里一片瓦从房顶滑落下来,十叔家的狗夜里叫声的次数,夏天的蝉鸣声,谁走了谁来了,都不会被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忽略。那时村庄周边的庄稼肆意生长,春夏秋冬都有自己的色调。如今,寒风将村西头无人居住的雷四家房顶吹塌了,这件事第二天并没有引起波澜。
某一天在书上看到林清玄写的“他们之所以能卑微地活过人世的烽火,是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有着故乡的骄傲”,我想起了故乡的一切,想起了它曾经的灯火通明、月色温暖,也想起了它现在的万籁俱寂、宛如空壳。荒芜的心底长出了丝丝藤蔓,它延伸的方向正是故乡。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