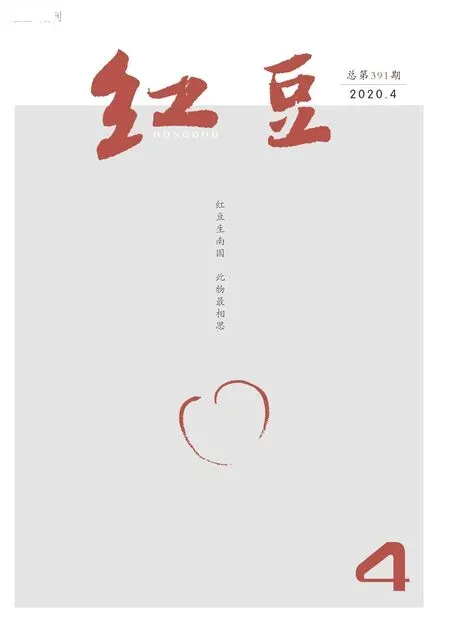高音
2022-05-26陈然
陈然
麦光储带领河西等人重访市立师范。说是市立师范,其实早已改成了职业大学,但他们习惯上还是叫市立师范。
那时候师范学校是多么好的学校啊,成绩非常好的初中毕业生才能上师范学校,成绩差一点的才去上高中。师范学校的老师也是很厉害的,那时教写作课的老师还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师范学校的文学社也是全省有名的,很多学生就是从这里爱上文学、音乐和美术的。但现在职业大学每年招收的都是高考成绩差、连专科都考不上的学生,老师的水平好像也降低了不少档次。现在你要是说自己是职大的老师,还不如说是某中学的老师光彩。
河西后来才知道,麦光储也是市立师范毕业的。她和滇生有时候称麦光储为师兄。麦光储说,他对师范学校是有感情的,是师范学校让他爱上了音乐。教他们音乐的是从省师范大学毕业的史红群老师。史老师眼睛有神,额头发亮,往那儿一站,就好像比日常生活高八度。滇生就笑了,说,你这个比喻太有趣了。麦光储说,可惜你们读师范学校的时候,史老师已经病退了。
他们走在操场上,操场还是原来的操场。滇生说有一次开运动会,一个男生扔标枪没把握好方向,结果标枪扎到了另一个男生的大腿,那个男生连人带标枪被送到医院。河西则说起班上一个女同学因失恋跳楼自杀未遂。几个人来到紫藤花架下面,他们惊喜地发现花架還像以前一样完好。那时大家经常在这花架下面读书、弹琴、唱歌。很多同学的诗歌或梦里,都出现过这个紫藤花架。麦光储深深地吸口气,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下我的故事。
从哪儿开头呢?还是先从史红群老师讲起吧。史红群老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爱国主义歌曲《我爱你,中国》。市立师范的音乐教师只有史红群一人,每年开学的时候,新生们在史老师的带领下演唱《我爱你,中国》。天空仿佛有百灵鸟飞过。大家唱着这首纯美、激昂的歌,感情一下子得到了升华。坐在窗边的同学,感觉或许更真切些,因为他们可以眼望蓝天。望不到蓝天的同学,便只好去望史红群老师的脸。史老师的脸像蓝天一样纯美,唱到“百灵鸟”的时候,她湿润的双唇成O型好看地张开,大家感觉到百灵鸟正在史老师的带领下,翩翩飞来。
这一首歌,史红群老师会教小半个学期。她反复地教、反复地检阅,并不断地翻新花样,有领唱、独唱、小组唱、大合唱、小合唱。学校的所有教职工,以及学校周围各家店铺的老板、老板娘,甚至其子女,都把这首歌唱得有腔有调。大家嘴上天天挂着“百灵鸟”和“蓝天”。有一回上级领导莅临学校检查工作,觉得这里的人特爱国,精神特健康。为此校领导受到了表彰,校领导还不点名地表扬了史红群老师。多年来,史红群老师的确为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争得了荣誉,作出了贡献。倘若学校举行节日联欢晚会,第一个节目一定是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倘若全市举行大会演,市立师范的经典节目一定是合唱《我爱你,中国》,并且一定能获奖。数年都是这样。若是有经验的评委,只要听到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请市立师范……他们就在计分栏内端端正正地填上高分。
史红群老师不但教学生唱,她自己也唱。每天清晨,她都到学校东边的小树林里去吊嗓子。咪——咪——咪——西——西——西……激扬、清越的嗓音振动着树叶,有如薄脆的金属片,给市立师范的日子镶上了一条亮丽的花边。空气清新得很,太阳就要破空而出,天空即将澄澈如洗,“百灵鸟”终于在女高音的带领下,款款飞来了。史红群老师面目洁净、眼含热泪,胸脯缓缓起伏,手放在胸前张开……学生们在蓝天、秧苗、硕果、青松里庄严地起床,穿上袜子,刷牙,洗脸,跑步,做操,晨读。森林无边,群山巍峨。小河荡着清波。他们像一根根家乡的甜蔗,骨节密实,神清气爽。他们也看到,从小树林里回来的史红群老师顾盼有神、容光焕发。史红群老师缓缓地踱步,目不斜视,一言不发。细心的同学还会发现,史红群老师柔美的外表遮着些凝重,眸子明亮而忧伤。
后来大家就听说,还孑然一身的史红群老师,大学毕业后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对方是她所在的师范大学的老师,一位才华横溢、思想敏锐的声乐系副教授。他是一位卓尔不群的音乐教授,不但教学生声乐,还教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单独教她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你,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崇尚先锋艺术的现代派音乐家,唱起这首歌竟然眼含热泪。据说他们相爱得很深,但后来不知怎么就分手了。
麦光储说,那时我跟班上的杜彩霞有一种朦胧的关系。元旦联欢晚会上我俩演唱男女声二重唱《外婆的澎湖湾》,之后就互有好感。那天史红群老师叫我和杜彩霞排练男女二重唱《我爱你,中国》,让她烦恼的是她没法把我和杜彩霞的嗓音提高八度。史红群老师的手从琴键上移开,在我们眼前划过。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高音!高音!!这不是外婆的澎湖湾,这是蓝天,是碧波滚滚,是白雪皑皑!你们的声音还应该向上!向上!!再向上!!!史红群老师神情激昂地喊道。
我和杜彩霞吓得愣在那里。脚踏风琴重新响起来。G调。大音阶,小音阶。我们的嗓音在史红群老师的牵引下,顺着白键黑键一级级地向上爬。难道真如史老师所说,高音是可以挖出来的?我们将信将疑。史老师一双柔美的素手在琴键上敲击,还真像在奋力挖掘什么,铮琮的乐声高高低低地流出。史老师要拔掉萝卜栽上葱,好让我们彻底地忘记“澎湖湾”。重新开始。悠远、嘹亮的引子,同样悠远、嘹亮的鸟的鸣音。到了“春天蓬勃的秧苗”那里,问题又出现了。史老师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不是我们的声音上不去。如果是独自一人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声音都可以爬得很高,但我和杜彩霞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结果声音就渐渐低了下去,又落到了“澎湖湾”的水平。
这个结果让史老师大吃一惊,她似乎明白了过来,自己就没想过这首歌是否适合二重唱或男女声二重唱,或者高音是否适合二重唱或男女声二重唱。这么说来,高音难道永远是孤独的?
麦光储说,为史老师终身大事操心的人从没有间断过。毕业班的班主任胡德量老师又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胡德量老师一向以严谨、稳重和细心著称,她介绍的人应该是极为可靠的。对方是第二中学的化学老师。化学老师姓董。这个小董啊,实在是晚熟,什么都不懂,红群,你要好好教教他。胡老师这样说道。
史老师和小董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花临湖的状元桥上。史老师后来说,化学老师小董和以往别人介绍的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她自己的心境却是发生变化了。在还未爱上他之前就已经恨上他了。他们沿着湖边的路慢慢向前走,湖水暗绿,发出物体腐烂的臭气。一些泡沫在上面啪啪地破裂,化学老师小董说那是甲烷形成的气泡破裂,我们听到了甲烷的尖叫。他们一边聊天一边暗暗打量着对方。化学老师小董的个子大概在一米七二,像高音i。只是他的胸腔里有高音吗?有青松气质、红梅品格吗?不过史老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提醒自己应该注意他的风度和他的身体。他看上去骨骼粗大,还是风流倜傥的,像她以前的一个同学。他的手也大,似乎可以让两种物质还未接触便已发生剧烈的反应。他的目光有些深藏不露,似乎颇有些阅历。忽然想起介绍人胡德量老师说他晚熟的话,史老师不禁扑哧一声笑起来。化学老师小董收回目光,也跟着笑起来。他似乎已经从她的皮肤和身体的曲线,准确地计算出她体内无机盐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麦光储说,即将毕业的时候,同学们有的一声不响,有的哭哭笑笑,有的抱头鼠窜。同学们都知道将来无一例外地要去乡下中学或小学当老师,而且很可能是后者。也就是说同学们要回到最初读书的地方去工作。同学们都已经尝到一点城市生活的好处,比如有水泥马路、自来水、电影院、商场等,可乡下学校那时候有的连电灯都没有。实际上,有一些同学觉悟得早并且开始了挣扎或叛逃。有的积极要求上进,以便将来不被分到乡下去,后来有的同学的确如愿以偿。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成功叛逃,他在师范学校毕业那年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清华大学,不过这得归功于他有一位当老师的父亲。
我向来是一个翻身求解放欲望不强的人,有点消沉,有点逆来顺受。那些同学挣扎或叛逃的手段在我看来均不可取或不可及。我绝不会为了不重新落回泥土而去抓什么我根本不感兴趣的救命稻草。我认为有音乐就足够了,当然还有爱情。我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同寝室的人对我都爱理不理的,不跟我下棋也不跟我打扑克。我逗他们笑,可他们却把头抬得更高。他们甚至取笑我的饭量,说我像一个女人,说我的嗓子好是因为我吃得少。我干脆说也许是这样。
谁都知道,长笛和短笛在音域、音色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八九岁时,我在湖滩放牛,一次两头公牛为一头母牛顶角。它们四蹄刨地,牛角互相顶着,发出“咔嚓”声。可能它们在想,谁厉害母牛就归谁。母牛显然也同意这个观点,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看,享受异性在它面前争风吃醋、龙虎相斗带来的陶醉感。那时我还不懂事,傻乎乎地在一旁大呼小叫,后来还拿一根杨树枝子去驱赶别人家的牛。那牛正处劣势,眼看在母牛眼里牛面丢尽,一肚子气恼。这下好了,它用牛角把我挑了起来,再远远地抛了出去。我从医院里捡回了一条命,却少了一截肠子。说不定正是这一截肠子,把长笛变成了短笛,把劣质音变成了优质音。我和杜彩霞合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已成为市立师范的校园经典曲目。或许它和史红群老师的《我爱你,中国》可谓双峰并峙,成了一道風景。
我觉得有必要把我和杜彩霞的关系确定一下。我们一起散步、唱歌、看电影,也拥抱过接吻过。当杜彩霞火热的嘴唇挑衅似的对着我的时候,我不禁心惊肉跳。我说我爱你,她眯着眼睛只是笑。我又说我爱你,她睁了睁眼说中国。她像一条泥鳅,美丽而俏皮。一天上午,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她递给我一本书,书里夹着张写着“中午请来广播室”的纸条。作为校广播室的广播员,从上学期起杜彩霞就大模大样地搬到广播室去住了。这给我们的约会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麦光储说,史红群老师和二中的化学老师小董,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史老师的房间。据史老师后来讲,那天黄昏,小董事先没打招呼,就径直闯了进来。史老师刚洗完澡,正在比画衣服。她站在镜前,忽然听到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史老师慌乱中也顾不上穿胸罩,把一件丝绸睡衣套在身上就去开门。
史老师没好气地拉开门,一看是二中的化学老师小董。小董老师装作什么也不懂的样子进来了。房间很小,史老师倒退着请小董坐下。她头发湿漉漉的,地上还有几团沾着脂粉气的水渍。小董闻着这气息,看到了放在床上的干净的胸罩,他的目光便从床上直接落到了史老师胸前。史老师这时要说有多害羞就有多害羞,她忽然想骂他,但小董的目光使她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女人的私密一旦被人窥破,她会立刻把对方视作共同享有者,从而表现得慷慨大方。她对他产生了亲密感,她说你要死啊。这样的骂人的话也只有对极亲密的人才骂得出。化学老师小董找到了催化剂,他说死就死,死在你这里比活在任何地方都好。
小董便一把把史老师抓了过来。她想完了,但她懒得动。她眯着眼听任化学老师摆布。化学老师的镊子、试管和酒精灯不一会儿都搁到了她身上,像螃蟹一样乱爬。他开始给她加热,她像中了魔法,动不了。森林无边,群山巍峨,河水淙淙地流着,清波从梦中流过。史红群老师感觉眼睛一热,忽然流下了泪水。
至于麦光储和杜彩霞,那天他离开杜彩霞身体时,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做了一个优美的弹跳。这时他似乎才注意到她是那样的瘦弱,两排肋骨庄严整齐。杜彩霞的神情是麻木而忧伤的。他吻着她的肩膀说你真好。他注意到,她颈下的皮肤似乎有一些擦不掉的污垢,乳下也有,肚脐眼里也有,污垢好像和皮肤已经融为一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他更为感动,重新吻了她,又说你真好。他老家把这些黑黑的污垢样的东西叫作垢骨朵,垢骨朵仿佛在尘埃里开花,仿佛出淤泥而不染。
杜彩霞坐起来,什么也不说,她一件件地穿衣服,穿到黑色麻纱布裙时,依然笨拙地抬腿弯腰,耳边还有隐约的轰鸣。这时的麦光储对女人的具体部位还不懂得欣赏,他爱的女人还是一股气流,一股带电的噼啪作响的气流。杜彩霞穿好衣服,沉思片刻,对他说你坐下。
麦光储坐下了。这时他心里温柔得很。杜彩霞说,光储,你不是一直问我爱不爱你吗?我跟你说,这之前我是爱你的,这之后我就不爱你了。我很高兴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你,现在我可以安心去做一个贤妻良母了,不过与你无关。谢谢你。从现在开始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你走吧。
麦光储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下楼时他还摔了一跤。不过摔得很舒服,让他忘记了其他的痛。他想幸亏摔了一跤,不然他恐怕没法走出那栋大楼。
他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后因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中学。其间他和乡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谈过恋爱,遭到了竞争对手的威胁并被打破了头。幸亏有音乐让他渡过了难关。不过他已经对声乐不感兴趣而专攻器乐,尤其喜欢箫和古琴。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在房间听《高山流水》和《平沙落雁》。过了两年,他争取到一个去师专音乐系进修的机会。毕业后技艺大进,成了师范附小的音乐老师。没想到竟然跟杜彩霞成了同事。杜彩霞从师范毕业后,嫁给了副校长那有点智障的儿子,或者说她因为答应嫁给副校长的儿子而争取到了一个留在城里的名额,被分配到了师范附小。
麦光储说,史红群老师和二中的小董老师结婚不久,史红群老师的精神就出了问题。她受不了化学老师那酒精灯一样的眼睛和镊子一样的手。他设置种种陷阱,仔细盘问她的前尘过往,而她往往就跌了进去。他的陷阱,有的像量筒,有的像烧杯,有的像漏斗,有的像冷凝管。让小董老师耿耿于怀的是史红群老师竟然不是处女,这让他心里化学反应连连。小董老师的化学实在是学得太好了,脑子里永远有用不完的化学方程式,对各种试纸、试剂、溶剂信手拈手,对各种催化剂、氧化剂、腐蚀剂运用自如。他给史红群老师表演了一次魔术。他把一块小石头丢进一个插了导管的密封玻璃瓶里,那里面盛了些淡黄色的液体。再把导管插进另一个密封的玻璃瓶里,不一会儿石头不见了踪影。然后他拔出导管,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进一个敞口杯里。接着他打开那个密封的玻璃瓶,里面好像盛满了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把一瓶空气倒进了杯子里,但奇怪的是,蜡烛还真的熄灭了。
他说你也完全可以是那支蜡烛,史红群老师就发出一声尖叫。小董老师说你叫吧,蝴蝶的尖叫声我都听过,你这不过是甲烷的尖叫而已。他对着那只空荡荡的瓶子喃喃自语,说真恨不得把你装在瓶子里变回石头。
后来尖叫就成了史红群老师的常态。她像是在噩梦里喘不过气来,空气像是比石头还重的东西,压在她身上,而她在奋力地把它们推开。但石头滚滚,源源不断。
据说史红群老师和师范大学声乐系副教授的分手源于一次游戏。副教授在吟唱了几遍“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之后,就以查看声带为由从史红群老师的身体里飞过去了。但他们很快由短暂的愉悦转向长久的烦恼。先是史红群老师不慎怀上了,她的想法是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慷慨激昂而又哭哭啼啼地说,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即使他不要她了,有了这个孩子她也会心满意足。为了说服她,他找到了言之凿凿的理由。他说,你忘了?你当时一直在吃药,服药期间怀的孩子多是智力障碍者。难道你想让我们一生都拖着一条尾巴吗?我的大小姐,你可要想清楚。好不容易说服她,但新的問题又来了,她要跟他结婚。他斥责道,俗气!俗气!怎么好上了就要往婚姻上扯?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吗?柴可夫斯基的悲剧难道还要重新上演吗?的确,在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创作、演唱了一组极有震撼力的作品,评论界声称他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已经开启。但是自从她不小心怀孕后,他的创作和演出质量明显下降。他很烦躁也很痛苦。他没有心情再抚摸她,说“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了。
他是爱她的。当初在解开她上衣的第一颗纽扣的时候,他的手少有地出现了颤抖。那是一个高音对另一个高音的渴望和期待。天籁。他说。不知道指的是她的身体还是她的声带。也许都是吧。他说,我又想跟你结婚,又不想跟你结婚。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听命于天。你拿一个五分的硬币向上抛,如果正面朝上,我们就结婚;如果背面朝上,我们就分手。
麦光储说,后来他我见过史红群老师一次,那时她已经和二中的化学老师小董分居,搬回师范学校住了。她已经不能上课了,师范学校里再也没有百灵鸟飞过了。她的那双眼睛似乎要从眉毛下飘到额头上来,好像唱歌跑了调,不肯待在正确的音阶上。她盯着手里的一枚硬币,对它说,你不要偏袒我,就按你的意志行事吧。她双手把它合在掌心,摇了几下,然后张开了手。硬币奋力切开了空气,直着上升又斜斜飘落,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责任编辑 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