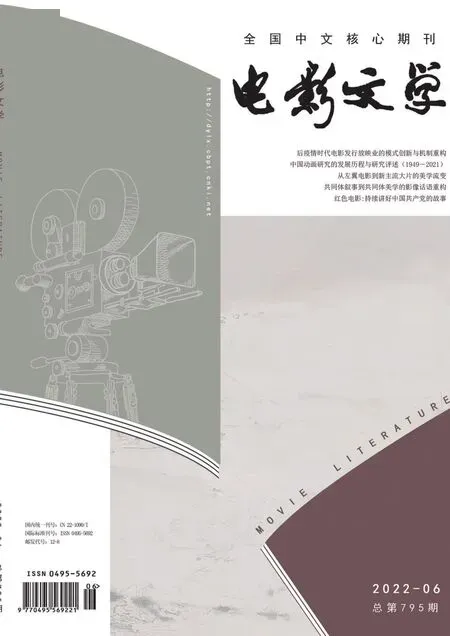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四个春天》的诗意化表达与美学探索
2022-05-23张振安
张振安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导演陆庆屹出生于贵州独山,其父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2013年陆庆屹回老家,用随身的摄像机记录了与二老过年的点点滴滴。自此,在接下来的三个春天,陆庆屹每次回老家,都会用摄像机记录下父母的日常生活,做菜、养蜂、弹琴、登山、诗词歌赋……纪录片《四个春天》推出后备受各界好评,并在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殊荣,成为近几年来中国内地口碑最好的小成本纪录片。能获得这种赞誉,与导演准确运用独特的镜头美学语言,将平凡的故事进行诗意化表达,休戚相关。
一、纪录片中“本质的真实”
纪录片在人文关怀方面较为突出,追求社会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思考的严肃性弥足珍贵,“真实”也因此成为衡量一部纪录片含金量的最高原则。《四个春天》的导演非专业出身,却大胆挑战了这一最高原则,无论是构图、机位设计还是分镜头安排,相比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该片的镜头语言都充斥着浓厚的主观意识,更像是在讲述一个精心编排的商业故事。而这种有意为之的镜头语言编排,正是该片对“真实性”这一核心主题的忠诚实践。
对“真实性”的追求,纪录片一直保持不变,就像新闻追求“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一样,记录内容本身本应是摄像机实时拍摄的情况,以当时所见、所听、所感、所闻为依据,从表象逐步深入内部,达到“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在真实性和客观性上纪录片都无法与新闻报道相比,但“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矛盾同样会体现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但在这点上,一般的纪录片创作者通常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即为了尽可能向观众表达“真实”的诚意,都会不自觉地向“现象真实”靠拢,乃至刻意在影片中使用所谓不加丝毫修饰的原生态式的镜头语言。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很多纪录片在镜头质感上非常粗糙,在美学意义上几乎完全失去了观赏价值。导演想要表达的思想主旨也被淹没在这种噪音中,出现信息传达失真问题。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自然也就无从谈起。陆庆屹则十分精准地把握住本质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春天》的真实性,是“本质的真实”。虽然影片的镜头语言充斥着导演的主观意图,但这种主观意图的目的却是要让观众以一种在场者的视角,不自觉地沉浸于影片语境中,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导演父母日常生活点滴,而向观众传达“真实性”的任务,也就在这种感同身受中不知不觉完成了。当然从专业角度讲,导演拍摄技术依然较为稚嫩甚至是业余,但这也恰恰正是该片在“真实性”上独具魅力之所在:长达四年的时间跨度,可以明显感受到导演拍摄技术的进步。这种技巧的进步不仅是导演自身诚意的证明,也凸显出影片作为纪录片最大的闪光点——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式平民故事。
二、电影美学的抽象化与工具化
电影美学是电影审美意识的抽象和升华,优秀的电影美学能使每一帧画面都准确传达创作者所希望传达的意图。在镜头语言上,本片导演大量镜头虽然琐碎,但拍摄对象都准确聚焦于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春节时的家长里短,较快速的分镜切换和讲究的构图也不会让观众出现视觉疲劳,并且特意以家中的天井作为视觉坐标,以此为基点,将横跨四个春天的整部影片进行有效串联,实现了让观众以最舒服的方式迅速融入陆家日常生活的创作目的。
人物形象塑造上,导演遵循纪录片的基本原则,未安排任何职业演员参演,无论家长里短还是人情世故,剧中人物所有行为动机都没有导演的刻意引导。虽然这导致剧中主要角色的外在形象相对粗糙,无法与其内心活动产生直接联系,达不到常规电影的美学追求,行为上也多机械性重复,让观众在观影时不免产生枯燥感,但这种粗粝的人物质感恰恰就是对普通人单调生活最忠实的反映,影片真实感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突出。在听觉语言上,为体现真实性,除片尾谢幕时的钢琴曲,导演坚持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配乐,所有音色均来自影片本身的同期录制:脚步声、切菜声、鞭炮声、笑声,哪怕是姐姐葬礼这个剧情的高潮点上,导演也坚持将葬礼现场的各种声音一一记录,乱哄哄一片,却将日常生活的真实性表达得淋漓尽致。
同时,导演也并非真的不做任何处理就将现实生活的片段以最大的客观性原封不动地截取,毕竟对生活片段进行截取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行为。本片从镜头剪辑、叙事结构与分镜设计,到人物拍摄时的构图角度、光照要求,乃至剧情与声效的搭配,呈现出的效果无一不是导演主观意图的表达。比如影片开头以黑幕的形式安插了首孝歌,故意为影片蒙上一层淡淡的悲伤基调。直到电影过半,才发现这首孝歌正是姐姐葬礼上两位守灵老人所唱,这一前后呼应是极明显的主观手法,但也只有这种恰到好处的主动染色才将导演对姐姐的情感乃至由此产生的对生离死别的感悟进行升华,将生活的真实衬托得足够鲜明,让观众更加立体地触摸到影片所要表达的情感。
归根结底,电影美学技巧只是工具,无论是刻意精致还是有意粗糙,与影片本意严重背离的表达理念都是错误的。《四个春天》乍看如一碗清水,一眼见底平淡无奇,但真品尝起来,唯有沉浸其中的人才会明白个中酸甜苦辣。导演对构图、剪辑、分镜设计等工具的运用,无论主客观与否,都是在为影片的这种独特气质服务,以求将“真实性”用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样的电影才算是具有了真正的美学价值。
三、剧情的诗意化表达与具体意向
诗意化表达的源头是诗歌。史诗之“诗”,就是对历史事件忠实记录。发展至今,西方主流的意向化诗意表达不再追求形式上的节奏和韵律,转而从非明晰的主题和非戏剧化的叙事来构成纪录片的诗性书写,把外在节奏转化成内在韵律。但中国电影人更喜欢追求将影片中的抽象情绪转化为具体意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东西方差异,自然与国情有关:“中国故事”自身独有的“东方韵味”天然就适合韵律化书写;而也只有将抽象情绪“降维”到具体意象表现上,才能更好地让中国观众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
导演对具体意象的表达十分精准,有意无意间,影片从第二个春天开始就出现了一条推动整个剧情戏剧化发展的故事线:姐姐陆庆伟少时离开贵州远赴东北读书,受地域文化影响,长大后,姐姐性格爽朗,爱说爱笑,颇具文艺细胞,备受父母喜爱。但这样一位热爱生活的姐姐,却被诊断出肺癌,并在影片第二个春天后便撒手人寰。从纪录片角度来说,导演对姐姐之死的处理始终是克制的,不仅镜头语言充满冷静,在剧情结构设置上也并未将这一事件设置在电影“起”“承”“转”“合”的“转”处,从而刻意达到强烈的戏剧效果。但从商业电影创作角度来说,导演的处理又包含明显的戏剧编排意图:将姐姐之死安排在“承”处,可以让观众在前两个春天初尝中国式家庭温暖而与导演获得初步共鸣后,迅速被推入导演所希望的轨道,不自觉地跟随导演镜头对生命价值这一核心命题进行沉浸式探索。之后的两个春天,通过对父亲整整一年不愿动乐器、母亲开始考虑自己死后父亲独自生活的艰难等细节片段的展现,影片后半段的基调始终笼罩在姐姐之死的阴影中。在“起”“承”“转”“合”四步用四个春天走完后,影片也就此戛然而止,足以证明导演这种及早推出姐姐之死的处理的确是有意为之。但这种处理方式却正是导演对中国式诗意化表达的完美诠释。
胡智峰在《电视审美文化论》中说,纪录片真实表达现实生活的美学价值,必然要以描述生活为开端,以发现生活为深入,最后在创造生活的升华中实现这一目的。《四个春天》的导演以春节这一最喜庆的中国传统节日为开端,却又符合三层美学论,赋予其不同含义。在第一个春天中,导演在讲述一个普通中国家庭过春节的各种琐碎日常,熏腊肉、做扣肉、放鞭炮,中国平民家庭最质朴的喜悦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直接传达到观众眼前,即所谓描述生活。在第二个春天中,父母日常生活的比例开始增加,并突出父母年复一年的老迈,即开始对“发现生活”这一层次进行提炼。随后以四月份二伯生病为引子,将这一段落的叙事重心逐渐过渡到姐姐之死这条主线上,让这种提炼效果达到高潮。到第三和第四个春天,原本由父亲承包的熏腊肉开始由二老共同完成,表明因姐姐之死,春节这种琐碎日常对这个家庭显然已经具备不同以往的含义。而之后,父母也用扫墓、养蜂、翻看旧家庭录像等全新的生活细节证明,他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创造生活”。由此,观众也不再是被动式审美,而是同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身为主人公的父母领悟生活、创造生活的过程中,并得出最终结论。可见,将姐姐之死安排在第二个春天的段落中,正是对三层美学论中“发现生活”层面的完美诠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看似客观的镜头,却达到了强烈的戏剧冲突效果,在不动声色中让原本平淡的琐碎日常以顺滑的姿态上升到价值观思考的高度,整部影片的价值也从单纯介绍中国平民生活的家长里短,升华到对当代中国民众、民族与文明的人文主义关怀,即对“中国故事”的一次准确讲述。在姐姐葬礼上,导演并未特意用近景镜头对准家人,以此凸出家人的悲痛,而是花费颇多篇幅拍摄两位乡里老人在守灵时唱孝歌的场面,在古朴又不失生活气息的大段唱词中,用蒙太奇剪辑的方式不断插入以中景镜头拍摄的家人守灵时的静态画面。悠然间,不仅姐姐的一生已概括其中,导演本人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也跃然银幕。这种对日常生活思考的升华,正是该片在诗意化表达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准。
四、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关怀展现
人文主义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是当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基石之一。电影艺术诞生后,其传播能力极大推动了人文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普及,而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也反过来与之结合,由此催生了各国独具特色的地域性人文主义。落实到中国大地,“中国故事”“中国美学”就成为这种人文关怀的具体代表,同时这也意味着,所谓“中国故事”,其本质上就天然包含一种传统、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基调。但当下一些中国电影人却经常把这种传统、平民和世俗故意诠释为保守、底层和边缘化,并必然要让影片在最后导向痛苦与反思。究其原因,是很多当代中国电影人习惯于跟从欧美电影的价值观。在他们眼中,唯有将平民阶层的痛苦无限放大,用“把伤疤揭开给人看”的方式来刺激观众的负面情绪,才符合二战后西方价值观语境下以批判态度去处理人文主义的潮流。但近年来诸多实例已证明,这种思潮在中国陷入了流于形式和审美疲劳的瓶颈。西方电影确是中国电影的源头和师傅,但记录生活又何必只能有“批判与揭露”这一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确取得较大进步,但在14亿人口庞大基数和千年历史的沉淀面前,区区40余年改革开放显然还不足以让大多数人就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尤其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对内,给当代中国普通民众带来巨大生存竞争压力,对外,则让中国普通民众直接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发生一系列碰撞与冲突,从物质到精神,当代中国民众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感、不安全感和自我认同危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相比中老年,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群体反而更渴望回归传统、更加“怀旧”,以求在传统中获得价值观共鸣与自我认同,而后者恰恰正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观影主体。在这种独有的文化语境下,“批判”这一行为天然带有的俯视姿态和否定句式自然会使大部分中国城市青年本能地产生厌恶与反感,人文关怀的主旨更适合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去展现,而中国观众也更希望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与影片创作者交流。中国影像要做到真正具有“中国味”,就必须在手法上做出创新,展现出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故事。虽然难以用语言和文字直接表述,但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的厚重是确确实实承载在每一个中国平民血液中的,他们用直觉就能发现一部影片是否有诚意、平等地与自己交流。此时影片制作者若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批判者与拯救者的姿态,对观众和传统进行接二连三的否定,必然要被观众抛弃。
因此,《四个春天》对传统的全面拥抱无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需求。在人物视角选取上,导演真实代入了自己作为独自在远方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人的身份,以春节这个城市青年唯一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的节日为契机,以第一视角切入家庭,随后过渡到对父母琐碎日常的描绘,让观众仿佛是以自己的视角观察自己父母的一举一动,直接戳中了当代中国城市青年那颗因生活压力而充满遗憾的孝心,让对父母的内疚获得了恰当宣泄。在对生活的描绘上,影片传达的是一种传统的朴拙自然的理念。从做饭、染发到养蜂、养花,影片里身在小镇的父母所做的事都很简单,但却亲力亲为,这明显是在暗示如今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我们过度追求物质,对他人和社会的过度依赖,由此导致人性的懒惰与对他人、社会关系的敏感。若能如影片中的父母那样,放弃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亲手创造一些事物,这样的生活虽笨拙粗糙,却朴素而淡然。就如影片中这座贵州小镇,虽不好看,但生活的自然与真实却无处不在,这对因过度物质化而迷茫,也因过度物质化而让自我过于渺小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无疑是最及时的一剂安慰。在所传达的情感上,影片寻求的是一种安宁的心态。鸡鸣狗叫的集市,高悬红灯笼的街道,忙里忙外的邻里乡亲,再加上父亲熏制腊肠时那一句乡音浓重的“安逸呀”,瞬间就把观众从大城市的高楼林立拉回到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地域特色的空间中。从准备年饭的老人忙碌的身影到夜空中漫天烟火,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所展现的不仅是中国人对传统、家庭、美食的信仰,更是在展现中国人珍惜当下、随遇而安、不奢求富贵的平和心态。“以后如果我们不在了也好,你们要记住家里的传统”,在作者充满温情的镜头下,老人这种对传统的固守,反而成为最值得当代中国社会珍惜的精神。在对价值观的感悟上,影片则在提醒观众,生活的安宁并不等于圆满,面对遗憾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坦然接受,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中国式价值观。小到每个春节后父母站在门前凝望子女远去,大到姐姐病死这种人生悲剧,剧中人物所代表的普通人在面对这一切时显然是渺小无力的,但离开的子女在下一个春节还会如燕子般归来,姐姐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在回忆中孕育希望,在缅怀中面向未来,中国人一代代生生不息,就是在这种过程中悄然实现的。
中国影像如今需要做的是探寻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东方神韵,发掘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而不是粗浅地迎合西方或模仿国际大片。在这个问题上,《四个春天》已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放低姿态,以质朴去用心雕琢的每一帧画面去捕捉生活的自然状态,哪怕是姐姐之死这种戏剧性事件也是在不动声色中让悲伤点到即止,将陆家人的喜怒哀乐都平等地放在观众眼前,诉说生命真谛,阐释别离轮回,在日常的平凡中寻找生命的张力,不知不觉间,中国故事、中国美学,乃至中国式人文主义关怀,都已得到了最好的展现。
《四个春天》的成功无疑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小成本艺术与人文主义电影的一剂强心剂。在艺术层面,该片以大胆尝试为传统纪录片探索了新领域,细致而考究的美学表达将中国纪录片的质量提高了一个台阶,以诗意化的手法为讲好传统中国故事注入了新血液,更以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方式实现了一次真正的中国式人文主义关怀。无论是艺术还是商业层面,《四个春天》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让世界看到,真正在用中国语境讲述中国故事的新一代中国电影正在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