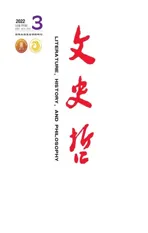墨家远源考论
——先秦墨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
2022-05-19高华平
高华平
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至清末,曹耀湘等始以为不然;而近代胡适则立为专论,以为诸子“学术之兴”,应如《淮南子·要略》所言,“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即“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然平心而论,《汉书·艺文志》在主“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的同时,实亦有所谓诸子之学“皆本于世变之所急”之意。《汉书·艺文志》于其《诸子略》曰“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云云,即是如此。故今天我们研究先秦诸子的起源,如果持《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为唯一正确答案,固有失偏颇,但如果像胡适那样,一概否认诸子学术与“王官之学”的联系,亦难称客观公允。
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先秦诸子的起源,既不能拘泥于“诸子出于王官”说,也不应完全否认诸子学术与前代“王官之学”的联系,而应该从春秋战国之前,三代“王官之学”的形成和演变与远古氏族、部落及国家(方国、酋邦)变迁的关系中,从更久远和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层面来探讨先秦诸子之学的起源和成因。
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辨
《汉书·艺文志》于《诸子略》“序”墨家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汉书·艺文志》对墨家源头的“序说”,除“序说”墨家思想部分之外,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此处“序”“墨家者流”为“出于清庙之守”一句中之“守”字,与其言其他诸子皆出于某一王官之“官”字不同;其二,《汉志》言其他诸子出于某一王官,皆与《周礼》所叙“王官”相应,而此处所谓“清庙之守”,则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故而对“清庙之守”为何种“王官”及其职掌如何,历来聚讼纷纭。
对于《汉书·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而其他诸子皆曰“出于某官”,二者之所以有“守”与“官”之不同,学术界现有的基本看法是,二者并无根本差别,应该只是缘于传抄之误:“《志》云‘盖出于清庙之守’,《汉纪》卷二十五,‘守’字作‘官’,此殆班《志》原文。《志》叙诸子十家,皆云出于某官,不应此处独异。宋翔凤《过庭录》已疑‘守’为‘官’字之误。今可据《汉纪》正之。”
“墨家者流”到底是“出于清庙之守”,还是“出于清庙之官”呢?因为在现存的所有文献中没有关于所谓“清庙”这一官职的具体记载,所以学者们对墨家的真正起源如何,就不免陷入猜测之中。有学者以为“刘歆之叙诸子……至其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尤为无稽之臆说,无可采取”。还有学者以《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家著作,首列“《尹佚》二篇”(班固自注:“周臣,在成、康时也”),即表明刘向以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非巫则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故墨家当如《吕氏春秋·当染》所云,以“清庙之守”为史官也;又因为上古巫、史不分,所谓祭祀也具有宗教性质,故曰:“清庙即明堂……(亦)即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乃祀五帝之所,为神教之府。”即既把“清庙之守”等同于史官,也将“清庙之守”等同于祭祀之官,谓“墨家者,古宗教家”也。
但自古以来学者对墨家所源出的“清庙之守”的种种猜测,却是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的。如曰“清庙之守”为主宗庙祭祀之官或“宗教家”,既未明其为何官,而称之为巫或史官,又与世所熟知的“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重复,且“今《墨子》书中绝未言及史佚”,后人辑佚《左传》《周书》所载尹(史)佚语及遗事,“亦与墨家之旨不类”,“亦未足定为其学之所从出”。同样,《汉书·艺文志》在“序”“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之后,接着再将墨家的“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亦归于“清庙之守”,这也是难以成立的。如所谓“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之所以不足以成为“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的证据,乃是因为此系建立清庙者之所为,而绝对不可能是主事于清庙之官之所为——既非主事于清庙之官者所为,则主事于清庙者又如何可借之以示“贵俭”呢?《左传·桓公二年》记臧哀伯曰:“君人者……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杜预注:“以茅饰屋,著俭也。”孔颖达疏:“《冬官·考工记》有葺屋、瓦屋,则屋之覆盖或草或瓦。《传》言‘清庙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无他文。”“君人者”不可能亲自去“以茅饰屋”(即饰清庙);“饰屋”者只能是《周礼·考工记》所记之建筑工匠也——而此类工匠不属于所谓“清庙之守”是无疑的。又如,所谓“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也似与所谓“清庙之守”并无关系。《礼记·文王世子》曰“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郑玄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同书《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孔颖达疏:“天子袒而割牲者,谓天子养三老、五更之时,亲袒衣而割牲也……不言教以孝者,与上互文。”可见,“养三老、五更”的目的,并非所谓“兼爱”,而在于“孝悌”也。《汉书·艺文志》“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之说,亦可谓无据矣。故《汉书·艺文志》此段以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墨家“贵俭”之说,出自《左传》“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其余养三老、五更,选士大射,宗祀严父,顺四时而行,以孝视天下”,以“附会《孝经》《三礼》而为之辞”,正如墨子称儒者公孟之言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墨子·公孟》)这实际是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墨家的源头,而非从所谓“清庙之守”中探求墨家之所出。而实际上,正如张舜徽曾经指出的,墨家之学之所出,“当以夏(禹)为说”:
《孟子》称“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盖“兼爱”之所出也。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熙然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见《淮南·精神篇》)盖“非命”之所出也。《论语》称“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盖“贵俭”“上贤”“右鬼”“尚同”之所出也。

墨家的“贵俭”“兼爱”“上(尚)贤”“右(明)鬼”“上(尚)同”等思想主张,实皆来自所谓“夏道”或“禹之道”,而如果从《周礼》中所记载的“王制”或“周官”来看,建立“夏道”或“禹之道”的夏禹本人,在上古文献的记载中,他在尧舜时代所担任的官职正是司空。故根据我的研究,《汉书·艺文志》所谓“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墨家者流,盖出于司空之官”或“盖出于匠人之守”。《尚书·舜典》曰: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史记·五帝本纪》袭用了这段文字,云:“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可见,在“周官”系统里,夏禹的确是出身于“司空之官”的。

二、司空之官与墨家的基本思想
《尚书·舜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皆曰舜命“禹作司空”,但二书随后却又有舜命垂作“共工”的记载。《尚书·舜典》云: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史记·五帝本纪》曰:
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
这里的“共工”之“工”,自然是指“百工”。孔安国《传》释《尚书·尧典》“允釐百工”为“工,官”;释“畴若予工”,为“谁能顺我百工事者”,亦皆取此。司马迁把此名改写为“谁能驯予工”,亦是此义。但“共工”显然是“顺我百工事者”或“驯予工者”,而非“百工”本身,相当于“工官”或“工师”。故《史记集解》解“顺我百工事者”或“驯予工者”引马融曰:“谓主百工之官也”,又直解“共工”即“为司空”,其职掌为“共理百工之事。”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以“共工”也作为官名(“司空”),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即舜似乎同时任命了两位司空,一位是禹(或称伯禹),另一位官名虽有所不同,被称之为“共工”,但实际也是司空的“垂”。
当然,因为文献中关于“垂作共工”的记载并不多见,故很难判断此“共工”之官是不是真的等于司空。《墨子·非儒下》“巧垂作舟”,孙诒让注“巧垂”曰:“毕云:‘《北堂书钞》引作“倕”,《太平御览》作“锤”,《事类赋》引作“工倕”。《太平御览》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俞云:‘“巧垂”当作“功垂”,字之误也。《周官·肆师职》注曰:“古者工与功同字。”然则“功垂”即“工垂”也。《庄子·胠箧》“攦工倕之指”,《释文》曰:“倕音垂,尧时巧者也。”《尧典》:“咨!垂,女共工”,是称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案:《山海经·海内经》云:‘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辞·九章》亦云‘巧倕’,又见《七谏》。俞说未塙。’”似乎“共工”与司空并不完全相同,他只是“顺我百工事者”或“驯予工者”,有些像是司空的属官,而且他以“巧”著称,故又被称为“巧垂”。而“周官”司空的职掌范围则大得多,除了上文所述《周礼·冬官考工记》郑玄注所谓“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之外,还有贾公彦说所谓“建国营国沟洫诸事皆掌之也”。故《周礼·冬官考工记》又有“匠人为沟洫”之说,陈澧因曰:“工事以治水为最大。匠人为沟为防,百余字而尽治水之法。”而《汉书·沟洫志》篇即曰《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云云,即禹亦以善“治水”著称。
古人很早似即已注意到“共工”与“司空”在职掌上存在差异,故他们对“共工”为何时代和何方神圣有较多讨论,以期通过确定“共工”其人及其时代归属,来解决此矛盾。《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徐元诰《国语集解》曰:

其实以上众说虽常互为抵触,却也是可以弥合的。所谓“共工”,既是上古传说时代的人名、氏族或部落名,也是官名、地名或方国(酋邦)名。此“共工”是上古传说时代居于“共”地的氏族、部落或方国(酋邦),因其以“百工”技术见长,尤善于兴建水利工程以治水,故在原有的母氏族、母部落中被任命为“工官”或“工师”,称为“共工”(即“共工氏”);而此氏族的居住地和首领亦被称之为“共工”(后因该氏族独立于原有的母氏族、母部族——“共”,亦被简称为“共”氏族、部落或方国)。“共工”氏族的首领曾先后被女娲氏或高辛氏或尧、舜“所灭”或流放,其成员也或被杀,或被流放,居住于原地者也或为其他氏族所统治,但却可谓屡次“灭”而不亡。《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鲁语上》则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所记略同,只是将“九有”改为了“九州”)这都是说“共工”本人或其氏族、部落与夏禹一样,是以“治水”或“平水土”见长的。《国语·周语下》说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共工用灭”。即是说,共工“治水”是发生在夏禹“治水土”之前的,夏禹应属于共工“治水”的继任者。故《国语·周语下》接着又说:“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州,陂鄣九泽,丰殖九谷,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夏禹和“共工”都曾任传说中尧、舜时代的“治水”之官,而且夏禹还是共工的继任者,共工的“从孙”又曾协助大禹治水,这才取得“治水”的成功。夏禹和共工的治水,虽然向来都认为二人有疏、堵之不同,但《汉书·沟洫志》有“禹堙洪水十三年”之说,《尚书·洪范》篇也说:“鲧陻洪水。”《国语·周语下》说:“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三人治水都有“堙”或“陻”的方式。徐旭生认为这种方式就是筑堤防,而当时“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水”也是“建国”“营国”或“营城郭,建都邑”之事,即是司空之职——司空可以说就是共工,共工也就是司空。《尚书》《史记》之所以记伯禹和垂同时被舜任命为掌“司空”之职的官,郑玄等人以“司空”不是当时的“常官”,只是临时性官职为解。这应该一是因为“司空之官”,乃出现于舜继尧之位而任命百官之后,在此之前则只见共工而不见司空,故旧儒注《周礼·考工记》即以为二者实存在时代先后的区别:“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二是因为《尚书》《史记》可能把本属于不同时代的垂和禹,说成了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故使舜命百官时出现了两个“司空”(为了弥合这一矛盾,便让这两个司空,一个名司空,另一个则名共工)。实际上,作“共工”的垂,这个人生活的年代应该较晚,当在夏少康之子伃(又作“予”“杼”等)之后,根本不可能与禹同时。《墨子·非儒下》以“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为例驳斥儒家“君子循而不作”,其所叙顺序为羿、伃、奚仲,最后方为“巧垂”。因《墨子》一书叙古者圣王君子如尧、舜、禹、汤、文、武等人,必严格遵循时代的先后顺序,故《非儒下》所叙羿、伃、奚仲、巧垂,亦必依时代先后为序。“巧垂”之前,奚仲“为夏车正”(《左传·定公元年》杜预注说他“为夏禹掌车服大夫”),但后羿则为取代夏后启之子“太康失国”之人,帝伃则为少康之子,当在夏朝前中期,故“巧倕”生活的年代亦当离帝伃时代不远,即不能早于夏朝中期。《尚书》《史记》把垂作为尧、舜时代同时被舜任命的司空和共工,时代上是存在明显混乱的(《释文》以“工倕”为“尧时巧者”,亦当是据《尚书》《史记》而产生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即“垂”为共工氏部落中的一个胞族的名称,以工巧著称,其后代亦被称为“垂”,这样也能解释得通)。因为文献中在舜命禹为司空和垂为共工之后,除了《荀子》之《议兵》《非相》和《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禹伐共工”之说外,基本上再没有关于“共工”的记载了,故此后共工氏部落是否承袭着“共工”之职,以及夏禹与“共工”或司空是否还有关系,那我们皆不得而知了。
当然,《尚书》《史记》的错误在无意中也可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认识“司空之官”的职掌,原是同时包括了共工和鲧禹的“治水”及“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以及垂或“巧倕”的“监百工”“造车服器械”等两个方面的。由此亦可为我们准确考察“盖出于司空之官”的墨家之“贵俭”“兼爱”“上(尚)贤”“右(明)鬼”“非命”“上(尚)同”等思想主张——寻找先秦墨家思想在上古“王官之学”中的真正源头,提供最正确的方向。
首先,我们看墨家的“贵俭”(具体体现为“节用”“节葬”等)与“司空之官”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说墨家之所以“贵俭”,乃因为其所出的“清庙之守”的“清庙”为“茅屋采椽”,故主张“贵俭”。但上文已经指出,“清庙茅屋”乃是“立社稷宗庙”的“司空之官”之所“守”,而非主持宗庙祭祀的巫史之所“守”,故“清庙之守”不能借此以示“贵俭”。退一步说,即使“清庙之守”可借“清庙茅屋”以示“贵俭”,但又如何因“茅屋采椽”而“节用”“节葬”呢?故以“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来解释墨家的“贵俭”思想,实有牵强附会之嫌,远不如以“墨家者流,盖出于司空之官”——司空(共工)有“治水”(“治沟洫”)之职合情合理。因为《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都记载说,帝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帝尧先后用共工、鲧治水,均告失败;舜使“禹作司空”,方始开启“治水”的成功之路。《淮南子·要略》曰:“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虆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由此可见,墨家具体体现为“节用”“节葬”的“贵俭”主张,原本与“清庙茅屋”并无关系,而是司空(共工)“治水”时特殊的环境所产生的。
其次,我们再看墨家的“兼爱”与“司空之官”的关系。《汉书·艺文志》以墨家的“兼爱”思想主张,也“出于清庙之守”,“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我们在上文已指出此说的牵强。这里要强调的是,“兼爱”的前提是“平等”,对所爱的对象并没有远近、亲疏、长幼的区别,否则它就是儒家的“等差之爱”。故具有浓厚儒家思想意味的“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是绝不可能“出于清庙之守”的——“兼爱”只可能出于上古传说时代最具有平等意识的“司空之官”。
“司空之官”之所以具有平等意识,这是由于其“监百工者”的职掌和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周礼·冬官·司空》篇已亡,《考工记》所记“百工”,即使是《司空》原来之名,亦只是其属官或“工师”之名,而非“百工”之“工种”名称。故今日言司空所“监”之“百工”,不可拘泥于其中到底有多少具体之“工”而论其平等意识。“司空之官”所监之“百工”,固不可与王、公、卿、士平起平坐,但在“百工”内部则应该是没有任何上下高低之分的。我们不能说其中的“舟人”比“轮人”或“舆人”重要,也不能说“矢人”比“弓人”重要或“陶人”比“匠人”重要。故曰:“墨家者流,盖出于司空之官”;而“司空之官”则因“百工”平等,是以“兼爱”。
其三,我们再看墨家的“上贤”与“司空之官”的关系。“司空之官”对待其所“监”之“百工”既最具平等意识,那么“上贤”就必是其思想主张中的应有之义。因为既然在“百工”之中人人平等,“监百工者”对每个“工人”都是无等差地“兼爱”的,那么在实际的工作任用或提拔某个或某些“工人”,就只能看谁有多少真正的才能了。这样,就必然会提出“上贤”的思想主张。
今本《墨子》书中有《尚贤》上、中、下三篇,是集中体现墨家“上贤”思想的文本。《经典释文·叙录》引郑康成《书赞》云:“尚者,上也。”可见“尚贤”即“上贤”。《说文解字·贝部》:“贤,多才也。”此“才”即“财”。然以“财”多为“贤”,非其本义。此由出土文献中“贤”字的形义演变可见。在《墨子·尚贤》三篇中,“贤”字虽有与“良”连缀为“贤良”一词以表德义之例,但更多乃表贤能义,即人的才能。《墨子·尚贤上》曰:“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文章接着又举古者圣王“尚贤”之例曰: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墨子为什么要以舜、益、伊尹、闳夭、泰颠这些人为例,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呢?这当然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古者”由“贱”而“贵”,靠才能上位的典型。《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朱熹都说:“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这说明,舜原本出身低微。益,又称伯益,伯翳,是皋陶之子,为嬴姓,而嬴姓和偃姓之“嬴”“偃”二字,“也仅为一声之转”,都是东方鸟夷部落“少昊(皞)之后”,也是出身低贱的。伊尹以庖厨而得“举”。闳夭、泰颠虽其事不详,然亦可类推。要之,他们都是靠自己的“贤能”而得以选拔的,故都成了墨子“尚贤”的例证。墨家之所以有此“尚贤”的主张,又不能不与其学出于“监百工者”的“司空之官”,而“监百工者”的“司空之官”最具平等意识,其选人用人必以才能优先为原则有关。
其四,墨家的“右(明)鬼”与“司空之官”的关系。《汉书·艺文志》以“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故“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即认为“右(明)鬼”,乃出于夏商周三代于明堂祭祀始祖及先帝。因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所以在明堂清庙,祭祀亡灵,就标志主事者或参与者——“清庙之守”是“右鬼”的。在今本《墨子》一书的“十论”中,“右鬼”观念是和“天志”之肯定“天”为有意志的人格,可以赏善罚恶联系在一起的。《汉书·艺文志》“宗祀严父,是以右鬼”,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且不说从今存《墨子·明鬼》(原有上、中、下三篇,今存下篇)来看,墨子立论仅针对“执无鬼论者”而发,全篇似仅在“明鬼神之实有也”,而是否“右鬼”则尚难确定。即使参与宗庙祭祀的“清庙之守”有肯定“鬼神之实有”之意,也不能反过来推导出肯定“鬼神之实有”(“右鬼”),必出于“清庙之守”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只是一个或然判断,而非必然判断——不在“清庙”祭祀,而在河边祭水神,在山上祭山神,在家中祭灶神,都可以有肯定“鬼神之实有”或“右鬼”的意识,但都并非“出于清庙之守”。
其五,墨家“上同”(即“尚同”)与“司空之官”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曰:墨家“上同”,是因其“盖出于清庙之守”,“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这是把“上同”与“右(明)鬼”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但同样是缺乏根据的。且不说“西周祭祖礼的重点和精神与商代有重要的不同:西周王室特别注重‘近祖’。金文中最重要的‘禘’礼,晚周皆释作‘追远尊先’始祖之祭,事实上不免有儒家猜测成分,与西周史实不符。西周金文中除了康王祭文、武、成王三代以外,其余诸王所祭俱以祖考两代为对象,并无追祭三代者”,根本没有“以孝视天下”的意思;即使就今本《墨子》书中《尚同》上、中、下三篇来看,也可断定“上(尚)同”与“清庙之守”的“以孝视天下”没有任何关系。《墨子·尚同上》开篇即明确说明“上(尚)同”主张提出的缘由,是因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议’。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目的是要通过乡同法于乡长,国同法于国君,天下同法于天子,天子同法于天的层层“上同”,达到一乡、一国,乃至全天下皆“同其义”,从而实现“乡治”“国治”和“天下治”。如何才能“一同”其“乡”“国”,乃至“天下之义”呢?方法就墨子在《尚同上》开篇所提到的与“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相反的情形,即要“有刑政”。

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
那么,这个“法仪”——“绳”“县(悬)”“规”“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何才能保持它的绝对公平正确呢?《法仪》篇又说: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孙诒让注:“学谓师也。”)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
但这个“天”并非“苍苍者”之谓也,而是有人格和意志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不仅如此,这个“天”还是“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的,“故圣王法之”。可以说,它既是绝对客观公正的标准,又是绝对客观公正而仁爱的裁判者,可以赏善罚恶。因此,要保证人间的“治法”的客观、公正、无私、仁爱,唯一的办法就是“莫若法天”,正如《天志下》所云:“故子墨子立天志,以为法仪。”——这也就是“上(尚)同”,即“上(尚)同”于“天”。墨子以“法天”为王公大人“为治”和“百工从事”所依据之“法”或绳墨规矩的源头和保证,这与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观点十分相似。西塞罗和奥古斯丁都认为:“各种治理人民的属世法律”,都是从“正确的理性”“最高的理性”或者说“神明的智慧”“神法”(“它是唯一的法律,永恒的、不变的法律”)而来的,“都是从这唯一的永恒律而来”的,因此,世间的秩序和法律就要服从于上帝永远的正义和永恒的法律,即服从于神法。这与墨子遵循的是一种相同的宗教逻辑。故“墨家者流”,实出于“司空之官”;“监百工者”的“司空之官”以及“百工”之绳墨规矩或“法仪”,皆“莫若法天”,其“为治”或“从事”,亦皆“右鬼”而“上(尚)同于天”——此亦墨家所以为“宗教家”也。
其六,墨家“非命”与“司空之官”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这是以“清庙之守”依《礼记·月令》之制而行政,与以为诸事“于己于人,皆属前定”者相反,故而可以对“执有命者”“非之也”。
墨家言“命”,本是与其所谓“法”“天”或“天志”“天鬼”结合在一起的。墨家认为,人间的一切“法仪”或“法”,都来源于“天”或“天志”“天鬼”,所以他们只是“尊天右鬼”。除此之外,他们绝对不承认还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法仪”的东西,更不用说“命”这样“一种外在的”和“客观的决定力量”了。故可以说,“命”是一种不被墨家所承认的对人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客观外在力量——它乃是对墨子之“天”或“天志”“天鬼”这个唯一最高神及其地位的否定。墨家要维护其“法仪”“天志”“右(明)鬼”的观点,“非命”就不能不是他们一种必然的思想主张。
或许有人会说,今本《墨子》书中有《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三篇,提出了以“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之“三表法”以“非命”,并没有说到“命”妨害了“法仪”或“天鬼”“天志”,何以见得“非命”是为了“尊天右鬼”(或者说墨家“尊天右鬼”,“是以非命”)呢?这是因为墨子认为,以“三表法”来看,“执有命论者”虽然表面上只是表现为“本之古者圣王之事”,妨害了在上位的王公大人们“发以为刑政”,而“下以驵百姓之从事”;但因为不论是王公大人的“刑政”“法仪”,还是“百工”所依据的绳墨规矩,最后都必然要“上(尚)同于天”——不相信“上同于于”的“百工”之“法仪”及其根本“天”或“天志”,反而相信所谓“命”,墨家能不“非”之吗?故《墨子·非命上》曰:“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三、上古传说时代的共工氏、少皞氏与薛国之历史变迁
墨家者流,并非如《汉书·艺文志》说出于所谓“清庙之守”,而应当出于“司空之官”。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上古时代,不同氏族、部落及国家皆有自己的“司空之官”。炎帝部落的共工氏、黄帝部落(实际应该属颛顼氏)的伯禹之族和少皞氏中的鸤鸠氏(“平水土”“营城郭”)和鷷雉氏(“监百工者”)之族都曾守司空之职。
“共工”,由字面的意思而言,即“共”氏族、部落或方国之“工”。《诗经·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郑玄笺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释文》:“共,国名。郑云:‘徂、共皆国名。’”《尚书·尧典》:“允釐百工”,《孔传》:“工,官。”故可以说,“共工”即是“共”氏族、部落或方国(酋邦)的“工官”(“工师”)。《尚书·尧典》《舜典》和《史记·五帝本纪》都说舜命垂作“共工”,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曰:此“共工”是官名,“谓主百工之官”,即都是将“共工”直接解“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者的。共工氏可以说是“共”这个氏族或部落的一个胞族,即“共”的“工”胞族。“共”这个氏族或部落本居于离周之镐京不远的地方,故与周人发生冲突而文王“伐之”。但“共”氏族或部落中的“共工”这个胞族,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即已随当时东迁的炎黄部落一起向东迁徙了,故文献中很早即已有关于共工氏与东部各氏族或部落发生冲突的记载。
由炎、黄部落与东夷部落冲突与交融的地点多在河、济、淮水流域而言,上古传说时代东迁后的共工氏的聚居地,应在今河南辉县的“共国”(此乃“共工氏”之国,而非其祖先所在的西部“共”国)。它位于太行山东南沿,其东北大约以共首山(即苏门山)为起点,沿淇水为限;西则以辉县西部“共首”为起点,属于共水、卫水、濮水、淇水的上游地区。《汉书·地理志上》“河内郡”下有“共”县,原注:“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说文解字·水部》:“淇水出河内共北山,东入河。或曰出隆虑西山。”段玉裁注:“河内郡:共。二《志》同。共,音恭。今河南卫辉府辉县治,古共城也。前《志》‘共’下曰:‘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北山,今辉县西北苏门山,其别阜曰共山是也。《诗》曰:‘毖彼泉水,北流于淇。’又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谓淇之源也。今淇水自彰德府林县流入卫辉府淇县境……与古入河者迥异。”《荀子·儒效》:“至共头而山隧。”杨倞注:“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卢文弨曰:“案:共头,即共首,见《庄子》。”《庄子·让王》“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成玄英疏:“共伯,名和,周子之孙也……共首山,今在河内。”《释文》引司马云:“共伯得归于宗,逍遥得意于共山之首。共丘(首)山,今在河内共县西。”可见,共工氏所居的“共工”之地,虽也名“共”,但却在太行山东坡由山地到平原地带。先秦两汉故书中出现的“共”,除上面《诗经·大雅·皇矣》中的“共”之外,其余概指共工氏之“共”。尽管此共工氏已是新的方国(酋邦),但所在区域已在中国的东部而非西部,所统治的基本民众固当以共工氏部落的人民为主。

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其末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载。
庖牺、女娲时代约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或在黄帝之前,而尧舜时代紧接夏朝,距“蚩尤作兵”的黄帝时代较远,故《帝王世纪》所记共工氏事迹,其发生时代亦应远在尧舜之前。《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杜预注:“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太皞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故“或以共工同(伏)牺、(神)农为三皇”。由《帝王世纪》所谓共工氏“任智刑”,“以水承木,非行次”来看,共工氏除了上文所引《左传》《国语》《尚书》说共工氏“为水师”,“能平水土”或“治水”之外,还实发现了水能“承木”的原理——可能始作木筏或早期的舟——于舟船之发明有功,确属于虽名为“共工”而不名为“司空”的“司空之官”。《说文解字·舟部》曰 :“舟,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段玉裁注曰:
郭(璞)注《山海经》曰:“《世本》云:‘共鼓、货狄作舟。’《易·系辞》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共鼓、货狄,黄帝、尧舜间人。”货狄,疑即化益,即伯益也。《考工记》故书“舟”作“周”。
《世本》说“作舟”的共鼓、伯益二人,这虽与《墨子·非儒下》的“巧倕作舟”不同,但细推它们却有相通之处。因为“共鼓”一名虽不见于其他经、传,段玉裁仅说其“为黄帝、尧舜间人”,但由“共工”“共伯”皆由地名或氏族名加官名而成来看,“共鼓”极有可能即是“共”地或共工氏部落的一位名“鼓”的首领。《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孙伯陵,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始为钟,为乐风。”《尚书·舜典》说舜让垂作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山海经》这里说鼓、延、殳三人都是“炎帝之孙伯陵”之子,与共工氏都属于炎帝氏族是无疑的。可见这里的鼓,应该就是共鼓。共鼓与延一同发明了钟,又可见共工氏部落的确以“工巧”见长。《世本》说共鼓与东夷部落的伯益一同发明了舟(要知道,伯益是被舜任命“掌山泽之官”的“虞”的,造船必先伐木,由伯益和共鼓一起“作舟”,那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很碰巧的是,《墨子·非儒下》说“巧倕作舟”,我在上文虽推断“巧倕”实际应该是夏朝前中期的人,似乎巧倕与此处将共鼓、伯益“作舟”不同,但共鼓、巧倕都是共工氏部落的人,而共工氏部落除了“平水土”之外,实还有发明舟船的技能。《尚书》《史记》中以该部落的首领为“共工”或“汝共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结合《帝王世纪》《世本》《墨子》诸书来看,共工氏部落“作舟”,正如所谓“奚仲作车”一样(《说文解字·车部》:“车,夏后时奚仲所造。”《山海经·海内经》:“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郭璞注:“《世本》云‘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作意,是以互称之。”《山海经·海内经》又说,“是始为舟”的番禺,“始以木为车”的奚仲、吉光,“始为巧倕,是始为下民百巧”的义均,皆是“帝俊”的子孙;而“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者,亦是“帝俊”其人。徐旭生认为《海内经》的这些传说,“出于华夏集团”,即炎、黄集团,“可以说没有疑义”。故可以推测,或许“帝俊”即是共工氏部落的始祖,故有如此传说),也有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共工氏仅因“以水承木”,发明了木排或木筏一类最原始的舟船,尧舜时共鼓、伯益加以改进,再到夏朝时“巧倕”进一步完善,始成为较为精良的舟,故不同时期的共工氏皆于“作舟”有功(《荀子·解蔽》:“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杨倞注:“倕,舜之共工……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当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不仅说巧倕发明了弓,其发明弓的过程也与“奚仲作车”相似)。
关于共工氏的氏族归属,文献上有不同的记载,且似互相矛盾。《山海经·海内经》又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这里既说共工是祝融所生,似乎应该属于颛顼(祝融氏)部落。《左传·昭公十八年》和《史记·五帝本纪》皆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历代皆以之为共工氏,即以共工氏出于少皞氏东夷部落,与颛顼(祝融)为一系,但《山海经》此处又将其始祖追溯于“炎帝之妻”,似乎更应该属于炎帝氏族。徐旭生认为,这种矛盾“大约是氏族分合的关系,并不是个人血统关系”;之所以有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祝融氏族到底是由高阳氏族分出,或者是由炎帝氏族分出,那传说的来源并不是一个,因而不相符合,我们既没有理由取其一而舍其一,也就不必强说”。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从共工氏部落由“炎帝之妻”到戏器生祝融,再到“由祝融生共工”的谱系,我们还可以猜想到其中可能隐含的更多历史。《史记·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帝颛顼高阳氏,尽管儒家的经传已皆将其整合为黄帝氏族的分支,但现代的研究表明,颛瑞高阳氏实出东夷少皞氏。《山海经·大荒东经》开头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皞)之国,少昊(皞)孺帝颛顼于此。”此“孺”或系与“乳”字通假,为哺育之义。《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曰:“(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皞)。”《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皇甫谧亦曰:“(高阳)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又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风”与“凤”初为一字,甲骨文常如此作,故太皞为东方鸟夷之族。《国语·楚语下》曰:“及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可见,颛顼继少皞为帝,属东夷(鸟夷)部落的一个分支。共工氏居于共水、卫水、濮水、淇水的上游,颛顼氏部落居于这些水系的下游——当时古黄河经此北流——汇入黄河故道。每到夏季暴雨引发洪灾,洪水汇入古黄河中去就会形成洪水泛滥。这个洪水对处于众水上游的共工族尚且深以为患,更何况是处于其下游的颛顼(祝融)氏族呢?
颛顼其人其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事迹很少,只说其为“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但无论从上面我们所引文献来看,还是从现代学者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颛顼氏实出于少皞(其先为太皞)族,属于东部鸟夷的一支。颛顼氏部落中,最先崛起的是帝喾高辛氏命为“火正”的祝融氏分支;祝融氏逐渐强大后,又分出祝融八姓;在祝融八姓中,又以羋姓一支最为强大,这就是后来的楚人。
楚人在祝融氏部落里成为强大的一支,其时间应该颇早。《说文解字·木部》曰:“楚,丛木,一名荆也。”说“楚”一名“荆”,应该是楚人迁荆山之后才得名的,时代实际较晚。祝融族中的“楚”这一支兴起应较早,至迟在夏商之际已经势力强大。《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出于祝融氏吴回之后,则曰吴回第六子为季连,“羋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熊穴。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直到周初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这才开始走向兴盛。

因此,如果说颛顼氏的一支,早期一般都称颛顼,随后则称祝融,再其后则称楚,称荆,实际都是说的同一族。所以,《山海经·海内经》说“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仍是说的颛顼氏与共工氏的关系。因为共工氏处于卫、濮、淇诸水之上游,颛顼(祝融)氏处于这些水系的下游,所以两大氏族经常因水灾而发生冲突。这种水灾,在上游的共工氏看来,本是天灾,他们也是筑堤修城,自顾不暇;但在下游的颛顼(祝融)氏看来,那完全是上游的共工氏以邻为壑,有意为之。直到《管子·揆度》还说:“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可见偏见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啊!在现实中,这种偏见则常演变成两个氏族或部落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这是把洪灾的发生直接归咎于共工氏。故《文子·上义》曰:“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列子·汤问》和《淮南子·天文训》等书则将这场冲突与战争描绘成了“共工与颛顼争为帝”,而战争之惨烈,到了天塌地陷的地步。《淮南子·天文训》曰: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 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战争的结果当然是颛顼(祝融)氏胜出,而共工氏被诛被灭。被诛、被灭,并非是说共工氏这个氏族部落完全被消灭,“靡有孑遗”了,而是说这个氏族或部落被征服或镇压下去了——有的固然被杀死,有的则如尧“放共工于幽洲”(《尚书·尧典》作“幽洲”,《史记·五帝本纪》作“幽陵”,《庄子·在宥》作“幽都”),即被迁徙流放了,有的则被俘成了奴隶,等等。《史记·楚世家》说祝融氏(重黎)诛共工“而不尽”,所以帝喾“诛之”,换了吴回来做祝融氏的首领(“火正”)。重黎之所以“诛之而不尽”,又未必完全出乎仁心,而实际也可能是贪图共工氏女性的美色,把共工氏女性的遗腹子视为自己的“螟蛉之子”,这亦未可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后人或以祝融为远出于炎帝部落,而祝融又“生共工”,就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共工氏和颛顼(祝融)氏两个部落间冲突和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现,其现实的起因固然在于发源于共工氏居住地的洪水淹没了下游颛顼(祝融)氏部落的居住地,使他所居的“帝丘”“楚丘”之类水中高地,成了水中的孤岛,岌岌可危,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故而引起双方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或战争实际未必不是代表了“司空之官”的墨家文化基因与代表了“史官”的道家文化基因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共工氏出于炎帝之族,可以说是炎帝族的“司空之官”,掌握着“治水”“筑城”“作舟”等技术,对技术、技巧极为重视,而祝融的后代则实为史官。《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史记·楚世家》本以“重黎”为一人,这里则始以之为二人,继则曰“绍重黎后”,似乎又以“重黎”为一人了。实则重、黎当为二人,《国语·楚语下》即以为二人。古人已注意太史公书中的前后抵牾。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即于此有辩,此不赘述。这里特别指出的只是,“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而史官的文化基因是在颛顼(祝融)氏那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道家是一直强烈反对所谓“智巧”和技巧的,甚至提出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老子·第十九章)和“攦工倕之指”(《庄子·骈拇》)的主张,对源于“司空之官”的墨家文化也几乎采取一种近乎敌视的态度。因此,如果从文化的根源来考察共工氏与颛顼(祝融)氏的冲突或战争,是否可以说二者实代表了墨家文化基因和道家文化基因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呢?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尧(及其摄政者舜)对共工氏的镇压和官制的改造,也并非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从《世本》所谓“共鼓、货狄(伯益)作舟”来看,属于共工氏的共鼓曾和出身于颛顼氏的伯益竟能一起“作舟”,可见这两个氏族或部落之间已经完全和解了,关系已是十分和谐。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又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则共工氏之子还成了后人共同祭祀的土地之神。这一传说也应该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正是在尧(及其摄政者舜)平息了这场共工氏与颛顼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或战争之后,共工氏也就基本淡出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可能是这个氏族或部落彻底地衰落了,也可能是由于处于共、卫、淇、濮诸河水下游的颛顼(祝融)氏认识到洪水的发生与上游的共工氏无关,因而与之和平相处了,从此也就没有共工氏新的故事了,也可能是由于颛顼(祝融)氏部落的迁徙,故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总之,这个曾活跃于当时中原大地的强盛的共工氏部落从此似乎不见了。在传世文献中,继夏禹为司空之后,则是殷先公先王冥继任司空;商初,则“咎单为汤司空”——“咎单作《明居》”。
由舜同时任命伯禹为司空和垂为共工这一事实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两点:一是司空和共工都掌治水、筑城、“监百工”之类的职官,它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名称,应该出于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不同称呼,炎帝族称之为“共工”,黄帝族则称之为司空——周人出于黄帝族,故周官中有“司空”之名而不见“共工”之称;二是自从“共工”和“司空”的职掌范围发生变化之后,“共工”只管“百工”的“奇伎淫巧”之类(由此后“巧垂”“工倕”差不多取代了“共工”可知),而“司空”则主要是司“治水”或营建工程。到了周朝因为又设置黄帝族系的“司空”,而不再有“共工”之名,人们对司空要同时掌管“治水”、营建工程和“监百工”,似乎不再清楚,故而对失传的《周礼·冬官·司空》一篇的内容产生了猜测。
由“司空”和“共工”原是黄帝族和炎帝族对同一掌管“治水”、筑城和“监百工”等职事的官职的不同称呼,又可知在上古时代炎、黄之外其他氏族或部落中,对炎帝族的“共工”和黄帝族的“司空”之官,也一定会有自己特有的称呼。《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属于少皞氏之苗裔的郯子,答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时即曰: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
对于以上这一段话,古人的注疏有很多解读,但关于黄帝如何“为云师而云名”,炎帝如何“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如何“为水师而以水名”,这些说法仍不清楚。特别是共工氏,本为炎帝族的别支,却“以水纪”,与炎帝水火对立,更是不知所以。顾颉刚认为前人对这些说法都“没有给以正确的解释”,“少皞氏鸟名官”实际是上古传说时代少皞氏部落以鸟为图腾的表现,以鸟为图腾的古代的“原始氏族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氏族必然扩大而为胞族和部落,或部落和胞族分析而为若干氏族”。因此,郯子所说少皞氏所命“五鸟”“五鸠”“五雉”和“九扈”之官,说明少皞氏这个部落,对于定历、行政、手工业、农业生产等许多方面是由各个氏族分工,他们的条理多么清楚呀!尽管“这里所说的各个氏族,实际上是一些氏族贵族”。但顾氏之说似仍有不足。因为他并没有注意到,或至少没有提到郯子言“少皞氏鸟名官”,应始终是与鲁国所采用“周官”相比较而说的。少皞氏的“五鸟”之官,应相当于“周官”系统的司历之官,或类似于《周礼·春官·宗伯》中的冯相氏。少皞氏的“五鸠”之官,或相当殷周时期的“五官”,即《礼记·曲礼下》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少皞氏的“五雉”之官,相当于“周官”系统中“冬官(司空)当有下大夫四人”之数,但《周礼·考工记》之“工师”或“工官”为“监百工者”,不知少皞氏为何只有木、陶、金、皮、色“五工”(《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九扈”亦是少皞氏九种“鸟官”,杜预注说这是“以‘九扈’为九农之号,各随其宜以教民事”。可见少皞氏的农业生产极为发达,应该超过殷、周,因为典籍中没看到殷、周有那么多的农官。
从这段文字来看,少皞氏是有自己“司空之官”的,但它并不叫“司空”,也不叫“共工”,而名之曰“鸤鸠氏”。杜预注:“鸤鸠,鴶鵴也。鸤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也。”从杜预的说法来看,少皞氏之“鸤鸠氏”(“司空”)的职掌似与黄帝系尧舜命伯禹为司空相同,都是“平水土”;而其“监百工”、管理“奇技淫巧”之职的,则属于《尚书·尧典》中尧“流共工于幽洲”之后舜任命的新的“共工”——“垂”的职掌。这在少皞氏中为“五雉”之“鷷雉氏”所掌(详后)。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如郯子自己所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他对少皞氏时的详情已不是很清楚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向于郯子所叙少皞氏以“平水土”的“司空”和“五雉(即“垂,汝工”)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分司原炎帝族“共工”一职的职官设置为可信。因为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曾对齐景公说,齐地原本即是少皞氏的司寇之官“爽鸠氏”的居地: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
晏婴的话说明,少皞氏确有胞族爽鸠氏,且世居齐地。爽鸠氏在少皞氏职官系统中,是司寇之官。此事实应该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少皞氏的其他二三十个胞族都居住在齐鲁之地,且皆是少皞氏“鸟名官”的“鸟官”,也就不用怀疑了。
根据现代学者综合传世文献和出土青铜器铭文进行的研究来看,在上古传说时代的今河南东部、山东半岛、安徽东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居住了众多的鸟夷部落,如太皞氏、少皞氏、颛顼、徐夷、淮夷等,其中少皞氏居住于以鲁国曲阜为中心的齐鲁地区。《左传·定公四年》曰:“武王克商……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郯子所叙少皞氏“鸟名官”者,包含“凤鸟氏”“祝鸠氏”“鷷雉氏”“春扈氏”等共二三十个胞族,已说明了他们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爽鸠氏”是少皞部落“祝鸠氏”五胞族之一,世代皆居于齐,直到春秋之末仍然如此。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鸟名官”的东夷族由于不断的氏族或部落冲突,特别是由于西周的周公东征等对少皞氏遗族的不断镇压、打击和驱逐,到春秋战国时留下来的少皞氏遗族就很少了,只有郯、莒、费、颛臾、邾、夷等一些附庸小国还在原地居住。至于势力较大的商奄、蒲姑等,前者除一部分遗民留在齐国、鲁国,成了齐、鲁人的奴隶之外,另一部分则被驱赶到了极远的吴地——位于今江苏常州城南的淹城即其遗址;后者则先是被驱赶至取虑(下邳),然后再驱赶,“直到东海边的苏州市才停下”。
当然,除上面提到的郯、莒、费、颛臾、邾、夷等少皞氏遗族之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延续特别长久的氏族或部落。这就是洪迈《容斋续笔》卷七中所谓“考诸经传,可见者唯薛耳”的“薛国(鷷雉氏之族)”:因为“薛之祖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自此受封,历商及周末,始为宋偃王所灭,其享国千九百余年,传六十四代,三代诸侯莫之与比”。《左传·定公元年》载薛宰对宋仲几“滕、薛、郳,吾役也”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根据薛宰(薛国之宰)的说法,薛国应该是一个由古老氏族演变而来的小国,其最初的“皇祖”是“夏车正”奚仲,其后继者则有汤之左相仲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奚仲其人,二是奚仲其职。《左传》“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杜预注:“皇,大也。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奚仲既为“夏禹掌车服大夫”,那时代自然是非常早的,应紧接尧舜时期。《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杜预注:“庶姓,非周之同姓。”孔颖达疏:“《谱》云:‘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为薛侯,今鲁国薛县是也。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武王复以其胄为薛侯。齐桓霸诸侯,黜为伯,献公始与鲁盟。’小国无记,世不可知,亦不知为谁所灭。《地理志》云:‘鲁国薛县,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可见,薛地自奚仲开始,一直为奚仲族所居,故《尚书·仲虺之诰》伪《孔传》说:仲虺“为汤左相,奚仲之后”;“武王复以其胄为薛侯”。但奚仲为夏禹车正,并非即与夏氏同姓,孔颖达说奚仲为“任姓,黄帝之苗裔”,这是不对的——奚仲应该属东夷少皞氏之族。理由有二:一是周初周公、成王“践”东方之商奄、薄姑,始得封吕伋于齐、伯禽于鲁,武王不可能“以其胄为薛侯”;二是经、传说某国某姓,常有将某国之统治者之姓氏与被统治人民之姓氏相混淆的情况。如齐、鲁之统治阶层伯禽族和吕伋族固然为姬姓和姜姓,但其被统治族群则主要为少皞氏之商奄、薄姑的遗民,简单称之为姬姓、姜姓或少皞氏之某姓,都是不对的。《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氏鸟名官”,杜预注曰:“少皞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孔颖达疏曰:“《帝系》云黄帝生玄嚣也……故《世本》及《春秋纬》皆言青阳即是少皞,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黄帝之子十四人,为十二姓,其十二有姬有已,青阳既为姬姓,已姓非青阳之后……事远书亡,不可委悉。”故孔颖达认为夏初以上的奚仲族即是“任姓,黄帝之苗裔”,应该是不对的。实际上,奚仲与《国语·郑语》国“昆吾为夏伯”的昆吾以及莒国一样,应该都是出自少皞氏。《世本·氏姓篇》说:“昆吾,己姓国,出自少昊(皞)。”又说:“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此是言十国皆任姓也。但这里的“舒”,即“群舒”,即是“徐夷”,皆嬴姓也。不过,《左传·襄公四年》云“寒浞处浇于过”,杜预注:“过,……国,东莱掖县有过乡。”《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子鱼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也是认为这一带的任姓国属于东夷氏族的,故《左传》和杜注都说“薛,庶姓也”,而“庶姓,非周之同姓”——显然不同于周人属“黄帝之苗裔”也。
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表明,居住于今山东滕州的薛国,的确属于上古东夷少皞(昊)氏之族。因为从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来看,“作为东夷古国的薛、莒等和由东方至西方的嬴秦”之殉人墓,“在殉人方式上”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充分“揭示出春秋中晚期鲁东南地区薛、莒等东夷古国殉人墓与嬴秦殉人墓在殉埋方式上的相似性应与二者在族属及文化渊源方面的共性相一致”。因而薛人与由东方迁至西方的嬴姓秦人一样,都是属于东夷集团的。
奚仲族应该属少皞氏之胞族,则所谓奚仲“为夏车正”或“为夏禹掌车服大夫”,就是少皞氏“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的“五雉”或“五工正”之一。杜预注曰:“五雉,雉有五种,西方曰鷷雉,东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翚雉。”孔颖达疏:“《释鸟》‘雉之属十有四’:‘其说四方之雉:西方曰鷷,东方曰鶅,南方曰翟,北方曰鵗。’舍人曰:‘释四方之雉名也,杜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先儒相传为说,杜从之也。”又引贾逵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东方曰鶅雉,抟埴之工也;南方曰翚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翚雉,设五色之工也。”《说文解字·车部》曰:“车,舆轮之总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段玉裁注:“浑言之,则舆轮之总名;析言之,则惟舆偁车,以人所居也。故《考工记》曰:‘舆人为车’。”又说:“《左传》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杜云:‘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然则非奚仲始造车也。《明堂位》曰:‘鉤车,夏后氏之路也。’……盖奚仲时车制始备,合乎句股曲直之法。《古史考》云:‘少昊时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强为之说耳。”若依共工氏之“共鼓”“垂”或“巧垂”皆有“作舟”之事而言,奚仲“作车”似可以理解为奚仲这一氏族或部落“作车”。奚仲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在夏禹以奚仲“掌车服大夫”之前,该氏族或部落就已世居此职,故谯周《古史考》才有“少昊(皞)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之说。
因此,奚仲为少皞氏“五雉”之一的“攻木之正”中的分支——“车正”,也是可以肯定的。这除了有谯周《古史考》之言为证之外,另一个根据是奚仲从根源上说应属于少皞氏之族——而且属于“攻木之工”的“车正”之官,这既与《周官·考工记》中的“车人”“轮人”“舆人”之类相应,更与“共工”(共鼓、垂)“作舟”相应,满足了少皞氏官制以司空(鸤鸠)与“共工”分司“平水土”“营城郭”与“监百工”之职官制度。当然,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难以肯定这个以司空(鸤鸠)与“五工正”(“五雉”)分掌“平水土”“营城郭”与“监百工”之职的官制设立,到底是哪个氏族或部落发明的。但由于炎、黄部落原是西部东迁而来的,西部地区比较干旱,至少“平水土”的现实要求没有那么迫切,故这一职官设置的首创权或许可归于东夷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吧。
另外,如果从本文前面提出的“墨家者流,盖出于司空之官”的观点来看,少皞氏也的确应设置有“平水土”“营城郭”的“司空”(鸤鸠)和“监百工”的“五工正”(“五雉”)这一“鸟名官”的职官系统,这样才与墨家首先出现于夏车正奚仲的故居地——薛国——相契合。
“五雉”中的“攻木之工”的职掌范围,因文献缺乏,固难论其详,但在远古时代,此职无非就是负责木材加工和制造的工作,主要如建造房屋的木构架、陆行所依靠的车和水行所借助的舟船等;因此,“作舟”的共工和“作车”的奚仲,无疑都应该是其属官。如果从氏族分属来看,则奚仲族应该属于“五雉”部落中“鷷雉”胞族的胞族或子部落,而且,这个以奚仲为皇祖的氏族或部落,在春秋战国时应该仍然生活在薛国这块土地上。这样,在当时薛国的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墨翟、公输班(鲁班)和墨家思想流派,也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关于墨翟的籍贯,《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所附记的“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并没有给出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历来学者基本皆在墨子为“宋人”或“鲁人”上猜测。孙诒让、张纯一等皆以《墨子》本书中《贵义》《鲁问》《非攻》中墨子出入鲁及与鲁人问答,以为足为“墨子为鲁人之塙证”。但经过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墨子应该属于东夷人,他的姓氏可能源于孤竹之君伯夷的姓“墨胎氏”或“墨台氏”,即《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所云:“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墨翟著书号《墨子》。”而且,“目夷入周后,即并为小邾娄国”;“目夷的地址”,“就在今滕县境内”,“滕东南有木石,即墨骀”。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想,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墨子实乃“周官”之“匠人”中的“车正”。《墨子·鲁问》载墨子曾对“削竹木以为鹊,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的公输子说:“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亦载墨子评论自己制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以为尚“不如为车輗之巧也”。可见,墨子实是一位精于“作车”的工匠,在那个“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不可使杂处”和“工之子常为工”(《管子·小匡》)的时代,墨子必是出于一个世代相传的“车工”家族——而这个家族应该即是世代相承此业的奚仲之族。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墨子同时代的差不多相同的地方,居然还产生了一位被尊为木匠始祖的能工巧匠,那就是上文所说的“削竹木以为鹊,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的“公输子”(即“公输班”“公输般”“公输盘”等)。这样的巧合,一方面固然说明了在我国的上古时代,士、农、工、商皆是“群萃而州处”的——能工巧匠往往同处于一乡;另一方面也就不难见出墨子、公输班这批能工巧匠的出现,与薛国这个自上古传说时代以来即为奚仲之族所居之地的关系。似乎上古少皞氏“五雉”部落中的“鷷雉氏”部落应该一直生活在薛国这块土地上,墨子、公输班则应该都是少皞氏中“鷷雉氏”部落的后人——墨子应该直接就是“夏车正”奚仲之苗裔,而公输班则应该是“五雉”(“五工正”)中的“鷷雉氏”(“木正”)后裔。因为自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鷷鸠氏所居的薛国,其地在汉为鲁国薛县,故以墨子籍贯为鲁人者,便想当然地把墨翟当成“鲁人”了;而公输班其人,则被径号为“鲁班”。但实际上,直到战国后期薛国才最终被齐所吞并,墨翟、公输班皆薛国人也。《墨子·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自古以来历代不同版本皆有墨子“起于鲁”或“起于齐”之异,但因墨子时薛国尚存,故当以“墨子起于薛,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为是。
在中国上古传说时代各氏族或部落的工官中,“车正”或本当属于“木正”的属官,故可以说奚仲一族本应该只是鷷雉氏的胞族,但从今本《墨子》书来看,墨子是既精于“作车”,充分继承了“车正”之特长,而又熟悉“百工之所从事”者,故《墨子》书中多以“百工之所从事”为譬(如《法仪》《辞过》《节用上》《节用中》《天志中》《非儒下》及《城守》十一篇等)。我想,或许当初的奚仲虽只是“鷷雉氏”部落中的一员(“车正”),但却是同时兼任着“五雉”之长或“百工之长”的(《淮南子·齐俗训》曰:“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奚仲为工。”正以奚仲担任的是尧的“工官”)。这就如共工氏的垂,他既是“作舟”的“舟人”,却又是“百工之长”的“共工”,但鷷雉氏(“攻木之工”)的首领却因其职掌范围所限,只是专精于“木工”——公输班或许就是这一部落及其首领之苗裔,故其特巧于“攻木”之术,而为后世木匠的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