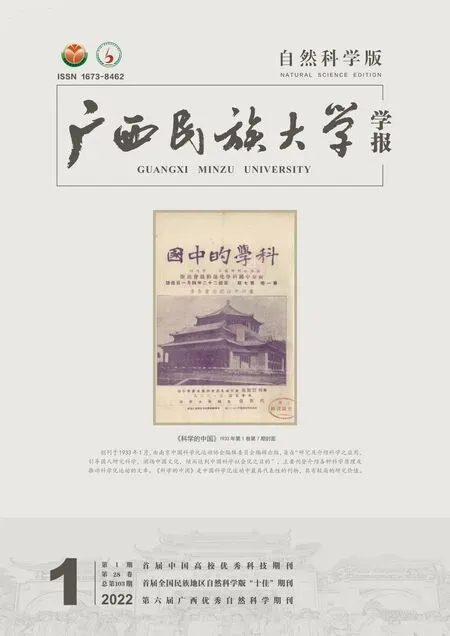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学大众》运营特点研究*
2022-05-18聂馥玲
张 航,聂馥玲
(1.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2.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科学大众》①以下简称《科大》,即该刊在民国时期通用的简称。创刊于1937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1946年再次复刊,刊物以“科学大众化,大众科学化”为办刊宗旨,启发民心,传递新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移交商务印书馆,1954年又转交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全国同类刊物中仅此一家。《科大》曾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赞许。郭沫若曾为刊物题写刊名,钱学森、严济慈、李四光、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都先后为该刊撰稿。刊物中多篇文章入选人教版初高中语文(必修)课本。[1]因此,《科大》是见证中国科学传播历史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目前国内关于该刊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董豆豆等归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大》的办刊宗旨与内容特色;王新生等对如何打造期刊科普特色进行了论述,此外还有学者就期刊在新形势下如何进行品牌创新和建构数字化运营机制等进行了探讨。[2-5]但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大》的发展模式上,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发展史少有论述,导致研究成果的失衡。因此,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大》的运营方式加以研究。
《科大》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背景下创刊的,当时提倡将世界科学应用和原理传播至国内,“以500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化。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通俗科技期刊应运而生。当时中国的此类期刊主要由各高校科研团体及学术性科学社团创办,[6]但《科大》却有其特殊性,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研究《科大》的运营特点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方式、运营理念有借鉴作用。
1 《科大》的资金来源
期刊的运营,资金来源是一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对于《科大》这样的民间期刊而言,在百业待兴的时局下,如何回笼资金保证刊物的常规运营,同时又能兼顾刊物的质量和广泛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科大》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广告收入和捐款所得,而社会捐助,主要来源于“一社”社友的捐助。
1.1 “一社”社友的捐赠和赞助
1935年3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学生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俞炳元、沈嘉英5人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怀着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在上海创办学生团体“一社”,想要“把同学们长久地联系在一起,在校能相互砥砺,出校能携手做事”。[7]该社又名“建设事业励进社”,表明其工作中心为励行建设。该社一度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当时最有凝聚力的学生社团组织之一。社团的宗旨为“以集团之力量,谋实业之发展、民生之改善”,由沈家桢担任社长,国内设有重庆、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台湾地区等分社,国外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分社。一社自办实业,开设了人人企业公司、宏光染料厂等,沈家桢是人人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科大》于1946年复刊后的发行人袁行健(袁明恒)先生即为上海宏兴染料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社”同时出版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各类书刊,设立大众出版公司(后改为民本出版公司),《科大》即为公司主要出版物之一,社团人数最多时达到320人。[8]发展的社友均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其中以留学生居多,集合众多科学家、工程师、实业家等,在当时有“青年专家团”之称,[9]例如:王安电脑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安,水利专家张光斗,工程院院士吴祖凯,唐山交通大学前校长唐振绪,国际航运巨子沈家桢、陈启元,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孙璿等,这些日后在科技界、企业界、教育界、政界卓有成就的人物都曾是一社社员[7]。可见“一社”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
1937年创办《科大》之初,为筹备资金,社员们合作翻译了一部英文科技书籍,送交出版公司后赚取了几百元稿费,并以此为基金,社员义务编辑、写稿,终于办起了第一期《科大》。1946年刊物复刊后,经济拮据,又是在“一社”社员创办的人人企业公司的支持下,在公司办公楼内腾出两间房子,划拨了一台电话,成立了一家小型的出版社——中国大众出版公司,使得《科大》的出版步入了正轨。[10]
由于“一社”社友多为留学生,在所属专业领域均颇有建树,且部分在国外定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这部分社员常为该社所办的刊物发动捐款以维持期刊的顺利出版,如由国外社友秦宝通发起、魏重庆主持的捐款活动,所捐额度达2000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大概可以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维持出版社6个月的运营。[11]
除直接捐款外,“一社”还特别设立基金会,主要由美国社友和美国进步人士推动成立,名为Chin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Inc。基金会的资金直接用于推动“一社”的常规运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之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便被用于支持“一社”旗下民本出版公司出版的几个科技刊物的运营。[12]
此外,“一社”专门拨出部分经费作为稿费,鼓励社友积极发稿:“为发扬出版事业,鼓励社友写作,所有民本出版社书刊上社友之著作,均由本社负担稿费,惟版权为社所有。”[13]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学大众》稳定的稿源。
1.2 广告与发行收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科学和工业均非常脆弱,《科大》人曾明确指出,“我们不想靠这个刊物赚钱”,认为办刊物“譬如在播种,它一定会有别的收获,但绝不是金钱”。[14]在纸张、排印等不断涨价的情况下,《科大》尽量保持不涨价,或少涨价,使其售价在全国同类期刊中保持较低水平。但当时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刊物的发行收入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运营,《科大》不得不加大广告发行力度。
当时“在中国办刊物是没有不亏本的”。[15]但《科大》由于广告经营意识强,方法多,使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独树一帜。在广告投放量方面,据记载:“创刊号广告占十三面又二分之一,打破全国科学刊物广告纪录。”[16]
在广告经营方面,也发挥了各渠道的积极作用。首先,《科大》广开门路,通过“一社”社友、热心读者等各种渠道为其招揽广告。“一社”曾为刊物专门在台湾地区、南京、天津、青岛、重庆、成都各地委派广告订户征集者和征稿人。又有专人为刊物招揽国外商品广告,如加拿大分社社友顾慈祥先生曾发函告知为刊物征得加拿大Renown面粉厂广告投放的消息:“该厂面粉广告‘利朗牌面粉’六期全页交于科大……加区另在进行一二出广告,一有成议,当再函达。”[17]类似地,《科大》为许多国外企业刊登了广告,如图1。
此外,《科大》以优惠的广告费用和优质的广告服务吸引商家:“本刊广告现在尚感不敷,希望诸先生尽量介绍,刊登长期,酌给折扣,并可代为设计。广告订单,承索即寄。”[18]表1为《科大》刊登全年广告所需费用。在《科大》封底外面刊登一年的广告定价是90元,封面内面刊登全页、半页、三分之一页及四分之一页一年广告费用分别为71元、40元、25元和20元。在目录页和正文页刊登一年广告,全页需43元,半页需24元,三分之一页需18元,四分之一页需14元。这个广告收费在当时是比较低的,以在目录页及正文页占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为例,1937年《科大》全年广告价为14元,当时该刊全年刊物订阅价为1.2元,刊登广告的费用是订阅价格的11.66倍。对比同时期的其他刊物,《新青年》全年四分之一版面广告费用为100元,全年订阅价为2元,广告价是订阅价的50倍。[19]《农艺新报》全年四分之一版面广告费用为150元,全年订阅价为5角,广告价是订阅价的300倍。[20]对比可见,《科大》广告价格较为低廉。

表1 《科大》广告收费例表[21]单位:元
《科大》在广告投放方面的许多努力颇有回报,刊物刊登的广告数量一直保持稳定,而且认识到了广告对《科大》发展的意义:“《科大》稍优于别人的唯有各位友好支持的广告收入……在广告上,敢恳请各位友好尽量相助,目前在销路、销数、售价上都当有差可称道的地方,为广告而登广告并非不值得,为赞助而刊登广告敢说亦不是全无意义。”[22]广告收入成了支持刊物按时出版、保证刊物质量和水准的重要因素之一。
2 期刊的发行主体
发行是传播期刊的一个重要渠道,《科大》的发行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时期。
2.1 生活书店
《科大》最初创刊时,采取的是独立编辑、联络专门出版机构代订代售的模式。当时专门为其做代订代售业务的机构为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由邹韬奋、徐伯昕等创办,前身是《生活》周刊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书业界备受瞩目。1937年《科大》创刊之际,生活书店的分店已达50余处,出书400多种,所属期刊10余种,拥有员工近100人。
生活书店出版作风大胆,经营特色别具一格:“或者为救亡而呐喊,或者为启蒙而低吟,或者为民主而搏击,无不关切时代的脉搏与痛痒。”[23]因其勇于抨击时弊的大胆作风,曾以“言论反动、思想偏激、诽谤党国”的罪名屡遭禁止,后因其刊发左翼文化,主张抗日救亡,被国民党政府压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阵营。
《科大》创刊后,当时生活书店的邮购科主任张锡荣(署名张希永)先生,是刊物一位负责人的同乡兼世交,在他的介绍下,征得书店主持人徐伯昕先生的同意后,生活书店接受了杂志的代订代售业务。《科大》成了该书店发行的第一种科学刊物。王天一先生在一篇回忆文中曾提到:“由这件事可见《科学大众》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向党靠拢。”[24]
2.2 民本出版社
1946年《科大》复刊后,改变了发行模式,在“一社”的支持下,专门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中国大众出版公司,后改名为民本出版公司、民本出版社,主要出版与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相关的各种书刊,特别是以通俗科学读物为主,发行适合一般民众阅读的理、工、农、医各科杂志及单行本。主要出版的杂志为《科大》《大众医学》《大众农业》《工程书报》等,虽然内容各有偏重,但体例大致相同。此外也出版各种科学字典、辞书和教科书等。文字风格均采用白话,格式均为横排,在当时很受读者认可和欢迎。[25]
“民本的目标很单纯,它只想在科学知识的普及这方面尽一点使命”,而且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教育别人的责任”。[11]另外在经营上,“尽量地使无一字浪费,无一纸空白”。[22]民本出版社力图让《科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一点贡献。
此外,在自办出版公司刊行的模式下,刊物的编辑和出版发行成为一体,既可以减轻经济压力,也利于相互团结、提升刊物的品牌效应和扩大影响力。民本出版公司内部分工明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今中国科技期刊运营中着力倡导的“编营分离”体制。[26]以《科大》为例,主编王天一与“《科学大众》月刊社”的编辑团队保证刊物的内容品质,发行人袁行健则主管期刊的出版发行事宜,推动刊物的顺利流通,内容和经营两者分离,各司其职,能够较好地确保刊物的长期稳定发展。
3 期刊的发行方式:征订为主,零售、赠阅为辅
对于期刊而言,订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可以让期刊提前获得资金,使运营资金更加充足,另一方面也能让期刊更好地了解读者的个人信息和阅读兴趣,实现与读者之间的优质互动,从而获得稳定的读者群体。[27]民本出版公司成立后,在刊物的发行上主要采取征订为主,辅以零售和赠阅的方式,并制定了相应的发行策略。
在征订方面,尝试以各种方式吸引读者成为长期订户,如在创刊纪念活动中发起“征求优先订户”活动(图2):“征求基本订户五千户,优先订户二千户,业已足额,兹再继续征求基本订户五千户,优先订户二千户。”[28]可见,刊物在当时已开始采用现被称作“饥饿营销”的方式,规定能够享受优惠的订户数量,订完即止,以此引导读者从速订阅。另外还承诺这部分读者可以获得较佳纸张、不会另售的刊物。这些举措给订户以优越感,可起到一定的促销作用。
此外,刊物在一则长期刊载的“谈《科大》售价,告《科大》读者”广告中,特别谈到订阅刊物的好处:可以提前收到刊物;对比零售读者将随时面对涨价的风险,订阅用户将享受长期稳定的优惠;可以减除中间利润,内地读者能够避免因运输价格导致的刊物价格过高;在篇幅增加后,订户也可以不必担心涨价。关于订户担心的诸如中途停刊、邮寄遗失等问题也均有应对之法,免除了读者的担忧。[29]
对于期刊来说,其价格已经固定,如果使用降价策略来促销,就会使得期刊企业的品牌形象受到一定损害。所以在期刊之外另附赠品是期刊企业可以一试的明智促销手法,《科大》正是如此,如:“本公司新编‘科学新知识手册’一册……一百余页,十万余言……凡订阅本刊全年者概赠一册。”[30]类似的以附赠赠品促销的方式,在吸引读者订阅的同时也宣传了其他读物,实现了互助共赢。
除订阅外,《科大》也以赠阅的方式辅助销售:“为便于介绍起见,特提出单本万册,供读者馈赠友好试阅,由本刊书就赠者姓名,代为寄达各受赠人。”每册书后也附试阅通知单供读者填写。同时承诺读者每介绍十份订阅,回赠刊物一份,以此类推。刊物还印刷了精美的宣传印刷品,读者去函即可获得,可用以赠送亲友同学,宣传刊物。[31]通过上述赠阅方式,起到了辅助推广刊物的作用。
4 期刊的发行策略
4.1 以“中国科学期刊协会”为重要传播媒介
因当时的社会状况不稳,像《科大》这种一般的民间科技刊物更是举步维艰,为继续刊物的出版,为民众带去科学,1947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科学期刊协会。这是一个集合全国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各种定期刊物的组织,组织各刊物相互合作,“以谋求编辑与发行上的联系与推进,希望对于中国的新科学有一点贡献,对于科学的新中国尽一点力量”。协会期刊均具备两个共同特性:“乃是服务的,而绝非牟利的;乃是启发的,而不仅是报道的。”[32]通过成立这一民间组织,希望能够让海内外读者理解这些刊物创办的不易并予以支持,同时也希望能借此引起政府和各方的重视,在发行和编辑上给予相对便利和协助。该协会成立时主要参与刊物即有《科学大众》《科学世界》《科学画报》《科学》《化学世界》等通俗科学普及读物,也有《工程界》《中华医药杂志》《化学工业》《水产月刊》《现代铁路》《纺织染工程》等专业科技学术期刊,创办初期共有协会成员刊物18种,后期规模持续扩充,至1947年12月,成员刊物增至20种,至1948年12月,共25种刊物加入此协会。
协会成员刊物中已有部分初见规模且影响较大的杂志,如《科学》《科学画报》等,这样一个由诸多知名期刊参与构建的科技传播团体,可以对当时知名度不足的刊物起到提挈和促进的作用,对当时复刊不久的《科学大众》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较大作用。
协会成立后,成员刊物共同刊发“中国科学期刊协会联合广告”,进行集体宣传。这样的互助共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前“集群化”“集约化”的管理理念,即集体共同管理模式,加强同类期刊的联合,促进集群建设。通过整合同类刊物,安排共同的协会活动,制作协会联合广告,最终以节约、高效、互相扶持为价值取向,使得协会各成员刊物均具备可持续竞争的优势。同时,协会的成立也对当时的民间科技期刊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鼓励各刊物积极向协会靠拢,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提升刊物质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科技期刊业的发展。
4.2 “一社”积极对刊物进行宣传和推广
《科大》除了加入“中国科学期刊协会”以促进宣传和提升知名度外,“一社”作为《科大》的母体和坚实后盾,也对《科大》的推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该社每月出版的《社报》,长期大量刊载《科大》的宣传广告及发展近况(图3),《社报》在该社社友中免费发行,又因该社分社遍布全国,这一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刊物提高知名度。
其次,“一社”还为《科大》在国外的宣传工作积极奔走。如《社报》72期中就曾刊载:“自上月起,每期寄三百本至美国区分社推销,每册售美金二角至二角五分,希望美加两区社友协助销售。美区分社为《科大》之发展,特组委员会……盼各地分社同样组织。”“加区分社对《科大》亦极关心,该社书记李善近社友曾寄来可供发表之资料,最近正接洽加拿大厂商刊登广告”。[33]此外,“一社”的主要负责人也经常出国为《科大》宣传。
再次,“一社”鼓励社友协助推销《科大》,以促成刊物的广泛传播。还特别评选出“推销英雄”公布于《社报》,并为帮助推销刊物的社友提供折扣价和赠送刊物的优惠条件(图4)。
最后,“一社”还为《科大》积极建构发行网。如《社报》中曾提出:“诸先生分别服务各地,如承介绍当地书店有自己的发行网,直接发书,收效必大。”[18]此外,“一社”让社友免费试阅部分刊物,期待社友在读完后予以推荐和批评,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4.3 在知名报刊上发布广告促进刊物传播
《科大》在高知名度的报纸、杂志等媒体上进行宣传,广开门路以促进发行。如《新华日报》《益世报》《大公报》《申报》《上海文化》等报刊均曾为《科大》刊登介绍和广告。[33]
以《大公报》为例。《大公报》在民国时期具有相当的声望,是当时国内外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也是舆论界的重镇,被联合国推选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该报曾出现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20万份。《科大》曾在其上海、重庆、香港、天津四个版上刊登书报介绍、出版信息、目录等各类信息(图5),对于提升刊物的知名度,促进发行起到了一定作用。
4.4 向各专门学会谋求支持
《科大》作为民间刊物,又无专业科学社团做后盾,在出版发行上并不占有优势,但刊物的编辑团队努力克服困难,一直积极向各专门学会谋求支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科大》邀请了当时国家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地质等专门学会的知名学者担任各专栏的主编,通过这种方式,刊物逐步获得了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同时在与各专门学会的接洽过程中,也使得刊物吸引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为其供稿,如竺可桢、曾昭伦、严济慈、贾兰坡等。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加盟能够提升刊物的专业水平,对刊物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也体现了当时科学界对刊物的认可。
在上述运营特点之下的《科大》,在内容方面也十分注重文章质量和栏目设置,加上刊物收获了兼顾专业背景和科学普及能力的作者群体,如此共同努力才促成了刊物的成功。
《科大》创刊后不久,因取材新颖,印刷精良,销量曾一度超过当时国内唯一的老牌科普杂志——《科学画报》。[34]王天一在刊物复刊三个月后撰文:“三个月来,得到一社全体社友的支持和帮助,销行的数字已达一万三千份,行销的范围到达东北、西北、华北、华南、华中各个角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方,订户数目仅仅上海已逾一千。”[35]在刊物复刊八个月后:“新生的科大,而能于八个月内达到一个连许多办书店的人都绝不相信的发行数字一万六千份,也全是这许多社友努力的收获。”“科大现在的销量,在全国的科学刊物中,也许还是全国的各种刊物,已经是站到第二位。别的刊物办了十多年,科大只八个月”。
《科大》也获得了较好的读者反馈,如刊物的“读者意见表”刊登后,据《科大》编辑部统计,仅三个多月先后已收到读者意见表七百余份。[36]
此外,在《电世界》举行的读者调查中,曾问读者除该刊外尚读何种刊物,“答案最多者为《科学画报》第一,《科学大众》第二。《科大》现在之地位,此当时一个极客观的证明”[33]。“一位国民小学的教师来信说他是省下买袜子钱来定《科大》的,一位士兵说他每月的开饷只一万元,定不起只好按期另买,杭州某个寺里有个僧人也来订一份,宁波和无锡有两个读者都是自己订了一份以后,再介绍十几个同学来订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37]通过此类事例足见《科大》在当时能够被大多读者认可,且口碑良好。
5 结语
《科大》作为一份民间期刊,自主经营,多方努力,力争获取社会各方面资源,使得期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其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方式对我们今天的科技期刊不无借鉴意义。笔者用中国科学期刊协会成立时的一段宣言来结束文章,以期能够真实体现当时如《科大》一般的科技期刊的生存状态及创办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这些刊物,都是民间的刊物,一向都是几个从事科学工作的团体或个人,有鉴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和科学建国的急需,从而就本身的力量,在这一条道路上,尽一点绵薄。这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我们各个刊物,站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应付,勉力撑持,虽至今天仍未尝稍稍苏息,这一段经历虽然极其艰苦,却未尝稍稍动摇我们的信念:中国终必要好好地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我们的科学研究与科学建设终必有发扬光大的一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