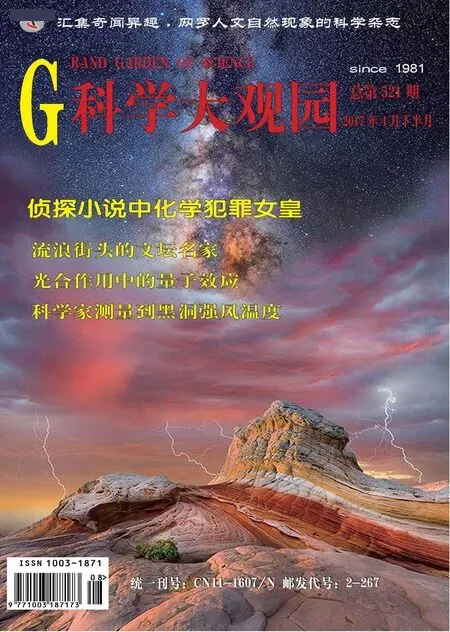当人类生命被设计
2022-05-18王立铭

日前,有消息人士称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已于近期出狱。
这条消息让我们回忆起2018年年底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在至少7对艾滋病夫妇的受精卵中修改了一个名为CCR5的基因,而且一对夫妇的双胞胎女儿已经出生。
2019年12月,“基因编辑婴儿”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两年后,2021年7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专家委员会发布《人类基因组编辑管治框架》和《人类基因组编辑建议》,首次提出了将人类基因组编辑作为公共卫生工具的全球建议,并论证了其安全性、有效性和伦理。
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浙江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王立铭就曾做出过详细解读。这一事件让我们思考,狂飙突进的生命科学研究究竟有无伦理和监管的边界。
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疑问:关于每个人类个体、关于人类这个物种、关于人类的未来,操起生物学这把利器,我们究竟能做什么,我们又不能做什么?正如王立铭在他的作品《巡山报告·基因编辑婴儿》一书中所说的:对于古老又年轻的生命科学来说,我们身处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至今,我们对生命现象的理解,空白要遠远多过已知。
以下内容节选自《巡山报告·基因编辑婴儿》,较原文有删节修改。

艾滋病,一种世界性的传染病。19世纪80年代被正式发现以来,艾滋病已经杀死了接近4000万人。这种疾病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入侵人体免疫细胞、破坏人体免疫功能所引起。如果没有接受有效治疗,缺乏免疫系统保护的艾滋病患者会被各种各样的感染所折磨,往往会在一到两年内死于结核病、严重的细菌感染、卡波西肉瘤等疾病。
截至目前,人类仍然没有发明出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办法。尽管华人科学家何大一发明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法(俗称的“鸡尾酒疗法”)已经能够大大抑制病毒的复制和传播,让患者长期生存,甚至寿命都和健康人相差无几,但是鸡尾酒疗法费用高昂,副作用明显,需要有经验的医生不断调整用药方案。
显然,这是一种只有在公共卫生系统高效运转的富裕国家才能普及的方案。而众所周知,艾滋病起源于非洲,至今仍有70%的患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在那里,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想要普及鸡尾酒疗法几乎就是痴人说梦。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那些国家,艾滋病的传播已经构成了不折不扣的公共卫生灾难。
人类在翘首期待着更好的艾滋病解决方案——更便宜的药物,更广泛的疾病知识普及,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卫生护理服务。还有,能从根子上彻底阻断艾滋病传播的有效疫苗。过去30年,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大药厂反复试验过各种各样的艾滋病疫苗,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2018年11月26日,时任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生物学家贺建奎,向全世界宣布,他找到了在人体基因上动手术,让人从出生起就对艾滋病免疫的新方法。这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专业,并在美国莱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才生,很明显是有备而来。一天之后,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香港举行,全世界超过500位这个领域的专家将云集香港,讨论围绕基因编辑——这项能够在人体基因上动刀子的超级技术的各种热点问题,包括科学细节、政策法规、伦理争议。选择在此时公布这个爆炸性消息,贺建奎显然意在这个生命科学热点领域里搅动风云。
在11月26日当天,贺建奎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布了制作精良的视频,向全世界公众详细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在视频当中,操着流利英语的贺建奎侃侃而谈,沉痛地表达对艾滋病患者的悲悯。他说,艾滋病患者的子女很可能会从父母那里继承可怕的病毒,因此会终身生活在社会的歧视当中。即便侥幸没有得病,他们也会终身担忧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他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救赎之道。他的实验室利用一种名叫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在至少7对艾滋病夫妇的受精卵中,修改了一个名为CCR5的特定基因。其中一对夫妇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已经出生了。这两个被贺建奎称为“露露”和“娜娜”的女孩体内,CCR5基因已经被永久性破坏。
面对艾滋病的巨大威胁,如果修改CCR5基因就可以让人先天预防艾滋病,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在基因层面,釜底抽薪式地预防艾滋病,岂不是比什么药物都来得更方便、更有效?这难道不是艾滋病治疗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发现,一次科学范式的大转移?
艾滋病病毒之所以能够那么精确地瞄准某一类特殊的人体免疫细胞,是因为这些细胞的表面,有两个天然存在的蛋白质分子被HIV 偷偷利用,作为它们入侵免疫细胞的识别标志。
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先回归到科学本身来讨论。首先得说明,用修改CCR5基因的方法来对抗艾滋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意。我们知道,当艾滋病病毒入侵人体后,它们能够精确地识别人体中的某一类免疫细胞,入侵并且杀死这些细胞,从而让患者丧失免疫功能,最终可能会死于严重的感染。艾滋病病毒之所以能够那么精确地瞄准某一类特殊的人体免疫细胞,是因为这些细胞的表面,有两个天然存在的蛋白质分子被HIV偷偷利用,作为它们入侵免疫细胞的识别标志。
通俗地说,一个分子负责指路,一个分子负责开门。这两个蛋白质分子,分别由两个名为CD4和CCR5的基因生产(在某些场合,CCR5这个“开门”分子可以被另一个名叫CXCR4的“开门”分子顶替,帮助艾滋病病毒进入免疫细胞)。CD4负责指路,CCR5负责开门。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人体当中天生就没有这个CD4或者CCR5基因,那是不是人就能天然对艾滋病病毒免疫呢?
还真是这样,而且人类世界已提供了这个猜想的天然证明。具体来说,有大约1%的北欧后裔体内,CCR5基因的两份拷贝还真的就出現了天然的基因缺陷(名为CCR5-Δ32基因突变)。因此,这些人就真的不太需要担心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天生的CCR5基因突变体,虽然确实也有一些健康风险,比如说得了流感之后反应更加剧烈,但是这些人的总体健康情况还是不错的。人类世界存在的这个天然的艾滋病防御武器,给很多医生和科学家提供了对抗艾滋病的思路。这包括曾经震动整个人类世界的“柏林病人”。1995年,在德国留学和工作的美国人蒂莫西·雷·布朗患上了艾滋病。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后,他体内的艾滋病病毒被有效地控制,他也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但是祸不单行,到了2006年,布朗又被一种恶性血癌——急性髓性白血病——击中。为了治疗他的血癌,德国医生格勒·许特尔决定使用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方法,为布朗更换一套全新的、健康的造血系统。这种常规用于治疗血癌的技术,可能读者们并不陌生。只不过这一次,在寻找配型合适的骨髓捐献者的过程中,布朗有着惊人的好运气:在骨髓库里找到了267个配型合适的捐献者!要知道,大部分苦苦等待骨髓移植的血癌患者,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配型。
之前那些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CCR5 基因缺陷来治疗艾滋病的办法,收益大于风险,最坏风险可控,所以我们支持对他们进行研究。但是这两条,都不适用于贺建奎的研究。
这个难得的奢侈让许特尔医生决定采取一个稍微有所不同的策略。他想要看看这么多合适的捐献者中,是不是有人碰巧携带了CCR5-Δ32基因突变。如果能够找到并移植这样的骨髓,许特尔医生猜测,也许可以同时治愈布朗的血癌和艾滋病。运气再次眷顾布朗,医生们果然找到了一位配型合适、同时携带CCR5基因突变的捐献者。在两轮骨髓移植之后,奇迹果然发生了——布朗的白血病被全新的骨髓治好,而他的艾滋病,也同时被CCR5基因缺陷治好了。至此,布朗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艾滋病痊愈的幸运儿。而“柏林病人”这个响亮的绰号,也注定会永载人类医学史。
天然情况如此,人工操作能不能模拟这种效果呢?毕竟,对于全世界那么多艾滋病患者来说,为他们每人寻找一份配型合适、也携带CCR5基因突变的骨髓,再安全顺利地完成移植手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看起来确实也有希望。2014年,美国圣加蒙公司还发布了一项临床研究的结果。他们提取出艾滋病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人为破坏这些细胞内的CCR5基因,再把这些细胞输回患者体内。他们确实也发现,如此操作之后,这些患者体内的病毒水平明显降低了,并且维持了几周。也就是说,破坏CCR5基因,确实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相对比较安全的治疗艾滋病的新思路。
但是,顺着这个逻辑稍微多想一点,你会意识到这项技术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那就是:从治疗到预防。既然HIV病毒的入侵需要CCR5基因,既然天生存在CCR5基因缺陷的人天生对艾滋病免疫,总体而言也还活得挺健康,那如果在没出生的孩子身上提前把CCR5基因破坏掉,不就能让自己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不需要担心艾滋病这种疾病了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思路和打疫苗差不多,都是通过某些技术手段,让人在没有接触某些细菌病毒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对它的抵抗力,做到了提前预防。这当然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贺建奎的工作思路。但是请注意,看起来都是操纵基因对抗疾病,但是迈出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是科学层面上。之前那些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CCR5基因缺陷来治疗艾滋病的办法,收益大于风险,最坏风险可控,所以我们支持对他们进行研究。但是这两条,都不适用于贺建奎的研究。先说收益大于风险。贺建奎修改了人类受精卵当中的CCR5基因,试图让出生后的孩子天生对艾滋病免疫。
但是请注意,根据贺建奎所说,这几枚受精卵的母亲根本就不是艾滋病患者。他们的父亲虽然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是在长期抗病毒治疗后,艾滋病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把父亲的精子经过严格的抗病毒处理然后人工授精,同时母亲在孕期注意防护,生出来的孩子100%不会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其实,就算母亲是艾滋病患者,用已经很成熟的阻断疗法,孩子也有99%的可能性不会被感染。退一万步说,即便这些孩子真的不幸患上了艾滋病,层出不穷的治疗方法已经把艾滋病变成了慢性病,并不影响患者的生存寿命。也就是说,这个基因编辑的操作,收益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反过来,这个操作的风险就太大了!基因编辑技术至今仍然是在蓬勃发展和快速推进的前沿生物学技术,就算是目前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也仍然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风险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这项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难以避免所谓的“脱靶”效应,很容易破坏人体当中原本正常的无关基因,导致可能非常严重的且从原理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遗传疾病。总而言之,这项基因操作给这两位刚出生的孩子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但付出的代价是各种根本无法预测和治疗的遗传疾病风险。这样的操作显然不符合人类世界最基本的伦理底线。
再来说说最坏风险可控。由于贺建奎是在受精卵当中进行修改基因的操作的,伴随着受精卵一次次分裂最终形成人体,这些修改将可能进入婴儿的所有细胞——包括生殖细胞。也就是说,这一次基因编辑的结果不光会影响这几个孩子,还会传递给他们的儿子女儿,他们的孙子孙女,他们的所有子孙后代!
这和之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患者有本质的不同。在之前“柏林病人”的案例和圣加蒙公司的治疗尝试里,只有患者的免疫细胞被替换或者修改了。就算没有取得成效,也不会影响患者的生殖细胞,因此也就不会影响患者的子孙后代。这可以看成基因编辑技术最后的防火墙——即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只有患者本人需要承担。而现在,这最后一层防火墙被突破了。
这些接受了基因编辑的孩子们,他们身体内携带的被修改过的基因,将会慢慢融入整个人类群体,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可能被基因编辑操作脱靶误伤的那些基因!从这个角度说,这项基因编辑操作的最坏风险是不可控的。人类可能需要很多年、很多代才会发现其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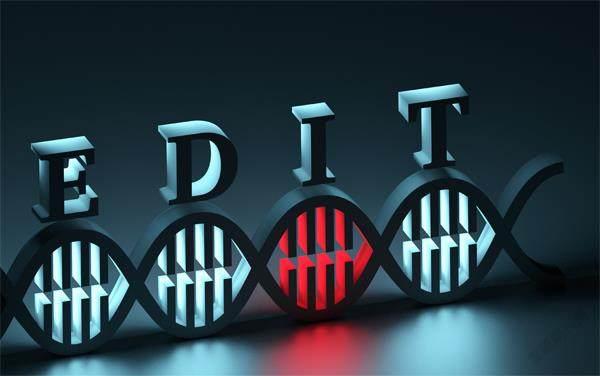
在科学的考量之上,我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那就是,对人类这个物种未来命运的担忧。把基因编辑技术从治疗推动到预防,大大延伸了这项技术的适用范围。由此产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边界在哪里?
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条边界非常难以人为划定。如果编辑CCR5基因治疗艾滋病很合理,那提前修改CCR5基因保护自己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既然如此,一个普通人也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得艾滋病,难道有错吗?再推演一步,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一个基因变异,会提高1%的某种疾病的风险,他要求做基因编辑降低风险合不合理呢?如果合理的话,那有万分之一的风险能不能做基因编辑呢?百万分之一呢?如果不合理的话,那到底存在多大的风险,我们才觉得应该允许做基因编辑呢?
更要命的是,一旦“治疗”和“预防”的边界被打开,“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更是一捅就破!如果一个人想要他(她)的孩子获得更多的肌肉,更高的个子,想要金发、双眼皮、高鼻梁怎么办呢?更有甚者,如果他(她)想要的孩子具有高智商和强大的语言能力、分析能力、领导气质呢?
如果刚才你还没觉得担忧,现在应该嗅到了巨大的危险吧。当然,必须得承认,今天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的理解仍非常粗浅,对于我们关注的绝大多数人类特性——从身高到智商,从性格到道德观念——我们还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基因差异带来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在今天就算有个疯子科学家想要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完美”人类,他也做不到。但是伴随着基因科学的进步,这些问题或早或晚都是会得到解答。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人类通过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已经陆续证明了许许多多人类特性都受到基因差异的强烈影响。人的身高,可能80%由遗传因素决定。反映人类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力和记忆力的智商,70%~80%是由基因差异决定;甚至,一个人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是更友善还是富有攻击性,是更倾向于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最大的单一影响因素,都是基因差异;在近几年发表的两项研究中,科学家们甚至发现,一个英国公民究竟投票给保守党还是工党,基因贡献了57%的影响因素;而一个男性在婚姻中是不是会出轨,63%是由基因决定!
当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些人类特性究竟是由哪些特定的基因差异所影响之后,基因编辑技术是不是就会天然地找到它的应用场景?到那个时候,基因编辑技术的推广是不是会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最重要的是,基因编辑会不会塑造永恒的不平等?
当然,人类社会已经充满了各种资源和能力的不平等。我们自然也没有天真到认为这些不平等会一夜之间消失。但是这一切至少是有可塑性的。家境贫寒的孩子努力读书工作也仍然可以出人头地,优越的家庭条件也有“富不过三代”的永恒困扰。但是,如果有了基因编辑技术的介入,一切就有可能不一样了。如果一部分人的孩子早早接受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改善”,他们就可以从外貌到智力各方面都占据竞争优势。要命的是,这些优势还是写进基因组里,可以遗传的,那么,其他的孩子可能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难道基因编辑这项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鲜花和掌声的新技术,勾画的是一条通向黑暗地狱的道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许会凝滞,但是似乎从未被逆转。在我看来,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人类世界,帮助我们战胜病痛,甚至是让我们自己更健康,可能都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2018年11月26日当天,在百度上搜索贺建奎的次数,数倍乃至数十倍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民级新闻人物——比如屠呦呦和袁隆平。跨越地域和圈层,贺建奎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人为修改人类基因、定制乃至设计人类婴儿这种可能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技术,呈现在全体中国人面前。而在那之后,争论依然喧嚣,历史还在向前。
2019年6月10日,《自然》杂志发表新闻声称,一位名叫达尼斯·雷布里科夫的俄罗斯科学家正计划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再次改造人类婴儿。这位科学家告诉《自然》杂志,他已经吸取了贺建奎的教训,开发了一种完全无害的基因编辑技术——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技术细节。因此,他打算重做一次贺建奎的實验,在人类的受精卵中修改CCR5基因,然后将胚胎植入女性的子宫内。也许,这次事件仅仅是又一个科学疯子的冒险。
但是透过贺建奎和雷布里科夫的举动,我们有更深层次的担忧。通过修改人类基因,创造全新的人体特性,乃至创造神人和怪物,是许多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的常用题材。
诞生于2012年的全新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技术,第一次把修改人类基因的门槛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稍微受过基本生物学训练的普通人,只需要几百美元,就可以在自家的后院里搭建一个简易的实验室完成对人体基因的修改。这种变化可以看成是前沿技术的民主化和大众化。在几十年前,计算机技术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在很多人家的车库里催生了一大批改变人类世界的公司,苹果公司和戴尔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现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当然了,历史也并不总是如此让人沮丧。2019年9月11日,另外几位中国科学家(北京大学邓宏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吴昊,以及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陈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报道了另一次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CCR5基因的尝试。
不要恐慌。这一次,中国科学家们恪守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在这项研究中,他们严格遵循了临床试验所在机构的临床试验管理规范。在这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单就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这个目的来说,这项研究并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在贺建奎事件的大背景下,这项研究、这篇论文仍然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为它说明,基因编辑这项技术不仅仅是野心家手中的玩物。在医学伦理的约束下,仍然有它的用武之地。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说明,中国学术界不仅仅有贺建奎,仍然有的是敬畏规范、尊重科学的真正科学家。在“基因编辑婴儿”的闹剧当中,小丑创造了历史。而未来的模样,至少还掌握在我们手中。
◎ 来源|节选自《巡山报告·基因编辑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