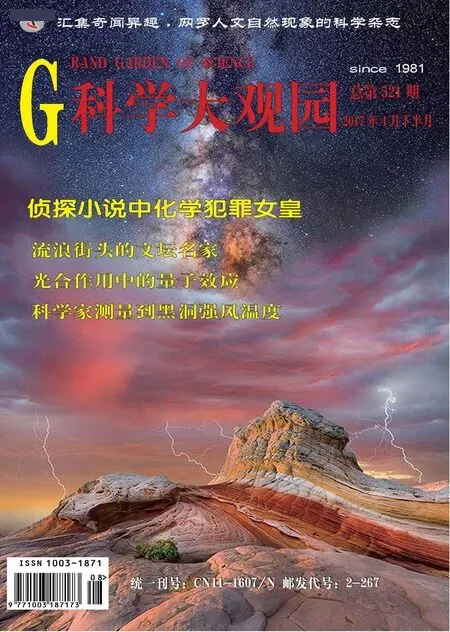无治理则无伦理
2022-05-18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我国全面推进科技伦理治理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健全完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和解决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补齐科技伦理治理的短板。这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展开了新篇章,标志着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治理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赵延东曾在2014年和2020年分别对全国科技工作者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科技伦理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情况及其变化趋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科技界各种违反伦理原则现象的普遍性在下降。
不过调查也显示,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还没有建立特别清晰的认知,尤其并未区分道德和伦理的差异。近10年来,科研人员总体科研伦理认知水平相对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
调查结果令与会专家感到既有些“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科技发展越快,就越凸显科技伦理的重要性,也就应该更加重视科技伦理的研究、教育和普及。”中科院院士裴钢表示。
随着我国前沿科技迅猛发展,很多领域进入“无人区”,出现了一些重大科技伦理事件。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存在政策规范透明度和清晰度不足、科学普及与科技伦理宣传不够、行政干预与公众参与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不健全等主要问题,建立一套完善规范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技伦理治理?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樊春良通过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科技伦理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法律、社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政府、科技界、伦理学家、社会团体、利益相关者、公众等以多主体、多种工具、多种方式共同解决科技伦理问题。樊春良列出了科技伦理治理的要素:倡导和遵循国际公认的科技伦理准则、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和评估机制、法律法规……
专家认为,治理包括传统意义的“管理”“监管”,但不限于此,还包括相关利益者和公众等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治理工具既包括伦理规范,也包括法律法规。
在专家们看来,科技的创新发展在让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突破传统社会形成的伦理规范标准,引发新的无既有准则的社会伦理问题。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正风表示,这是由发展的内在属性决定的,“科技在消除不确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此外,科技发展的对象由‘物’到‘人’,伦理治理相对不再简单,需要重建人类群体的构成逻辑,形成新的关于行为‘正当性’的社会契约”。
我国要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抓住历史性机遇,建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世界科技強国,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前所未有的社会伦理问题,建立行之有效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意见》首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治理要求,从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开展科技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进而从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制度、监管、教育培训等方面,系统提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重大举措。这构成了我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顶层设计,反映了我国科技伦理整体治理的突出特点。
这种顶层设计和整体治理特点,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体现了党和国家做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总体思路。这种顶层设计和整体治理特点,也是适应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紧迫要求,解决我国面临的特殊问题。相比欧美等科技先行国家,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起步较晚。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伦理委员会的雏形,即西雅图肾脏移植委员会,该委员会围绕血液透析技术进步而带来的稀缺医疗资源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与投票,决定哪些人可以接受相应治疗,被称为“上帝委员会”。70年代初,维持生命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国社会出现关于患者生死抉择自主权问题的社会争议,对于缺陷新生儿治疗、尊严死和安乐死等伦理问题的决策咨询导致了医院关于“预后意见”伦理委员会的成立。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人体试验的丑闻使得更多社会力量促动美国建立和发展科研机构伦理审查体系。1972年美国“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事件曝光后,机构、部门层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逐渐规范化。自1995年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逐渐形成了与总统任期相一致的国家伦理委员会建制,并负责就重大伦理议题前瞻性地向总统直接提供咨询与决策意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医院、科研机构层面先后引入了伦理委员会制度,但发展不平衡。除医疗卫生机构80%以上按要求成立伦理委员会,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成立伦理委员会的比例普遍较低。其中,一些科研机构、大学自发引入伦理审查机制,最初主要是适应论文国际发表和科研国际合作的需要。由于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一定程度存在体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发展领域不均衡等问题。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还不能适应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要尽快有效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我国科技健康发展,必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整体推进科技伦理治理工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医院、科研机构层面先后引入了伦理委员会制度,但发展不平衡。除医疗卫生机构80%以上按要求成立伦理委员会,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成立伦理委员会的比例普遍较低。
《意见》的出台表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社会共识基本形成,一体化推进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顶层设计初步建立,这有利于多措并举、协同推进科技伦理治理工作。
在为《意见》出台感到欣喜的同时,受访专家心中仍有担忧。
“具体怎么落实是个问题。” 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教授张迪认为,政策落实主要有两个难点,一是各部委之间能否打破固有壁垒,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和平台;二是我国目前缺乏相关专业人才,“这可能会阻碍我国近5~10年的科技伦理治理进程”。
此外,他担心的还有政策落实的“度”的问题。
“一种是只说不做,谈多了就谈滥了,大家觉得虚无缥缈,摸不着头脑;另外一种是管得太严,伦理审查的内容太多太细,会影响科研的合理开展。”张迪说。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说,未来各科技领域如何确保科技活动相关方的充分知情,是落实《意见》的重点和难点。“《意见》强调不得侵犯科技活动参与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人工智能为例,特别是涉及个人数据的相关应用,在真正意义的用户知情权、用户选择权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大连理工大学科技伦理与科技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伦理学会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伦表示,建立和完善省域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则是落实《意见》的重点和难点。
“难点在于理顺省域各厅局科技伦理治理的职责和权限,实现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关键,要将科技伦理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要作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地方营商环境等工作的重要任务。”李伦说。
对于政策落实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受访专家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针对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的研发活动还没有明确的伦理审查制度的问题,曾毅指出,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制度发展和实践相对较早,可以为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科技伦理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參考。

在借鉴的同时,需要充分认识不同领域之间的伦理问题及治理方式的差异,发展适用于各个关键科技领域的伦理与治理框架。
李伦也认为,可以借鉴国内外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经验,“比如,探索建立专业性、区域性科技伦理审查中心,建立科技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机制,设立单位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等”。
不过,尽管医学领域是国内最早开展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领域,张迪指出“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张迪参与了医疗机构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的伦理审查工作,发现一些医学领域科研人员在伦理方面的意识依然有待提升。
他建议建立独立可靠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每隔几年评估一下各机构科技伦理治理水平和效果,包括现有科研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伦理认知水平,以及医疗机构、院校的伦理审查能力等。
从科技伦理治理更长远的发展来看,张迪建议:一是要加强人才建设,培养懂科学、懂技术、懂伦理、懂治理的专业人才;二是要加强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科研人员的伦理培训,“这种培训不能是形式上拿个学分或拿个证就行的,而是要探讨新的模式和方法,让伦理理念真正根植在科研人员心里”;三是加强伦理教育,从小培养青少年科技伦理和道德意识。
此外,李伦认为,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也是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
落实《意见》还需加紧制定和完善科技伦理的规范和标准。
他建议,出台科技伦理治理实施的细则,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的清单,建立科技伦理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设立国家级科技伦理研究基地,加强科技伦理理论研究,增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
◎ 来源|综合中国科学报、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