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限定与非限定结构中话题成分的逆向约束及其二语处理研究
2022-05-13马志刚
马志刚,火 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词典学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基于短语结构的语法表征理论认为,英语的母语句子处理机制在解析含有填充词-空位关系的句法依存结构(filler-gap dependency)时,首先需要激活变量成分并将其储存在工作记忆中,然后在语法表征允准的每个空位上重新提取该变量成分,最后再整合到其次范畴化成分(subcategorizer)选择的补语位置上(Kluender &Kutas,1993)。这种句子处理策略被称为语迹重新激活策略(TRH:Trace Reactivation Hypothesis)。但目前相关的二语研究显示,尽管句子中的空位有助于英语母语者更快建立起填充词-空位之间的句法关系(Gibson & Warren,2004),但二语者均采用把填充词直接与题元动词联系起来的句子处理策略(DAH:Direct Association Hypothesis)(Marinis,Roberts & Felser,2005),而且二语者的母语类型学特征并不会影响其句子处理策略,即无论母语中是否允准WH移位,各二语组均采用直接联系的处理策略。据此实施的二语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英语关系结构的各种变体句式来鉴别上述两类假设(TRH vs.DAH)的适用范围和成立程度,而目前采用其他有助于剥离句法和语义信息的复杂句式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为少见。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语表征和处理是否等同于母语这一学界富有争议的课题,本研究针对可以明确区分句法和语义信息的逆向回指现象(backward binding),通过英语话题成分在限定和非限定结构中的不同句法表现和语义解读来进一步验证浅层结构假设(Clahsen & Felser,2006)和本质等同假设(Hopp,2007,2012)的相关断言(即TRH vs.DAH),进而为中介语语法的理论构建及其二语处理研究提供另一维度的实证依据。本研究第二部分简述相关的二语研究背景;第三部分基于最简方案的语段理论分析英语限定/非限定性这两类具有逆向回指的话题句;第四部分是实证调查方案和结果分析;第五、六部分分别是讨论部分和结语。
二、研究背景
心理语言学研究显示,移位成分在句间连续循环移位(successive cyclicity)的语言学理论假设在英语母语者的句子理解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Kluender& Kutas,1993;Gibson & Warren,2004:56)。如下以(1)中的例证予以说明:
(1)a.The consultant claimed that the proposal had pleased John.
b.Whoidid the consultant claim ____ that the proposal had pleased ____?
c.*Who did the consultant wonder [WH-ISLANDwhich proposal had pleased____]?
d.*Who couldn’t you decide [WH-ISLANDwho should sing something for ____ at the party?
Kluender和Kutas(1993)及Gibson和Warren(2004)采用不同实验手段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针对(1)a宾语从句中的宾语提问而形成的b中,中间空位的存在有助于填充词整合到其次范畴化的基础位置上,而c和d中的移位会因WH岛屿结构的存在而被阻断,从而形成不合法的句子。同类研究为母语语法表征中存在抽象的语言学结构(包括空语类和层级性)提供了心理现实性依据。这种母语句子处理过程的完美实现主要依据基于结构的句法信息而非词汇语义线索,而这正是母语语法处理句子的主要特点,但习得二语的成人对于中间空位的敏感性非常钝化,似乎并不能在其中介语语法中加以充分表征(Marinis,Roberts & Felser,2005)。
事实上,对于成人二语习得很难达到目标语的本族语水平这一中介语现象,二语学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理论试图加以解释(Bley-Vroman,1990;Hawkins & Chan,1997;Hawkins & Hattori,2006;Clahsen & Felser,2006;Tsimpli & Dimitrakoupoulou,2007)。其中的浅结构假设和可解读性假说均认为,在实时的二语理解中,二语学习者只能构建浅层结构的表征或者出现特征失效现象,而构建本族语表征所需要的结构性细节(包括不可解读特征)在中介语语法中并不存在。由于浅结构表征仅仅包含基本的论元-谓词关系,缺乏句法信息的精细表征,因此,二语理解依赖的主要是词汇语义的连贯性和篇章语用的合理性。但与此观点相左的实证研究也为数不少。比如,Hopp(2007)就认为,二语表征本质上与本族语表征并无差异,而且Omaki和Schulz(2011:583)针对英语岛屿限制的二语处理研究也显示,二语者完全具备本族语的语法能力。因此,可以为英语关系从句构建出含有详尽句法信息的结构表征。
与本研究中的中介语回指处理直接相关的研究也支持本质等同说,比如,Felser和Gunnings(2012)在线调查回指词解读的二语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英语母语句子解读的研究结果(Gibson & Warren,2004),即二语解析机制完全可以构建出包括成分统制在内的抽象句法表征,而这显然与浅结构假设的观点并不一致,因为缺乏层级性的中介语表征是无法为先呈现的回指词确定逆向先行语的,而二语者的离线表现与英语母语者并无显著差异(Felser & Roberts,2007)。为进一步求证中介语语法表征的实质,本研究基于句式的限定性,以英语话题结构中的逆向回指对研究对象,实证调查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是如何为逆向回指词构建语法表征的,从而为中介语语法理论的构建提供进一步的实证依据。
三、英语话题结构中逆向回指的语段理论分析
如上节所述,本质等同说和本质差异说均具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两种观点都认可二语者和本族语者在解析过程中受到词汇信息的引导,但差异说强调的是,二语者对结构信息的依赖程度显著低于本族语组。更重要的是,这种倾向性并不会因为二语者的母语背景不同(以及二语水平不同)而有所变化,属于有效的中介语归纳,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valid generalization in interlanguage)(Felser et al.,2003;Papadoupoulou & Clahsen,2003;Roberts,2003)。为求证前述基于英语关系结构和疑问句所得结论的适用性,本研究选用能明确区分句法位置和语义解读的逆向回指现象,并以同样含有填充词-空位关系的英语长距离话题句作为语言学素材来检验二语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构建出中间空位等抽象的本族语表征。本节先简述逆向回指及其在英语话题句中的表现。
就英语反身代词的指称确认而言,在结构上受到恰当先行语的成分统制是实现反身代词语义解读必备的句法限制。依据最简方案的拷贝理论(Chomsky,1995),(2)a中的反身代词可以与其他两个名词同指,而其中的后者在表层线性序列上似乎并不能成分统制反身代词(居后于反身代词),但该句的深层结构b显示,这种逆向回指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包含反身代词的最大投射QP在嵌入句动词的补语位置上具有同等的拷贝成分,即斜体的[Q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2)a.Joe wonders 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Jim bought.
b.[CP[TPJoe wonders [CP[Q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TPJim bought [Q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c.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does John think that Jim bought?
d.[C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Cdoes][TPJohn think [C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Cthat][Q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TPJim bought [QPwhich picture of himself]]]]]
同样的逆向回指也存在于如(2)c所示的主句选用桥梁类动词的复合句中:在线性序列上居后于反身代词的John和Jim均可以成为其合法的先行语,而且整个句子可作两种解读(dual interpretation),原因就在于包含反身代词的句首疑问性QP在执行非论元连续循环式移位的过程中在句中遗留下三个拷贝成分,如(2)d所示(分别标为斜体、黑体和下划线部分)。由于拷贝成分无语音拼读但却可以获得语义解读,因此,在逻辑式中可以分别成分统制Jim和John的中间拷贝(具有黑体和下划线),从而可以为反身代词提供恰当的指称确认。事实上,这种逆向回指现象也同样存在于如(3)所示的英语单子句和双子句话题结构中。
(3)a.John, I like ____.
b.That girl, I think that John believes that Bill likes ____.
c.The manager, the consultant claimed ____ that the new proposal had pleased___.
d.The manager, the consultant’s claims about the new proposal had pleased____.
e.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thinks ___that Joe believes ___ that Bill will talk about ____.
对于执行WH等非论元移位类语言而言,(3)a,b显示出英语话题句的长距离移位属性,而c,d分别是有、无中间空位的英语话题句。依据Marinis,Roberts和Felser(2005)的研究,英语母语者在 c和 d中的句末空位上会呈现出显著的行为(反应时)数据差异,因为只有c中的中间空位会助化非论元成分整合到其次范畴化题元位置上(displacement,移置性)。而本研究所关注的逆向回指话题句基本上等同于c类,因为其中的中间空位是否具有助化作用是可以得到实证验证的(修订后的句式类型如e所示,详见下文)。
为了选择具有对比显著的测试材料,本研究中的测试句所采用的主句动词均为既可以选择限定性补语又可以选择非限定性补语的兼类动词,因此,首先需要基于(非)限定性来区分英语中的长距离话题结构的句法变异性,如(4)是基于语段理论对相关测试材料的分析。
(4)a.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expects that Joe will mention at the press.
b.John expects [CPthat [TPJoe will mention books about himself at the press]].
c.John expects [CPbooks about himself [Cthat]Joe will mention < > at the press].
d.[TOPICPBooks about himself[TOPIC,][TPJohn expects < >that Joe will mention< >at the press]].
遵循Chomsky(1995)和Adger(2003)的处理,移置成分在所有潜在的结构位置上都会遗留下拷贝成分,因此,(4)a类话题句实际上是经历了如b,c两个步骤的移位后生成的,其内部结构,如d所示(< >表示移位成分的拷贝位置)。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关话题结构二语处理的近期研究中(Yuan,2017),话题成分是否采用逗号予以标记在示例部分和附录材料中并不一致,而本研究则认为,标记汉语话题成分的形式标记可以是语音上的停顿也可以是书面语上的逗号,因此,d中采用逗号作为话题投射(Topic P)的中心语,这种分析实际上等同于日、韩语中采用专用话题标记的形式处理,而这有助于受试者对实验句中话题成分的辨识。上述如(4)所示的限定句中的移位既满足管约论中移位只能跨越一个S或TP的领属原则(Chomsky,1986),也符合最简方案中非论元必须在逐个语段间执行连续循环移位的要求,如(5)中是对应的非限定性话题句中的成分移位。
(5)a.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expects Joe to talk about at the press.
b.John expects [TPJoe to talk about books about himself at the press].
c.[CP[TPJohn expects [TPJoe to talk about books about himself at the press]]].
d.[TOPICPBooks about himself[TOPIC,][TPJohn expects [TPJoe to talk about < > at the press]]].
显然(4)d和(5)d之间的差异在于含有反身代词的话题成分在前者的中间位置上具有结构空位< >和题元空位,而在后者中只具有题元空位而缺乏结构空位,而这种结构空位的数目差异可以基于语段理论得到解释:限定性话题句具备嵌入的中间CP语段,因而话题成分可以经历中间空位,而非限定句缺乏嵌入的中间CP语段,因而其话题成分无需经历结构空位,二者的对比性分析图示如(6)a,b所示。

b.[TOPIC P Books about himself, [TP John expects [TP Joe to mention < > at the press]]].

对于检测英语二语者是否具备中间空位语法表征的研究而言,(6)a中的移位既符合语段不可穿透性条件(PIC:Phase Impenertrability Condition)(Chomsky,2021),也符合管辖和约束理论下的领属原则的要求,但b中的移位仅仅符合语段不可穿透条件,但却因移位跨越两个TP而违反领属原则,因此,其合法性并不充分。同时,a类限定性话题句的可习得程度也理应显著高于b类非限定话题句,因为前者中的回指词可以具备两种逆向解读,因而被习得者所接受的概率较高(因为居前的两个名词短语均可以为其提供所指),而后者中的回指词只可能具备后一种逆向解读,因此,居前的两个名词短语更容易对恰当解读造成干扰,因为习得者必须首先具备局域性的语法知识(locality)。
至此,基于语段理论和领属原则对(6)中语言学材料的分析显示,通过是否具有结构上的中间空位以及能否为其提供唯一的恰当解读可以鉴别出二语者的中介语表征是否等同于本族语表征,进而判断二语者是否和母语者采用相同的句法理解机制来解读同类语句。如下基于上述的语言学分析呈现本研究的设计方案和实证结果。
四、实证研究
参照Marinis,Roberts和Felser(2005)及Felser和Gunnings(2012),本研究采用自定步速阅读句子的考察范式来对比本族语表征和中介语表征的异同。基于前文的语言学分析和二语研究的相关论断(Clahsen & Felser,2006),如下的实证测试材料主要针对句式的(非)限定性和话题成分的语义解读而设计。考虑到结构因素和语义因素可能是同时影响参与者的合法性判断和句子理解行为的,同时还考虑到英语母语者和英语二语者对测试材料的敏感性(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本研究针对英语母语组和二语组分别采用包含两个自变量的被试内方案,从而可以排除因被试的个体和群体差异引发的干扰效应,并将研究聚焦于两组被试的判断模式是否一致方面。
1 实验材料
依据Carnie(2021)和Culicover(2009),本研究选取既可以选用定式句又可以选用不定式句作补语的ECM类动词,包括believe,expect,know,think和suspect等。实验测试句中的主语均含有反身代词或相互代词,如(7)a所示的逆向双指的限定性话题句和(8)a所示的逆向单指的非限定性话题句。
(7)a.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believes that Joe will talk about at the press.
b.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believes ___ that Joe will talk about ___ at the press.
c.John believes that Joe will talk about books about himself at the press.
对于参加工作近10年,并一直在农村从事数学教学工作我来说,基本的教学技能和基本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陌生。2011年我怀着梦想和期待,走进了涡阳耿皇学区寺后小学,在那里,我经历了风雨,得到了成长,收获了知识和经验,获得了些许家长的赞许。
d.The comprehension question: The books are about John, Joe or BOTH?
(8)a.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believes Joe to talk about at the press.
b.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believes Joe to talk about ____ at the press.
c.John believes Joe to talk about books about himself at the press.
d.The comprehension question: The books are about John, Joe or BOTH?
在上述(7)a和(8)a中,表层语序上包含回指词的话题成分因居前的位置似乎都未受到相关名词的成分统制,但在语义解读方面,(7)a中主句和从句的主语均可以约束话题中的回指词,而(8)a中只有不定式从句的主语可以约束话题中的回指词。这与(7)b和(8)b中的空位是相对应的,但这种解读的实现要求句子理解者能够将句首的话题成分回溯到其次范畴化的题元位置上,如(7)c和(8)c所示。由于英语反身代词并不能作句子的主语成分,因此,在呈现(7)a和(8)a中的话题成分时可能会引发句子理解者的重新分析,因而可以作为测试句型中的关键区域。同时,主句动词后是否具有结构上的中间空位也是区分两类句式的关键部位,而区分的主要形式依据在于区域6中采用的是限定性助动词will还是非限定性的不定式标记to,因此也是本研究中的关键区域。依据Marinis,Roberts和Felser(2005)的研究,非论元移位成分(包括话题成分)在被整合到次范畴化的题元位置上时,(7)b和(8)b是否呈现出反应速度和时间方面的差异是区分本族语表征和中介语表征的重要指标,因此也是本研究中的关键区域。(7)d和(8)d中的理解性问题的回答既有助于判断母语者和二语者的理解差异和参与实验的投入程度,也可以从理解程度的视角说明母语表征和中介语表征的异同。如下表1呈现的是实验材料的区域划分情况,为行文方便,分别标为(9)a和b。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相关的二语句子处理研究的测试材料中,具有WH形态标记的移置性成分被视为变量成分并被储存在短时记忆中,而表1区4中的成分首先因为逗号(或停顿)的存在而可能被语法解析机制分析为话题成分,进而由于其反身代词的变量性质被激活后储存在临时记忆中。其次,表1(9)a的区5中可以添加标句词that(具有可选性),但考虑到实验材料的效度和一致性,即为了确保两组实验句的差异具有唯一性,因此未予以明示;两类测试句中,区6中不同的助动词有助于确定限定性的结构属性,从而为中间空位提供形式标记,而表1区7中的题元位置则可能因本族语或中介语的表征不同而呈现出反应时差异。

表1 实验句中关键区和对照区示例
2 实验实施和受试
本研究自测步速阅读任务中的实验材料包括可以选择限定句和非限定句作补语的英语ECM类动词和结构类似的干扰句(提升、控制等)。每个实验句都含有嵌入句(限定或非限定)。为了防止出现收尾效应(wrap-up effects),即关键区域出现在句尾而产生的干扰效应,主句均采用it is said that的形式开始,而从句均以at the press结束。在测试过程中,受试必须连续按键才会逐次呈现实验句的不同区域;每个实验句呈现后都紧接着出现阅读理解问题(计算机自动记录回答正确率),受试必须按F键或者J键来回答对或错。比如,在呈现完实验句(7)a后立刻出现简单问句(7)d。所有按键时间均被计算机以毫秒为单位自动记录,所有实验句均采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常用词编写并以拉丁方平衡形式随机呈现实验句(每个受试对应一种版本)。在三位常年教授大学英语的教师判断的基础上,研究者基本可以确定,这两类测试句均是二语输入中出现频率极低的句式,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表层句式和其中词汇的输入频率差异对本研究课题的影响,并把研究工作聚焦于关注深层句法表征方面。
如上表1显示出本研究实验句的8个测试区域,其中的区域4,5,6,7均是关键区,而其余的区域均可作为对照区。考虑到回指词还包括同样属于变量成分的相互代词,本研究还在每个实验句中采用了相互代词的测试材料(其从句主语相应地采用复数性质的名词短语)作为补充调查的材料,主要是为了平衡和消除两类回指成分造成的词汇性差异。为了确保所选二语受试可以接受英语话题结构,以及具备英语及物句中的回指知识,研究小组先在60名大三(通过四、六级)的大学生中进行了合法性判断(具体例证如前文所示),并在接受度为1~7的里克特量表的基础上选取能明确辨识相关句式合法性的 30名高水平受试参加自定步速阅读实验。另有 20名国内各大学任教、求学或经商的英语母语者作为对照组应邀参与实验并同二语组受试一起获得同等赠品。
3 实验数据预处理
参照相关的实证研究(Frazier,Clifton & Randall,1983),本实验的程序编写是在Psychopy软件上完成并逐段呈现的(Roberts,2012),所有测试均在认知建模实验室中集中完成。正式实验开始前有指令解释和练习项目的操练。自定步速材料全部都是逆向话题句(限定和非限定各半),所有测试句的随机化原则是经由限定性和语义解读(双自变量)在两个水平上的交叉平衡而形成的四种呈现条件,从而可以保证每个受试只经历一个版本的测试项目(拉丁方平衡),并且在每种条件下都能阅读到所有类型的测试句,具体例证如(10)所示。
(10)a.限定性单指话题句
It is said that rumors about himself, Mary believed (that) Joe would mention at the press.
b.限定性双指话题句
It is said that rumors about himself, John believed (that) Joe would mention at the press.
c.非限定性单指话题句
It is said that rumors about himself, Mary believed Joe to mention at the press.
d.非限定性双指话题句
It is said that rumors about himself, John believed Joe to mention at the press.
上述实验条件呈现出由ECM动词所形成的两类测试句(限定和非限定)。限定性的区分体现在标句词(that/ø)和助动词/不定式标记 to,而解读差异则经由从句主语的性别确定为单指和双指。所有测试材料均以非累积性移动窗口的技术方式呈现在屏幕上。数据预处理删除各测试条件下组均值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值,因此,关键区中有 1.6%的数据和关键区后有 1.9%的数据未纳入统计分析。实验过程延续约35分钟。被试对判断题的统计分析正确率显示出其参与实验的投入程度,因而无整体数据被删除(均值=90.5,标准差=1.21,数值范围在80~95之间)。另外,本研究关注的是高水平二语组处理句子的认知时间进程是否也和英语母语组具有一致的模式,而这也是本研究采用自定步速研究范式的主要动因。为了行文表述和对比方便,如表2先呈现本研究自定步速任务后执行的英语逆向回指话题结构和英语约束知识的语法判断可接受度结果。

表2 自定步速后执行的语法可接受度判断任务的统计数据(相关群体配对检验)
表2显示,在语法可接受度判断中,两组被试的判断结果都具有或接近边缘显著性,这说明两个组不仅具有充足的元语言判断能力,而且都具有英语限定性、话题句和回指的显性语法知识,而这就为判断后续的自定步速阅读中受试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可资比对的基准。由于该测试中的例句与SPR中的测试句具有结构相似性,因此,为了规避熟悉度效应,该测试实际上是在SPR测试后进行的(并进行了相应的词汇替换)。需要指出的是,该测试结果中,即便是英语母语者的判断均值也相对较低,可能的原因就是该类测试句主要基于前述的语言学理论设计而言,因此,在输入频率和熟悉度方面均较低,而且测试句也都具有多重嵌入句,因而容易引发处理困难,这与实验研究中的常规情形一致(生态效度较为不充分)。
五、实验结果呈现
本研究中的母语组和二语组均参与所有测试项目,但考虑到二者间的可比性程度还是相对较低,因此如下有关母语组和二语组的推断性统计分析在本研究中均分别独立处理。为了使两个组判断模式之间的(非)一致性模式更为坚实明确,本研究在相关的区域均汇报基于受试的F1值和基于测试项目的F2值(简称受试分析和项目分析)。下文先呈现阅读理解问题的回答结果,同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把阅读理解问题回答错误的所有试次及其参与者的相关数据均予以删除。
1 阅读理解问题的准确性分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限定性因素和语义解读因素被预测为都会影响两组受试对句末问题的回答,而实际结果表明也的确如此。具体而言,就句末阅读理解问题回答的准确率而言,母语组为95.7%(标准差=5.6),二语组为88.9%(标准差=5.4),而基于限定性和语义解读两个因素对两组的数据分别执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英语母语组和二语组对阅读理解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受到任何单一因素的主效应的影响(所有Fs < 1),但结构因素和语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却达到了显著水平:英语母语组(F1[1, 19]= 8.87,p < 0.05;F2[1, 27]= 13.24,p < 0.05),英语二语组(F1[1, 29]= 6.21,p < 0.05;F2[1, 27]= 9.03,p < 0.05)。这说明本研究测试句的正确理解需要结合句法和语义两个因素才能实现,这从另一视角说明本研究的设计方案具有合理性,也是能够揭示出英语逆向回指话题句的句子处理过程实质的研究方法。同时,从测试项目的总体判断情况看,非限定性单指句的判断准确率显著低于限定性双指句,而且两个受试组均如此,这也印证了前文基于语段理论的分析,毕竟只有非限定性的逆向回指话题句违反了领属原则(但符合PIC原则),因而不具有充分的合法度。另外,基于交互效应显著而执行的后续对比结果显示(选择性的两两对比),限定性单指话题句的准确率显著高于非限定性双指话题句,而非限定性单指话题句的准确率显著低于限定性双指话题句。总体看来,英语母语组的准确率判断模式符合前文语段理论的预测,即其行为模式符合语言学理论的分析(本研究缺乏被试间变量,因此无需采用Post Hoc的各项检验,而且简单效应检验及其结果与阅读理解问题的准确率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有关简单效应检验的讨论将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展开)。
下面汇报母语组和二语组在关键区域的行为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数据处理中,每种条件下以及每个区域中超出组均值3个标准差以上的数据均未被纳入统计分析。在逐个区域的数据分析中,非关键区域1~3属于词汇完全匹配对等的区域,而且母语组和二语组均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也未出现任何虚假效应),因篇幅所限不予详细呈现。
2 英语母语组的阅读时间结果分析
尽管区域4中在两个测试句中也都是词汇匹配对等的,但与第3个区域相比,英语母语组在区域4上的反应时均值显著延长(限定句:t[19]= 5.71,p < 0.05;非限定句:t[19]= 6.09,p < 0.05)。同时,针对区域4中的数据所执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结构因素(限定性)和语义因素(回指)既无主效应也无双向交互效应(Fs < 1),而且基于受试和项目的统计分析结果均如此,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在两组受试的语句输入中,尚未判断出句式的类型以及解读的歧义性。然而,区域4中的这种耗费认知资源的处理模式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因为区域5的均值不仅显著高于前两个区域,而且与区域4之间执行的相关群体取样检验也具有显著性(限定句:t[19]= 10.21,p < 0.05;非限定句:t[19]= 11.01,p < 0.05)。这说明,英语母语组对两类测试句中的区域5付出了更多的认知处理资源。可以据此认为,英语母语者的确会把含有反身代词或相互代词的话题成分(区域 4)视为变量成分,在将其加以激活后储存在工作记忆中(区域5)并留待后续句流呈现。
就区域5中反应时数据的无关群体取样的对比而言,英语母语组对明确标记为限定句的判断反应时显著长于对应的非限定句(t[19]= 8.09,p < 0.05),可能的原因是限定句的处理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因为英语母语者在处理限定性话题句的过程中正在经历主动创造缺位的认知心理过程(active gap creation),因此,会主动支出资源以便尽早为话题成分寻找到结构空位,并试图把保持在短时记忆中的话题成分并入该(中间)空位。针对区域5中的数据所执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结构因素(限定性)的主效应显著(F1[1, 19]= 10.05,p < 0.05;F2[1, 27]=20.01,p < 0.05),语义因素(解读歧义性)的主效应显著(F1[1, 19]= 11.97,p <0.05;F2[1, 27]= 12.05,p < 0.05),而且双向交互影响也具有显著性(F1[1, 19]=23.21,p < 0.05;F2[1, 27]= 23.04,p < 0.05),这说明英语母语者在动词believe呈现之时,决定句式类型的限定性因素和决定解读歧义性的语义因素以及二者间的交互均开始产生影响:具有标句词that的限定句允准其前具有中间空位,从而诱发语法解析机制把储存在工作记忆中的回指性话题成分执行重构,从而可以为反身代词提供一种解读,但无标句词的非限定句则因缺乏形式标记无法确认中间空位的存在,因而最直接的处理策略就是留待后续句流中呈现新的名词性成分,从而造成非限定话题句的处理速度较快(反应时较短)。针对英语母语组被试分析中显著的交互效应,经由程序语句改写而执行的简单效应检验进一步说明,在限定性水平和非限定水平加以固定的情形下,回指解读的简单效应都显著。这说明,对于英语母语者而言,回指解读效应解读(即单指/双指)会受到句式类型的影响(后续研究将深入探讨)。
上述对比中,基于受试和项目的统计分析结果和判断模式基本一致,因而可以认定这种判断模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可信度。简言之,对于限定性逆向回指话题句而言,英语母语者所形成的语法表征中可能的确存在中间空位,即如It is said that books about himself,John believes < > that Joe will talk about at the press,其中的中间拷贝位置< >上可以容纳话题成分被回溯其中,从而为第一种解读提供了结构空位,这与Gibson和Warren(2004)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英语母语组在对应的非限定句中则缺乏这种中间空位,因此,在句流呈现过程中不可能形成结构空位,更不可能把回指词解读为主句主语,符合前述语言学理论的分析。
英语母语组在区域6上的反应时呈现出和区域5大致一致的判断模式:对限定句的判断速度显著慢于非限定句(t[19]= 32.01,p < 0.05),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区5中的溢出效应所致。同时,针对区6中的数据所执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限定性因素具有主效应:F1[1, 19]= 16.06,p < 0.05;F2[1,27]=8.94,p < 0.05,但语义解读因素和双向交互均无主效应(Fs < 1)。这说明,尽管助动词will和to这两个时态投射(TP)的中心语成分对于标记句式的限定性类型具有明确的形式导向作用,但对母语者的语义消歧并不具有积极的助化作用。事实上,区域6中的词汇组合基本上可以视为主语+助动词的匹配对等模式,因此,其反应时差异的确可以归因于受区域5中判断模式的后续影响所致(spill-over effects)。
对于本研究至关重要的是,英语母语组对词汇完全匹配对等的区域7的判断模式呈现出与区域5中完全逆转的显著不同,相关群体取样的对比检验显示限定句的判断反应时显著低于非限定句(t[19]= 7.42,p < 0.05),这说明真正影响英语母语者的是动词次范畴化选择的补语空位位置(题元指派位置)。尽管两类句式均具备这一空位,但由于限定句在句流中已经具有中间空位,因此,在把话题成分整合到该题元位置时所经历的移位距离较短,而非限定句中缺乏中间空位,因此,同样的移位操作需要经历更长的移位,因而耗费的认知资源较多、处理的反应时间较长。换言之,英语母语组在处理限定性逆向话题句时,话题成分在题元位置上的整合可以得到中间空位的助化,从而耗费较少的认知资源。这印证了Marinis,Roberts和Felser(2005)的研究结果。事实上,对区域7中的数据执行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结构因素和语义因素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s <1),但双向交互影响则具有显著性(F1[1, 19]= 4.23,p < 0.05;F2[1, 27]= 10.24,p < 0.05)。这进一步说明,在英语母语语法表征中,句式的限定性和回指词的语义解读只能以交互方式影响逆向话题结构的句子处理过程。英语母语组在最后的区域8中的行为判断模式基本上与区域7一致,不过其中也可能具有因句子收尾而产生的虚假效应(spurious effects)(限于篇幅,不予详述)。
3 英语二语组的阅读时间结果分析
选用区域3作为对比基准,英语二语组在区域4中的两个测试句上的反应时均值显著延长(限定句:t[29]= 8.09,p < 0.05;非限定句:t[29]= 12.87,p < 0.05)。针对二语组在区域4中的数据所执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重复了英语母语组的判断模式:限定性因素和解读因素都缺乏主效应也不具有交互效应(Fs < 1)。考虑到汉语反身代词可以出现在主语位置,因此可以认为,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为激活英语反身代词也同样付出了额外的处理资源,从而导致区域4的反应速度慢于区域 3,这也可能是母语处理机制的一种正向迁移所致。然而,与英语母语组不同的是,二语组在区域5中的处理模式并没有因为限定性不同而有所差异(t[29]= 12.02,p > 0.05),这与英语母语组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说明英语二语组并没有因为限定性标记that的存在而在ECM动词后假设出结构空位。换言之,呈现两类英语句式时,英语二语者似乎并没有从限定性的视角对二者加以区分,这可能与其母语(汉语)中是否存在限定性之分的类型学争论有关(详见下文讨论部分)。而且英语二语组在区域5上的反应时数据也并不比区域4更长或更短(限定句:t[29]= 19.21,p >0.05;非限定句:t[29]= 14.52,p > 0.05)。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浅结构假设的断言,中介语语法并未表征结构空位(即缺乏空位),而且二语者也并不会主动在首个及物动词后创建空位,从而导致限定句和非限定句在中介语处理过程中缺乏区别性。同时,针对区域5中的数据执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既无主效应也无交互效应(Fs <1),这与上述英语母语组以不同方式明确区分限定句和非限定句的处理模式完全不同,而且英语二语组漠视限定性因素的处理方式说明他们对句子所在的结构信息非常不敏感,由此对两类测试句所形成的表征模式中均缺乏中间空位:即如It is said that books about himself,John believes that Joe will/Joe to talk about at the press,其中均无中间拷贝位置< >,因此也就无法把话题成分加以重构并形成额外的语义解读,这与Felser和Roberts(2003)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中介语语法并不表征中间空位也不能提供额外解读。更有甚者,区域5所呈现出的这种钝化处理模式一直延续到区域6和7:针对这两个区域的数据所执行的所有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均未呈现出主效应和交互效应(Fs < 1),而且针对区域7中两类句式的相关群体的取样对比检测也不具有显著性(t[29]= 10.92,p > 0.05),这很有可能就是英语二语组在处理限定句和非限定句式时均采用直接联系的处理策略(Pickering & Barry,1996),因此,他们在把话题成分回溯到题元空位上并无任何显著不同,或者说,限定性因素对于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而言根本不具有任何影响作用(或甚微)。换言之,英语二语组对限定句中从句动词的次范畴化补语位置的处理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构空位的助化,因为在成人二语者的中介语语法表征中可能根本就不具备形成中间空位的结构信息。
六、分析和讨论
依据语言学理论分析(Ross,1967)以及相关的心理语言学研究(Kluender &Kutas,1993;Gibson & Warren,2004),填充词-空位结构的表层语序中,填充词的基础位置表现为次范畴化成分(sub-categorizer)的补语空位,而在与其次范畴化成分再次建立联系之前,填充词必须保持在短时记忆中。在句流逐渐延展过程中,一旦出现语法机制可以允准的结构空位,那么,语法解析机制就会从短时记忆中重新提取填充词。考虑到句子处理需要达至较高的效率,语法解析机制必须尽快为填充词寻找到结构空位,这是母语语法解析的典型操作过程。但本研究基于同样的理论依据展开的成人二语句子理解研究则发现,中介语语法处理机制本质上只能依据词汇语义线索把填充词整合到其题元位置上,其句子处理过程中缺乏结构空位,也不具有任何抽象的语法单位。就研究材料而言,基于浅结构假设的相关系列实证研究(SSH)主要聚焦于英语WH问句和关系结构中的填充词-缺位依存关系,而本研究则选用含有逆向回指的英语话题结构作为研究材料,并且基于限定性和语段理论对相关的研究材料做了甄别性分析。因此,无论从理论分析视角还是从实证设计视角都比现有研究更为精细、充分,而且最后所得的部分结论支持中介语语法缺乏空语类(中间空位)以及层级性的浅层表征观点。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为类似的观点提供了更为深入的理论解释:母语(汉语)中缺乏区分限定性与非限定性语法范畴的形式标志是造成二语者无法建立结构空位的语言学深层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可以认为,汉语中缺乏标记限定性句补语的标句词that和呈现非限定性的助动词to,而且汉语名词成分无任何格位形式(以及时态和一致性形态),因此,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处理类似于(9)a和b这样的实验句时对句式的限定性特征缺乏敏感性,因而无法通过创建结构空位来区别二者。这显然属于母语(汉语)类语言中的处理策略发生正向迁移所致。因此,与前述(6)中所示的英语母语语法表征不同,本研究中的中介语语法表征很可能具有如下(11)所显示的语法表征模式:无论是限定句还是非限定句,其中,嵌入的子句均为缺乏CP层的TP投射,因而缺乏可以回溯话题成分的Topic P 投射(Rizzi,1997):
(11)a.[TOPICPBooks about himself, [TPJohn expects *[TP(that)Joe will mention< >at the press]]].

b.[TOPIC P Books about himself, [TP John expects [TP Joe to mention < > at th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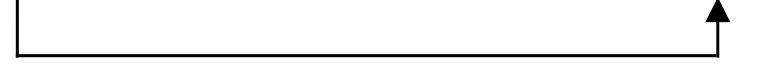
如前所述,本研究中的成人二语组可以把含有反身代词的话题成分视为语义并不确定的变量成分,因此,在句流中首次呈现时被语法解析机制激活后储存在短时记忆中。但由于二语句子处理机制会受到词汇语义线索的引导,因此,(11)中的话题成分在被整合时,两类测试句的加工过程中,二语者均以同样的方式把话题成分直接整合到题元位置上。显然,成人二语者所采用的就是Pickering和Barry(1996)所提出的直接联系的句子处理策略,因此,在(11)a中缺乏具有星号*的位置。与前述(6)相比,二语者对于句法信息的敏感度显然是非常受限的:成人中介语法中,限定性嵌入句缺乏CP语段投射,因此,尽管他们能把移置性成分也能回溯到题元位置上,但这种整合耗时费力,需要支付更多的认知资源。这基本上符合浅结构假设的断言:二语句子处理并不会采用基于短语结构的加工策略;二语学习者对二语句子的理解和消歧主要是基于词汇之间的语义信息或篇章语用信息。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测试以及现有研究中的其他测试都说明,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习得动词的屈折形式方面也可以具备较为丰富的语法知识(比如,能为动词提供各种屈折形式,能给名词指派宾格等)。然而,本研究结果似乎说明,成人二语者并不能把已经习得的形态形式与抽象的结构范畴(限定性句类)联系起来。这种形态形式和句法结构之间缺乏自然联系的表现具有典型的中介语特征:非母语者把词的形态视为与句式类型无关联的孤立现象,因此,即便是在句流中呈现标句词 that,也不一定能触发其解读机制并将所在句式分析为限定性从句,进而将该部分分析为语段单位。而就英语母语语法的处理机制和处理效率而言,句子表达式的推导生成应该以句段(phase)为单位执行,每个句段经由词汇序列以及次序列决定并储存在短时记忆中,而且推导生成的程序必须遵守连续循环性(strictly cyclic)。显然,本研究中的英语母语组对于实验材料的处理过程基本上符合该论断,也表现出如(6)a所示的连续循环性,从而也能够为包含在话题中的反身代词提供两种解读。依据Chomsky(2021)的论断,这种连续循环式解析过程的实现和两种解读的获取都离不开位于CP语段边缘位置的中间空位。事实上,当今的诸多语言学理论都认同的观点是:句法依存关系跨越不止一个子句时,句间必定会具有过渡性的结构位置(intervening clause boundary),即总是具有某种中间性质的语言学结构介于填充词和其终端缺位之间。正是这种中间位置的存在为构建填充词和空位之间的句法依存关系提供了中转站的作用,从而使得母语语法对句子的处理过程更为有效(Filler-gap dependencies are mediated by empty categories at intervening clause boundaries.)。这种中间空位在桥梁类动词选择的句补语中最为明确,如Books about himself, John thinks < >that Joe will definitely talk about < > at the press.这也就是语言学理论分析中通过移位生成的典型句法结构。
事实上,在心理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内,上述填充词和缺位之间的依存关系是研究者们展开实时在线处理复杂句法结构时采用的主要语言学选材标准。目前针对填充词-缺位结构的二语处理研究主要围绕英语类语言中的 WH疑问句和关系结构展开,其中的移位成分往往具有可辨识的移置性特征,即WH成分从句中动词的论元位置上移到句首,而移位动因往往是句法形式的要求使然,因此,这种操作通常被视为不影响句子基本语义的句法信息。由于浅结构假设提出基于句法结构的处理策略并不能被成人二语者充分利用的观点(Clahsen & Felser,2006),因此,近期的二语句子处理研究大多对浅结构假设提供确认或否认的证据,其实证研究也大都以英语类语言中的WH移位为语言材料。
而本研究在测试材料的选择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将限定性特征与移位操作结合起来,从而对中介语表征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法维度。需要指出的是,近期 Yuan(2017)通过增加语种和语料的多样性试图否定浅结构假设:在处理汉语基础生成类话题句(BGT)的过程中,英语母语者既可以利用语义线索也可以利用句法线索;二语者和汉语母语者一样,对语义信息和句法线索都很敏感,对汉语基础生成类话题句的处理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句法处理方式。但是Yuan(2017)的研究理据并不充分,因为其研究材料中,句首的两个NP都没有形态标记显示出其填充词的性质,而且句流呈现过程中也缺乏结构空位,因此,这类基础生成的话题结构并非是检验中介语处理机制的恰当语言学材料。而本研究中的长距离话题中的话题成分不仅采用逗号明确显示出其填充词的性质,而且还有反身成分包含其中,因而完全可以被视为是具有变量性质的非论元成分,而正是这类具有移置性,而且语义也并不确定的话题成分为成人二语句子的处理造成了理解困难。Clahsen和Felser(2006)曾指出,二语者只能采用伪句法分析和浅层结构的处理模式来理解英语句子,因为其中介语语法缺乏本族语表征,并不具备隐性的本族语语法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按照本族语模式来处理复杂句子。而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基本上支持这一论断,英语二语组对于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两类话题句的理解过程中,的确是依据词汇语义信息和谓词论元结构模板来为话题成分确定题元位置的,即为二语句子进行最简单的语义解读并赋予简单的语义表征,并没有为语义表征提供详尽完整的句法表征(without mapping detailed and complet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s onto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可见,英语二语组主要采用基于意义的这种简单处理模式,而非基于短语结构信息来处理目标语句子的。
七、结语
就理论观点的渊源而言,浅结构假设(Clahsen & Felser,2006)的观点实际上延续了本质性差异假说的理念:中介语表现(即便是达至母语水平的二语者)主要是基于词汇语义的连贯性或篇章语用的合理性来实现其二语需求的,而本研究中英语逆向回指话题结构的实证研究为该论断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就本研究的测试材料以及测试结果而言,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处理两类测试材料时受到母语语法类型学特征的影响,即限定性范畴缺乏形式标记的汉语语法表征影响了英语限定性特征在中介语中的表现,因此,他们并不能即时在线区分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句法结构,更不能为二语输入指派恰当的组合规则和语法限制,因为他们缺乏构建二语语法表征所要求的恰当机制。母语句子处理过程的尽快创建空位(以便尽早建立句法依存关系)以及工作记忆中保持填充词的时间尽可能短的处理策略能否在中介语语法中得以兑现理应得到二语研究者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