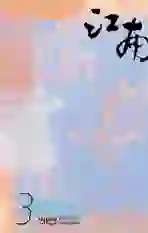冬至
2022-05-06许静
许静
冬至的前一天晚上,崔丽芬又梦见了自己母亲。
母亲站在马路对过的梧桐树下面,朝她招招手。梧桐树的枝叶绵延开去,铺满整个天空。崔丽芬张口喊“姆妈”却发不出声,她努力穿过人群围成的圈向母亲跑过去,母亲却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些陌生的、形状模糊的面孔不断向她涌来。梦醒过来,崔丽芬心肝还在别别跳。救护车尖锐的声音从远处响起,渐强,倏地从空中划过,她又想去小便了。
早上六点十分。崔丽芬在马桶上坐了半个来小时,尿不出来。窗外黑漆漆的,几户早起人家的灯光透过光秃秃的梧桐枝条疏疏地散落下来,还没触及地面便立刻被黑暗吞没了。她蜷缩起身体,膝盖抵在胸口处。下身每刺痛一记,她脸上的肌肉就狠狠回缩一下。起来的时候,腿一麻,一只拖鞋不小心被踢到了洗脸台下面。
外面天微亮起来,太阳还没完全出来,整个天空都裹着层灰蒙蒙的雾。崔丽芬不停地喝水、小便,站在厕所间的窗前发呆。外面有孩童起早上学的声音,都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辆汽车被堵住出不去,哔哔哔发出刺耳的喇叭声。立刻有人高声咒骂,梧桐枝条也像受了惊惶,噼啪打着窗户。人们从单元楼里进进出出,向生活飞奔而去,融入寒风中。崔丽芬从来记不清他们的面貌。
崔丽芬在这房子里住了五十年。头三十年与母亲一起住,母亲过世后就剩她一个人。这些年四周都建起了高楼,她这片矮房就像掉到了井里。她又住一楼,白天也见不到多少太阳光,大多数时候黑黢黢的。老邻居很多已不在或搬走了,这一片是学区房,又搬进来很多带孩子的年轻人。崔丽芬曾经上中介那里打听过,她这个房子能卖两百万,就打算卖了房子去住养老院,可回到家想想又后悔了。
不远处转出一个矮墩墩的人影,崔丽芬转过身拖着一只光脚从厕所间出来换了鞋,到镜前梳洗。崔丽芬一张方脸,高颧骨,从侧面看有点像演员陈冲。这副面相年轻时显老,老起来反倒显年轻了。每个早晨,她都会用雪花膏把这张脸擦得喷香;眉毛弯弯细细,乌中带青,是老底子的那种样式;齐耳根的短发染了棕色,烫成泡面卷。为保持身材,她不吃肥肉,又吃十几种营养保健品。
小杨四十来岁,在这一片做社工已有十多年,是个看上去很和气的东北女人,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崔丽芬这里来一趟。崔丽芬总觉得如果自己有女儿,肯定会比小杨更漂亮一些。小杨夹了一只大包进门,一张圆脸潽出羽绒服外面,说:“阿姨,冬至给你包了点饺子。”
崔丽芬乜斜着小杨,说:“你们北方人冬至吃饺子,我们这里吃年糕的。”她心底里有些瞧不上小杨这些外地瓜佬儿,但每次又盼着小杨过来。
“我把水饺给你放到冰箱里冷冻,你拿出来烧很方便的。”小杨憨厚一笑,自己拉开冰箱。老式的华日冰箱时不时就发出吃力的嗡嗡声,好像一个不停抱怨的老人。冷冻层结了很厚的霜,被速冻食品塞满了;冷藏箱里是各种腌制食品以及可以速热的饭菜,葱姜也按照每次的用量用保鲜膜包起来。
小杨一边往里塞饺子,一边咕哝,“阿姨,你家冰箱里的东西太多了。”
“这样我心里安耽。就怕万一出什么事我不能出去买东西。”
小杨又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她回答:“老样子。”
小杨说:“今年冬天真冷,好像晚上还要降温。五幢里的陈大伯早几天走了,这个冬天已经第几个了。”
“有老话的,阎王来收人,老人难过冬。”崔丽芬看着窗外,一只麻雀在外面的枯树枝上跳来跳去。
“天这么冷,你还出去跳舞吗?”
“老早不跳了。”
说到这里,崔丽芬想起自己上一次去跳舞的时候,红太阳广场的音乐喷泉还在为庆祝国庆节播放《我和我的祖国》。
她五年前的春天开始去那里跳舞,第一次是被老姐妹带去的。她不喜欢广场舞,嫌土气,这里跳的是交谊舞,双人跳的。跳舞的男同志少,会跳舞的男同志更少,而且早都是有舞搭子的。剩下都是些歪七歪八的老头子,拿着保温杯靠在栏杆边看热闹。有次一个女人穿黑色丝袜来跳舞,崔丽芬听见两个老头在旁边议论,这个腿,好去电视上做广告了。
崔丽芬屋里头待不住,早上就出去跳舞。一开始没有舞搭子,她就一个人站在后面跟着人家跳。崔丽芬跳舞的时候,举手投足颇有些风韵。她蹬一双仿中跟皮鞋,随着音乐的变化一下一下踩出步点。
脚上的功夫,是她在学校文宣队里练出来的。为了跳上喜儿,家常的布底鞋,她站坏了好几双。脚指头破了,涂上药水、贴上橡皮膏继续跳。她羡慕芭蕾舞鞋,就仿照画报上的样子,用两根带子缝到鞋子上,再绑到腿上,两条腿勒出乌青。
第一次跳上喜儿,是跟文宣队去农村演出。那天她坐在同伴的自行车后座,穿一件阿姐的蓝卡其,袖子卷起两圈,翻出里面白衬衫袖边,两支麻花辫拖到胸口。自行车出了庆春门,越过铁路,骑上乡间小道。旁边是整块整块方方正正的稻田,风一吹,稻浪好像旗帜一样上下翻动,她鼻子底下全是稻田的香味。
红太阳去跳了几次,一个男人走到她面前站定打量。崔丽芬斜眼朝他一扫,男人戴一顶黑色皮面贝雷帽,身上一件深红色衬衫,外面套着黑色小马甲,蛮时髦的样子。就是脚上一双不黑不白的旅游鞋有点掉价。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梁雁翎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响起来,崔丽芬走到前面去跳舞。
“神经病,这样看。”她觉出他的注视,在心里暗骂。
“你一点没变,还是噶好看。”男人脸皮实厚,仍然跟在她旁边。
崔丽芬绷着脸,没去搭理他。
跳舞场上这种男人很多,专门来吊膀子的,要么骗钱要么骗色,崔丽芬对这種人向来没有什么好脸色。
“你不认识我啦?”男人在崔丽芬旁边说,旁边几个跳舞的同伴朝他们这里看过来。崔丽芬想尽早摆脱他,她借着舞步闪到旁边去。男人也跟上来,他不由自主伸了几下手,妄图想要抓住她,却什么也没抓住。
“我谢天明啊。”他说。
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崔丽芬又别过头去看。看清了他的样貌,忽然说了声:“哦哟!”
道路边的梧桐树叶,在春天刚刚出芽。天空浅蓝色,云朵舒展开来,阳光照在梧桐树上,嫩芽闪出金光,一颤一颤的……
小杨费力塞好饺子,又从包里拿出几张碟片,递过来:“我给你录了好几部韩剧,你有得看看了。”
崔丽芬家里的碟片播放机,是十多年前外甥回国时给她买的。以前弄堂口有个租碟店,崔丽芬在那里办卡借韩剧碟片,后来店倒灶了。关门的时候,老板送了几套碟片给她。她最喜欢看《大长今》,反复看了好几遍,一直到碟片再也播放不出来。“没想到这种东西也有寿命啊!”那天她拿着坏掉的碟片,在心里这样嘀咕。
小杨问她:“阿姨,你喜欢哪个欧巴?”崔丽芬扑哧地笑了,说:“那些欧巴都好做我孙子了。”
说到这里,崔丽芬又说起年轻时很多人追她。当年的追求者,有的当官了,有的发财了。其中一个追她的,高鼻梁,深眼窝,像电影明星,后来和一个乡下女人结婚了……
小杨感叹:“要是生活像电视剧一样就好了。”
“要活成电视剧做啥,一辈子过过很快的。”崔丽芬说,“各人有各命,那辰光如果我不用照顾我姆妈,说不定也老早就结婚了,如果那辰光结婚,伢儿都有你噶大了。”话一说出口,崔丽芬就有点后悔了。她也不知道今天自己是怎么回事,忍不住要跟小杨讲起这些陈年不古的事体。
小杨敷衍地听着,哦了两声没有在意。这时手机响了,她到旁边去接电话。过了一歇,小杨进来说:“阿姨,我还要去趟陈大伯家里,代表社区去慰问一下。陈大伯还是福气好的,儿女一直陪到最后。前几天新闻里讲,哪里有一个老头子没了,一个多星期才被人发现。”
说罢,她又从包里掏出钥匙,放到桌上,说:“月底我妹妹结婚,我要回趟老家。这段时间就不過来了,这个钥匙先还给你。”
崔丽芬没动。
“你要是不放心,我让同事每个星期往你这里打一次电话。” 小杨安慰似的又说了句。
崔丽芬说:“钥匙你放到门口的水表箱里去吧。”
“年底了这样不安全,这里又是老小区,外面也没有装什么防盗门。”
小杨走了。崔丽芬把钥匙扔进了方桌的抽屉里。
到九点钟光景,太阳才从对面高楼转出来一角,发出一圈淡白色的光。镜子连着大衣柜,崔丽芬一样一样搬开衣柜前面的东西,几大箱保健品,一只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用的净水器和一个不太灵光的理疗仪。
她在镜前拧开口红盖,谨慎地避开嘴唇破皮处,一点一点,动作小心,好像在做什么精细工作。镜子里,鲜红的口红与灰紫的嘴唇形成一道细微的边界。
接着又换上一件藏青呢大衣,是她退休那天去百货大楼买的,花了六百八十块,只穿过一次。那天是送阿姐出国,过安检口的时候阿姐捏着她的手说:“芬芬,对不起,姆妈就交给你了。”阿姐说一个字摁一记。阿姐出国后,来过一次信,说了些想念以前的话。姆妈的追悼会外甥赶回来了,崔丽芬和他一起把母亲安葬了。
为搭配藏青大衣,崔丽芬找出条玫红尼龙围巾,又从鞋柜里取出一只鞋盒,里面一双白底蓝花软底皮鞋。但她脚尖肿着怎么都穿不进去,好不容易脚尖进去了,脚跟又露在外面。脚肿得厉害,仿佛涨满了水,已经明显超出了鞋子的尺寸。她只能重新把鞋放进盒子,用脚踢进床底下,一直踢到看不见的地方为止。
崔丽芬出门穿过小区中心花园。五幢前面搭了棚儿,一只硕大的白色花圈迎面而来,她急急别开脸,低头快速穿过那里。走到公交站,车子刚刚过来。崔丽芬靠窗坐,经过“红太阳”的时候,透过车窗看见有人在那里跳舞,有几个是她熟悉的身影,但叫不上来名字。
崔丽芬开始和老谢搭档跳舞的时候,青色的梧桐果悬挂在枝上,像一串串风铃。跳了几次,老谢就告诉她,他和老婆关系不好,老早分开了,他现在一个人住在武林路上的房子里。
“你呢?”老谢问,“也离婚啦?”
崔丽芬笑笑。
休息喝水的时候,老姐妹凑到崔丽芬耳朵旁边,说:“你们两个倒是蛮配的。”
崔丽芬拧上杯盖,说:“我是来跳舞健身的,又不是来寻男人的。”
跳吉特巴的时候,老谢带着崔丽芬。他掌心有些泛潮,指头冰凉。另一只手触摸到她的腰上,虎口恰抵在她的腰肢,崔丽芬闻到他身上有股黄酒混合着樟脑丸的味道。他们随着节奏快速旋转,每一次重心的转移,他都稳稳接着她。指尖挑着一缕阳光,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甩出半个光圈。
崔丽芬和谢天明是在学校文宣队认识的,第一次说上话却是那次去农村演出。崔丽芬上台跳喜儿,跳大春的同学临时拉肚子不能上台,找不到人代演,他们的节目就要被取消了。
崔丽芬哭丧着脸坐着,瞪着脚上的新鞋。这是双白色塑料底的黑面方口搭袢鞋,庆百前一天刚到的货,姆妈就托人给她买回来了。
那天下了学,崔丽芬就看见姆妈双手捧着鞋盒站在门口的梧桐树下,梧桐树的毛絮在她头上落下好几簇。鞋盒上,画着一只飞舞的燕子。姆妈把鞋盒交到她手上说,学费延迟再交,我们喜儿怎么能没鞋穿?晚上,阿姐从厂里下了中班回来,姐妹俩便轮流换上新鞋在地上跳舞,一直跳到隔壁人家敲板壁,她们才作罢。
“崔丽芬,你们到底还跳不跳?”报幕的进来问。
谢天明刚说完“三句半”下来,他掀开帘子,说:“我和她一起跳。”她欣喜,回过脸去看他,他却没再看她,已经走开去换衣服了。
他们在台上跳喜儿和大春重逢的一段。崔丽芬在台上大跳,旋转,疾走,一头白发在身后飞舞。谢天明演的大春从外面进来,认出喜儿后握住她的手,同她一起跳。他的手结实又有力,原始的力量让她觉得自己是一只轻盈的燕子。他们逐渐默契起来,竟比原来的搭档更加默契。他们的动作因此更加大胆了,也更有了自信,当他再一次稳稳托着她的时候,她嗅到他身上浓重的汗味。塑料底的鞋子在舞台上踩出啪啪啪的声响,崔丽芬内心像是被什么点燃,就连最细微的喘息也能让这火焰喷发出来。他们就这样不停地跳着,那一刻,崔丽芬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喜儿,谢天明就是她一直等着的爱人。
下了台崔丽芬向他道谢,谢天明对她笑,一颗汗珠顺着他的脖子流进的确良白衬衫里。其实她的头发也湿了,一绺一绺贴在脖子上,粘得她痒痒的。他的笑容有些羞涩,却一下子照进十六岁的崔丽芬混乱的内心。她看着他,盼望着他能再对她说一些什么。这时几个女生一起进来,谢天明转头对她们讲起笑话。崔丽芬看到这里忽然放心了,却也失望了,她为自己的自作多情很是懊恼了一阵。后来她和谢天明偶尔还在文艺汇演的时候遇见,却再也没有什么交集。
“红太阳”的跳舞队组织去乌镇搞活动,老谢带了单反照相机去。女同志们缠牢他,她们挥舞着彩色丝巾要他拍照。老谢也不拒绝,不停地给她们拍。崔丽芬坐在逢源桥上,老谢也要给她拍照。崔丽芬佯装生气,让他去给其他人拍。
老谢说:“你不喜欢我给别人拍,那我就给你一个人拍。”
逢源桥左右两边,中间一道雕花木板。崔丽芬走一边,老谢走另一边。崔丽芬望过去,木板恰好遮住了老谢半张脸。什么左右逢源,还不是隔着一道墙?崔丽芬心里想。天空开始落毛毛雨,细细密密落在河里,水晕一圈一圈荡开去。
活动结束时大家聚餐,那些女同志就盯牢崔丽芬,目光好像盯着阶级敌人,崔丽芬很讨厌这样的目光。然后,她们之中就有人开始隐隐约约向她打听她和老谢的关系。
“一个人以后到了养老院,瘫在床上,看护不给你喝水不给你洗澡,很惨的。子女再好,不如有个老来伴,吵吵架儿也不要紧,要求不要太高。”女友又试探着问,“你和老谢走到哪一步了?”
崔丽芬的脸霎时发热起来,好像做了什么坏事被人捉了正着。她的喉咙有点发抖发紧,仿佛一开口就会泄露出秘密来。话语在喉咙口来回滚动了半天,她用一种不同寻常的高音说:“我又不寻人,要寻也不寻他这种的。”
乌镇回来的晚上,崔丽芬回家,老謝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安全到家,我就放心了,再会再会。
脱衣服的时候,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一张纸。崔丽芬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封信。信里只有一段话,用铅笔写的,像是从什么诗里抄来的。她匆匆看了一遍,心里就模糊有了答案。她立刻像做贼一般把信叠了塞进桌下的抽屉,又抬起头,视线转向旁边每一扇窗户,好像害怕窗户外有人正在偷看。洗漱了出来经过方桌时,她忍不住拿出来又读了一遍,果然看见落款处写了一个“谢”字。真当肉麻,崔丽芬心想,不过又是有些欢喜的。那个夜晚,崔丽芬不停地翻身,窗台底下的野猫发出一声声暧昧不清的叫声,搅得她心烦。
第二天早上老谢又来电话了,约她出去下馆子。
崔丽芬低声说了句:“十三点。”挂了电话,转身就涂了口红出门。
老谢请她在延安路上的知味观吃饭,点完菜老谢又要了一瓶黄酒,接着他从包里拿出来身份证和户口簿。户口簿是武林路的地址,上面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按照他的说法,老婆老早离婚了,两个女儿结婚都迁出去了。一个女儿在国外,另一个女儿也在外地。
“只要你点头跟我一道,我就把你户口迁进来,有了户口,你以后也有拆迁补偿款的。”
老谢门牙处套一排假牙,讲起话来就松动。
“十三点,哪个要同你一道!”崔丽芬骂他,接着又说,“你不要想打我的主意,我没有伢儿,我这套房子老早给我外甥了。”
“吃好饭,到你房子里去看看好吧?”
“为啥要看我房子,我们啥关系?”
老谢嬉皮笑脸说:“我晓得你对我有意思的。”
他咪一口老酒,接着说:“我每个月留一千块钱零用,其余都归你,以后你当家。”
“你想养我啊?”
老谢说:“我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没老婆,没人关心的。”
崔丽芬讪讪道:“这个年纪我们都要自己管自己,身体第一。”
她夹了一只小笼包到他面前的小碗里。
她开始注意打扮,头发烫了卷,指甲涂上红色,指尖的桃花霎时一朵接一朵地开了。
母亲以前就常讲,女人家一定要学会打扮。她总是将女人的命运与打扮紧密联系起来,并时时告诫两个女儿。那年冬天,月经刚刚从崔丽芬身上消失,母亲的记忆也倏然飞走了,她时常认不出崔丽芬,但却仍然记得自己的这句警句。
母亲因为多年前的脑梗塞导致右半身瘫痪,崔丽芬每天要为她吸痰,按摩。母亲整个人干缩在方桌前面的躺椅上,脖颈那里的皱褶一叠一叠的。尘埃在阳光中缓慢集合,在她后面形成一道肮脏的彩虹。她忽然从打盹中惊醒,用混浊的双眼看着崔丽芬说,你也要好好打扮,去寻个对象来!崔丽芬回她:“我也去结婚,哪个来照顾你?”
道路两边青色的梧桐果成熟了,变成了棕色,毛茸茸的球果爆裂开。风一吹,空气里都是飘浮的黄色毛絮,好像无数精灵,飘在崔丽芬周围,企图窥视着她最最隐秘的活动。崔丽芬跳舞的步子仍然轻快,却变得杂乱。她时常方寸纷乱,思绪不宁,一种莫名其妙的窘态让她变成了笨手笨脚的样子。
老谢给她买了鞋,原价一千多,老谢老实告诉她是打了五折买的。崔丽芬舍不得穿,一直放在家里。转天她送了老谢一块表,浪琴牌的,五千多块,是她一个多月的退休金。老谢天天戴着手表到人家面前显洋,好像自己是什么成功人士。
崔丽芬开始变得尿频尿急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发展到后来,连续好几个晚上,她起来上厕所发现尿里有血。她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膀胱癌。她不信,拿了报告单,又去别的医院检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医生告诉她,她是高级别浸润型膀胱癌,极易复发和转移,需要切掉整个膀胱,终身戴尿袋。
“一开始可能是不太方便,不过时间长习惯了就好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劝慰她:“阿姨,这个病做了手术,治愈率还是很高的。之后只要保持好生活习惯,三五年肯定没问题的!”医生说得很流利,也很诚恳,大概每个患者他都会这样说一遍。
崔丽芬不说话了。她多体面一个人啊,怎么能挂着尿袋到处走?
医生最后嘱咐她:“你回去和家属商量一下,尽快做手术吧。”
崔丽芬好几天没去跳舞,老谢给她打电话她不接,信息也不回。再去的时候,她故意和别人跳。老谢不高兴,把她拉到旁边。崔丽芬生气了,说:“你以为我在做啥,我跳舞是为健身,又不是勾引男人。”
老谢比她更生气,转身就走。过了一歇,又折返回来。他努力挣扎了一番,开口问她:“你究竟对我有啥意见?”
她没提防他还会回来,喃喃地回答:“没意见。”
老谢离开的时候,崔丽芬瞪着他的背影发呆。她头一次觉得这个背影很陌生,他的后脑勺仿佛蒙了霜,发色透出一层灰,后背衬衫后面隆起一道皱褶。
老谢不再给她打电话,她心里多少觉得有些对不起他。十月份的时候,她又去了一次红太阳,没碰到他,一起跳舞的人说,老谢有段时间没来了。再后来,就是前几个星期,她听到老谢出事了。那天晚上她刚刚吃好饭,就看到新闻里讲,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家人一星期后才发现。崔丽芬打老謝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老谢给她发的上一条信息是在四个多月前,问候她过得怎么样。崔丽芬坐在电视机前面,捧着手机忽然哭了出来。
她以前常听老谢提起武林路的房子,却从没有去过。崔丽芬从公交车上下来,沿着一路的梧桐树拐进弄堂。弄堂越走越逼仄,头顶纵横交错着电线,把天空分割成一块一块。
崔丽芬走上四楼,门是开着的,门口堆满打包好了的东西。进门正当中央,挂着一张老谢的黑白照遗像,是他年轻时的模样,高鼻梁,深眼窝,像电影明星。
崔丽芬看着相片发呆,这时候一个女人拿着扫帚过来,问她:“你哪个啊?”
崔丽芬说:“我是谢天明的朋友。”
“我阿爸早两个礼拜前没的。”
“我晓得的,我过来看看。”崔丽芬把准备好的白包交给她。
那个女人“哦”了一声,接过白包,让崔丽芬进屋坐。房间里面乱七八糟,女儿正在收拾老谢的东西。崔丽芬偷偷打量老谢女儿,宽脸盘,细眼睛,和老谢长得不像。崔丽芬低下头,心里隐隐生出些庆幸。
“我在外地上班,放假才回来一趟。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哪里晓得阿爸老早已经跌翻在家里面了。”老谢女儿在那里絮絮叨叨,这句话她肯定已经对人解释过很多次,“是脑溢血。”她又补充了一句。
崔丽芬起身要走,一眼瞥到放在桌上的表。她认出来,就是她送给老谢的那块,应该是从老谢手上摘下来的。崔丽芬想去拿手表,手刚伸过去,就被老谢女儿抢先一步拿走。
老谢女儿警惕地瞪着崔丽芬,手里仍然握着扫帚,骂道:“什么人,死人的东西也偷,信不信我马上报警。”
崔丽芬嗫嚅着:“这个是我送给他的。”
老谢女儿抬头看看她,目光忽然变得凶狠起来,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她抬手打了崔丽芬一个响亮的巴掌,骂道:“我还以为是哪个,原来是你这个婊子!你给我滚出去!”
崔丽芬被打得向后退了几步,她扶着墙,拼命想要站定。
“人都被你害死了,快给我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你阿爸死掉同我啥关系?我们都好几个月没联系了。” 崔丽芬被推到门外,但是眼睛仍然直直盯着眼前的女人。
“你以为我们不晓得,天天勾出去跳舞。年纪噶大还要做小三,破坏人家家庭。”紧接着,老谢女儿把手里的扫帚扔出来,撞到崔丽芬腿上。
楼道里灌满了风,崔丽芬的耳朵里都是尖锐的风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隐约的碎裂声,似乎来自窒息的胸腔。巨大的风暴将她整个人卷起,就像卷起一根枯树的断枝。
“你说清楚,什么破坏家庭?”崔丽芬听见自己的声音闷闷的。
“滚出去,滚出去!”老谢女儿突然关门,动作粗暴,崔丽芬猝不及防,手指险些就被夹到。
动静闹大了,几个邻居上上下下过来看热闹,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崔丽芬被围在人群当中,她的眼睛木然地从周围一张张陌生的脸上转过去。她张大了嘴,像是想要大哭或者大喊,但是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崔丽芬瘸着一条腿从老谢的楼里出来,脚掌被冻得硬邦邦。走在弄堂里,前面两只狗正在打架,一声声狗吠让人心惊。老谢女儿尖锐的声音不断在她耳畔回响:婊子,婊子,婊子;一会儿又成了母亲殷切的念叨:寻个对象来,寻个对象来,寻个对象来;最后成了老谢的声音,老谢说,我不给别人拍,我就给你拍。崔丽芬站住脚步,忽然回头,弄堂口空无一人,日光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最后折在一面斑驳的墙上。
街边没有红绿灯,崔丽芬站着等待过马路。冬日里的阳光薄到透明,梧桐树的叶子只剩下最后几片,不规律地吊在树枝上,从树杈望上去,天空好像被打上一块块灰绿色的补丁。路上无数的人和车,鱼一样游来游去,从建筑物中穿梭往来。盯得久了,形状模糊,竟不真实,仿佛他们始于某一处的旧时光,即将要去另一处的未来。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崔丽芬从冰箱里拿出饺子下锅。以前姆妈在的时候,总是会说,冬至大如年。冬至的早上,姆妈一定一大早出去买年糕。早上白糖蘸年糕,中午油墩儿菜炒年糕,晚上一顿雪里蕻汤年糕。崔丽芬正长身体总是觉得吃不够,便偷偷把阿姐的年糕舀几块到自己的碗里。
晚上八点,电视上正在播放电视剧。崔丽芬收拾了碗盏,吃下止痛药。她从抽屉拿出钥匙放在桌上,像个放大的惊叹号。她记得,这是这个房子配的第三把钥匙,第一把是黄铜的一字钥,有次她下班忘带钥匙走不进家,就特意另外又配了三把,一把交给姆妈,一把放到阿姐那里备用,一把给了她的小外甥;后来换成开防盗门的十字钥匙,姆妈已经不在了,阿姐卖了国内的房子跟儿子出了国。几年前十字钥匙不小心断在了锁眼里,就连着锁一起换了。
崔丽芬躺在床上,重新读了一遍阿姐的信。虽然每天都读,但每次还是总让她想起以前的事。关上灯,困不着,又出不去。她仰天看着天花板,感觉腰腹的疼痛跟针刺似的,密密麻麻把身体刺出一个一个的小窟窿,水分就从这些窟窿里头一点点地蒸发、消失。
崔丽芬把老谢的名字从通讯录里删掉了。她又去把门锁拉开,只闩上了上面的链条。这样即使自己倒下了,还有人能用工具弄断链条把她弄出去吧,她在心里想。忽然之间,一阵难过袭来,胸口好像豁开一个巨大的空洞,能把一切都吞噬进去。
死的时候,大概就我一个人了吧。
对面高楼霓虹灯的光亮投射到天花板上,红黄蓝绿的光斑,像花花绿绿的糖纸,又像万花筒。外面隐隐约约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歌词大概是: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
窗外,梧桐树的秃影子贴着窗户晃动,空气里忽然有股稻田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