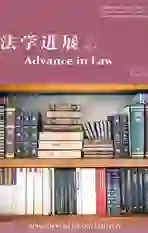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建设
2022-04-29胡遥远
胡遥远
摘 要|在 2015 年民诉解释出台之前,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明标准的适用始终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2015 年民诉解释第 108 条和 109 条的立法意图就是将混乱的证明标准统一起来,而自从解释出台后,学者们对于证明标准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且普遍认可了第 108 条所确立的一般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第 109 条所确立的几类特殊情形下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的提高或降低近年来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但学者们普遍得出了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的共识。本文以民诉解释第 109 条为基础,重点论述特殊情形下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并以劳动争议诉讼这一特殊情形为主要论述对象,提出劳动争议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与一般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有所区别,意图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 年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首次明确了民事诉讼法领域的一般证明标准 为高度盖然性标准,在民事诉讼证明领域意义重大。在该解释中除了对一般民 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确立,还对于两种特殊情形的证明标准予以提高至排 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向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看齐,而这一证明标准的提高也 是理论和实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下文除了对特殊情形下的证明标准进行分析, 同时也以我国的劳动争议诉讼为例,主张在劳动争议诉讼领域降低证明标准。 由于我国对于劳动争议诉讼并没有设置程序特别法,实务中,劳动人事仲裁委 员会和法院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性事项一般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所以在确立劳动争议案件的证明标准时,也通用的是民事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但是,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从案件的性质角度以及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均与一 般民事案件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劳动争议双方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能够获 得诉讼资源的渠道和可能性、付出的成本等等,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考虑 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时应当与一般民事案件加以区别,并以构建多元 证明标准框架为最终目的。
二、对民诉解释第 108 条和 109 条的反思
(一)确定一般标准的意义
在出台 2015 年民诉解释之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证明标准领域的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参照的是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 73 条的规定 a。由于该规则中并未明确出现证明标准的有关字眼或具体标准,所以只能依最高人民法院时任大法官的解释,将此项规定认为是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但是通过该条规定的文义解释,我们只能得出有关证据的取舍的规定,而并不是待证事实的证明,同时,法官对于高度盖然性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标准应用。
正是由于上述缺陷,2015 年民诉解释的第 108 条a 以法条形式明确了举证责任以及人民法院对真伪不明的待证事实的态度。对该条规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 得出108 条分别从本证与反证的角度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明确,具体来说, 将“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作为本证的证明标准,该标准也可以认为是法 官内心确信的程度,而反证的标准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即认定该事实不存 在。”以动摇心证为其证明标准,符合民事诉讼证明的一般原理。从该条规则 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逐步构建起了二元的一般证明标准。
(二)特殊证明标准
民诉解释第 109 条的规定列举了五种特定情形下的证明标准提高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该五种特定情形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的事实,另一类是关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
对于第一类事实,笔者以为提高其证明标准似为不妥,有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以《民事诉讼法》第 112 条b 所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法律对于恶意诉讼无疑是持严厉打击的态度,但 109 条的第一款规定提高了原告也即受损害方的证明程度,而这无疑与第 112 条背后保护受损害方的立法目的和是不相符的。其次,具体到实体法律规范中,《合同法》第 52 条和第 54 条c 是关于认定合同《合同法》第 54 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无效以及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但是在认定合同无效以及可撤销的表述中并没有使用明显地、显然、确实构成欺诈胁迫等具有明确确定性的字眼进行要求。所以也可以认为民诉解释对于两类特殊情形证明标准的提高缺少了实体法依据支撑。最后关于此类恶意诉讼的事实证明标准的提高,使得原被告之间的证明负担不对等,原告往往作为受害者的身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却极大地增加了原告的证明负担,不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
而对于第二类事实,即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情形,提高其证明标准有其合理性。笔者在这两类情形下认同适用该证明标准最大的原因在于从这两类情形的本身特性来看对于双方的诚实信用程度具有极大考验,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双方证言相互矛盾的情形。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提高证明标准至排除合理怀疑有利于查清真相,维护公平正义。具体来看,在口头遗嘱的情形下,由于口头遗嘱具有易篡改、易伪造的特征,并且我国《继承法》第 17 条a 对于口头遗嘱的成立也有其特殊要求。从法条内容来看口头遗嘱的成立及生效要件相当严格,所以以一个相对较高的证明标准门槛作为口头遗嘱情形下的证明标准也符合口头遗嘱的特殊性与成立条件的严格性。而真正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得到保护从而有利于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设并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减少讼累提高效率。在赠与事实情形下,由于双方当事人仅受一般道德价值观念的约束,赠与行为的认定对于双方的诚实度信用度是个极大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产生纠纷若被告不能拿出充足证据证明赠与事实的发生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就应当认为该赠与事实不成立,该证明标准的提高对打击虚假赠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从而保护了真正的受赠人的合法权益。
三、一般证明标准在特殊类型案件中的适用的不合理性——以劳动争议案件为例
虽然 2015 年民诉解释已经注意到了几种特殊情形下的证明标准与一般证明标准的区别,然而除了第 109 条所规定的情形,在其他的特殊情形中仍然以一般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为一般证明规则,而一般证明规则的适用对于某些特殊民事诉讼的类型就体现出了其缺陷与不足。在一般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具体适用体现为对于同一事实,当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意图证明的事实相反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判断,若一方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的证据的证明力,即应当认定证明力大的一方证据所主张的事实。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基于很多案件类型的特殊性,单纯的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具有很多不合理性。下面以劳动争议案件为例,虽然劳动争议案件在诉讼阶段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同时适用的也是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规则,但笔者认为运用一般证明标准来处理这类案件对于当事人双方,尤其对于劳动者一方来讲并不公平, 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理论基础
首先从劳动法的内容和其特征来看,许多制度的设置具有公法的特征, 例如劳动关系的建立、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具体规定、劳动条件等都由法律直接规定,若将调整平等主体的私法法律直接适用于这些制度规定,显然与其公法的调整方法不相符合。其次,从主体来看。民事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具有相互平等的法律地位,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也是对等的,地位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而具体到劳动关系领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以平等的法律地位来看待,或者说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关系。劳动者依附于用人单位,受用人单位的制度制约,显然若直接将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作为劳动关系的调整规范将会有所缺陷。最后从法律调整的客体范围来看,民事法律主要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而劳动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内容上除了调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还会涉及非财产关系,例如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制度等等。
从上述劳动法与一般民事法律之间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在劳动争议中适用一般民事法律缺乏理论基础,并由此得出在劳动争议中适用一般民事证明标准的不合理性。
(二)不符合实质正义
在近代民法的理念中,正义一般表现为形式正义,而形式正义仅着眼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是公正的,就认为在具体当事人之间实现了正义。形式正义的理念得以确定的两个基本逻辑前提是平等性和互换性,同时这一理念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a 然而梁慧星教授指出,二十世纪以来,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企业方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劳动者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弱者。许多用工单位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条件、安全条件和卫生条件,在雇用契约中订入各种苛刻的、违法的条款,实际上双方经济地位和实力对比悬殊,并无实质上的平等,迫使弱势方劳动者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b 而劳动争议的最终追求则是实质正义,强调调整后的结果的内在公正,所以劳动争议追求实质正义的理念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形式正义理念。
(三)可能造成案件处理不公的现象
普通的民事案件的举证规则一般为“谁主张,谁举证”,以普通的借款纠纷为例,原告用以主张借款事实存在的往往是借条或其他用以证明存在借款事实的证据,而若此时被告拿出了相反的证据例如原告收到借款的收条以证明其已还款,则此时待证事实就进入了真伪不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可以利用结果责任和高度盖然性标准判决原告败诉 c。然而在劳动纠纷中,往往涉及的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在劳动报酬、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纠纷,此时最常见的证人证言的来源一般是用工单位的其他员工,基于其他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的雇佣关系,劳动者一方往往陷入举证困难的境地。此时若法官继续依照高度盖然性作为判断标准似乎与实质正义并不相符。因为一般都是与劳动者有切身重大利益的事项才会涉及劳动纠纷,若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作为用人单位的证明标准似乎偏低,不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造成案件处理不公的现象。
四、劳动争议证明标准区别于一般民事诉讼的合理性辨析
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对于调整劳动争议类型的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笔者建议将劳动争议诉讼的证明标准与一般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区分,认为这是解决劳动争议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的可行路径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将证明标准进行区分是具有操作性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后,二者之间就具有了上下级特点的隶属关系,如何倾斜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并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使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是劳动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由于双方举证能力不平等,对双方的举证能力进行平衡的方式之一就是降低特定案件的证明标准a。在论证这一证明标准的合理性时,这里就以确认劳动关系案件这一实务中常见的劳动争议诉讼为例。首先从形成证据的能力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针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劳动争议,显然相较于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形成证据的能力。用人单位通过与劳动者签订管理文件,从而保留了各项文件中的内容作为证据,并且证据来源并不仅仅限于书面的劳动合同,同时对劳动者的日常管理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用人单位如果规范处理和管理各项文件规章,在纠纷中提出反驳证据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并不是难事。在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也不仅仅是书面劳动合同一种形式。对比来看,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劳动法律中,例如德国法对劳动合同就没有书面形式的要求,而是以赋予雇员有要求企业制作关于其主要劳动条件的书面证明的请求权所替代。除劳动合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社会材料可以辅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例如员工名册制度、纳税登记及社会保险的征缴记录等等都可以证明劳动关系存在。
具体到我国法院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司法典型案例的研究中,用人单位通常没有做到规范的管理和严格依法用工,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对劳动合同的某些条文性质进行偷换概念,以此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如最高法院于 2019 年发布的公报案例江苏某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曾某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a。本案的用人单位主张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但本案的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并不符合劳务合同的法律特征,而是与劳动关系法律特征相符。在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有充足的能力形成证据,而形成证据也是其法律义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涉诉的劳动纠纷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用人单位怠于履行形成证据的义务。对于用人单位的这种懈怠,不仅要在实体法上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 还需要同时在程序法上对其进行制裁。适当提高用人单位的证明标准就是一种合理的程序法上的制裁手段,对于用人单位没有履行法定证据形成义务而导致劳动者无法掌握证明力较强的证据,或者用人单位主观上就没有使劳动者掌握关键证据的态度,对劳动者提出的关于搜集证据的请求持有消极的态度。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必要认可劳动者手中已取得的证明力相对较弱的证据。在这种程序法的制裁之下,当涉诉的是严格依法用工且管理规范的用人单位时,劳动者可以通过举示劳动合同,而对于一些依其个人能力无法轻易取得的证据,则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据来证明劳动关系已经建立 b。而当劳动者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时,用人单位以其所掌握的证据很容易提出反证进行反驳,这样就平衡了双方的证明能力,从而逐步减少确认劳动关系争议的出现。
上文虽然仅以劳动关系的确认诉讼为例论述了区分证明责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在关于劳动争议诉讼的其他类型争讼中,区分证明责任的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五、对证明标准在劳动争议处理中进行再构造的建议
将普通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适用于劳动争议诉讼中既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不能平衡劳动争议双方的法律地位,所以笔者主张应该将证明标准在劳动争议中的适用进行调整。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将劳动争议诉讼分为劳动者诉用人单位以及用人单位诉劳动者这两种情形下的证明标准分别予以讨论。
(一)用人单位诉劳动者应当适用区别于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虽然实务中用人单位诉劳动者的情形相较于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的情形并不具有常态化,但对于一项制度或者规则而言,能够尽可能地将所有可能的情形考虑完整是制度本身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之所以提高了用人单位诉劳动者的证明标准,理由主要有二。首先,在普通的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用人单位支配着整个生产过程、工作场所以及劳动者。而用人单位的这个支配地位结合危险领域说以及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强弱,可以得出,当损害结果发生在用人单位所支配的场所中时,证明责任应当发生转移,应由支配者承担对故意、过失、因果关系等要件进行证明。其次,从劳动关系双方离证据的远近程度来看,用人单位离证据的距离比劳动者离证据的距离更近。这里的离证据的距离指的是当事人获取证据的难易程度以及举证的难易程度 a。一般来说,距离证据更近的一方应当承担更重的证明责任,而在证明标准领域中就体现在证明标准的提高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用人单位在劳动争议诉讼中适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应该比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低。 如果一味地提高用人单位的证明标准至刑事诉讼中严苛的证明标准,则会产生民刑交叉等一系列问题,劳动争议诉讼从其本质上来说还是民事诉讼,所以笔者并不主张将用人单位的证明标准提高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将用人单位的证明标准提高至笔者所主张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能够在证明标准领域最大程度地减轻劳动者的证明负担,从而以证明标准角度对劳动争议诉讼之间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进行矫正。
(二)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的案件适用区别于一般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108 条将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确定为高度盖然性标准,也就是说当涉诉双方提出的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都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就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的情形,一般来说学界达成了降低证明标准的共识,但是具体的降低程度尚未有所定论。笔者认为对于劳动者所承担的证明标准应为低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具体来说当劳动者所提出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的,即可认定劳动者达到了其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劳动者的主张。将证明标准降低的理由在于裁判者在实务中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劳动者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例如在确认劳动关系诉讼中,当劳动者举证出示工作牌、工作服或者有了同事的证言,法官一般即可认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而此时的证明责任就转移到了用人单位一方,从而减轻了劳动者的证明责任,保护了其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对于劳动争议诉讼而言,证明标准的设置应当与一般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区分,对于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的案件,应适用低于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对于用人单位诉劳动者的情形则适用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六、结语
本文首先对我国民诉解释中涉及证明标准的第 108 条和第 109 条进行了分析,笔者对于 108 条与 109 条的所持态度有所区别。对于民诉解释第 108 条, 笔者看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于统一实务中的证明标准的决心与实际行动。该条 规则所确立的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实务中的证明 标准乱象,明确了证明标准的具体含义,在实践中对于法官在判决书的判决理 由部分对证明标准问题的阐释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和法律支撑。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实务中的复杂情况非单一的法条所能罗列的,在具体案件对证明标准的 判断也离不开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对不同类型的案件所持的证明标准 也应结合个案情况进行讨论。对于民诉解释第 109 条所规定的两类特殊情形下的证明标准的提高,笔者于上文分别讨论了两类情况各自的合理性,简单来说, 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类事实即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提高其证明标准不利于维 护被害者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对于第二类事实,在口头遗嘱或赠与的情形下, 提高其证明标准能够有效打击社会中的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现象,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
本文的重点在于对劳动争议诉讼中各方证明标准的划分与论述。笔者受民诉解释第 109 条的启发,试图对劳动争议诉讼这一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分析。笔者关注到劳动争议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地位以及举证能力的差异,结合此种案件类型的特征与劳动法相关理论,主张不能将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适用于劳动争议诉讼领域,笔者以确认劳动关系这一劳动争议领域的典型案件类型为例分析了一般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适用于劳动争议诉讼的理由,并且提出了应分别确立双方的证明标准。笔者的建议简单总结为: 当用人单位诉劳动者,应当适用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当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的案件则适用低于一般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将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分别予以区分,拉开相互的证明标准差异,以达到实体法上的平等,并以此希望可以传达构建多元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念。由于实务中的劳动争议诉讼种类复杂多样,笔者也仅以劳动争议诉讼的双方主体作为证明标准的讨论分类对象,对于本文中尚未提及到的其他情形或者实务中更加复杂的情形,我们应该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证明标准的讨论,无论是高度盖然性标准还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最终的目的永远是向着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所前进。当然,除了在证明标准上进行区别,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也是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另一条可研究的路径。
在实务中,大部分的民事案件所依据的证明标准仍为一般的证明标准,即使是在一些特殊领域中的纠纷也依旧适用我国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也符合我国国情与社会期待。例如笔者所查阅到的一个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a,在肇事船舶逃逸、海事局调查未能给出明确结论、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审查认定肇事船舶并进行责任划分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以高度概然证明标准来认定事实符合查明案件真相的一般规律。
构建多元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除了在理论研究中需要更长远的发展外,笔者深信完善多元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制度离不开司法实践的探索,通过调整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而作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的建立有利于诉讼价值的平衡,并且有利于追求司法正义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of Proof Standards in Civil Litigation
—Take Labor Dispute Litigation as an Example
Hu Yaoyu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B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was introduced in 2015,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ivil procedure in our country, we can not reach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Article 108 and Article 109 of the Civil Litigation Interpretation in 2015 was to unify the confusion of the proof standards. Since the interpretation was introduced, scholars have also conduct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oof standards, and have generally recognized them. The general civil litig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Article 108. The improvement or reduction of the civil litigation certification rules in several special situations established in Article 109 has also caused a lot of controvers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on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civil litig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 in my country. Based on Article 109 of the Civil Litigation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focuses on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labor dispute litigation, and proposes the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in labor dispute litigation and general civil litigation. The standard of proof should be different, and it is intended to make suggestions on the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Civil litigation; Proof standard; Divers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