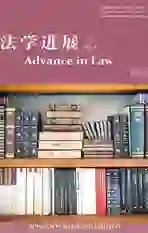刑法解释论视角下的高空抛物问题
2022-04-29唐佳辉
唐佳辉
摘 要|高空抛物入刑几经波折,最终被归为扰乱公共秩序罪这一节下的一个罪名。作为新罪,高空抛物罪难免存在为求条文言简意赅而解释不清,甚至因此使人产
生误解的情况,因此有必要详解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内容,揭示认定、处 理高空抛物犯罪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参考。 本文认为,高空抛物的主观要件为故意,而客观要件则需分析“高空”“抛 掷”“物品”等概念含义,对存疑之处做出合理解答。此外,高空抛物罪的设立是否会导致民刑混淆,刑罚滥用或者因为难以确定责任人而使之形同虚设的问题也值得探讨,但仅有理论研究明显不够,还需司法实践的经验予以佐证。未来,高空抛物罪的内容还需更多解释和指导案例使之得以充实,有待刑法界给出恰当合理的答案。
关键词|刑法解释;高空抛物;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刑罚滥用;罪名虚设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社会现实的变更迫使整个群体对其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反省并做出调整,进而催生新的制度体系。在司法机关无法沿用从前的经验化解新的矛盾时,立法机关就有必要将这类情形纳入法律评价的范畴或将原有法律进一步予以细分,為司法实践提供相应的处理标准。
二战后,由社会变化推动的法律变革步伐明显加快,且更多倾向于解决实 际问题、回应公众需求及平息人民对于现代社会潜在风险的焦虑感。“法律的 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我国近年来的司法、立法改革亦是如此。经过几次 修改和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修(十一)》)最终定型, 也让高空抛物问题有了答案。以往司法机关应对此类案件时,一般都按照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但在这种模式下,不仅存在行为是否“足以危害 公共安全”难以判断的问题,又可能导致量刑畸重,罪刑不均衡的现象,因而 长期被学界诟病。事实上,本次修正案的草案一次审议稿也曾一度陷入前述的 困境,而其后的修正案则对此予以修改,相对地弥补了原先的漏洞。
新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是更多疑虑的来源;立法上的 争议尚未得出结论,执行方面的问题却蜂拥而至。为缓解相关的诸多矛盾,体 现法律的明确性,除再立其他法规外,就需要对新法所述内容做出详细解释, 解读其立法精神,从而为实务提供必要的参考,正所谓“法律未经解释不得适用”。本文将运用刑法解释的相关理论,阐述对高空抛物问题的理解,并提出一些看法。
一、对高空抛物罪主观要件的理解
一般而言,高空抛物罪的主观要件表现为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概括故意。当然,学界也有观点认为,高空抛物行为的罪过形式可以视情况不同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a,但这种说法一方面容易与“高空坠物”情形混淆,将应由民法评价的内容纳入刑法范围,造成民刑混淆,破坏法制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也不利于维持刑法的谦抑性;另一方面,《刑修(十一)》将高空抛物罪的量刑标准确定在较低的范围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过失犯罪相比故意犯罪通常量刑更低,即使通过法律将高空抛物的过失形态确定下来也会使该罪的法定刑形同虚设。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其 2019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高空坠物犯罪的认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就包括“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说明司法机关对于过失高空抛物罪也持否定态度。因此,从刑法体系的完整性、立法的科学性和司法执法的便利性考虑,本文采用“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为故意”这一说法。
二、对高空抛物罪客观要件的解读
根据《刑修(十一)》的内容,高空抛物罪的客观要件表现为“从建筑物 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且需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换言之,认定一行 为是否构成高空抛物,不仅要求包含“高空”“抛掷”“物品”等要素,还要 存在严重的情节。刑法修正案对这项新设罪名的描述简洁明了,属于简单罪状, 有利于社会公众理解和把握;但该罪状中不少要素还有待解释,可能给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的工作人员带来困扰,有待解释阐明。本文认为,关于对该 罪客观要件的理解,不妨从以下几点进行拓展。
其一,对于“高空”的理解。高空一般指等压面在 850 毫巴以上的、距离
地面较高的空间,而高处作业则是指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m 以上(含 2 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本文认为,从体现立法精神的目的出发,可以对“高空” 一词做扩大解释,即高空不仅应指对流层下部以上的大气区域,还要被广义理 解为可能有物品从此处坠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场所,而“高处作业”中对 于高度的限定可作为参考。以此来看,只要符合高度要求,不论是在建筑物、 树梢、悬崖甚至移动的交通工具上,行为人抛掷物品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均可符 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当然,“高空”概念的扩张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1) 首先,如果有人从已经在千米高空的飞机上扔下物品,而物品在空中坠落一段时间后砸中了某人,认定为高空抛物似无疑问;但假如该物品是从地面上抛出,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落下造成严重后果,是否可认定为高空抛物?笔者认为,为应对“高空”被泛化理解的情形,需要对这一概念做出限制解释,
即高度应以行为人所处高度为准,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m 以上(含 2 m)。
(2) 其次,还可能出现物品虽从高处抛下,但在坠落过程中被卡住,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后才又落下的情形。笔者认为,鉴于此前《意见》中“充分认识此类案件中侵权行为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造成的严重损害,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的精神和《刑修(十一)》将高空抛物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意图,如果物品从被卡住的高度落下,依旧可能严重损害他人人身财产权利的,仍可视为符合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
(3) 最后,修正案将高空抛物罪添加到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说明“高空” 需要符合足以使“抛物”行为具有扰乱公共秩序效果的条件。相较于此前草案 一次审议稿将高空抛物罪归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做法,第三次审议稿(修正案 正文)对该罪的归类明显是在发现高空抛物这一行为的复杂性后在立法上做出 的让步——高空抛物既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也有可能只会单纯地对确定的某一 个人造成损害,还会出现并未侵害到他人的人身权利,而只是严重损坏了他人 财物(如用石头、砖块将他人停放于楼下的汽车砸坏)等诸多情形,因此纳入 适用范围更宽泛的扰乱公共秩序罪相对而言更合理一些,也便于司法机关判断 行为是否构罪。针对《刑修(十一)》的上述做法,也有学者提出,是否扰乱 公共秩序似乎与是否在高空抛物无必然联系,即使在低空抛物也同样能扰乱公 共秩序。a 本文对这种说法抱有异议,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如前文所述,将“高空”扩大解释为可能有物品从此处坠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场所更有利 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其具体高度可参考高处作业标准暂定为在坠落高 度基准面 2 m 以上(含 2 m),而“低空”如何理解却尚无详细可靠的思路—— 如果与“高空”相对,将其高度确定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m 以下,不难发现由于要求的高低差过小,所谓的“低空抛物”极易与常见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 等行为混为一谈,例如在楼梯上向下面的人扔下重物,致其伤残等;第二,公 共秩序含义为“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秩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则是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负面干涉,将主要对公共生活而非公共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 高空抛物归为其中一类与将其归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与其他罪名相 比更为合理;第三,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也说不通,按照该观点延伸理解,将高 空抛物归在任何一种罪名下都可能被认为不妥:质疑者大可以提出“是否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似乎与是否在高空抛物无必然联系,即使在低空抛物也同 样能危害公共安全”等类似理由将任何试图给高空抛物行为确定在某个罪名下 的努力抹杀。除这种说法以外,本文对将“高空”中对高度的要求强行与危害 公共安全类犯罪联系起来,认为“高度会对能否危害公共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 并引用动能、重力势能等物理理论等得出“‘高空与危害公共安全之间是相 辅相成的”结论的观点? 也有不同意见。高空抛物罪对“高空”的要求并不应仅限于能够产生足以造成破坏之动能的高度。在实际生活中,从高空抛下带病菌 的医用棉絮、硫酸等腐蚀性化学药品甚至一般的水等并不会因其动能而造成严 重损害的物品,也可能符合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当然,这类行为还存在构 成想象竞合或者法条竞合等的概率,本文在此暂不多论。
其二,对于“抛掷”的理解。“抛掷”一词,既有“投、扔”,也有“丢弃、弃置”的意思。根据我国近年来高空抛物案件实际情况和此前《意见》、目前《刑修(十一)》的意图来看,采取“投、扔”的说法更为合理。但以此理解也有 一些问题。
(1) “抛掷”的行为是否要经行为人之手亲自抛下?目前,无人机技术被逐渐推广到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无人机货运也被提上日程。如果行为人将物品吊在无人机下方,将无人机升至高空后放下物品,造成后果的,能否构成本罪?再如,行为人将物品放在管道内或者光滑的木板上,再将管道或木板倾斜放置以使物品自然滑下,能否构成本罪?本文认为,应当从保护人民切身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即是否經行为人之手亲自抛下并非必要的构成要件,只要扰乱公共秩序,利用无人机、倾斜的管道或木板等工具来使物品落下也可符合本罪的客观要件。
(2) “抛掷”的方向是否存在要求?如果向上掷出物品达到一定高度,情节严重的,是否构成本罪?例如,将一大批氢气球向上抛出,正好妨害到直升机或者民间低空飞行的飞机正常航行,或者在某一幢楼的楼顶足球场踢球,将球向上踢到另一幢楼某户人家的阳台处,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是否应视为符合本罪构成要件?本文认为,尽管这类情况可能存在,但极为少见,将其解释为高空抛物的一种情形不符合民众的常识判断,也不符合本次立法意图,反而容易导致刑法的可预测性和明确性下降,因此将其排除在本罪的适用范围外, 以其他罪名处理为宜。但如果物品被向上抛出,经过一段时间后下落至地面, 情节严重的,则可视为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3) “抛掷”的时间应如何确定?换言之,什么时间点可以被视作高空抛物罪的成立时间?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即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要求达到主客观相统一。本文认为,“抛掷”的时间被确认为物品脱离行为人控制范围,且具有对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实际损害的能力之时较为合适。
除上述问题外,“抛掷”作为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的区别也值得注意。由于“抛掷”这一实行行为的存在,高空抛物更多地被视作是行为人故意的、主动的行为, 而高空坠物则是行为人过失的行为或者与人无关的物品自然掉落之现象。然而, 二者有时也会发生混合、转化,如前文中提及的物品被投掷到空中时被卡住, 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又落下的情形。对于此类情况,本文认为,应将其视为一个 整体的过程。如果行为人已经实施了高空抛物的行为,而物品被卡住时其有阻 止物品继续坠落造成恶劣后果的能力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了损害发生的,可 以视为犯罪中止;有能力却不采取措施,放任事故发生或者没有能力阻止事故 发生的,仍以犯罪既遂处理。
其三,对于“物”的理解。《刑修(十一)》将高空抛物罪从危害公共安全罪划入到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无疑是对“物”的范围的扩张:原本该罪要求物品被抛出后危及公共安全,而二审稿之后只要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的严重情节即可构罪;换言之,即使被掷出物品本身的危害性不大,在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例如,向下抛下纸飞机这一行为本身危害不大,纸张一
般也不具备能用于伤害他人的属性,但如果纸飞机刚好坠落到受害者的要害部 位(如眼睛等),造成损害的,仍应视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法益的变更导 致了“物”概念的变化,但并未明确“物”的认定标准,因此仍有一些存疑之处。
(1) 除了常见的高空抛落物品外,一些不常见的事物能否作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对象或媒介仍有不明确之处。以其中一个特殊情形为例,“人体”能否 视为高空抛物中的“物”?本文认为,可区分情况理解:假如“人体”为尸体, 即被抛下的“人”在落下前已处于死亡状态,则可将其归为“物”的一类,情 节严重的,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触犯高空抛物罪、侮辱尸体罪等多个罪名, 可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人体”为活着的人的身体,就应当将 行为人在高空将人抛下的行为视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等危害公民人身权利的 犯罪,根据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一般而言处罚更重的罪名定罪处罚。然而, 以上所述还只是通常的两大静态情形,而现实中的犯罪却是动态的、难以预测的: 例如,将一个活着的人从足以致死的高空抛下,但受害者在半空中却因惊吓过 度导致心脏病发作或碰到高压电线等原因死去,遗体落下后才造成严重后果, 情节严重的,应作何处理?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应参照第二种情况,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情形处理,但需要运用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进行综合判断。根据 “介入因素三标准”,行为人将他人抛下这一先前行为将人置于险境,制造了 极大危险,与结果有因果联系;将一般人从高空抛下的先前行为通常不会引发 心脏病发作或者触电等介入因素的出现,但这只是一般化的情境,如果行为人 事前已知晓被抛下的人有心脏病等疾病或者下方有高压电线等设施却依旧实施 其犯罪行为的,即处于具体化的情境下,则表明介入因素并无异常;心脏病等 突发疾病或者触电这类介入因素导致被抛下者死亡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确实较大, 但介入因素并未阻断先前行为制造的危险流——即使没有这些因素,被抛下的 人也会因为高度而死亡。综合前述,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文认为将其 视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危害公民人身权利犯罪较为妥当。此外,还可能出 现另一种情形:行为人将怀孕的妇女从高处抛下并造成严重后果,情节较为严 重,但妇女在被抛下前已经因为难产等行为人以外的原因死去,而腹内的胎儿 仍处于存活状态,直至落地才彻底死亡。本文认为,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胎儿
是否属于法律上的人。根据我国法律,胎儿未出生前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人, 因此行为人抛下的只有妇女的尸体,应以高空抛物罪、侮辱尸体罪等择一重罪处理较为合理。
(2) 如果物品并非被完全抛出,而是被系上锁链或绳子,行为人将其抛下并造成损害后又收回的,是否可视为高空抛物?本文认为,这类行为实际上与前文中提到的利用工具抛掷物品的情形并無多大差别,因其在侵害社会公共秩序这一法益的方式、结果上并无二致。
(3) 高空抛物行为本身存在是多个因素的集合体,因此在不同情形下表现也有所不同。同一属性的物品,由于其落下的高度、下方的环境和场所不同, 造成的损害也不一致;不同属性的物品,即使落下高度、下方环境等均相同, 后果也往往各异。例如,含有剧烈毒性的化学药品从高空被抛至坚硬的水泥地面, 可能在日晒下挥发,不一定造成严重的情节;但如果该药品被抛至作为城市水 源的河流或水库内并污染了这一片水域,则可能同时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高 空抛物罪,择其中之重罪即投放危险物质罪处理。另外,高空抛物行为对受害 人的表现也可能不尽相同:如果抛下的是花粉、油漆等可能使某些敏感人群引 发过敏反应的物质,健康人可能并不受多大影响,但对于过敏者而言则有危及 生命的可能性。
三、认定、处理高空抛物犯罪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类近年来才被公众关注并被社会予以负面评价的行为,高空抛物入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曲折。立法者首先将高空抛物罪归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后来又将其划入扰乱公共秩序罪的范畴,无疑是对高空抛物行为性质捉摸不定的表现。实际上,也有学者指出,“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分别认定为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重大责任事故、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罪”?,或者“根据不同行为情况,应将其分别评价
为故意杀人(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寻衅滋事罪”?,再或者 “既有法律手段足以规制该行为,刑事立法应保持谦抑性,无须新增条款加以 规制”b。然而,本文认为,从此前《意见》及本次《刑修(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的意图来看,为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回应社会公众意见,通过设立 新罪以突出高空抛物的社会危害性仍是有必要的。此外,如果将高空抛物行为 分别按照不同罪名处理,难免存在无法涵盖所有情形,因而不能定罪处罚的现象。再者,我国立法本来就有将一些侵犯多种法益的复杂现象立为单独罪名的先例, 如恐怖活动犯罪等。
本文虽然对目前立法将高空抛物罪归为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做法表示认同, 但对如何认定该罪仍有一些疑虑。目前,我国大量高空抛物案件均为民事案件, 即使依照先刑后民原则,等刑事案件结案后再进行民事诉讼,也往往因为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等原因将刑事案件搁置,仅处理完民事部分。c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案件刑事部分尚未办理完毕即进入刑事部分,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民刑交叉 ,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结果发生冲突的现象e,而民事侵权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标准的差异亦会给案件证明带来诸多问题f。此外,高空抛物罪的定罪门槛相对较低,即使行为人的作为达不到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罪的严重程度,也可能被认定为高空抛物罪并受到相应处罚,很容易出现“醉驾入刑致使该类犯罪占全国所有犯罪比例飙升”的类似情况。犯罪圈范围扩张可能导致刑罚滥用,进而使刑罚效果大打折扣。与前两种负面影响相比之下,高空抛物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似乎显得较易于处理,即只需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惩处即可。但实际上这种竞合也有一定问题:例如,行为人的高空抛物行为同时触犯高空抛物罪与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如果择一重罪则可能适用寻衅滋事罪等罪名,进而致使高空抛物罪的适用范围也连带着扩张开来。
與认定一行为是否构成高空抛物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同,处理高空抛物犯罪主要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侦查、起诉阶段。前文中已有提到,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很有可能遇到找不到高空抛物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证据, 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究物业公司等其他责任方的责任。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无法使法律对真正的行为人予以谴责,当然也不能让刑法发挥一般预防或者特殊预防的效果。
四、结语
将高空抛物行为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探索尝试之一,不免存在许多不足。实际上,本次《刑修(十一)》不仅试图对高空抛物做出恰当的评价,还力图将基因编辑胚胎、诽谤英雄烈士等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但这些规定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不明确、不协调或者可能引发现有法律体系内部冲突等问题,除再立新法外,就只能通过解释、指导案例等方式将现有法律予以说明。既然短时间内频繁立法不现实,那么以解释等形式修正立法存在的疏漏和不足显然更现实一些。本文已对高空抛物行为做出了一些解释其概念框架的探索尝试,也说明了一部分认定、处理高空抛物犯罪过程中有一定概率会面临的问题,但司法实践中相关机构处理高空抛物犯罪的方式仍可能与本文理念背道而驰。法学理论脱离司法实际就只是纸上谈兵;具体如何运用法律条文则是司法适用领域的问题。高空抛物罪的设立对纠正高空抛物的恶性行为作用如何,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The Problem of Throwing Objects off High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Tang Jiahu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After several twists and turns, throwing objects from high above was finally classified as a crime under the section of the crime of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As a new crime, high altitude parabolic sin unavoidably exist for section brief explanation is not clear, and so misleading, even so it is necessary, the subjective important document and objective important document content, reveals that, the processing may fac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high altitude parabolic crime, which 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for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ubjective element of throwing objects from high altitude is intentional, while the objective element needs to analyze the concepts of “high altitude”, “throwing” and “objects”, so as to give reasonabl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n addition, it is also worth discussing whe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of throwing objects from above will lead to the confusion of civil punishment, the abuse of punishment or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crime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responsible person. However, only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and it needs the experience of judicial practice to prove it. In the future, the content of the crime of throwing objects from high altitude needs more explanation and guidance. The case should be enriched and the criminal law circle should give a proper and reasonable answer.
Key words: Explanation; High altitude parabolic; Subjective requirement; Objective requirement; The penalty abuse; Setting up meaningless char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