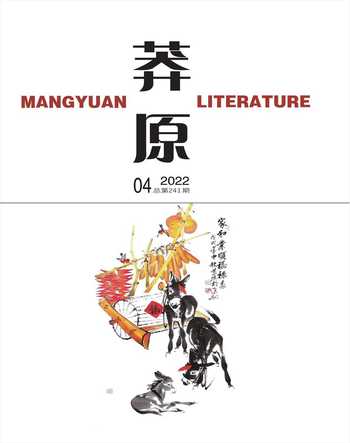光阴深处的河西走廊
2022-04-29刘梅花
刘梅花
唐宋时期的河西走廊,人们的日常光阴是怎样的呢?我没去过,不知道。不过,读古籍,似乎能窥视到丁点儿痕迹。
有一种吃食叫饵糕,平日不常吃,过重阳节时食用。敦煌文献《寺院破历》寥寥数语:“粟陆斗,麦壹斗换黑豆,登高日用。”
粟就是谷子,碾去壳之后,叫小米,古时叫粟米。还有一种谷物叫糜子,也叫黍。糜子碾去壳,叫黄米。这两样是古河西走廊的主粮,西夏文献里到处可见粟米糜子。
换黑豆来,要做饵糕。饵糕是个什么样的吃食呢?大概是粟米和黑豆蒸熟,搁在石臼里捣,像糯米糕那样的。另一种说法是粟米蒸熟,黑豆磨粉,蒸熟的米和豆粉搅拌在一起,捏饼上锅蒸。还有一种说法,粟米黑豆泡好,磨成浆,掺入一些馅料,葡萄干红枣之类的,装盘蒸熟……如今,河西走廊已经没有饵糕——有些食物吃着吃着,就消失了。
不过,我们端午节吃的卷糕,有可能从唐宋的饵糕演变而来。大米或者糯米泡好,放一些红枣葡萄干,蒸熟。菜籽油炸出碗口大酥软的油饼,把米糕卷起来,这种吃食在端午节享用,叫卷糕。
唐宋的河西走廊重视重阳节,吃饵糕。如今,河西走廊的人更喜欢过端午节。在天祝藏区,这一天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登高,看香柴花,吃卷糕,喝雄黄酒。这种过节的方式,令人怀疑是把古人的重阳节挪到了端午节。
藏区的九月草木凋零,天地一片萧瑟,冷风吹过,高处不胜寒,所以被遗弃。端午节天气温暖,花开草绿,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可以挪来古人的饵糕过节。
翻古籍,古人三餐会留下一些食物的名字。饼很多,胡饼,蒸饼,烧饼,菜饼,肉饼,汤饼,各种饼。大概那时候把面食都统称为饼。
“供缝皮匠八人,逐日早上各面一升,午时各胡饼两枚。”这种胡饼大约是普通的烧饼,发面烙的。现在河西走廊大街小巷都是大饼铺子,也叫白饼子,碗口大,一顿可以吃两枚,想来和古代的胡饼大小差不多。
凉州的厚锅盔,烧鏊子,有草帽那么大,估计是唐宋大户人家的胡饼,或者是行军打仗时的干粮。
我小时候,家里来客人,父亲就会做一顿油胡旋饼。开水烫白面,揉光滑,擀薄,淋上胡麻油,卷起来,复擀成薄饼。锅里放胡麻油,搁饼子烙,慢慢地旋转,烙得柔软焦香。
敦煌文献记载:“油胡饼子肆百枚,每面贰斗入油壹升。”我觉得爹烙的油胡旋饼,就是唐宋油胡饼。如果从字面看“每面贰斗入油壹升。”似乎是把清油直接揉到面里,事实上不是那样。是把清油淋到擀开的面皮里,卷起再擀。这样的饼子有层次,更加柔软可口。
唐宋人吃的蒸饼,是我们的蒸馍。从壁画上看,很相似——除了文字,古人还给我们留下壁画,不然后世之人不知道他们长啥模样,吃啥食物。
小时候,农忙时间大人们没空做饭,就蒸一锅馍馍,顿顿吃馍。我吃过发霉的馍馍,颜色青灰,掰开有霉丝。我不想吃,可是尕姑姑戳指头骂个不停,只好吃掉。我打不过她。那时候的人皮实,一次也没中过毒。不知道古人吃不吃发霉的蒸饼。
菜饼倒是很寻常,如今的河西走廊,到处可以吃到菜饼。发面擀饼,卷入各种蔬菜,再次擀薄,铝锅烙饼。我吃过苜蓿菜饼,苜蓿嫩叶开水焯过,剁碎,掺入面粉揉成团,蒸熟或者煎饼。味道一般,不是多么美味。毕竟苜蓿是牛羊吃的草,不是正经蔬菜。
西夏谚语里,时不时出现菜饼。西夏近两百年时光,凉州是西夏的辅都,菜饼大约是从河西走廊传到西夏各地的。
唐诗里出现一种胡饼,叫肉饼。面饼烤熟,劈开,裹上切碎的羊肉葱白,撒上胡椒粉。现在凉州城的北关市场卖这种胡饼,叫肉夹饼,饼子雪白,卤肉鲜嫩,甚为美味。
汤饼还有个名字叫馎饦。敦煌文献中记载:“早上馎饦,午时各胡饼两枚,供玖日,食断。”那么,早上吃的馎饦是啥美食呢?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馎饦,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
敦煌文献中将乱撒的“馎饦”比喻为雨点一般落下——馎饦空中乱撒,恰似雨点一般。
细读,原来馎饦就是河西走廊的揪面片嘛。這种吃食简直太寻常,两三天不吃就想得不行。凉州的羊肉揪面片,十几个人围着一锅沸腾的大锅下面片,真的雨点一样密集纷飞。雪白的面片配上炒好的羊肉菠菜西红柿,简直美味得让人流口水。
走在凉州小巷子里,小饭馆门口店小二在吆喝:“羊肉面片,羊肉香头子,进来吃嘛。”让人觉得烟火人间,温暖又真实,可心可意。
我们藏区虽然羊肉不缺,但是招牌却是葱花面片。葱花是野生的,从山崖上掐来,晒干。面片揪得很小,叫尕面片,煮好,搁一撮野葱花,刺啦一勺子热油泼上去,味道鲜美得难以叙述。只有吃过,才知道野葱花的魅力。
汪曾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兰州人吃惯了自家牛肉面,瞧不上别处拉面。走出河西走廊,他乡揪面片我也瞧不上。河西走廊的揪面片,是从唐宋雪花一般纷繁而来,别处哪里能比。
我们村有一种面食,叫“饦疙瘩”。凉水兑入面粉里,筷子搅和,搅成一团,饧几分钟。水开,拿筷子拨入沸腾的水中,“饦疙瘩”两头尖中间鼓,像一个个小鱼儿。待煮熟捞出,浇上羊肉臊子,撒葱花,再调一勺油泼辣子,滑溜劲道,特别好吃。农忙时节,许多人家喜欢吃“饦疙瘩”。不费时间,又抗饿,干一天的活都不会腿软。我喜欢吃酸菜“饦疙瘩”,大概我爹总是给我们做这种饭,味蕾有了记忆。
古人吃什么菜呢?萝卜,蔓菁,葫芦,白菜,葱蒜,各种野菜。
敦煌文献记载:“面壹斗,园间累葫卢架墙众僧食用。”
“葫卢”也写作“壶卢”,即葫芦,从西域传来。河西走廊的人们把南瓜叫窝葫芦,番瓜叫西葫芦。那种江湖郎中卖药的葫芦,可以当水瓢的葫芦,我们叫吊葫芦。
我的邻居会做一种“驴嘴唇”烩面,配菜必须是西葫芦。荞麦面温水和面,柔软一点。揉成面团,搓成长条,拍扁,切厚片。厚片的荞麦面片下锅煮熟,捞出,浇料汁。西葫芦切厚片,猛火炒熟,拌上煮好的厚面片,汤汤水水,简直太香了。荞麦面片煮熟的样子厚墩墩的,颜色青黑,边缘有弧度,特别像驴嘴唇。
某次外出,在不起眼的一个小馆子里吃到“驴嘴唇”烩面,配菜里多了洋葱,味道比邻居家差一点,没那么醇浓清香。我觉得洋葱这种菜很败味,无论哪一道菜里有洋葱,都会减味,蚀掉一部分食物清香。
河西走廊野菜多,野胡萝卜就是一种。古人把野胡萝卜叫土参。《五凉志》记载:
“土参产山田中,形似参而不坚,味甘,春秋月掘根,蒸食。”
当然,也有一种药材叫土参,但此土参非彼土参,是两种植物。野胡萝卜春天耕地时最多,一犁铧下去,翻出白花花的野胡萝卜,又肥又大,样子和人参有点像,质地虚,味道甘甜。
吃的就是野胡萝卜根。暮春,它开始抽枝长叶,茎直,不很粗壮,多分枝,表面粗糙带细毛。开一种伞状小白花,一团一团的,低调朴实,淡淡的香味。撒叶抽枝的野胡萝卜根就不能吃了,只吃春天还未发芽的那种。
野胡萝卜根捡回来,淘洗干净,铁锅添水,铺一层野胡萝卜。烧开水,再铺一层面粉,慢火焖煮。这种饭叫焪焪,没点能耐做不出来。水不能多,多了粘成一团。但也不能少,水少了面蒸不透,半生不熟。只有老奶奶们才能把握火候。煮半小时左右,水煮干,闻到淡淡焦味时,筷子散开面粉,慢慢扒拉,让每一根野胡萝卜上都裹一层面粉,干撒撒的。最后浇上一勺子热油,搅拌均匀。
焪焪饭不用菜,直接吃。野胡萝卜淡淡的甘甜味,面粉蒸出的清香,有一种独特的山野之味。我在山里住的时候,春天家里总是吃焪焪饭,能吃得特别饱。有时候姑姑们做,那就太糟糕,焪焪饭要么黏糊成一团,要么一盘散沙,真是浪费了面。
姑姑们都脾气大,饭做焦煳也不能随便咕哝,不然一脚抄到门外去——叫你吱吱叫。有得吃就不错了,还挑。
野胡萝卜根天生是个素食物,切碎,包素包子也很好吃。古时寺院里常常吃这种素包子。今年春天,院子里几个大妈雇了一辆车,去深山里挖野胡萝卜,回来包包子。我尝了一个,手艺确实不行。调料太多,反而淹没了食材本有的味道。
至于蔓菁,历史也很悠久。《本草纲目》里说,蔓菁自古出河西。有可能是张骞从西域带到河西走廊的。河西古人最常吃的蔬菜应该就是蔓菁,《五凉志》到处可见蔓菁的影子。
蔓菁做的凉菜,清爽可口之极。如果是冬天的话,就吃腌蔓菁菜,泡了辣椒,味道甘甜清香。蔓菁有两种,白蔓菁和黄蔓菁。黄蔓菁比较好吃。小时候家里有蔓菁畦,奶奶不许随便拔。瞅空就偷了吃,拔下来擦掉泥大口啃,味道清甜甘冽。
有一回被尕姑姑告密,剛拔下蔓菁,奶奶拎着拐棍追来。仓惶逃跑时,从土坎上一头栽下,几乎摔晕。摔得过猛磕破嘴唇,满嘴的血。至今嘴唇里面还留着一道疤。
唐宋的河西,还有一种菜也是常吃的,叫菘。《五凉志》里,菘的记载也很多。菘就是白菜,一种黄芽小白菜,一种大白菜。我爹炒白菜,叫活捉小白菜。黄芽白菜拔来,开水里烫一下,切碎爆炒,味道清淡。
我爹常常给菜取个奇怪的名字。比如一碗小米汤,配个白水饼子的早餐,他叫月亮过江。听着就很清汤寡水。
冬天吃腌白菜。小时候吃洋芋搅团,下饭菜必须是酸白菜。黄芽白菜从大缸里捞出来,热油猛火炒,老远闻见都流口水。唐宋的人们吃不上洋芋搅团,因为洋芋还没有。但菘是可以吃到的,不知道他们炒了吃还是煮了吃。
唐代边塞诗人里,岑参是重要的一位。他在河西走廊逗留时间多。《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写道: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这首诗里出现了犁牛和野骆驼。犁牛是杂色牛,有可能是退槽下来不能干活的老牛或者伤病了的牛。健康牛不会烤了吃。野骆驼倒是很多,我小时候,沙漠里常常可以看见大群的野骆驼。酒泉太守置酒相待,又烤犁牛又煮野骆驼,可见对客人隆重到了什么程度。想来野骆驼也不会好吃,因为太大了,又笨又粗糙。
凉州街巷有卤驴肉卖。老天,我可不敢吃。鸽子也不敢吃,狗肉也不敢吃。有个朋友告诉我,她吃了马肠子。真是难以想象,是怎么吃下去的。
河西走廊的古人也吃沙枣花,《五凉志》里叫金铃花,说金铃花形似铃而小,故名。开时,香闻数里。我觉得沙枣花是世界上最纯净的香味,一点点甜,清香袭人。
读小学时,每逢沙枣花开,小孩子们都去折枝,一大束,找个空罐头瓶书桌上清供,香味让人沉醉。老师点名,从一束一束的沙枣花后面找出一个个小脸蛋来,眼睛里也是笑,这些小捣蛋鬼们。
沙枣花饭做法和榆钱饭差不多。摘来的沙枣花清洗干净,拌上面粉上锅蒸。蒸透之后,搅拌均匀开吃。榆钱饭和沙枣花饭我都没有吃过,我爹不喜欢野味的食物,大概他小时候各种野菜吃烦了。他就喜欢吃干拌面,配上家里种的蔬菜。
一个人的童年,对整个人生影响巨大。我们穷其一生,都在承受童年的种种痕迹,都在寻找与童年和解的密码。喜好也和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河人吃沙米,也是古来有之。《五凉志》记载:“沙米,丛生沙漠中,似蓬,色白,叶尖有刺,米藏彀中,雨涝始生。草籽,年饥则充腹。”
沙米是沙蓬草的种子。古时把能吃的草籽都叫野谷。沙米,灰条草籽,黄毛柴草籽,都是野谷。西夏后期,野谷可以充军粮。
沙蓬收割回家,晒干,棒子猛捶,敲打出来沙米,做成一种吃食叫沙米粉。沙米和粮食一样,耐饥,果腹,长筋骨。《救荒本草》记载:“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
饭,俗名登粟,一名沙米。”
沙米晒干,浸泡在凉水里,泡软。铺开麦草秆,倒一层沙米。合拢麦草秆,使劲儿揉搓成细浆,用细箩滤。滤好的浆汁下锅烧开,盛入盆中晾凉。待其凝结,切条切块,浇上油泼辣子,老陈醋,味道鲜美之极,焦香焦香,吃过不能忘怀。
去年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小镇吃过沙米粉,有一丝焦味,很馋人。小镇上一窝一窝慕名而来吃沙米粉的游人,舔嘴咂舌,吃得万分过瘾。其实我是担心的,游人太多的话,会把沙漠吃穷的。沙蓬的草籽,并不多,尤其天旱的年间。
河西古人也吃沙葱,《五凉志》提到沙葱。沙米和沙葱应该是凉州多。
沙葱不高,长不到一尺。纤细,柔嫩,一丛一丛生长在戈壁,沙滩,荒沙野岭。沙葱疏疏落落,生长得很零落,不喜欢挤在一起大片大片那样。葱叶尖而细弱,也抽薹开花,淡紫的,有点粉,有点白,很寻常。
雨水稠的一年,沙葱也稠。遇上干旱年份,也找不到几根。没水,可怎么活呢。其实我一直觉得沙葱活得很散漫,闲闲的消磨时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无用之事。比如开几枝花,在风里晃荡啊晃荡。
若是说到味道之鲜美,沙葱绝对顶呱呱的。这样的野味,自有一种天然纯净。沙葱包饺子,不用调料,就一点轻盐那就特别美味。凉拌也不错,颜色碧绿,特别下饭。沙葱有人工栽种的,味道比野生的柔和一点,也好吃到停不下来。
我爱吃沙葱拌面汤。干面粉潮一点水,搅拌成面粒,水开了搅一锅稠稠的面汤,调点切碎的沙葱,一勺麸子醋,清淡暖胃。
古人说,草衣木食。编草为衣,以树木果实为食。这是一种清贫但格调相当高的生活。不过,古时的乡野人家,食草的时候多。各种野菜不都是草嘛。是草木保管着大地,养活着我们的光阴。
闲时读古籍,无非就是想窥探一下古人的生活。有时候,我有个奇怪的想法,希望吃到和祖先一样的食物,过和祖先一样的生活——长袍阔袖,席地而坐,陶器里盛放着简单的食物,篝火,沙漏,读一册一册的木简。尽管这个想法很荒唐,但允许自己胡思乱想一下。
虽然千年时光,但就人类的进化过程来说,并不漫长。我们还在吃祖先吃过的沙米沙葱,白菜蔓菁。我们虽然远远地和祖先散开,远得无边无垠,但猛然一回头,我们还在祖先留下的食物体系里转悠,说着和祖先一样的方言,过着和祖先一样的生活习俗。我们并没有远离祖先。
饵糕,野菜,面片,胡饼,汤羹,是光阴的小舟。我们搭乘这叶小舟,想返回唐宋的某个时分,看看祖先被风沙和时光包裹住的日常光阴。那光阴淡淡的,温暖的,苍凉的,让人忍不住想拥抱。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