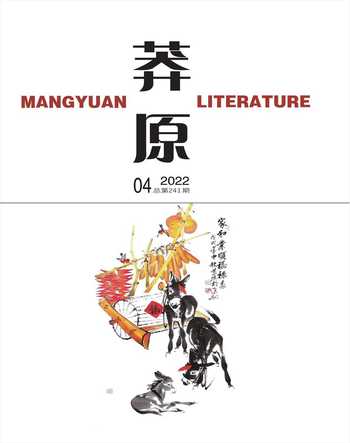小说讲堂:修改
2022-04-29张炜
张炜
修改的第一个环节
一部作品总要经历修改这个过程,这是所有作者都明白的道理。但因为特别浮躁,或者因为没有修改的机会,有人也可能放弃这个环节。除此之外,一般都要将作品修改几次,尽可能地让自己满意。鲁迅先生说过:在交稿前,文章至少要改上几遍,把可有可无的字和句去掉。
一个成熟的作家,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是不可能把一部没有修改的作品送走的。否则,那才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一部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修改?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少修改的机会?
鲁迅先生当年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想到一点就写。”很多人以为,鲁迅的意思是在下笔之前,要想得非常充分了再写。反面的例子是,有人一冲动就把字落在了纸上。这显然有些冒失。
其实现在来看,鲁迅的这句话中还透露了一个写作学的问题。“不要想到一点就写”,这里面似乎蕴含了其他的奥秘:想到多少再写呢?想了多少才算瓜熟蒂落?难道想得越多越好吗?再说想得完全熟透,就一定会写得更好吗?
鲁迅先生在说一个十分微妙的事情,这是指动笔前的一种“心事”。
原来作品在心中刚刚滋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成长,并经历一遍遍的“修改”。这些“修改”可能是漫长的,十分漫长。但无论多么漫长,它都只能算做“修改的第一个环节”——因为它不是在纸上进行的,而是在心里做起的。
有写作经历的人会发现,作品在心里有一个孕育的过程:有了感动,有了描述的欲望,之后会让这粒种子植在心里,慢慢让其发芽、长大,最后才在纸上写下第一笔。
实际上,这粒种子从萌发到落在纸上的这个阶段,有时是很漫长的,或许还要跋涉千山万水,历尽艰辛。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只要它一天不能落在纸上,这个过程也就一天没有结束。事实上,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通常总是长于在纸上书写的时间。
如果省却了这个过程、人为地缩短了这个过程,结果常常会让人失望。因为它不可省略不可取代、甚至是难以重复的——一旦开始了纸上的涂抹,即是预示了第一个修改环节的结束。
有人忽略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过分急切,不愿让那粒“种子”在心里存留得太久。
一位拉美作家谈自己刚刚出版的一部美妙的短篇集时说道:“这其中的一些篇目是二十多年前的构思了。”有人听了会想:凭他这样的大师,多少名篇杰作在世上流传,这些几千字的短章还要魂牵梦萦二十年?他们会将他的话当成一位功成名就者常有的那种夸张,是一种“极而言之”。他说二十多年都没有把它写下来,是因为还不到时候——现在终于有可能把它一篇一篇写出来,成为你们看到的这本薄薄的小书。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在作家心中被不断地丰富着,历经了许多思考,最后总算趋于成熟。他没有过多地谈论纸上工作的情形,似乎对后者没有太多的兴趣。显而易见,作家谈的是那个漫长的“第一环节”,即心里的修改。
越是杰出的作家,作品留在心里的这个过程越是微妙——他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个阶段中的每一个变化。这就像一位面包师施放了酵母,烤制还没有开始的这个时段。这对于即将出炉的面包来说是至为关键的。
这种心中的修改有一个特点:它并非总是处于那种主观逻辑很强的状态,甚至还会故意保持一种模糊感。他可能在写其他的作品,只将未曾开始的另一部作品掷在心的一角,许多时候连想都不想。但实际上他的潜意识并没有停止运动。人的思維器官有一个奥秘,它就像电脑一样,只要不执行删除指令,那么这个文件就一直在大脑沟回里存放着。潜意识会把储存的这个文件管理好,并时不时地打开来,在人的意识休眠时慢慢修补。这个过程既神秘又朴素。这当然是不自觉的。
有时候的确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你想写一个东西,因为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未能完成;但是停上一个月、停上一年或很多年以后,它突然就以非常成熟的面貌呈现在你的面前——你有了更好的办法去处理它,它正以从未有过的感动召唤着你,让你非写不可。在整个存放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由潜意识修葺了许多次。
尽管如此,也并非要作者一味地依赖这种心中的搁置,不是说在心里放的时间越长越好,以至于像某位作家那样——他竟然在日思夜想中将整部书烂熟于心,结果差不多都能背出来了。那么他剩下的工作,不过是从心里抄出那些句子而已。这就走向了反面,完全没有了文字落地那一刻的生鲜感,反而扼杀了应有的创作冲动。
可见心中的果实过于熟透,也就没法完好地采摘下来了。
这就是修改的第一个环节,它多少有些神秘,但真的特别重要。我们也许找不到另一个阶段,可以替代这个环节。
修改的第二个环节
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他每天工作时,总是要写到一个比较顺利的部分,即十分清楚下面该怎样进行了才停止下来;第二天写作前,把第一天写成的文字从头修改一遍,直改到上次停止的那个地方,再开始新的写作。
这种修改,是与写作同时进行的,我们可以将其看成修改的第二个环节。
大概作家们都会这样做:边改边写。不过也有人善于在纸上一气呵成,把修改留给最后。看来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实际上却容易将第二个环节给省略掉。因为每个环节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它似乎是不能随意挪动的。
当我们再次接续写作的时候,把前一天形成的文字仔细改上一遍,这样做的特殊意义又在哪里呢?
首先,这会使昨天的文字在相对冷静的思维面前接受一次检验和判断。因为文字刚出大脑的熔炉还是滚热的,隔一夜或一天,它就会冷却下来。在文字冷却的时候修改订正它,总会更客观更准确一些,我们可以做得从容一点。
这样做的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创作前的预热——让已经冷却下来的思维慢慢热起来。因为你就要开始一次新的创作了,需要让一切回到从前一样的热度中,以便进行冶炼。没有这个状态不行,热度不够不行。我们看某些作品,在阅读中常常会感到个别局部显得呆板、凝固不化,与整个篇章的文字格格不入,不够协调——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工作停止后,重新接续时没有让思维充分预热,没有让滚烫的思维将文字熔化。
一般来说,没有进入创作过程中,许多因素就不可能激活。这需要慢慢进入,需要一架思维机器的启动。思维这架机器就是这样,它一开始运转总是比较缓慢,达不到相应的速度。它没有沉浸到该次创作所需要的语境和情境里,没有抵达那个特定的语态、创作态中去。可是我们又不能空空地等待。要解决这个难题,也许只有从头阅读和修改业已形成的那些文字,一点一点捕捉作品的律动和气息,最后将思维提升到上次停止那一刻的热度——这时一切才可以重新开始。
这既是对前边工作冷静下来的理性检视,同时又是新的创作的一次预热、一次激活。
预热和判断,这要解决情绪的问题、逻辑的问题、语感的问题。在停止创作的时候,你会离开那个特殊的、创造的世界。你的思绪,你的说话方式,在那个虚构世界里通行和应用的东西,都因为工作的停止、因为“走出”,被世俗生活冲散、改变和刷新了。这样,当你再次面对一张稿纸的时候,就必然需要费力地寻找和接续,找回原来的笔调以及热情。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每一篇作品的笔调都会有些微调,都会根据具体的情与境发生某些变化。所以要回到原来的笔调,原来的气息,不然一切都没法进行下去。
修改的第三个环节
在整个作品完成之后,一般来说要停顿一段时间,也就是将作品的毛坯搁置一边,让其冷却下来。一本刚写成的书,里面交融了多少炽热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刚刚煅造出来的器具,摸一摸还是烫人的,要抓到手里细细打磨它,一定要在逼人的热度退却之后才能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冷处理”。
但是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也有人不愿停歇,完工之后立刻开始从头修理起来。这或许是一个遗憾。应该尽可能地停息一段时间。停上多久才好?如果沉得住气,那就至少停上一两个月或者更长。这段时间,用来把出炉之初的那种热度降温,使我们能够贴近它,也能够有一些冷静和超然。这将会比较客观地看待那个时刻的激动,检视那个时候写下的所有文字。这是个困难、然而非常愉快的工作。你会尽量要求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他人一样,从头打量自己的作品。
这个阶段,你努力在意识上靠近那种“陌生”的状态,这样就会从磨得灼热的思维轨道里脱离出来,达观地理智地加以诸多判断。思维飞速旋转时写下的那些文字,这时要经受一次严格的挑剔和质疑。
沉入写作的时刻也许主观性越强越好,可以任性而执拗,完全不必顾忌别人怎么看,不在乎别人的思路,不受一些观念的影响,哪怕飞扬跋扈。这样才会获得更大的自由,一些超绝的奇思才会在这样的情与境中形成。但是一旦写罢,一部作品固定、确定、完成之后,这场“高烧”过后,也就不得不站在非常客观的立场上来回头检视了。
比起伏案工作的日日夜夜,比起那时的各种想象与激动,这会儿的作家也许显得“平庸”和“世俗”了一些。但这是完全必要的。
这就是修改的第三个环节。一般来说,所有的作品都要经历这个环节。
类似的环节还要经历多少次?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了不起的作家,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拉美作家,他会在这个环节上持久地做下去——即修改很多很多遍,以至于使原来的作品面目全非。再比如海明威,他自己说,他会把一部书的开头重写三十或五十次——我们看了以后有忍不住的惊讶,会觉得他是夸大其词。当我们自己终有一天遇到这样的写作场景时,当我们也需要这样艰难地修理自己的文字时,才知道这不仅没有什么夸大,而且是极其真实的表述。
海明威写作最早是用铅笔,后来用上了打字机。一部稿子用那种老式的打字机改上五十遍,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五十遍的劳动!五十遍的重新开始!这么多的艰辛,只不过为了求得一次顺畅、生动、和谐,让自己满意——完全满意。
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写作:我们可能没有海明威那么成熟、那么有才华,可是出自我们手中的作品又改了多少遍?不要说五十遍,扎扎实实地改过五六遍,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一想,也就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我们找到了最基本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耐心不够,修改得不够,没有在这个环节上下足力气,没有流下足够的汗水。
今天,也许动辄出手万言、纵横涂抹的“才子”们极不愿意听这些话,不以为然。实际上类似的启发同样来自鲁迅。他说:哪里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和聊天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训练自己的文字,其过程就是训练自己的耐烦心,训练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這是一种漫长的、超越一般的耐力,因为我们面临的工作需要极其仔细、认真和专注。事实上,这样的素质在谁的身上最早出现,谁就可能是一个成功者。今天是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只要涉及耐性、努力、爱和品格这一类,有人听了立刻就会觉得虚虚的,是漂亮话而已,太平常太浅直。但我却认为,这恰恰也是最有意义的强调。
一个人往往在年轻时,其创作经验和才能没有得到相应积累的时候,就是说比较幼稚的时候,反而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更为自信,更少修改。我们乐于尝试“一稿成”——有时会在稿纸上先把页码编好,比如说估计这篇小说会用200页稿纸,就先自在稿纸上编好200个页码,然后就从第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填满——最后把写成的稿子顺一遍,一部作品也就算完成了。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切都开始改变。作家就像一个中医大夫,看病越久,用药也就越加谨慎。那些老大夫在开药方的时候,有时加一味药减一味药,加加减减极为小心,如履薄冰的样子。倒是那些年轻的大夫,胆子很大,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其实我们知道,中医的药方中一般没有几味致命的猛药,多几克少几克没什么,害不死人的。可是老大夫为什么还要那么谨慎?只因为他治了一辈子病,太知道药的力量了。他知道这一味下得不对,它的作用会潜隐其中,后果将要一点一点显现。他对使用了一辈子的草药,在知的深度上当是更进一步的。
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也是如此。他是使用文字和词语的专门家,太知道词汇和文字的力量了。他知道文字的作用在这个作品里不仅是立竿见影的,而且还会是潜隐的、长久的,它会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他知道这里面的一些奥秘和隐藏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个方面是极为谨慎和苛刻的。
我们的修改无非就是要回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字和词像老中医对待一味中药那样审慎,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一个人到了年近五十的时候,也许会真的弄懂修改五十次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五十次是怎样的一场劳动、是一个什么概念。一部作品是由无数具体的“部位”组成的,它们都会让你在五十次的修改中一一揣摩,该是多么繁琐的一种工作。其实即便修改了五十次,你也未必满意。最后出版了,你再看一遍,也仍然会觉得哪个地方,比如哪个字和词用得很有问题。
我知道有一位中年作家,他的新作中的某些篇章,特别是一些开头,改了不止三五十次。这么多年改改放放,还是不尽如意。他说总觉得自己追求的那种意味没有释放出来。有时候不是意味,而是其他,比如觉得它启动的“速度”不对。是的,一部书因为长度还有其他因素,开头时给出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一部作品的“速度”和长度有关系,和叙述的笔调也有关系。作者要控制它的“速度”——这个“速度”靠个人去感受,先将其确认,然后再调动技能、运用文字去加以掌控。这方面,哪怕你做到了一点点,也需要更动许多文字才能达到!
作品启动时的“速度”出了问题,整部书的叙述就会手忙脚乱。它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速度”。它的“速度”当然要根据全书的发展不断加以调整,绝不会是一个匀速。这里说的“速度”可不是情节发展快慢的问题,而是语感和语言的调度方式,是情与境的交织状态以及感受。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启动的“速度”不会着眼于情节的发展,而要始终盯住语言本身。要对语言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才能有所感悟。这是靠长期的专业训练才会掌握的一种能力。
有时候不是“速度”,而是意味——因为开头的意味如何,必然左右着下面的叙述、叙述的色彩和韵致。所以有人说,长篇的第一笔就决定了整部书的基调。这样说并没有夸张。开头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寻找某一种笔调。如果一开始笔调有了问题,你当然要更改,要大幅度调动文字。
所以,某位作家说他开头部分修改了三十遍五十遍,一点都不让人惊讶。那不是夸张。
作家在网络时代、商业时代,在各种信息蜂拥的情况下容易浮躁。所以说能写下来都不容易,都需要特别的耐性,再要辛辛苦苦地修改,有些划不来。可惜这不是一个划得来划不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的工作。一般写作爱好者可以对自己放纵,一个专业写作者或有志于此的人,除了对自己苛刻再苛刻,也许并没有其他的出路。
在这些环节中,作家或许会觉得十分充实和愉快。原来它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会从每一句成功的修改中获得一次享受。他会看到改动的效果,一次次的进步,产生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感受是很重要的,离开了这种成就感和愉悦感,再没有什么更好地推拥一位作家往前走了。他由此获得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持久而可靠。
修改的其他环节
除了如上讲的这三个环节,是否还有其他的机会?如果有,我们就可以抓住。比如说来了清样以后,作家就有机会做一次很重要的修改了。事实上这不是一般的机会,写作者都有体会:当你面对清样的时候,与面对稿纸的修改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时刻,心态当有不同。你会感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的更动都更有效也更致命,好像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你会慎重再慎重。
面对清样的修改免不了要更为拘谨。作品变成铅字之后,面貌毕竟有些不同,有一种不难察觉的客观性质——你以前看到的是手写或电脑打印的文本,现在它排出版来了,庄重而又陌生。这个时候的修改会让作者的神经绷紧起来。
一般来说,出版社是不希望看到作者退回一张张改动繁多的清样的。但这也没有办法,作家不仅不会去考虑印刷的麻烦和成本,相反还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一寸一寸往上攀登。
最后有人会问,作品出版之后还有机会修改吗?肯定是有的,但可能说起来有些复杂。因为有的读者,特别是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会对这种修改提出异议,有时还会发出尖锐的批评。
但这种工作是可以具体分析的,即一位作家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修改了自己的作品。修改说到底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行为,而不是相反。一般来说,如果一位作家修改旧作不是为了其他,比如遮掩什么历史过失,而是为了追求表达得更加纯正和生动,那就是无可厚非的。
实际上,只有作者才拥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但要运用得当。或许作家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这个权利也是有限度的。他在修改后的作品上要加以注明才好。
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也会失去修改的权利,这时他就应该自愿放弃这个工作了。当一部作品在特殊的情况下出版,或者形成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一般来说很多年過去之后,作家也就不应再去改动了。比如,如果一位作家把自己更早的成名作拿出来修改,显然就有点不合适。况且它已经出版许多年了,有了相对广泛的影响和许多版本。他如果抓住再版的机会,把当年写的幼稚的地方改得成熟一些,把不太满意的情节和人物重新写一遍,这就不够得当,这样做,其实是超越了一个作家的权限。
一部作品在发表前,多放一段时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前面说过,这个时候你即便不去碰它,潜意识还是要不停地运动,它会在沉默不察的时刻、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不断地得到修葺,最后呈现出一个新颖的、出乎意料的结果。有人说,漫长的修改大多是为了让文字更好;但其他方面的改变往往更为重要。比如说思想层面、结构、情节,都要一一涉及。
一个仔细和敏感的阅读者,会识别作品中最细微的气息变化。一部得到反复修改的作品和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作品,阅读感受完全不同——它们的语感和其他,如气质方面,都是不尽一样的。
修改很少的作品,一气呵成的作品,在美学品格上倾向于单纯。有些所谓的“激情写作”就是这样。它们线索单纯,意味单纯。如果将其反复修改之后,就难免要加上时间留下的重重叠叠的痕迹,给人一种繁复的意象。这种情形究竟如何,对阅读是利是弊,还需要仔细讨论。
我认为一部厚重深邃的作品,大多数时候恰恰是要获得这种繁复之美的。单纯是一种美,就像有些作品一类,它即美在单纯。可是大多数的长篇小说却要追求一种“繁复之美”。一部吸引人的、难忘的单纯之作,可以是名篇,让一代代人爱不释手,但仍然可能并没有复杂深刻的思想。它是美好的,但不是巨大的。它里面也许缺少那种很难用语言表述的、重重叠叠的、不同方向不同思维的集合。正是这种集合,才使长篇小说有了自己独具的厚度。
我们看一些作品,会觉得它似乎话里有话,有不同的思维向度,其表述竟然很难让人概括。它里面其实充满了作家个人在创作那一刻的犹豫、探索,甚至是徘徊的痕迹。这些痕迹复杂交错,而且相互之间还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它们竟会在作品里形成另一种和谐——这部作品的深度也就因此而变得不可预测。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其实正是人性的深度、生命的深度,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够给予。
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写了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即她的代表作《阿德里安回忆录》。这本书她写得很久,很慢。它花费了作者相当漫长的时光。原来这是作家二十几年前写过的一个稿子,后来又被中年的她废掉了。她在反复的修改中,已将原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了。一次次重写、停顿,延宕了这么多年。她全部的作品数量并不很多,但却十分精致深邃。可见所有深邃的作家都具有反复修改的耐心。
作家的另一个幸福,就是身边有些信得过的人——你觉得他们的意见很重要,就会给他们谈和看,听一下宝贵的意见。你可以把作品拿给不同层面的人看,他们的意见会是不同的。比如说,社会实践者会从现实的角度给出意见;文体家则会格外挑剔形式问题。你还可以给一个很耐不住性子的人看,给年轻人看……他们提出的意见必然会带着某个层面的特征,这一切都将从正面和反面给予难得的启示。
人人都有一得之见,修改者如果“会听”,能够合理汲取,将是最好的一件事。
这里,我们把再普通不过的“修改”作为一个单元来讲,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它甚至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品质。我们现在的某些文学作品写坏了,其部分原因就是它们的创作者压根儿就不想好好地修改。他们要使自己的整个工作方式吻合于这个商业时代、快餐时代,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修改絮语
关于作品的开头/如何把一个人物写得传神/全知视角的自由与节制
有的作品开头并不够好。可是我所了解的是,那些开始的段落起码改了十遍,才变成目前的样子。
可见开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原因。一部作品的开始,作家要考虑的问题千头万绪,笔底下却只能写相对简单的文字。他的牵挂太多,可以说不堪重負。还有,就是顾虑太多,不放松,人一紧张就会动作僵硬。所以说作家们常常谈作品开头怎样反复改动。有的小说本来要写一个比较单纯的故事,要避免讲得枝蔓,于是开头更难。
许多作品是以写人物开始的,这样好像比较便捷,也相对保险。
写一个人物可以不去雕刻他的五官,而只是强化其他方面——读完后,读者却会细致地感受到他的面目神色。写人物的肖像也并不一定要具体地勾画那张脸:可以画他的背影或侧影,可以画他的大致轮廓;当然也可以精雕细刻他的鼻子、眼睛或头发。总之是为了服从于叙述的要求、你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切都要在心中把握,要控制它。
不光是写人物的外在形态,写人物的内心也有很多的区别。比如这部小说是采用全知视角去写的——我、你、他,这个“他”就是全知视角。用第三人称去写似乎很自由:它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作家都可以去写。因为这个“他”是全知的。如果用第二人称“你”,或者是第一人称“我”,就很难做到了。如果用“我”的话,写到“我”的时候可以随意,“我”对自己可以是全知的;可是写到“我”之外的另一些人和事,就很难直接写出来了。别人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我”要知道,是需要其他条件的。
有人可能说,为了方便,那么就让我们用第三人称吧,这样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使用全知视角的“他”,看起来最方便最快捷,实际上也不尽然,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物极必反的。特别自由了以后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无所约束地运用这种自由,就会把小说写砸了。它需要你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自由,有所节制。
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写了一个历史人物——玻利瓦尔。这个人是“拉美之父”,在美洲大陆被称为“解放者”。他有一个梦想,即把整个拉丁美洲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最后死去的时候很落寞,疾病缠身,统一的国家也没有形成。他在拉丁美洲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国家的广场上都竖有玻利瓦尔雕像。
马尔克斯的这部书是写玻利瓦尔生命的最后岁月,即解职后坐着船沿一条河航行的日子,大约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这本书就使用了第三人称。作家采用了全知视角,却极为节制。本来作家可以凭借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书中所有人的心事,什么都可以写。但是读下去我们会发现,马尔克斯并没有这么做。他并没有滥用手中的自由。
书中写到了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就是不写主人公玻利瓦尔在想什么,好像一次都没有写——这种克制必然来自一种设计,是有意为之。如果作家在架构这本书的时候想得不透,就很难这样写。让人不解的是,马尔克斯使用了全知视角,却在最需要洞悉和表达的主人公面前,将这种自由放弃了。
修改的耐心和等待/两本书的对比/内在法度和严整感
《迷宫中的将军》只有十多万字,作家搜集材料却耗费了长达数年的工夫。成书前后的修改,简直繁琐到了难以言喻的地步。从一开始结构,他就在不停地修正,直到最后成书,他还是在不停地修改。这时候一些朋友帮助了他——远在大洋另一边的玻利瓦尔研究专家不止一次指出他的一些技术性错误,还有其他种种问题。
为了写作此书,他细致研究了玻利瓦尔出行期间的天文资料,如某一日某一时是否满月、星星的位置、河流潮汐等等。他编制了详尽的人物年表、大事纪。这种准备的耐心,扎实的功课,显示了大匠的风范,透露了即将远行的信息。
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年之后的作品,他的创造力仍处于上升时期,如日中天。经过了艰苦漫长的写作训练,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自由的天地。他还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庞大市场的纯文学作家之一,有多少出版商在等待他的新作。但这些似乎都没有构成负面的干扰。他的自由体现在非凡的忍耐力上,体现在非同一般的工匠心上。他太懂得依赖时间了,知道时间会馈赠什么——时间能够给予的一切,绝非才华和勤奋之类所能替代。
我非常惋惜的是:眼下书出得太快!某些创作可能是这样形成的:昨天晚上刚有点儿想法,今天早晨就开始写了,并且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写完。这似乎是显示才华的一个方法。如此一来,仔细的修改当然是谈不上的,因为它将很快变成了清样,变成了市场上的书。现代印刷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辅以最好的装帧,让类似的产品一本接一本摆在架上,既是销售又是展示。这是不值得效法的。
我们即使在最顺利的时候,也不能想象自己是讲故事的“天才”,因为在粗糙的语言面前,这种“天才”是不存在的。假使故事和表述水准真的可以剥离来看,那么这个故事即便还算可以,讲出来也会有无法忍受的噪音,令人难以倾听。
打磨,修葺,起码是为了声音的圆润和流畅,从而降低一部文学机器运转时发出的隆隆噪音。现在我们常常对一些时尚阅读望而生畏,主要就是害怕这种无所不在的噪音,会让我们的耳膜受损,最后致聋。十九世纪那样的美好阅读不复出现,除了有声像影视制品的干扰,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出在写作者本身。作家们没有了忍耐力,没有了细细打磨的工夫,所谓的“创作”不过是不断地将那些浮躁的匆忙散布出来。
将文字浸泡在时间的水流里,一再地洗涤,只为了让其洁净。人的思维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完善,将松散的东西勒实,绷紧,最后让整部书变得非常牢固,让书的内在张力加大。
有人或许会担心这种反复思忖、反复改动会折损原有的感性和灵性。他们认为这样写出来的书有可能不自由不舒展,绷得太紧。这种情形是有的,所谓的文风拘谨。但是这与松垮稀薄相比,仍然还是要好得多。一部书内在法度严谨,读起来张力就大。
作家到了后来,出版作品变得很容易,有了一定的名声,也会同时失去原来的那种战战兢兢和小心谨慎。随便丢一颗种子在心里,还没等成熟就往外掏,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省略了第一个环节,即在心里修改的环节,所以一开始就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有些作家前后作品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令人惊愕,其原因往往是放弃了对自己的严苛要求。
一般来说,好的读者能够培育好的作者。每个时代的阅读质量是不一样的。要学会读书也许并不容易——不光读思想、语言、意味,还要读出作家本身,读出他写作这一刻的真实状态——这才算读懂了一部书。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比如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后来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二者虽然都是杰作,却在质地上大为不同。
《百年孤独》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写得很苦,运思长久,改动较大。读过之后,常常会觉得它绷得很紧——实际上它在纸上落下第一笔之前,已经在作家的心里不知修改了多少遍——不止一次地全盘推翻,走一步退两步,左右观望——这种慎重和严苛,最后仍然能从文字间感受到。
关于它的成书过程,有一本书叫《番石榴飘香》,里面谈得很是详尽生动。里面说,马尔克斯最好的一个作家朋友,是哥伦比亚人,马尔克斯曾跟对方讲过《百年孤独》的内容,这些显然是已经成熟的构思。他跟这位好朋友一遍遍地讲着这本书。后来对方又把这些故事讲给了其他人。不久书出来了,这位朋友赶紧到书店里买了一本——读完以后大骂马尔克斯,把书扔了,说自己简直给骗了,这跟那家伙当时讲给我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想见,马尔克斯跟他的朋友讲述时也未必故意虚晃一枪,未必是声东击西,当然更不可能是欺骗。当时他在心里就是那样架构的。他不过是在第一个修改环节里改变了它而已,最后把它变成了后来的那个东西——落在纸上之后可能又有许多修改。当年他能够口述给朋友,这已经说明那个构思相当成熟了,完全可以写了——结果最后仍有如此大的改变。
这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百年孤独》。
看完《百年孤独》,再看《霍乱时期的爱情》。后一本是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声名鹊起之后的重要作品。这对他来说,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生命阶段,生存的挣扎不再,崎岖的道路已告结束。生存状态必然会影响到写作状态。马尔克斯是一位大匠,是一个人,人性中共通的东西会潜在他的身上。果然,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与从容,还有自信,满溢在新的作品之中。
大家对照这两本书,可以试一下阅读的敏感。都是那么好的书,但却是两种美、两种质地。这儿不仅是指前一个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后一个吸收了传统的法国小说的一些技法——这只是外部的改变,是它的外壳。它的内在改变才是最致命的。作者的心力和心情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
后者比起前者,在第一个修改的环节上,控制力好像运用得完全不同。尽管马尔克斯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二十多年前就在心里酝酿的,是一个同样经历了长长的准备的作品,只是一直没有把它写出来。但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从中感到他在第一部长篇里经历的那些犹豫和痛苦。相对来讲,这一本书完成起来较为顺畅,也较为松弛;就是说,比起过去,它在第一个环节上有些放任。所以它读起来有另一种流畅和饱满感,十分自由。
作品如果放在心中煎熬,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某种拘谨和严谨就会同时出现。它在不由自主中被思维的那些线索勒紧起来,变得紧实。这期间还会形成独有的内在法度,给人一种严整感。这同时也是由一个作家纯熟的经验所反复控制和作用的,而不仅是一般的修改所能达到的效果。
比起《百年孤独》,后者缺少一些“繁复之美”,没有充斥“矛盾”,没有那些咔咔嚓嚓的思维的冲撞声,没有纠缠和堆积,没有相互交织犹豫、一次次调整所留下的隐痕。它的美学倾向偏于单一和流畅。当然,这同样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一部具有别样魅力的杰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只是它们究竟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不同。
心中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文字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光色和速度
修改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像构思中的那个“原来”,忠实于那个“原来”,而是不停地推翻和修补那个“原来”。只要修改,就要不同程度地推翻过去,即改正错误,使其变得更好。这就要看“原来”的错误犯得大小了。“原来”的错误犯得很大,就会将其大幅度纠正一通;“原来”从头到尾都错了,那就要从头到尾去改正;局部有错误,那就把局部改过来。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在改正错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还要犯下新的错误。最后对的多、错的少,这样积累起来也就通向了成功。它或许留下了一些微小的、不断犯下的小错,让这些东西留在里面,也就化为我们所说的那种“痕迹”。我们需要它们。
一部作品不停地打磨,有时也并非为了使其变得特别“光滑”。有名的例子,是罗丹雕塑那尊《巴尔扎克》:刚完成时很多朋友看了,都说这只手雕得太好了,总是夸奖这只手。罗丹端量了一会儿,默默走向前去,只一下就把那只手敲掉了。
世界上竟然有这种修改!他专门把特别完美的部位去掉了。因为他在观照全局,他心里装下的是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对于作品的整体来说,毁掉这只“完美的手”可能更好。可见让一部作品的每个局部都变得流畅光滑,有时反而是败笔。
我们有一个体会:当一部作品写得非常流畅、顺利的时候,他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一口气读下来;但是读完了却常常有种不满足感——单薄或简单。它好比是一条直冲而下的水流,为了浇灌,作者或许不得不出手阻止它:这儿挡一下,那儿改一下道,总之让水流变得稍微缓慢一点。这样水流经过的地方,会有更大的滋润力、渗透力。
缓慢和畅快,语势的把握,都在分寸之间。属于叙述节奏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修改中最让人头痛的事情。情节发展激烈的时候就一定要使叙述速度提升?也不见得。这要服从于整体的节奏,只能决定于作者调动全部的叙述技巧去控制。作家始终掌握语流的速度和方向:哪个地方要慢,哪个地方要快,哪个地方要光滑,哪个地方要粗糙,要做到一切都了然于心。
除了速度,还有明与暗的运用,这是光的使用。我们阅读中会发现,有些作品,比如长篇作品,某些局部给人阳光灿烂的感觉。这当然是光的投射作用。这一点和绘画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不一定直接写“这个地方阳光灿烂”、“空气透明”,他是通过调动文字、通过意象和语感等一切的文学手段,达到这样的阅读感觉,让人感受这儿“阳光灿烂”。有的场景,的确需要光,需要炽热的光。作家正是靠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激情,将一些小说场景变得闪闪发光。与此相反,有些地方则要写得阴郁,让其暗淡下来。
我们对于阴郁和冷色同样是不陌生的。文学叙述进入这样的地带,会有一种沮丧感将人笼罩。它与那些强光地带是交相映衬的,它们在作品中相得益彰。也就在这种光色的对比中,小说的叙述一路往前发展。
小说显然不可能在同一种色彩、同一种气氛和同一种节奏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作家要用文字表达出不同的气味、光色和速度。你唯一的武器就是文字。你没有发声演奏的乐器,没有摄像镜头,也没有画笔;你只能靠文字去解决明暗的关系、速度的关系、节奏的关系,还有——强烈的高亢的声音或者相反。
所有这一切,作家写在纸上之前,也就是在第一个修改环节里,可能早已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有的则是第二个环节中才趋于完成的;也有的是在第三个环节中才真正找准了基调,将它固定下来的。可见修改并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真正的创造。
短篇与中长篇的区别/阅读是他人的一次收获
写作短篇的时候,精力或许要特别集中,它需要写作者在单位时间内有更加丰沛的情感。它尽管篇幅不长,却仍然有可能放在心里很长时间,像马尔克斯的《异乡客》里的篇目那样,构思几十年才开始写到纸上。
从经验上来说,短篇和长篇放在心里的时间都会有长有短,但短篇进入第二个环节之后,也就是开始了纸上的写作之后,还是会比较快地完成。这不仅是篇幅的问题,还有写作心态的不同。写长篇要从长计议,写短篇要一气呵成。
一个万把字几千字的短篇,大概不宜将写作的过程拉长到几个月。它需要作者高度地集中精力、笔力,调度自己的能量,尽可能不间断地记录到纸上。而后就是修改了。它留给你修改的余地,也要比中篇和长篇小得多。
但较长的短篇也许稍稍有些例外。例如海明威有一个短篇叫《大河双心》,写一个从战场回来的年轻士兵,他掮着一个大背囊,走到一条河边,吃点东西就开始钓鱼:怎样钓鱼、怎样烤鱼……把这个过程细细地写完了。小说单讲情节似乎没什么看头——既没有发生爱情,也没有发生死亡,就是一个人走到这儿,看这条河不错,然后开始安顿下来,野炊,安放帐篷,做饼,吃东西。他极有耐心地钓鱼,钓上来,烤一烤吃了。但它却很吸引我们——这是因为看似平凡的生活描述中,饱含了丰厚而深邃的人性内容。而且,从语感上看,从内敛的文风上看,从一些隐隐的痕迹上看,我们会辨认出这是一篇经过了反复修改的作品。
真正的纯文学作品不靠外在的节奏快捷去吸引人,而是靠内在节奏的绵密——由此产生一种让人不忍读完的魅力。海明威的这个短篇大约有一万五千字,却有某种中篇小说的气质和蕴含。像类似的短篇小说,可能也要历经反复修改,让其留下一些“繁复之美”。但这并不是典型的短篇小说。
可见同样是修改,修改短篇和中长篇是不一样的。短篇不能过多地容纳作家在不同的时空里施予它的不同境界和别样思绪——而长篇和中篇就能够容纳。因为后者的写作过程是漫长的。作家会在修改的时候,再加给它一些漫长感,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它甚至需要、也必然需要再一次丰厚。作家要用自己在不同时空里的不同激动、感触和情绪,重新去弥补它,充实它。
一部长篇,仅仅是纸上的写作就用了五年时间,改了二十次——可是读者并不知道这些,或者不会在乎这些,反正要通过一次性的阅读去领略,获得你这五年十年的劳动、包括一次次修改留下的所有痕迹、总的印象。读者的阅读好比一张网,而你修改和写作的过程,就是不停地在同一片水里扔一些鱼苗、饲养它并让它长大。读者并不管你饲养了多长时间、放养了多少鱼苗,他只是一网拉上来,看的是最后的收获。
可是作为写作者,却要用不间断的、漫长而琐碎的劳动,来满足读者这一次性的获取。所以聪明人当然要尽可能地为读者准备更多的东西,要处心积虑地存贮。他会在较为从容的时间里不停地加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由此可见,作家应该把更长时间里的生命奥秘、包括技巧,堆到别人这一次性的阅读里面去,让他有一个特别丰厚的收获。
反复修改的利与弊/潜意识就像一只等待长大的小兔子
有人担心反复修改之后,会把作品改坏;还有人担心过度地修改,会使行文变得疙里疙瘩,造成不必要的阅读障碍。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仍然不是放弃修改的理由。
谈到“繁复之美”,有时就是破坏原来的流畅和简单。前边说过,流畅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好的,它可能也是“简单”的同义词、一个不好的症候。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形之下,思维会呈现出多种层次,对事物有多种观照的角度。不同阶段的修改就是为了增加思维的层次,借助時间的智慧。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今天考虑了一件事情,明天又会改变。为什么?就是一夜之间让你想到了事物的另一面、想到了其他的解决办法。
民间有一句话说得好:“夜间纵有千条路,白天照样卖豆腐”。就是说晚上打算得很好,有很多开拓性的想法,可是天亮了想一想,觉得还是不能这样做,还得回到很现实的道路上去。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容易在无边的夜色里想象,是有利于主观膨胀的环境,可以想得很多;到了白天,满眼熟悉的参照物都一一出现了,那你就会在这个客观的环境中判断夜里的思路。
创作的过程是主观膨胀的冲动时刻,活鲜与新异都依赖这种状态,但是也有其他风险。这就是要回到冷静、要用心修改的理由。
还有,作品在叙述中总是要陷入个人语境的,你会在一种语调中尽显天真烂漫,觉得一切都非常合理、非常有意思。可是一旦你从激动的创作态里走出来,再看你在那个时刻的一些激动放言,有时就会觉得可笑。那不是一个客观的产物。这就是你在新的参照物下,让思维回到了自己的“白天”,回到“卖豆腐”上去。
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不现实的东西,它当然需要主观的冲动,如果总是“卖豆腐”,肯定是平庸无比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而无视这种“豆腐规则”。就是说,它需要作家回到貌似“平庸”的客观判断,来阻隔和阻止一些不合时宜的“浪漫”想象。整个创作和修订的过程,就是这种一会儿客观一会儿主观,是两者的交织与合作,不断地平衡、博弈,让思维在这种状态中丰实和饱满。
创作中,伏案工作时,大可一意孤行。订改则要借用一点客观的思维标准,不断地权衡、考验、阻隔,不再完全顺从主观的浪漫和流畅——二者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复杂的关系,这样绞拧着作用于你的创作,让其向前发展。不同风格的作家会有一些区别,但在这方面大致都是一样的,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这两股力量的交集。
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会充分意识到这两股力量,并让其恩惠于他的写作。这里面好像充满了生命的奥秘。
调整和运用自己的潜意识,给它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潜意识在创作中的作用太大了。如果在落笔之前和之后过于仓促,就等于没有给潜意识留下相应的活动空间——它有一个慢慢成长、长大的过程,得给予必要的时间。一只小兔子生下来,如果不到两个月,它是长不了那么大的。作品为什么在构思中、在完成之后要拖延和存放一段时间?这好比一只小兔子,要让潜意识像它一样长成长大,来发挥作用。
让小兔子自己成长,不要反复地抚摸它。作品写完了放在那里,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好像把原来的创作扔掉了遗忘了,其实并非如此。潜意识的小兔子待在它的角落里,一天也没有停止生长。只要时间到了,回头一看,它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