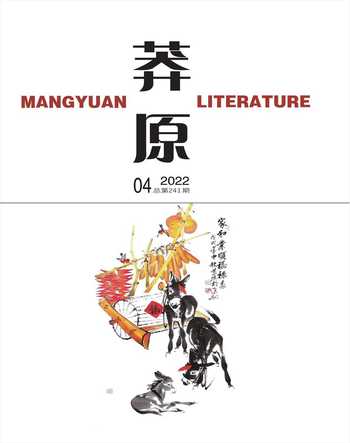满地瓜花黄
2022-04-29倪月友
倪月友
一
满世界都是黄,晃眼的瓜花黄。
我想不起其他颜色是什么样子,看不见的刷子把我记忆中的其他颜色擦掉了,只有黄色无处不在。黄色的潮水街冷清清的。瓜花黄的奶娘从街东边走来拉着我说:东子,我们回家!透骨的冰凉传遍我全身,我打了个激灵,说:奶娘,酉阳好耍吗?她埋着头,声音嘶涩,不好耍,哪都不好耍,只有陪东子才好耍。
她拉着我回寨子。我们遇见些熟人,没打招呼。
奶娘从黄口袋里拿出件衬衫说:这白衬衫你穿一定好看。明明是瓜花黄衬衫,为什么说是白衬衫?我不愿和她争,争起来她会伤心。我是她儿子,怎能让她伤心呢?
我去房间换衬衫。换好后我感觉浑身的赘肉在衬衫里荡来荡去。奶娘在阳光里眯着眼打量我说:嗯,好看,好看!她又在流泪。我问:奶娘,为什么哭呢?她笑了,黄色的泪水闪闪发亮。她说:你好看,奶娘高兴呢!我想让她给我讲讲酉阳。我还没去过酉阳,可好多人都搬进了酉阳城里,寨子里人越来越少,房子只剩下个壳儿。以前为一锄泥土也要打死人的土地长满了铁蒿。野猪也不时蹿进寨子。
杨二毛在酉阳买新房后给奶娘发了请帖。奶娘说:杨二毛看得起我们孤儿寡母,一定去。我穿着衬衫在寨子里游荡。到处是瓜花黄,瓜花黄树,瓜花黄房屋,我也仿佛悬在瓜花黄的空气里。
我怕遇见那些顽皮的孩子。他们向我扔石子和泥块,还大声喊傻癫子!看到他们我会跑开。要是奶娘看见了,会耐心地说:田传、张锋、宋亮,你们莫欺负我儿,他造孽得很哦!他们便大笑着散开了。奶娘拉着我说:东子别怕,我们走!我跟着她,像两只飘在低空里的瓜花黄风筝。
奶娘低头流泪。她宁愿泪水掉进泥土,也不让我看见。奶娘带着我去地里挖洋芋。我把洋芋捡进箢箕,把藤子归成一堆。她微笑着夸我:东子要是脑子不坏,该是多好的男子汉啊!她夸着夸着,泪水又流下来。我不说话,假装不看她,干得更起劲。
我在寨子里荡来荡去,想有人夸我衬衫好看,然后我就说,奶娘去了酉阳,新衬衫是在酉阳买的呢。
天空逐渐模糊,奶娘还没喊我回家吃饭,暮色中飞过几只鸟影,发出响亮的叫声。我看见毛大伯正在院里洗脚。他大声对我说:东子,穿新衣服啦,哪个买的白衬衫,好看呢!我很纳闷,明明是瓜花黄衬衫嘛!不过我还是很得意他夸我好看。我说:奶娘在酉阳买的呢!他嘿嘿笑着说:哦,酉阳买的,高级!我心里美滋滋地回家。张伯娘、王幺娘和王姑爷都夸我白衬衫好看。我心里舒坦,像踩着一缕瓜花黄的风,跑得飞快。我看见李峰家院里也长满了铁蒿和露水草。
天色晚了天空要关闭眼睛,我将什么也看不见。我慌慌地往家赶。头顶不时传来噼啪噼啪的声音。淡黄的天空不时被一些影子划开。奶娘说那是夜屎八,老鼠偷吃盐就成了夜屎八。正胡思乱想,听见奶娘在呼唤我。路边的铁蒿晃动起来,起风了,天要黑了。我大声回答着奶娘的呼喊向家里奔跑。
奶娘站在院子里,一抹淡黄的光照着她。她说:要吃饭了,去哪里了嘛?
奶娘,都夸我新衣服好看呢!奶娘忙笑着说:东子好看,穿新衣服更好看。走进屋,我们置身瓜花黄的灯光中。我看见了奶娘脸上淡黄透明的泪水。她为什么总流泪。我不想她不高兴,更不想她流泪。
二
奶娘關了灯,我熟睡过去,梦见了瓜花黄的梅,瓜花黄的伯伯。瓜花黄一消失,我就成了瞎子,什么也看不见,成为瞌睡的俘虏。
出事那天,瓜花黄铺天盖地涌过来,粉刷了树林田野、天空大地,粉刷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其他色彩,我不是我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和李峰才上初二。
王幺娘说李峰早结了婚,妻子漂亮,小孩也聪明,在城里读好学校。
昨天热得我全身漏汗。山坡下,操场上有同学在打篮球。穿红衬衫的伍老师从校门口走出去。我好想看到梅的影子,可她不在。梅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姑娘,她对谁都和气,每次考试前三名。可李峰并不服她,很多人都不服她。说她是悄悄用功把成绩搞上去的。伍老师表扬梅,李峰和几个男同学带头起哄。
李峰领着一伙手持棍棒的少年向我冲来。我汗水流得更猛了,汗珠滴在灰尘里噗噗响。
我喜欢梅,可我不敢打抱不平,我不敢惹那些同学,也不敢对梅表达爱慕。才上初二呢,爱慕的想法简直荒唐。
是矮胖墩儿先动的手。木棒击中我脑壳时,我听到了“咔嚓”一声响,短促、锐利,充满痛感。天空、大地和少年被看不见的刷子瞬间刷成了瓜花黄,全是瓜花黄。我跌坐在泥地上,脑壳木楚楚地疼痛。
梳偏分的少年踢我一脚说:狗日的,还屌不?我歪过头轻轻说:不屌了。少年们哈哈大笑。短头发少年蹲下来拍拍我脸说:耶,狗日的可爱嘛!喊老子爹,不打你。
我说:爹。
少年们又一阵哄笑。短头发少年得意地站了起来。远山顶上搁着瓜花黄的夕阳,大山的嘴巴把它一点点吞下去。我脑袋里的疼痛平息下来,满眼瓜花黄渐渐变淡。
李峰在我面前蹲下挑衅地看着我。李峰和我都是潮水街西边山坡寨子的。以前我们两家来往密切,还转活路种苞谷和打田栽秧。李峰的老汉李槐在水泥厂帮工,没时间干农活。我伯伯便常帮李峰奶娘磨面挑水。他说帮助女人应该,气力用了气力在。
李槐不高兴,上门骂伯伯多事。伯伯辩解说:我帮忙还不好吗?李槐大骂:谁要你帮,关你卵事。李槐走后,奶娘把火钳使劲摔在火铺上说:家懒外头勤,锅巴冷饭胀死人。伯伯说:隔壁邻舍,帮忙也要不得?奶娘喊起来:帮,我看你是想帮到人家床上去。伯伯羞愧地小声说:你这婆娘说些啥哟,天句地句乱说。奶娘和伯伯都不说话了,又各自忙着活儿。
李峰用食指抬起我下巴说:崽儿,这些是我兄弟,以后给老子乖点,不然见一回打一回。他身上有股刺鼻的腥味,像梦遗的气味。他突然使劲捏住我下巴大吼:崽儿,我的话记住没?我说:记住了。李峰满意地带着少年们走了。
寨子西边李槐家祖坟塘紧挨我家自留地,交界处有棵鼎罐粗的杉树。李槐说坟塘周围一丈内的树木都是风水树,杉树是他家的。伯伯说杉树在自留地边上,影响庄稼生长,所以杉树我家也有份。李槐找劳力把杉树砍回了家。伯伯上门讨说法,李槐火冒三丈地提斧头要砍他,幸好毛大伯抱住他,招呼伯伯快走。伯伯要不回杉树,灰溜溜地回了家。
奶娘数落他:明明狠不赢,偏要去,真不知死活。伯伯苦着脸说:我至少该上门问问吧,不然被人当傻子。奶娘冷笑:本来就是傻子,还怕人家当傻子,谁愿拿鸡蛋碰石头?伯伯低下头,脸红到了脖颈。
少年们走后。山坡下学校操场的人影逐渐模糊,瓜花黄的天空暗淡了。我拍拍身上的黄泥灰,困意漫漶,黄昏静寂,没鸟鸣也没蝉声。我强打精神冲下山坡,跑进教室。
瓜花黄的灯光刺眼。读报课的预备铃还没响,同学们在大声讲话。梅在和同桌讨论什么,看见她,我心里隐隐麻了一下,像蚂蚁突然爬过脚板心。
李峰一脸严肃坐在教室靠后边的座位上,桌子上摆着书本。他偷偷瞟了我一眼,又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假装看书。
我是被李峰约到学校后面坡上的。我正在食堂吃饭。李峰端着碗站在我面前说:吃饭后去后坡上的大石头下等我,有事找你。从我们两家吵架后,我和他就很少来往。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中学在离家很远的龙潭街上。后来他和龙潭街上好多街娃混得熟,有时还参加街娃打群架。
我想他不会把我怎样,毕竟我们都是潮水人。我准时来到大石头下。大石头三米多高,十多米宽,像堵墙立在学校后的半坡。没想到李峰会喊那么多人修理我。还好他们没要我命,也没让我流血。
第一节晚课,教数学的张老师喊大家复习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提醒大家牢记德尔塔公式。我脑子一片空白,想不起德尔塔是什么。我问同桌王亚红,她翻了个白眼说:德尔塔就是个像刀刀样的三角符号。我问在哪一页。她拍着桌子说:你傻瓜吗,老师今天才讲,在37页。我把书翻到37页,瓜花黄的书页上全是淡黄的文字,小节内容是一元二次方程解法。我没找到德尔塔。我说:王亚红你好坏,明明没有德尔塔嘛。后排的刘晓珊热心地帮我指着个三角符号说:这就是德尔塔。那小小的三角符号,果真像刀刀。之前我数学成绩还可以,现在居然很多符号和公式都看不懂了。我有点沮丧。
自习下课后,张老师背着手在教室转了两圈。见我还在看数学书,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哪晓得我已经看不懂了呢!张老师走后,我走出教室,沿着走廊外没灯光的路面出去。以前我喜欢这条没灯光的路,安静、凉爽。可今夜我眼前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一团团睡意袭来。我害怕倒地睡过去,连忙退回教室,懵懂地坐在座位上。第二节是物理课,我发现只认得些简单的字,其他什么也看不懂。
下自习后我踩着一路瓜花黄的灯光回寝室。李峰叼着烟进寝室,烟头一亮一灭。我上铺王贵说:耶,你崽儿屌起了哟!李峰迅速瞥我一眼。恶狠狠地对他说:你是不是皮子紧了?王贵不敢接话。我浑身哆嗦,全身起鸡皮疙瘩。熄灯钟响寝室灭灯,我一下睡过去,仿佛是和灯光一起睡去的。
早上我睁开眼,满眼瓜花黄。瓜花黄的空气、房屋、铺盖。我脑子里像装满了水,胀得痛。我进教室打开课本,发现好多字都不认识了。我努力回忆那些似曾相识的字,越想头越痛,脑壳中那看不见的刷子正在刷去我对所有字的记忆。
我去伍老师办公室说想退学。他吃惊地看着我说:怎么回事,成绩那么好,怎么要退学?我找不到理由,只好傻笑。他看着我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给我讲了一大堆要读书的道理。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把他罩在瓜花黄里。他很精神也很慈祥,像谁家的奶娘。他讲完问我: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接下来两天李峰都缺了好几节课,没谁问他去了哪里。我上课老是拿错课本,经常挨老师批评。我只好让王亚红帮我拿。起初她不肯,当她发现我真有问题时,就主动帮我了。
我无法完成作业,老师点名批评我,骂我自甘落后,鬼混日子。伍老师把我喊去,问我究竟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他又滔滔不绝给我讲道理,讲得我很累。
伍老师终于发现我脑子出了问题,通知伯伯和奶娘把我领回去。奶娘背着个大篾背来接我。她说伯伯在家骂我,也骂她,骂得她浑身发抖。奶娘背着我的铺盖箱子,我跟在她后面。出校门时,我看见梅正趴在教室外的栏杆上看我们。
三
伯伯在桂花树下绞纤索,像要把手脚连同身体都绞进去。我们走进院子,奶娘累得呼呼喘气,像要拉破的风箱。院子里很安静,空气却像要爆炸。伯伯看见我们,撇撇嘴,把脸转向另一边。奶娘把铺盖箱子卸在阶沿上。我想给伯伯打招呼,可见他转过脸,心里害怕,不敢和他说话。
奶娘做好晚饭喊伯伯吃。他无声地坐下使劲扒饭。一连几天伯伯都不和我说话,我也不敢和他说话。他逐渐颓唐,愤怒在他身体里生霉发酵,酿成伤感落寞,酿成拖拉疲沓,胡子长得掩盖了嘴唇,油腻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像洒了胶水。
天一黑我就眼前漆黑,不由自主睡过去。迷糊中我仿佛听得见清洗锅碗的声音、宰猪草的声音、柴火燃烧的声音。窗上一出现淡黄的亮光,我就会醒过来,就会穿衣起床。没谁来看我,孩子退学这种事很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寨子里好多孩子都只上完了小学,我还上到了初二呢。
奶娘常带我上山挖洋芋。她在前面挖,我在后面捡。阳光照着,她热得脱下衣服,干瘪的乳房在胸前晃荡。我动作慢,她扔下锄头帮我,她问我:在学校是不是和谁打架了?
我说没有。她说:为什么不想上学了?
我说我脑壳痛,一上学就痛,书本上的字我都忘了,一个都不认识。她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好像有把刷子几下就擦去了我对知识的记忆。
她说:脑壳还疼吗?我说不了。她问:还晕吗?我说不了。她说:去医院看看。我说:又没病,不去。她流下泪:将来我老了,你怎么办哦?看到她流泪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赶忙捡洋芋。
伯伯越来越苍老邋遢。他不和人说话,别人和他打招呼也不答应。开始别人骂他二气,后来晓得他精神出了问题,都可怜他。张伯娘说:以前飞起来的汉子,现在说垮就垮了,人啊,真说不清楚!王幺娘说:虽然德发是上门女婿,可把家撑得像模像样,他垮了那家就麻烦了。
奶娘把洋芋背篼顿在阶沿上。伯伯没回来,天色暗下来,我无精打采,满眼瓜花黄越来越淡,像涂的黄泥巴。奶娘燃起火,点上煤油灯。火光和灯光让我抵挡住了瞌睡。我坐在火铺上看奶娘煮饭。她眼睛肿得好大,是偷偷哭肿的,火光把她的脸照得很亮。晚饭熟了伯伯也没回来。
奶娘站在院边土墙上呼唤伯伯。伯伯始终没答应,她就一直呼唤。伯伯终于站在她面前,她把他带进屋。她没想到突然要照顾退学的儿子和神戳戳的丈夫。
伯伯端起饭碗扒拉两下突然哭了。他鼻子嘴巴挤出一堆无声哭泣,泪水像滚豆。奶娘说:哎,莫哭莫哭,快吃饭。我以为她也要哭。她很从容地照顾我们,没哭。
伯伯不和人说话,常莫名其妙地流泪。他又瘦又黑,落魄邋遢得像抽了筋骨,完全看不出当年帮人挑水磨面时的健壮。很多人都知道我变傻变痴呆了。王姑爷说:怎么回事,不是读书读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傻了?
奶娘眼角爬上了鱼尾纹,鬓角有了白发。她怕遇见熟人,远远看见熟人就绕道走,实在绕不开,就谦卑地对人家微笑,像欠了人家的债。别人总绕来绕去向她探听我的情况,安慰她别担心,会好起来。她努力忍住内心的痛楚,不断点头,像听话的孩子。
我趁奶娘煮饭时跑出门,在寨子里乱逛。奶娘煮好饭就站在院边土墙上喊:东子,回来吃饭啦。我和伯伯从不同地方跑出来跟着她进屋吃饭。我和伯伯都像是她的孩子。她默默忍受着操持这个家,让家不散,让我们有家回。
奶娘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孩子。他们老来得女,把她当宝。她二十岁时伯伯上门做女婿。伯伯家穷,弟兄三个全是单身汉,他是兄弟中最小最聪明的。刚结婚时,别人夸他能干,力气大会计划。后来我和李峰一起考上了龙潭的中学。人家羡慕我们,说我们家将来有搞头。
伯伯脾气暴躁,奶娘做得不好,他就大声斥骂。外公外婆去世后,他更无顾忌。我做得不好,他也会大声骂,我很怕他。他们本来打算要两个孩子,可生了我后,就再也怀不上了。
春天瓜花黄的阳光照得山寨、树林和田野很精神。伯伯突然不再出去晃荡,成天围着奶娘说话。奶娘领他去理发刮胡子。他又精神起来,脾气也比以前温和。
奶娘下地挖土,伯伯也下地挖土。我背着小背篼跟在他们后面。刚下春雨,到处生机勃勃,鸟语花香。他们从地里掏出胖嘟嘟的折耳根,抛给我。我把横七竖八的折耳根理顺,捏成把,用丝茅草捆紧,扔进小背篼。他们看着我笑。不上学真好啊,我从没感到这么幸福过,真想大喊几声。可我喊不出来,只好更快活地劳作。伯伯爱吃折耳根。晚饭时,奶娘给他拌了一大碗。我喜欢听他咯吱咯吱地咀嚼,喜欢看他享受的样子。
出正月十五,李峰就背着大包包出门打工,他是我们寨子第一个出门打工的。毛大伯问李槐:李峰为什么不读书啦?
李槐说:娃儿觉得读书没意思,读好了也不一定赚钱,伍老师都没劝住他,铁定要出门,把课本都烧了。毛大伯摇摇头:这孩子不读书太可惜。我隐约觉得李峰退学和我有关。
晚饭时伯伯说:哎,东子,给你说。他不是要给我说,而是要和奶娘说话。他们总称对方东子,我的名字就是丈夫或妻子的名字。我的名字和命都嵌进了他们命里。伯伯轻声地和奶娘说农事,说季节变换,说往昔时光,也说人情世故。
伯伯吐了口气说:我认命了,这人啊,不管怎么扳,都扳不过命,命中只在八合米,横遍天下不满升。奶娘放慢吃饭速度,眼里汪满泪水,没接他话。
孩子们开始奚落我。他们试探着靠近我,在我身后哧哧地笑,轻声喊我:东子,东子。我转过身他们立马站远。牛牛说:东子流大鼻脓了,那么大还流鼻脓。我使劲吸了下,鼻涕打个旋进了鼻孔。他们大笑起来。我也笑了。福胜说:东子笑个屁,那么大还流口水。我又使劲揩了揩下巴。他们又大笑起来。我也嘿嘿地笑起来。
牛牛说:东子你是读书读傻的吧?他们一阵哈哈大笑,快活地齐声喊起来:傻子!东子傻子!哈哈哈。
早饭时伯伯双手按着肚子喊痛。细密的汗珠在他脸上汇合成溪流淌下来。他蹙着眉对奶娘说:东子,肚子痛,很痛!
奶娘慌忙试他额头,刮凉刮凉的。她说:东子,我们去医院吧!伯伯说:痛得狠,怕还没拢医院就要死。她越是慌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伯伯呻吟起来,这个早晨仿佛充满了绝望。我望着痛得像犁耙的伯伯,看见一束鲜亮的瓜花黄从他头顶钻出来,弯弯曲曲地升起了去。奶娘给他冲了杯白糖开水,搀扶他喝下去。
疼痛没止住,汗水一串串淌下来。伯伯说:东子,还有吴茱萸籽没有,给我吃几颗。奶娘翻箱倒柜找到一小捧吴茱萸籽,倒了半杯热水给他吞下。这是个不消停的早晨,到处挤满瓜花黄的声音。蝉在树林里、叫鸡子在草丛里、黄蛤蟆在水塘里断断续续叫嚷。没有风,风藏到了哪个旮旯?没有风,风声却漏了出来,灌进我耳朵,脑壳晕乎乎的;灌进我衣服,衣领翻起来。奶娘焦急地转来转去,满头大汗:怎么办呢,先人!
伯伯的呻吟逐渐小下去。奶娘理着他的头发,轻轻问他:好点了吗?
噢,好点了,老天爷,总算好点了。
伯伯微闭着双眼喘粗气,额头上的青筋一起一伏。突然他拉过奶娘的手,费力地向我点点头。我向他挨过去,把手搭在他手上。他的手冰凉,湿滑。他望着奶娘,断断续续地说:带,带好东子。嘭!伯伯身体里发出沉闷的声响。闪电般的瓜花黄从他身体里射出来,消失了。我吓得连忙缩回手。
伯伯在奶娘怀里瘫下去。奶娘泪水奔腾,声嘶力竭哭起来:哎哎,德发,德发!我第一次听她喊他德发,不喊他东子。
东子,你伯伯走了,只有我两娘母了!奶娘拉着我说。
奶娘,伯伯不是在这里吗?
他扔下我们走了,只我两娘母了!奶娘说。
奶娘不像撒谎。我问自己:伯伯为什么要走,去了哪里?是嘈杂的声音把他带走了吗?
东子,摸摸你伯伯,让他放心上路!奶娘说。伯伯的嘴微微张开,半睁着眼。我摸他额头,光滑柔软冰凉。我心里说:伯伯,走吧,想走就走吧。
洗净后的伯伯先躺在两块泡桐板上,又被装进了棺材。
瓜花黄的歌声唱了几天,人们抬着淡黄的棺材出去。我站在阶沿上没流泪。奶娘弓着身子跟在抬丧队伍后面,哭得像个孩子。
四
我不信伯伯在那淡黄的棺材里。我记得奶娘说:东子,你伯伯走了。对,伯伯只是走了,脱下身体的壳儿走了,他的声音、影子和魂也走了。他一定没走远,还藏在寨子某个角落。伯伯天性调皮。我刚退学那段时间,我找不到他,只有奶娘呼唤,他才从某个角落跑出来,神秘得很。现在他也一定藏在寨子某个角落。嗯,他只是走了。我想奶娘大声喊东子。她一喊,伯伯就会跑出来。他太调皮了。
伯伯走后奶娘几乎没笑过,总说:东子,只有我们两娘母了,要听话噢。我说:奶娘,我大了,听话。她摸着我的头长长地叹息。
我想奶娘大声喊东子。我有意躲她,在寨子里到处乱窜,东家柴场、西家竹林,甚至寨边的坟塘。我尖着耳朵等她呼唤,只要她呼唤,我就迅速跑回家,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伯伯。
在寨子里,我得尽量躲着孩子们。他们两个三个跟在我后面,边向我扔泥巴边喊:傻子,癫子,傻癫子!一看到孩子,我就迅速缩着身子躲过去。只要有田传、张锋、宋亮带头,其他孩子就格外卖力。
我不是怕孩子们扔土块石块、喊傻癫子,是怕被他们发现,免得奶娘向他们打听我。我还要躲大人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去了哪里,免得他们告诉我奶娘,让她轻而易举找到我。
奶娘找不到我也不大声呼唤我了。她把饭煮熟后,就在寨子里到处寻找,竹林、树林、园子、坟塘,到处寻找。她焦急、匆忙,满头满脸都是汗。她眼力越来越好,嗅觉越来越灵敏,我影子一晃,她就会看见。有时候我影子还没晃,她就闻到了我气味,走过来拉着我回家。
为了让她大声呼喊我,我想出了好多点子。我爬上臭烘烘的牲口棚埋在苞谷壳里,牲口棚气味扰乱了她嗅觉,她终于找不到我了,她依然没大声呼喊我。她向人家打听:看见我家东子了吗?人家说没看见她就慌了,忙去人家的粪池边,寨子的高坎边、水沟水氹边找。她找不到我就坐在地上哭。泪水一串串掉下来,伤心透了,她怎么就不大声呼喊呢?
看到她伤心我连忙跑出来,站在她面前。她愣一下,拍打着我肩膀哭得更厉害:去哪里了嘛,吓死奶娘了!我大声说:谁叫你不喊东子,你大声喊东子,我就出来了。我把手拢在嘴上示范了一遍。我的声音好响亮啊,传得远远的,好像每个角落都能听见。她笑了。这是伯伯走后她第一次笑。
我正在坳田看蚂蚁拖虫子,突然听见奶娘在大声呼喊我,那么响亮动听。我忙兴奋地跑回家。我想伯伯听到喊声一定會从哪个角落出来。可我失望了,伯伯没出来,还继续藏在哪个旮旯。我沮丧地跟在奶娘后面,感觉吃什么都没滋味。
伯伯是不是嫌我跑出来得太快,才不跑出来呢?我在柳树湾摘野豌豆时,又听见奶娘在呼唤我,充满慈爱和担忧。我没答应,故意拖延一会儿才走出来。我还是没看见伯伯,他还坚决地藏着躲着。我心里埋怨他:真犟,奶娘呼唤东子了,怎么还不现身,还不回家吃饭?真是太不讲理、太调皮了。
伯伯就在寨子里,我要把他找出来。奶娘喊我跟她上坡做活路,我不去;喊我跟她去赶场,我也不去。她拉我诓我骂我,我也不去。我要用大把时间找伯伯,不信找不到他,他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奶娘说过他只是走了。他走不了多远,就在寨子里。我在寨子的小路上疯狂奔跑,只要我跑得快,他就会躲不及,被我发现。
我跑啊跑,胸腔里最后一丝气都要抽完了,还是没看见伯伯,他躲得太快了,像阵怪异的风,说不见就不见了。也许他会变成一件衣服,一双拖鞋,一顶帽子或一个瓶子,然后藏进荨麻林,竹林,树洞,苕洞,坟塘旮旯得意地看着我忙碌和寻找。嗨,我相信不管他怎样变,我都会认出来,我要和他比,和他斗。我在寨子里每个地方仔细寻找,只在奶娘大声喊我时,我才会恋恋不舍回家。
人家都说我疯出马了,不好招呼,杀了人都不抵命。孩子们根本不怕,依然跟在我后面嘲笑我,奚落我,向我扔石块土块。我不在乎,小屁孩懂什么?
万事通赵幺公对奶娘说:这细娃肯定中邪了,要找先生料理。奶娘找打太保的冉先生给我驱邪赶鬼。冉先生在我家堂屋又唱又跳,还鼓着腮帮吹牛角。牛角声低沉悲怆,狗不吠了,蛤蟆不吵了,虫子也不叫了,寨子像被收拾进了一个大罐子,很安静。冉先生吹完牛角,又跪在堂屋念咒打卦。奶娘不断从地上捡起卦子递到他手里。瓜花黄的灯光照着,他们看上去很神秘。奶娘佝偻得像饱经风霜的稻草人,冉先生肥实得像大草凳。他终于打顺了卦,站起来烧了纸钱。临走时,他抱走了我家一只大叫鸡。
我跑累了也找累了,伯伯真是太会躲藏了,我连他的影子也没找到。我不甘心,还在寨子里到处游逛,我相信一定会遇见他。奶娘没法,只好由着我。她每次在院子里大声呼唤,我就会立马跑到她身边。
打太保的冉先生爱上了来我家。每次来都静静地坐在火铺尾巴上抽烟。黄色烟雾在屋里乱窜。他已很苍老,儿孙们都在外面打工。他悠闲地吐出口烟说:这些读书娃啊,都读糊涂了。奶娘疑惑地看着他,等他继续往下说。他说:东子把脑子读乱了,不过总有一天会好的,可李峰就扫皮了,大天白日抢人家耳环,进了班房,一辈子的污点啊。
奶娘俯身捅了捅火,没说话。她只担心她的东子,对谁进班房不感兴趣。冉先生自感无趣,从嘴里摘下蜡黄的烟杆,在鞋尖上磕出烟屁股,揣上烟杆走了。
我正蹲在油菜地边看黄蚂蚁拖黄蝴蝶。毛大伯在我面前蹲下来嘿嘿地笑,说:东子看哪样?
看黄丝蚂衣儿抬飞娃儿。
他又嘿嘿地笑,问好耍吗?我说好耍!
他说:我教你喊黄丝蚂衣,会喊来好多黄丝蚂衣。我说:你喊嘛!他向周围看了看轻声喊起来:黄丝蚂衣儿,来抬朒儿(肉),黄丝蚂衣,来抬朒朒(肉)。喊了两遍也没喊出更多蚂蚁。我望着他嘿嘿地笑。我想说大把年纪了还吹牛。但我忍住没说。
他突然挨近我轻声说:东子,冉先生常去你家耍吗?我点点头。你奶娘喜欢他不?我说不晓得。
他在你屋耍得夜深不?不晓得。
东子怎么不晓得呢?我睡得早。
他们抱过吗?他给我比了个手势。我说没看见。
真没看见还是假装没看见。真的没看见。
你说实话,我给你糖。他掏出一颗糖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说真的没看见。他见我坚决地摇头,把糖给我,转身走了。
我把糖块放在一只黄蚂蚁前面。那蚂蚁围着糖块转了一圈后飞快地爬走了。很快它就领着一大群蚂蚁来搬糖块。
寨子里前天走了些年轻人,昨天又走了些年轻人,今天早上好像也走了些年轻人,寨子越来越空。
可奶娘常说寨子是十几年来慢慢空的。她说:东子,十几年走的人多了,寨子都快空了,年轻人都在外打工。
我不想纠正她,免得她又伤心。我看着天边鲜黄的云彩说:嗯,我要等伯伯回来。奶娘笑着说:走了的人,哪还会回来。
我说:他肯定没走远,还在寨子里。奶娘说:对,还在寨子里,他哪里走得远哟。我嘿嘿笑起来。她看看我,突然又流泪了。她嘶涩着说:东子,你都快三十了,怎么还缓不过来?
我埋下头轻轻说:奶娘,我缓过来了。她叹着气摸了摸我头,挤出笑容说:嗯,我们东子缓过来了。
新年李峰开着辆越野车进了寨子。王幺娘说他在外面做了老板发了大财,还在酉阳买了几套大房子,现在回来接他奶娘和伯伯去城里住。
李峰家阶沿上坐了好多人,他叼着烟坐在门边。我站在小路上听他们说话。大家都在议论那辆越野车。李峰的奶娘在请大家吃瓜子和糖果。李峰对我笑了笑,不像喊人打我时那么凶。他进屋提出包糖果给他奶娘,还对她说了什么。他奶娘走过来笑盈盈地把糖果塞给我。大家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看我们。
新年刚过,李峰带他父母离开寨子去了县城。
秋收后,寨子里的老婆婆们没事就串门。张伯娘坐在我家门槛边对奶娘说:不晓得李峰几时想转了,要出钱把潮水街进我们寨子的公路铺成沥青路。奶娘蹲在灶门前煮猪食,没接话。
老人们都说李峰仁义,搬出去了还掏腰包给寨子铺沥青路。寨里到县城买房的越来越多,哪家买了房,都要在新房办酒席邀请老乡亲。奶娘去酉阳吃了很多次宴席,对县城也好像熟悉了。
她的话越来越多。一会说寨子空了她心也跟着空了;一会说寨子空了好,清净些。每次早饭时,她都说:东子啊,我都老了,你还不清醒,我死了,你怎么办?
五
奶娘脸色淡了,没了光泽,眼角和脸颊也起了皱褶。
不晓得梅怎么样了,毕業了吗,或者也出门打工了?还有王亚红,还因为邋遢被嘲笑吗?
寨子很难看到年轻小伙子,更别说年轻女人。来我家耍的冉先生走了,被装进淡黄的棺材抬上了坡。后来毛大伯常来我家耍,一段时间后他也不来了。他宁愿一个人在家也不来我家。过年时他儿子媳妇回来看他,给他买了高档瓶子酒,还给他好多钱,也不晓得对他说了什么。
每天醒来,我都看不见奶娘,不晓得她何时起床出门的,也不晓得她去了哪里。阳光铺满院子时,她才满头大汗回来。我问她去了哪里,她有时说下地薅红苕,有时说割油菜。
她太累,坐在阶沿上用棕叶扇打凉。汗水干了,她才烧水洗澡。天气热,她光着上身从细屋出来。乳房吊在胸前,像黄色的老丝瓜瓤。她见我盯着她乳房看,用手托了托蔫蔫的乳房说:东子,莫看这口袋空啊,你可是这口袋养大的。我嘿嘿地笑起来。她也笑了,脸上挂满了泪水。
太阳还没升起来,奶娘也不在。寨子很安静,我在寨子走了几圈,一个人也没看见,更别说看到伯伯了。我决定去潮水街看看。我戴上顶破旧的草帽,沿着寨子前的田坎走出去。潮水街也冷清,即使街道两边添了好多新房,却看不到几个人影儿。我从街西头走向街东头,好多房门都紧闭着,很久没人住。我到处张望着,希望伯伯突然从哪堵墙后走出来。
走完潮水街也没见到伯伯,我很失望。突然从瓦房后面跑出一群孩子,挂鼻涕的小男孩指着我哈哈大笑。其他孩子也哈哈大笑起来。后脑勺有撮黄毛的小子大声说:癫子喂,是傻癫子,对门坡的傻癫子。我回头就走。他们笑得更响亮。还齐声喊起来:癫子,癫子,傻癫子。我好泼烦他们,使劲跑起来。他们不打算放过我,追了起来,一边追一边喊。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砸在肩上,停下一看是土块。孩子们见我停下也赶忙停下,嘻嘻哈哈笑一阵,又开始喊我傻癫子,远远地向我抛土块。我忙转身跑回寨子。
回到家,我感觉好累,胸腔里的小风箱噗哒噗哒响,眼前闪烁着深深浅浅的瓜花黄。奶娘从院外走进来,见我满头大汗呼噜呼噜喘气,惊慌地跑过来拉着我焦急地问:东子,怎么了?我结巴着说,没怎么,好累好累。
她见我满身泥土,禁不住哭了,边给我拍泥土边说:就在家耍嘛,别出去,那些狗娘养的心狠啊……我看着她,觉得她好像变了。我记得她从来没骂过谁。
我坚信伯伯藏在潮水街。每天起床后就戴着破草帽去潮水街,从街西头往东头走,一直走到瓦房处才折回来。我想象着伯伯突然走出来的样子,他可能会喊我东子,可能会责备我怎么跑到街上来。我正要回寨子,突然看到了奶娘的身影。她那么瘦,那么单薄矮小,像黄纸人儿。
她正要转身躲到墙边。我大声喊起来:奶娘,我看到你了,嘿嘿嘿!她站住了,也看着我笑。她快步向我走过来,拉着我手往家里走。
奶娘,你上街做什么?我问她。
东子,不上街嘛,街上也不好耍。
我喜欢上街,嘿嘿。我不告诉她我为什么上街。
奶娘,你上街做什么呢?我继续问。
你上街我要远远跟着,不让那些狗娘养的欺负你!
难道昨天,前天,大前天,奶娘也在跟着我吗?我怎么没看见呢?奶娘也能跟着我,不让我发现?我很伤感。原来奶娘也会突然走了,去哪里藏起来,让我找不到她。
想到她要离开我,我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可她立马又紧紧抓住了,看着她瘦小的手,我不忍心再次挣开,由她抓着。
李峰捐款的进寨公路终于开始硬化了,乡间热闹了些。
一连几天,奶娘都没下地干活。她就坐在木椅子上抓住我的手给我说话。她说寨子以前好热闹,说她奶娘和伯伯多么温顺,多么慈祥,多么爱她。
她说年轻时寨子里好多年轻小伙子都爱她,上门说媒的人起串串,可家里要招上门女婿,那些爱她的小伙子退缩了。她满脸笑容拉着我的手,看着远处不停地说啊说啊。
我说:奶娘,你不下地干活,以后我们吃什么?
田土都撂了荒,种了庄稼也没收成。
那我们不是要饿死吗?
我们有政府救济款呢,不大吃大喝就不会饿死。
突然,她拉紧我手说:东子,你要缓过来,明年你才三十三,缓过来了找个媳妇。
我说:奶娘,我哪没缓过来,一直都缓过来的。
奶娘说:对,我们东子一直缓过来的。她说完笑起来。霞光照到阶沿上,我们变成了金黄色。一眼望出去,到处都开着南瓜花,一直开到了天上。
我不知道我们是何时睡过去的。我被鸟声吵醒时,奶娘还在睡。这个早晨除了鸟声,再没其他声音,好安静。我好饿,想奶娘给我做吃的。我喊她,推她。她微闭着眼不理我。好饿啊,奶娘怎么能不理我呢?我反复推她喊她。她也不理我。王幺娘走进了院子。
东子,你奶娘怎么了?王幺娘问我。
我饿了,她睡了,我喊不醒她。
王幺娘忙走过来喊奶娘,奶娘没答应。她一试奶娘的鼻息就慌了。她使劲摇奶娘,大声呼喊。可奶娘就是不答应她。
王幺娘说:东子,你奶娘走了。
说完,她摸出老人手机给组长打电话。组长领了一帮人来我家,在院坝放了挂鞭炮。他们把奶娘抬进细屋。女人们在灶屋烧水,准备给奶娘洗身子。
我看着他们忙碌,心里想:伯伯还没找到,现在奶娘也走了,我去哪里找他们?想着想着,我嘤嘤地哭起来。
有个老妇人看见我哭,大声对其他人说:你们说东子傻,是癫子,你看人家哪里癫了傻了?都会伤心呢!
另一个老妇人大声喊组长。组长跑过来问喊什么。她说:东子还没吃饭呢!饿死了你要负责哟。组长抠了抠乱蓬蓬的脑壳,喊过一个老妇人,让她回家给我舀碗饭。
我吃了好大一碗饭,打了两个嗝,感觉身上有了力气。
我不停地想:伯伯走了,奶娘怎么也要脱了壳儿走呢?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连同伯伯一起找回来。
我戴上破草帽,顺了个打火机,沿着寨子前的田坎走出去。我走过潮水街,走过那座瓦房,我家的嘈杂声越来越远。
回望我家,屋顶上升起几柱浊黄的烟。我继续往前走,寨子和潮水街向身后退去。我已走过我上学的中学门口,我没有看见伍老师,没有看见梅和王亚红。
我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太阳落了山,天空艳黄,又慢慢变淡。夜晚就要降临。夜晚一来,汹涌的瞌睡就会袭来。瞌睡扑来,我会突然睡倒。必须想办法,我点燃了路边的垃圾和柴火。火光升起来,火焰热辣辣的,我看到了奶娘和伯伯瓜花黄的脸,他们向我微笑。我感动哭了,看不见的刷子突然消失,透过泪光,我看到了人世间丰富的色彩;阳光普照,田野青翠,田传、张锋、宋亮唱着歌儿从我身边走过;李峰、王亚红、刘晓珊和梅也从我身边走過,棉花糖般的温暖缓缓向我簇拥过来。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