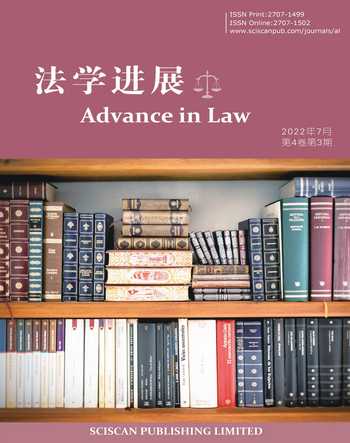袭警罪的规范分析与司法适用
2022-04-29孙承程苑嘉辉
孙承程 苑嘉辉
摘 要|袭警罪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为了确保该新设罪名得以正确适用,本文将从规范层面和司法适用的角度予以分析:第一,该新设罪名保护的
法益为警察的执法权和人身健康权,并且该双重法益中还存在主次区分;第二, 对本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应当进行“先实质后形式”的审查,从而将辅警纳入 此罪的保护范围之内;第三,本罪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对象应当包含人员和警用 物品;第四,本文将从教义学角度对本罪的相关概念如“暴力行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等进行解析,并且和妨害公务罪进行区别, 以便更为精确合理地适用本罪名;第五,对于该罪的司法适用的展望,笔者认为, 只有严格遵守审慎入罪、宽容出罪的态度,才能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真正 彰显司法的权威与公正。
关键词|袭警罪;妨害公务罪;刑法谦抑性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明确袭警罪的规范和具体适用具有必要性
对于袭警罪的设立而言,必须肯定的是,由于警察职务的特殊性,会比其他职业面临更多的风险,因此袭警罪这个新设罪名的设立符合了警务工作的现
作者简介:孙承程(1998-),女,浙江杭州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苑嘉辉(1996-),男,河南周口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文章引用:孙承程,苑嘉辉.袭警罪的规范分析与司法适用[J].法学进展,2022,4(3):111-123. https://doi.org/10.35534/al.0403011
实需求,通过加大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的处罚力度,有力地保障了警察的执法权的正常行使,保护了警察在履职过程中的人身健康权。但是,执法者在享受该新设罪名带来的法益保护便利的同时,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也日益复杂,因此,在处理一般的违法行为和冲突事件时,应当严格遵守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审慎入罪、宽容出罪的态度处理警民关系,不宜轻易地动用刑法规制警民冲突,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二、明确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内容
法益指的是某种特定罪名所要保护的刑法上的利益,确定新设的罪名所要 保护的利益的范围及适用的界限,有利于明晰严格的入罪门槛和合理的出罪标 准、此罪与彼罪的科学划分,通过精准的定罪量刑更好地规制实施了相关行为 的行为人,同时彰显刑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袭警罪的“罪刑价目表”较为严厉, 因此,明确其保护的法益有利于约束公权力,防止司法权无谓地扩张导致滥用, 从而真正体现司法的公正。对于袭警罪冀图保护的法益内容,目前学界主流的 观点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警察的执法权,防止执法相对人以暴力的方式 干扰警察执法、扰乱社会秩序,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该罪名保护的法益是警察的 生命健康权。笔者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应当为警察的执法权和警察的人身健 康权的结合,并且主要侧重于前者,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法分则的不同章节的特定保护法益来看,立法者设置袭警罪, 并且将其置于刑法第六章的“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章节之中,该章节中的罪名共同规制的行为均为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因此,袭警罪作为妨害公务罪的第五款内容,其主要规制的行为也就不言自明,也应当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非以暴力的手段和方式侵害警察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a。更进一步而言,如果认为该法条描述的行为中包含了对于危害警察人身安全的行为的规制,那也应当是由于该种暴力袭击的行为在扰乱社会秩序的同时还危害了警察的人身安全,因此才能纳入该新设罪名的保护范围之中。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警察的本质仅是一个职业,其人身安全和其他公民的人身安全应当受到同等待遇的保护,如果警察在执行公务时,执法相对人以暴力行为进行袭击导致侵害了警察的人身健康,完全可以以刑法第四章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进行规制,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伤害的目的,则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主观带有杀害的目的,则也可以通过故意杀人罪论处,并不需要刑法第六章单独规定一个新罪名对警察这一特殊群体的人身权利进行重复强调,这样会导致立法资源的浪费。
第二,从防止对某一人群过度保护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设立袭警罪已经使得警察这个群体的人身健康受到了优于其他国家公职人员法律层面的保护, 虽然承认警察相较于其他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确实会承担更多的危害人身安全的风险,但是在实践中,其他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危险,例如,法官也有可能因为负责宣判某一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而被当事人记恨,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可能遭遇顽固抗税者的攻击。由此可见,如果认为刑法有必要对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的人身安全进行分类保护,那么就会导致出现袭击法官罪、袭击税收人员罪等大批庞杂的、荒谬的罪名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势必会造成刑法分则罪名泛滥;另一方面,如果刑法仅以新设罪名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而不保护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就会由于过高地夸大了警察的法律地位而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进一步而言,在警察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工,不同警种面临的风险也各不相同,例如,对于刑警而言,其职责就是与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因此需要刑法倾斜性保护其人身安全,对于网络警察而言,其日常的任务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操纵着计算机穿梭于虚拟空间之中,因此面临因为职务行为导致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可能性较低,由此可见,刑法单独为所有的警察设置罪名保护人身安全并无必要。
第三,从袭警罪本身的构成要件来看,该罪为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袭击正在执法的警察的行为即可入罪,在法条的后半部分将严重危害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具体危险规定为该罪的加重情节,由此可见,要构成该罪,造成被害警察的人身健康损害并不是必备的犯罪结果的构成要件,这就可以顺势推导出该新罪名的保护法益的内容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为警察的人身健康法益 ?。
第四,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在普遍设立了袭警罪的英美法系中,袭警罪 保护的法益仅为警察的执法权,这是因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较轻,因此不能包 含对于生命健康的法益保护,如果执法相对人以暴力的方式袭击警察导致损害 警察的生命健康,则通过其他的重罪进行规制,如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等。但是对于我国的袭警罪而言,其量刑幅度最低三年、最高七年,故意伤害罪致 人重伤的量刑幅度最低三年、最高十年(排除手段特别残忍的情形),由此可见, 我国的袭警罪可以包含重伤以下的损害结果,因此本罪除了维护社会秩序之外, 其保护的法益中还应当包括一定的人身权利。
第五,结合立法目的与立法精神,也应当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之间具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必须予以肯定的是,设立该罪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行为人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是通过侵害警察的人身安全得以实现的,一言以蔽之,两个不同位阶的法益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b,即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的法益仅是手段,保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法益才是立法者最终想要达成的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内容应当是社会秩序法益与人身权利法益二者兼而有之,并且,较为重要的是保护警察这个群体承担的维护社会机能的运转秩序的职责之上。
三、明确袭警罪的犯罪对象
袭警罪的客观行为构成要件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履职的警察,对于在本罪保护的犯罪对象中,除了具有编制的正式警察之外,是否还应当包含辅警,学界对此众说纷纭。
认为该罪的保护对象不应当包含辅警的学者主要给出了如下两方面的理由:其一,从刑法的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辅助即协助、帮助的意思,辅警并没有警察的法定身份,因此缺乏相应的职务范围内的权限和责任 ?,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具有正式编制的警察因其法定职责而较容易招致潜在的危险,因此需要专门立法加以保护,辅警由于不具有法定职责,因此不具有专门立法加以保护的权利;其二,从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来看,在 2000 年,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的批复》指出,合同制民警在执行公务期间,具有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权力外观,因此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相应规范予以规制,但是辅警只能由具有政治编制的警察带领履行职责,其并没有单独执行公务的权限,因此不能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权威与尊严,由此可见,将辅警认定为袭警罪保护的对象属于类推解释 b,导致对于该罪名的犯罪对象的设置明显超出了立法目的的射程含义之外,违反了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认为该罪的保护对象应当包括辅警的学者也主要给出了如下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正如刑法认定身份犯时应当以实质职务为核心,对于具有特殊身份的犯罪对象的认定也应当淡化外在的身份,才能更好地实现立法者保障特定职务正常履行的初衷。在 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规定了虽然辅警的履职行为必须依附于具有正式编制的警察的带领,但是只要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那么其执法行为就应当视为具有正式编制的警察的履职行为的延伸,由此可见,二者的执法行为具有一体性和完整性 c。另外,正如前文所阐述的保护法益的角度而言, 新设的袭警罪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警察执法权的正常行使,那么一切扰乱该执法权的行为都应当属于该罪名规制的范围之内,即扰乱辅警的执法行为的暴力袭击,也应当以袭警罪定罪量刑,这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是对于法条规定的犯罪对象先进行形式判断、后进行实质判断,根据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理所应当的结论;其二,对于大部分普通公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能分清辅警和具有正式编制的警察的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的外在形象的区别 ?,由此可见,辅警在执法活动中就是象征着国家公权力的权威,代表着公安机关执法者的严肃形象,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对象之中,符合一般公众的认识需求。
综上所述,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即将辅警纳入本罪的保护对象之中。因为在民事关系中较为注重外在形式的区分,如无权代理行为在被代理人承认之前效力待定,但是刑法是保障法,在其他部门法无力调整某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时,通过规制该种行为来保障其他部门法能够正确实施,由此可见,刑法在明确其规制对象之时更应当注重实质而非外在形式。既然袭警罪的设立目的是维护警察执法权的正常履行,那么刑法就应当对于辅警在职权范围内辅助行使的执法权予以同等保护,是否具有正式编制导致行为效力的不同应当属于行政法或民法所调整的范畴。
四、明确袭警罪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对象
在众多对于该新设罪名的研究中,对于该罪名所规制的暴力行为是否应当包括对物的暴力还是仅仅局限于对人的暴力的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探讨的热点。笔者认为,本罪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对象不应当仅限于对人的暴力,还应当包括对物的暴力,理由如下。
第一,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应当保持一致。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在公安部和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印发的《关以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毁坏警用车辆和警用设备,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的,以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由此可见,在妨害公务罪中扰乱执法秩序的行为的作用对象包括警察和警用物品,那么袭警罪中规制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对象也不应当仅限于人员。
第二,警用物品是警察的外在象征,并且和警员自身安全息息相关。无可否认的是,警用物品通常印有警徽,因此可以看作公安机关权威的具现化象征 ?。并且,袭警罪中的“物”应当进行狭义解释,仅限于警员履行职务所必要的和警员人身安全密切相关的物品,因为该种物品是警察行使执法权用以保护自身安全的保障设备,如果侵害该种物品,则会间接阻碍执法活动顺利进行、危害警察的人身安全,即行为人攻击警员本身和攻击警用物品所造成的危害具有等价性,因此将该种物品纳入此罪名规制的范围内符合该罪保护法益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袭警罪是抽象危险犯, 构成其入罪门槛的暴力行为的危害程度小于妨害公务罪,因此,如果暴力袭击警用设备但是并未危害警察的人身健康,那么应当以妨害公务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
第三,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日本的刑法学者同样认同将针对警用物品的暴力袭击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内,他们对于袭击警察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对象一般适用扩大解释,认为暴力行为并不需要直接对警察的身体施加不法的有形力,也可以施加于处在该警察的指挥下辅助履行执法权的辅助人员,或者施加于象征该警察的“手足”、成为其正常履行职务所必要的辅助器具之上,从而在物理载体上实质性地影响该警察的身体健康和工作能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刑法规制对象的解释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和实践经验进行灵活变通,既然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内容是警察的执法权,那么只要是能够阻碍执法权行驶、危害警察人身安全的行为都应当纳入该新罪名规制的范围之内,不应当死板地对人的暴力和对物的暴力进行区别。
五、对袭警罪的相关概念的教义学分析
第一,对于“暴力袭击”的分类和特征而言:(1)“暴力行为”应当仅指有形力,排除无形力。袭警罪规制的暴力行为应当仅指撕咬、抱摔、殴打等能够给警察造成实际肉体损害及肉体损害风险的有形力,由于该罪保护的法益是警察的执法权和警察的人身健康权,因此只有物理意义上的阻碍行为才有显示扰乱执法行为和损害人身安全的可能性,以电磁力为代表的无形力并不能产生相近的现实危险;(2)“暴力行为”应当仅指硬暴力,排除软暴力。硬暴力 和有形力的概念类似,均指物理上的强制力,软暴力指通过寻衅滋事、聚众造势的方式,使得被害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慌的心理强制手段,从刑法的体系解释来看,如抢劫罪、强奸罪等其他将以暴力侵害人身安全作为客观要件的犯罪都明确要求能够实际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物理性暴力,因此,为了保证刑法的内在统一性,应当将袭警罪中的暴力也解释为物理上的暴力而非心理上的强制;
(3)“暴力行为”应当具有出其不意、防不胜防的效果。从一方面而言,以 社会上一般人的标准来看,该种暴力行为应当表现为突然爆发的猛烈行为,正因为被害人难以料到、缺乏预防,因此才有实际造成损害或产生较大威胁的可能性;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执法的警察属于熟悉对抗训练和犯罪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因此,对于执法相对人的行为的突然性,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果依据警方的丰富经验判断执法相对人本身就具有较大的暴力倾向,那么在执法活动的过程中,行为人由于情绪不稳定,因此突然实施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升高,那么其确实对警察实施了诸如殴打、抱摔之类的暴力行为,就不能视为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从而尽可能减小行为人入罪的可能性;(4)“暴力行为”应当具有瞬时性 ?。瞬时性意味着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并非持续的、恒定的状态,而是打破双方对峙的平衡暴起发难,可以是从无到有的情形,例如,执法相对人在警察实施执法行为的一开始就掏出防狼喷雾对着警察的面部喷洒,也可以表现为行为升级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先进行撒泼打滚、辱骂推搡的行为,然后突然掏出防狼喷雾进行更进一步地干扰执法的行为;(5)“暴力行为”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警察在进行某些执法 活动之时,对于执法相对人暴起发难的可能性是有所预料的,例如,醉酒者、惯犯等群体,前者由于思绪混乱因此难以控制自身行为,后者由于惧怕重罚而具有强烈的脱逃动机。但是,如果警察面对一个初犯的柔弱妇女或孱弱老者, 实现预料对方暴起发难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因此该种不可预见的暴力袭击行为的危害性就更大;(6)值得注意的是,从惩罚犯罪的角度而言,由于该罪 是抽象危险犯,因此行为人实施的暴力压制并不要求完全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能力,即使尚未完全剥夺被害人的反击能力,也不影响对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执法相对人往往会出现情绪激动、态度恶劣的情形,采取推搡、拉扯警察的行为阻碍执法行动的开展,司法人员应当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对于其中人身危险性不大的,不应当以犯罪论处,通过行政罚款等手段就可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第二,对于“正在”的时间范围而言:(1)对于执法工作的事前准备工作和事后收尾工作应当视为执法活动的时间范围之内,例如,开车前往执法目标所在的场所的行为,正如刑法规定犯罪预备之所以要受到处罚是因为该种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是实际着手实施犯罪所必不可少的前置条件,对于法益具有现实的危害性,因此,执法活动的事前准备和事后收尾也应当和实际执法的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是完成执法任务所必不可少的环节;(2)警察在非工作时间实施的履职行为应当视为在执法活动的时间范围之内。结合该罪保护的法益来看,正如前文所言,应当突出实质上的职务履行,淡化形式上的身份和时间条件,从而体现对于警察履职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的立法鼓励。
第三,对于“依法执行职务”的合法性认定而言:(1)在行政法中,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五要素为主体违法、事实依据违法、法律依据违法、程序违法、明显不合理,一个执法行为只要违反上述五要素其一,就会导致损害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进而应当判定为违法行为,因此,如果执法相对人对于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反击,应当视为捍卫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如果对于执法人造成损害结果远远超过防卫的必要性和相当性,可以以故意伤害罪等罪名进行规制;(2)在行政法中,瑕疵执法行为指并未符合上述五要素,仅是在程序或处理方式上具有少许缺陷的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别在于并未实质性损害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例如,交警在开具罚单时应当先敬礼,如果其遗漏敬礼的步骤,虽然不符合执法的流程,但是并不影响其后续开具罚单行为的合法性。笔者认为,执法相对人对于瑕疵执法行为的袭击,如果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则应当以该罪名进行论处,理由有三:其一,在司法实践中,考虑到现实执法环境的复杂多变,并且执法者并非机器人,面对某些情况难免会出现态度上的生硬和言语间的冲突,但是由于该种疏忽和缺乏礼貌的危害性不大,因此可以视为情有可原的缺陷;其二,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在决定某种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制裁之时,司法者的目光应当始终在行为和规范之间来回流转,不应当考虑其余与此无关的因素”?,由此可见,执法者的执法行为存在的瑕疵应当以相关的行政法规予以规制,执法相对人对执法者实施的暴力袭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刑法进行规制,即不同部门法掌控的领域不同,二者应当平行处理、区别对待;其三,从损害程度的相当性的角度而言,在袭警罪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中,警察即便实施瑕疵执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瑕疵执法行为仍然处于合法执法的范围之内,因此警察作为袭警罪的保护对象,其受保护的程度仍旧大于执法相对人作为瑕疵执法行为的权利受损方的保护的程度。
第四,对于“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主客观的标准而言:(1)从主观要
件而言:其一,该罪的犯罪对象是警察,因此要求行为人对于执法对象主观上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并不知道并且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准进行衡量, 行为人也不可能认识到对方是警察,则不符合够成本罪的主观要件;其二,行为人主观上对于袭击警察的态度存由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对于损害警察的人身健康和扰乱社会秩序抱有过失的主观态度,则也不构成本罪,由于本罪的法益内容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警察的人身安全,因此,更进一步而言,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仅存有损害警察的人身安全的目的而无阻碍执法权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目的,则应当将其暴力袭击警察的行为认定为发泄情绪或者恶意报复的行为,如果造成了刑法规定的轻伤及以上的损害结果,则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进行规制;
(2)从客观法定刑升格的要件而言:袭警罪的法条规定中,加重情节表述为“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造成具有人身危害性的危险 状态,对于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的标准, 目前主要有两种如下学说:其一为“强调说”,支持该种学说的学者坚持该法 条前后情形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即前半段的使用枪支、管制刀具及机动车的 行为与后半段出现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并非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加重处罚, 一言以蔽之,法条前半段对于行为的列举仅是一种强调的叙述方式,行为人只 要具备了前三种行为,就可以直接升格其法定刑,并不需要切实出现实际的危险。在刑法分则中,采取类似的描述手法并不鲜见,例如,在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 安全罪中,立法者列举了放火、决水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手段明确了该罪 规制的犯罪方式的相同属性,并且以抽象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 只有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才会以该罪进行处罚,由此可见,要构 成本罪,必须达到危害行为和危险结果二者的相互结合,缺一不可。这种规定 的目的是对允许该罪规制的行为进行限缩,从而达到减少入罪的刑法谦抑性的 目的。笔者认为,该种学说值得更进一步商榷,根据刑法的体系解释的逻辑来看, 袭警罪的法条描述方式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类似,那么二者的构成要 件也应当类似,要构成前罪,也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和造成的结果都符合法条 前后文的程度限制后,方才可以入罪;其二为“递进说”,坚持该种观点的学 者认为必须结合现实的案例,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 否达到需要加重处罚的程度。笔者较为赞成“递进说”,因为在司法实践和一 般人的认知中,行为人手持枪支给警察带来的危险一定大于手持管制刀具给警 察带来的危险,因此在具体的案例中,对于如何判断是否已经达到“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判断标准也应当是不同的,这样才能保证个案正义。
六、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竞合和区分
第一,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言,袭警罪是特殊的妨害公务罪,其在妨害公务罪对于社会秩序法益的保护的基础上增加对于警察这个特殊群体的执法权和人身健康的法益的保护。由此可见,一个行为如果构成袭警罪,则一定同时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存在差异。有如下不同之处:(1)前者的法条描述的行为是“暴力袭击”,后者的法条描述的行为是“暴力威胁”,通过语 义可见,构成前罪要求的行为的暴力程度应当大于后者;(2)前者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符合刑法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即构成本罪,而后者必须达到扰乱特定 主体履行职责的危害后果方可构罪;(3)前者可以包含的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高于后者,正如前文所言,袭警罪的量刑幅度和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幅度具有重叠, 因此其能够包含一部分致人重伤的严重后果,但是不能包括死亡的结果,而在 后罪中,刑法明确规定其只能包含轻伤的结果,如果造成重伤、死亡的结果的, 应当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相竞合择一重罪论处。由此可见,构成袭警罪 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
七、对于袭警罪等新罪名的司法适用的展望—— 审慎入罪,宽容出罪
从袭警罪的设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犯罪化的趋势,众所周知, 袭警案件是作为近几年社会的热点问题得到了刑事立法者以设立新罪名的方式 予以回应,除此之外,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还有负有照护职责人员 性侵罪、高空抛物罪、非法催收债务罪等一系列积极回应社会热点的新罪名一一出现,这不仅是积极预防性刑法观逐渐成为刑法界主流思潮的具象化,也 是通过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达到对于集体法益的保护的刑法价值观的逐渐转变。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通过扩大处罚范围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公民行为、调整社会 秩序;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司法领域,过度地犯罪化无疑 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导致刑法公信力降低,更容易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通过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严守刑法适用边界的方式防止不当扩大 刑事处罚的范围,即通过审慎入罪、宽容出罪的方式,来平衡刑法惩罚犯罪、 保护人权的本质内涵和应有功能。
Normative Analysis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Sun Chengcheng Yuan Jiahui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crime of attacking the police is a new crime i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rim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level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first,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new crime are the polices law enforcement power and personal health right, and there is a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tinction in the dual legal interests; Second, the scope of the criminal object of this crime should be examined “substance before form”, so as to bring the auxiliary police into the protection scope of this crime; Third, the target of violence in this crime should include personnel and police goods; Fou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gma,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is crime, such as “violence”, “being”, “performing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seriously endangering personal safety”, and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public affairs, so as to apply this crime more accurately and reasonably; Finally, for the prospect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by strictly abiding by the attitude of prudent conviction and tolerance, can w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and truly demonstrate the authority and justice of justice.
Key words: Assault on police; Crime of obstructing public servic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